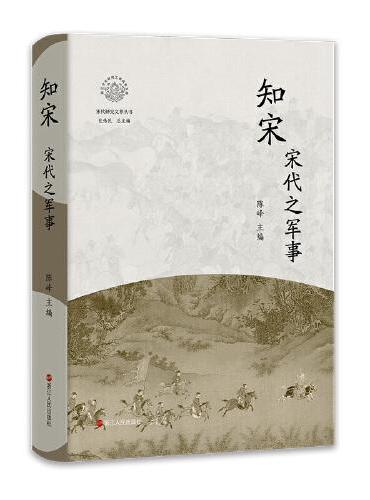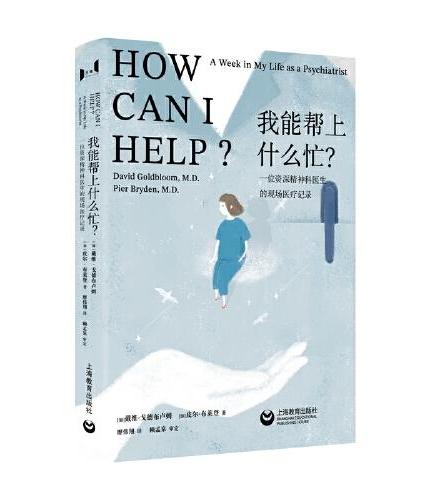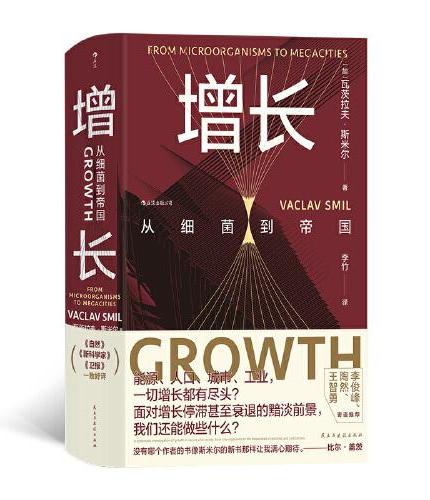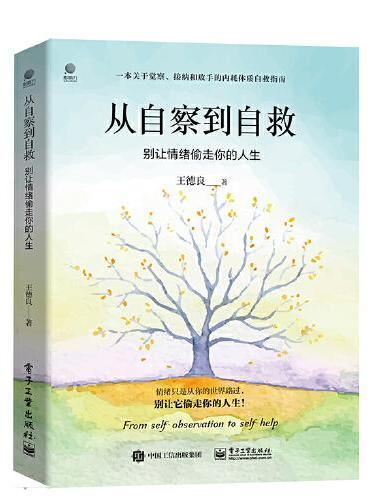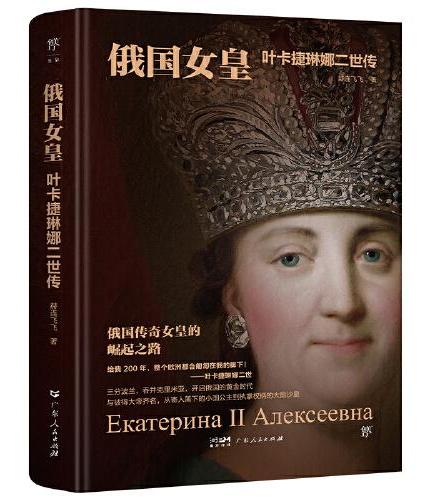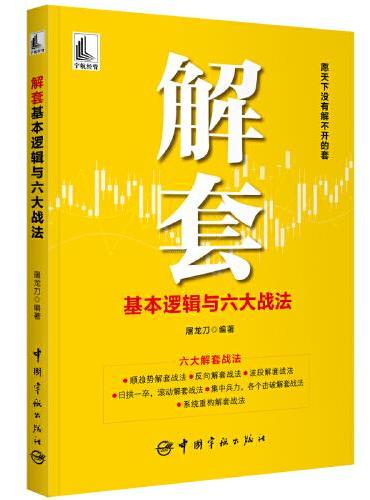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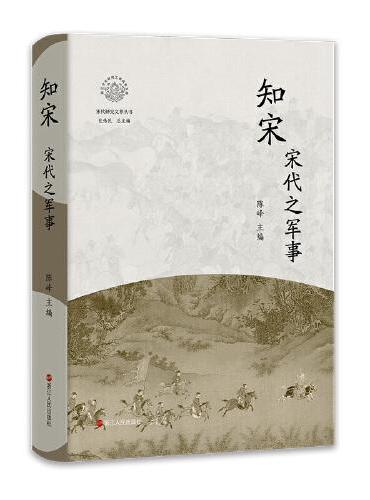
《
知宋·宋代之军事
》
售價:NT$
4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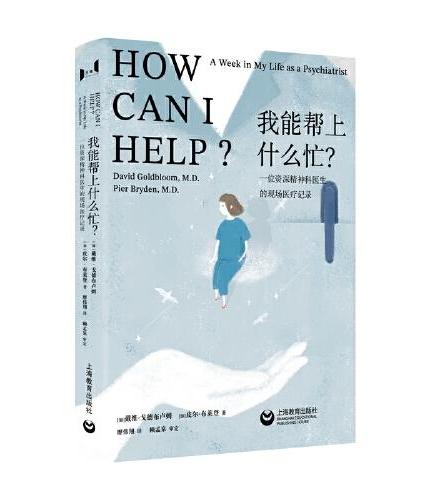
《
我能帮上什么忙?——一位资深精神科医生的现场医疗记录(万镜·现象)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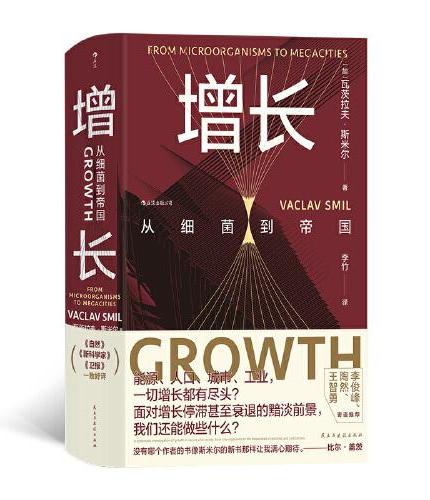
《
智慧宫丛书026·增长:从细菌到帝国
》
售價:NT$
8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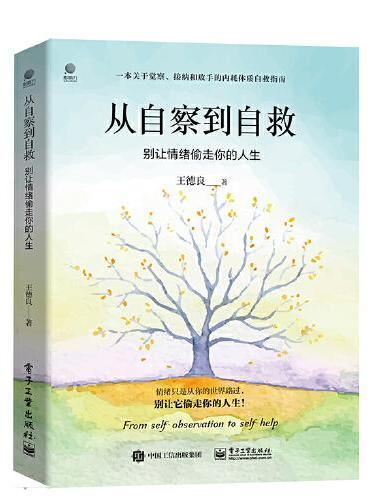
《
从自察到自救:别让情绪偷走你的人生
》
售價:NT$
420.0

《
晚明的崩溃:人心亡了,一切就都亡了!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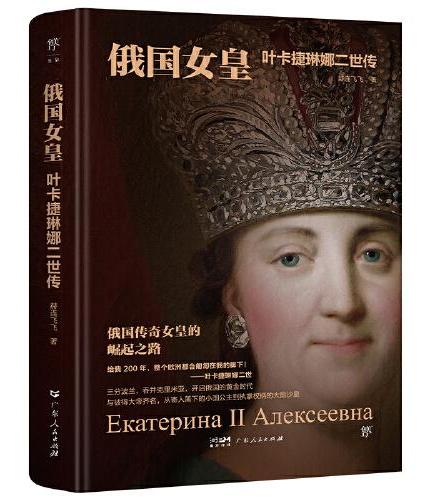
《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精装插图版)
》
售價:NT$
381.0

《
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
》
售價:NT$
2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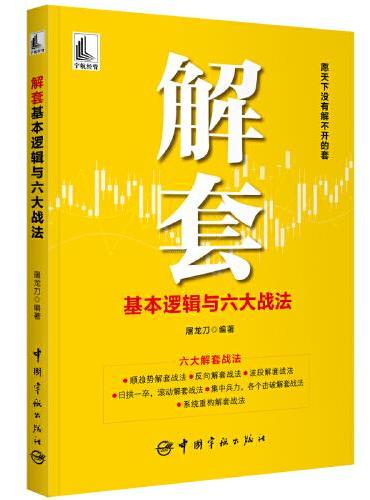
《
解套基本逻辑与六大战法
》
售價:NT$
274.0
|
| 編輯推薦: |
本书卖点
1.大咖作者口碑之作,畅销海外十余年。保罗·约翰逊是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曾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2000年“百大人物”,代表作《知识分子》《摩登时代》。本书是约翰逊的经典作品,曾得到《出版人周刊》《科克斯书评》《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联合推荐,畅销海外十余年,海外读者好评如潮。
2.短小精悍,精彩纷呈,讲述苏格拉底传奇的一生。他生长于雅典、深爱着雅典,他向民众教导知识,还曾为雅典而战,却被雅典人审判、定罪,最终被处死……本书以精炼的笔法,描绘苏格拉底生命的轨迹,概述苏格拉底是谁以及他的个性、生活、主要思想,展现“哲学化身”苏格拉底波澜壮阔的一生。
3.跳出柏拉图的叙事围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究竟是真实的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的傀儡?他所表现的,到底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还是柏拉图的思想?保罗·约翰逊明辨二者差异,去伪存真,挖掘真实鲜活的苏格拉底。
4.描绘广阔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雅典的纷争与衰落。在描述苏格拉底的同时,全方位描绘与苏格拉底交往的人们以及雅典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雅典这座苏格拉底挚爱之城的纷争与衰落。
5.叙事简洁清晰,可读性强,
|
| 內容簡介: |
他貌不惊人、衣着朴素,常常光脚漫步在雅典的大街上;他教导人们独立思考,他充满智慧,却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他生于雅典、深爱雅典,曾为雅典而战,却遭到雅典人的不公正审判,最终以一杯毒酒结束生命。他是“哲学的化身”苏格拉底。
这是一部短小精悍又精彩纷呈的传记,它记叙了苏格拉底充满传奇色彩的生命历程,探讨苏格拉底的主要思想,同时全方位描绘了与苏格拉底交往的人们以及雅典的城市生活图景,展现雅典这座苏格拉底挚爱之城的纷争与衰落。书中叙事简洁清晰,跳出了柏拉图的叙事围城,还原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描绘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苏格拉底、每个人心中的苏格拉底。
|
| 關於作者: |
作者:保罗?约翰逊(1928—2023),当代著名历史学者,曾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百大人物”。他曾长期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知名报刊供稿,其著作涵盖历史、哲学及宗教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知识分子》《犹太人史》《摩登时代》等。
译者:郝苑,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尼采和新尼采主义、新实用主义、自然主义、存在主义以及哲学解释学,已出版《作为哲学家的尼采》《尼采:生命之为文学》《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等多部译著。
|
| 目錄:
|
第一章 充满活力的人与口技表演者的玩偶 1
第二章?拥有追求幸福天赋的丑角 11
第三章?苏格拉底与雅典乐观主义的巅峰 29
第四章?哲学天才苏格拉底 57
第五章?苏格拉底与公正 80
第六章?雅典的腐化与苏格拉底之死 104
第七章?苏格拉底与哲学的化身 138
延伸读物 145
索引 147
译后记 162
|
| 內容試閱:
|
苏格拉底的“无知之知”
译后记(节选)
毋庸置疑,苏格拉底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与思想家之一,然而,正所谓熟知非真知,关于苏格拉底的生动描绘不少,关于苏格拉底的无可辩驳的事实却不多。苏格拉底一生的言行激起了人们的一系列疑问与困惑:苏格拉底何以被德尔斐神谕称为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苏格拉底这个最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却主张自己一无所知?苏格拉底这个主张自身无知的人又为什么会强调知识与美德的关联?既然知识与美德存在重要关联,苏格拉底何以又会认为美德是无法传授的?一生都将美德当作自身哲学主要关切的苏格拉底,何以会被控诉犯下了败坏雅典青年的罪行?倘若雅典对苏格拉底的审判是不公正的,苏格拉底为什么不选择逃离雅典,而是坦然接受了这次不公正审判的死刑判决?
应当说,这些疑惑并非仅仅导源于可靠历史材料的缺乏,这也与苏格拉底表述自身信念的方法有关。正如王尔德所言,“真理之道乃悖论之道”,苏格拉底大概是最熟练地使用王尔德所倡导的这种反讽手法的西方哲学家之一。苏格拉底的反讽手法所产生的种种悖论式的论断,也为理解他的哲学与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克尔凯郭尔就敏锐指出了理解苏格拉底的困难的关键所在。
苏格拉底所最注重的是他的一生和世界历史之间的关系……他没有著书立说,后世对他评判也就无所凭依;我想象我即使和他生于同世,他也会永远难以捉摸。他属于那种我们不能只看外表的人。外表总是指向一个相异和相反的东西。有的哲学家谈论自己的观点,而在谈论中理念本身就会明确地呈现出来。苏格拉底不是这样的一个哲学家,他的话总有别的含义。总而言之,他的外在与内在不和谐统一,其实毋宁说他的外在内在总是背道而驰:只有从这个折射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他。显而易见,理解苏格拉底迥异于理解大多数别的人。
这也就意味着,仅仅僵死地依靠一种实证主义式的史料堆积与梳理是完全无法把握到苏格拉底思想与生存的实质的,归根到底,苏格拉底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是要由有经验和有性格的人来书写的。如果一个人不是比别人经历过更伟大和更高尚的事,他就不能解释过去的任何伟大和高尚的事”。凭借丰富的社会经验、敏锐的批判意识、宏大的智识视野与广博的学识,著名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撰写的这部铿锵有力而又生动的《苏格拉底》,为深入理解苏格拉底,澄清上述困惑带来了诸多相当有价值的启发。
苏格拉底的著名研究专家格雷戈里·弗拉斯托主张,苏格拉底思想的“核心悖论”是他关于无知之知的宣言,也就是说,当苏格拉底得知德尔斐神谕的内容时,他得出的结论却是,正是他的无知才让他成为当时在雅典最有智慧的人。根据约翰逊的提示,要对这个悖论形成恰当的理解,就必须参照雅典智识氛围的历史语境。
众所周知,在苏格拉底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是由伯里克利来统治雅典的。伯里克利统治时期的雅典,不仅在文化艺术与商贸经济领域创造了辉煌的成就,而且在军事与政治领域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通过领导希腊人粉碎波斯帝国的两次入侵,创建提洛同盟,雅典在诸多希腊城邦中确立了它的优势地位。可以认为,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已经成为整个希腊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雅典的统治阶层与市民阶层无不沉浸于乐观主义的巅峰之中。
乐观主义固然可以极大地提升雅典市民的自信,让他们以更大的激情投入城邦的各项建设中,然而,很多事物恐怕都难以摆脱“物极必反”的规律。当雅典的乐观主义走向极端、偏执与虚妄时,这种乐观主义对雅典城邦的深远影响就很难说是正面的。正如丘吉尔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前普遍流行的乐观心态所做的评论,“极端的乐观主义,让投机事业变得愈加疯狂……人类能发挥最高的技巧和辛勤,当然是好事,因为这对彼此的利益都有难以计算的好处。可是实际上所取得的成果,远远不及所带来的虚荣、幻觉和贪婪,直到那种带着光环的外表被破坏得体无完肤”,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雅典的乐观主义。这种极端的乐观主义让雅典的政治家对自身与斯巴达的军事实力做出了错误的评判,并使雅典在其后发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走上了衰败的道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无知地自信的人表明他们自己不是勇敢,而是疯狂”。
应当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遭遇失败之前,雅典人毫不动摇地普遍持有这种乐观自信的政治态度,而这种政治态度也深深影响到了他们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的智识态度。苏格拉底热衷于与各个阶层和行业的雅典人进行交谈,在交谈的过程中他惊讶地发现,无论是政治家、诗人还是工匠,他们都有一个通病,即总是自以为知道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
苏格拉底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无知,而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身的无知,后者的无知更加糟糕,因为把不知道的事物臆想为已知的事物,这恰恰是思想中所犯一切错误的重要根源,“唯有这种无知被冠以‘愚妄’之名”。相较之下,“真正的无知是更为有益的,因为真正的无知很可能带有谦逊、好奇和虚心等特点;而只具有重复警句、时髦名词,熟知命题的能力,就沾沾自喜,自以为富有学问,从而把心智涂上一层油漆的外衣,使新思想再也无法进入,这才是最危险的”。
因此,苏格拉底比其他雅典人更有智慧的原因在于:苏格拉底对自身无知的认识,让他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他会由于自己的智识困惑而不断去反思世界与反思人生,而真理的探索恰恰就因这样的困惑而生。大多数相信自己的看法已经是真理的雅典人就不太可能如此努力地去做这样的反思,他们难免会将自己的心智封闭在流行的偏见与谎言中而不自知,他们对自己持有的信念越自信,他们就可能离真相或真理越远。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主张自身无知,并不是像怀疑论者或虚无主义者那样要否定真理的存在,恰恰相反,他是希望通过揭示普遍存在的无知来培养一种智识上的谦逊品质,以便于让人类更加积极主动地去追求真理。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为了通过知识达至真理,“主体必须改变自己、转换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与自身不同”,“如果认识活动没有通过主体的改变来做准备、陪伴、配合和完成,它是无法最终给出通向真理的道路的”,因此,通过知识获取的真理就不是完全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真理,而是对主体拥有某种塑造作用的真理。“真理就是让主体澄明的东西;真理赋予它真福;赋予它灵魂的安宁。简言之,在真理和通向真理的途中,存在着完成主体自身、完成主体的存在或改变主体形象的某种东西。”
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并不仅限于让主体把握住真理,而且还要通过直言的方式将这些通过认知活动获得的真理公之于众。苏格拉底的直言探讨的主要不是技术和能力,而是“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关联着本质的、基本的说真话实践。在关心人的领域说真话,就是质疑他们的生活方式,考验这种生活方式,界定其中哪些可以被鉴别为、被承认为好的,相反,哪些应该被抛弃、被谴责”。
正是依循以上这条思路,苏格拉底将知识与美德联系了起来。为了通过求知获得真理或真相,一个人就必须拥有谦逊的智识品质,就必须拥有开放豁达的理智德性。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接受了真正的知识与真理,那么他就会改变他封闭于种种幻相的庸常生活方式,消解他原有的傲慢、偏执与狂热,进而形成理性而又有节制的美德。
苏格拉底深信,“无人自愿作恶”,人们选择作恶,通常是缺乏知识导致的恶果。倘若缺乏必要的知识,一个人就会误认为某些恶行有利于自己的真实利益,某些招致自我毁灭的欲望是值得追求和满足的,某些投机与冒险的愚蠢行为可以从虚幻的宏大叙事中获取崇高而又辉煌的意义。倘若拥有充分的知识与理性,一个人就会抛弃这些恶行、疯狂的欲望与投机冒险的行为,逐步形成审慎节制与勇敢公正的精神品质,进而导向一种拥有美德的幸福生活。总之,在苏格拉底看来,在一个人培育自身美德的过程中,知识与理性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
——选自(英)保罗·约翰逊著,郝苑译《苏格拉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编者按:本文选自《苏格拉底》第五章《苏格拉底与同态报复》,标题为编者自拟。本文阐述了苏格拉底的正义观,以及苏格拉底对“以牙还牙”的同态报复的坚决反对。
苏格拉底: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错误的,就永远也不要去做这件事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智术师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就“什么是公正?”这个问题给出的回答展开了争辩。色拉叙马霍斯的回答是:“公正就是强者的利益。”他说,在每个社会中,界定公正或不公正的规则是由统治的精英,即社会中最强大的那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确定的。苏格拉底并不接受这一点,但他没有给出自己的答案,第一卷在没有得出结论的情况下结束。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不再是他自己,而是变成了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但我们在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了解到的是,苏格拉底认为,每个问题都应当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加以判断,有道德的人不难区分公正与不公正。他反复用或许是最坚定的语言表明,公正地行动优先于所有其他的考虑要素。苏格拉底说,最好是忍受任何事情,甚至是忍受死亡,而不是做出不公正的行为。他在《申辩篇》中说道:“倘若一个人拥有任何价值,除了公正的行为,他无论如何都不会重视其他任何考虑要素—甚至不会重视生命本身。当他行动时,重要的仅仅是,他的行动是公正的还是不公正的,这是好人的行为还是坏人的行为。”苏格拉底对公正行为的最高权威的强调被人们广泛接受,在苏格拉底两代之后的伊索克拉底在《泛雅典娜节献词》(Panathenaicus)中的如下坚定陈述就表明了这一点:“违背正义而赢得的胜利比在道德上公正的失败更受人鄙视。”
显而易见,苏格拉底关切的并不是抽象的正义。他关切的始终是实践行为。正如色拉叙马霍斯所暗示的,苏格拉底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持有的一个常见观点是,公正通常是一种私利的形式。当被问及“公正是什么?”的时候,一个希腊人会回答说:“一个人对他的朋友做好事,对他的敌人做坏事。”苏格拉底不会持有这样的解答。“一个公正的人既对他的朋友做好事,但肯定也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做好事,并由此设法将敌人转化为朋友。”这个观点以多种版本出现,这个主题始终是让恶回归善。这就接近于基督那个“转过另一边脸颊”的建议。苏格拉底在《克力同篇》中清楚地说道:“作恶、以恶报恶,或者当我们遭遇邪恶时通过反过来作恶而保护我们自身,这些永远都不是正确的做法。”恰恰是这个清晰的观点,标志着苏格拉底在这个地方背弃了任何伪装中与任何处境下的道德相对主义,并且坚定地选择了道德绝对主义。倘若你知道一件事是错误的,就永远也不要去做这件事。
这种行事准则导致苏格拉底跨越了另一个历史上重要的道德分水岭,并完全否定了由个人和城邦尊奉的最根深蒂固的希腊行为准则之一——同态报复法。当然,同态报复并非希腊所独有。对于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源自野蛮部落制的社会来说,这都是常见的,而同态报复也谨慎地摸索出了诸多变得文明的模式。在希伯来的《出埃及记》,紧跟第20章的内容是,上帝对摩西与以色列人给出了十诫—它们似乎在许多社会(即便不是绝大多数社会)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随后的那一章则针对打斗中伤害孕妇的情况,以严厉的方式制定了同态报复法(《出埃及记》21:23—25):“若有别的伤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我们不知道《出埃及记》这本书是何时编撰的,但有一个理论认为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这就让这本书的编撰者成为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同时代人,而赫西俄德是仅次于荷马的道德导师。赫西俄德比《出埃及记》走得更远:“倘若一个敌人开始说或做对你有伤害的某件事,你肯定必须要对他双倍奉还。”这比希伯来的圣贤拥有更强的报复心理,后者仅仅要求以一只眼来还一只眼,而不是以两只眼来还一只眼:这种做法将会是错误的。
苏格拉底坚决反对同态报复的整个理论与实践。在《克力同篇》中,他规定了他的这个命令的五个原则。我们永远不应当做不公正的事。因此我们永远不应当以不公正的方式进行回报。我们永远不应当对任何人做坏事。因此我们永远不应当以恶报恶。对一个人作恶,无异于以不公正的方式行动。苏格拉底完全意识到就其重要的本质而言,他拒斥了希腊传统的道德与公正。因为在他宣布他的五个原则之后,他立即补充说:“几乎没有人相信或将会相信这些原则。在确实相信的人与并不相信的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共同的基础。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在鄙视另一方。”
苏格拉底的这个立场是在同态报复问题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具有鲜明而又直接的重要性时被人们接受的。公元前431年,欧里庇得斯为他的《美狄亚》(Medea)做好了准备。苏格拉底几乎肯定在观众之中。这部令人惊骇的戏剧是一个以正义之名实施复仇的故事。美狄亚的所作所为与她所遭受的痛苦是完全不相称的,欧里庇得斯要证明的一个论点或许恰恰是,倘若同态报复(或复仇)被接受为公正的原则,那么相当难以在实践中确保报复可以与冒犯相对应。美狄亚说过,她所实施的是“在神的帮助下的公正回报”,但她事后承认,她“敢于去做最不虔诚的事情”。“不虔诚”这个词是重要的,因为它表达的暗示是,“公正的报复”这整个概念或许是不虔诚的。我们知道,苏格拉底至少在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戏剧中对他做出了帮助——“修补了这部戏剧”。或许是苏格拉底说服了这位诗人在《美狄亚》中插入这行文字。
接下来在四年之后,这整个问题以最惊人的方式在战争与政治的现实世界中发生。雅典人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置米蒂利尼,它是莱斯博斯岛的主要城市,这个城市背叛了雅典人。它在当时已经为雅典的军队所占据。惩罚问题被交付雅典的公民大会讨论。这些城市在激烈的战争中往往是毫不留情的。斯巴达人与雅典人或许会残酷地实施在他们看来是公正的惩罚。在西斯提亚、米洛斯、斯基奥涅与托罗尼这四个例证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或许会被我们称为种族灭绝。但这些大屠杀是由军队的指挥官根据他们自身的权威而执行的。公元前427年,雅典的民主公民大会经过充分的辩论之后接受了这个决定。由于蛊惑民心的政客克里昂的华丽言辞,公民大会通过了这样一个决议,它命令指挥官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米蒂利尼的所有成年男性,并将那里所有的女人和小孩都卖为奴隶。
这种经过民主辩论的斩草除根或种族灭绝的动议,在希腊的历史或就我所知的任何历史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显然让大多数人感到称心满意。但它必定让包括苏格拉底(我假定他当时也在场)在内的少数人感到震惊。我愿意认为—事实上,我很肯定—他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影响。在投票之后,克里昂马上就派遣了一艘船去米蒂利尼,将公民大会的决定带给指挥的将军,并指示他在公民大会可能进行重新考虑之前就执行这个决定。而公民大会确实进行了重新的考虑。温和派在经过一个晚上焦虑不安的讨论(我假定苏格拉底参与了这次讨论)之后,他们的领袖狄奥多图斯(Diodotus)第二天呼吁公民大会撤销他们的决定。他的论据绝大多数都是注重实际的。他说,恰恰是米蒂利尼的寡头政府,而不是平民下达了这次叛乱的命令。绝大多数民众都站在雅典这一边,并迫使这座城市向如今占据该城市的雅典军队投降。在惩罚寡头执政者的同时去惩罚民众,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有罪的是寡头执政者,而平民是无辜的,他们实际上站在雅典这一边。这种不公正会被雅典所有的同盟者与殖民地注意到。狄奥多图斯说:“我认为,对于帝国来说,宁可让我们自己承受不公正的对待,也不要去消灭那些我们不应当去消灭的人,不管这么做有多么正当。”最后这句话揭示了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思想,人们从这种权宜之计的一般性论证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思想,这让我相信,狄奥多图斯容许自己至少部分地接受这位哲学家的指引。他并没有走得那么远,以至于拒绝将同态报复作为公正的原则:狄奥多图斯还是想要赢得投票的。他做到了这一点。决议被撤销了,他们立即派遣了一艘快速的三层划桨战船去米蒂利尼撤销对将军的指令。幸运的是,这艘战船及时抵达,雅典与雅典民众的声誉得到了保全。
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是这样一段经历,苏格拉底的观点在这时被直接应用于公众的活动之中,而不是缓慢地经过数代人之后才成为全体的共识。我们拥有坚定的理由来相信,苏格拉底的私人干预为确保这个结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神的声音或许阻止了他成为政治家,但这并没有禁止他设法以真正的正义之名来影响政治决议,而这种真正的正义对立于作为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社会标准规范的虚假正义。
苏格拉底对同态报复的拒斥是他的哲学生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它同样是哲学史中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对此的最佳讨论是格雷戈里·弗拉斯托的《苏格拉底》的第7章(我强烈建议读者倘若有时间,就去细读这部论著)。苏格拉底所论证的立场特别强硬。它是最严格的道德绝对主义。他所说的实际上是:倘若你对其他的某个人做了某件坏事,更不用说对许多人做了某件坏事,那么不仅这件事本身如此糟糕,而且对你来说也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它实现的任何好处都不可能补偿这种恶。这件坏事或许赢得了一场胜利乃至赢得了一场战争;或许为你带来了你所珍视的一切,为你带来了快乐、舒适、安全与长寿;或许激起了你的爱人、你的家人与朋友的赞誉;或许就像你所认为的那样,对于他们的自我保存与你自己的自我保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倘若这是错误的,那么你就不可以去做这样的事。即便它会帮助你赢得整个世界,你也不可以去这么做。倘若你只有通过对其他人作恶才可以保持自己的生命,那么你的生活本身就会是不值得过的。
这是一个艰难的学说,毫不奇怪,在过去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这个世界的人们通常会发现难以遵循这个学说,即便在原则上接受这个学说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某些证据表明,柏拉图发现它是艰难的,而大量引文表明,亚里士多德也不太相信它。他觉得复仇是人性中始终存在的冲动,就像导致复仇的愤怒一样根深蒂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将愤怒定义为“强加报复性痛苦的愿望”。对我作恶,无论如何这都没有给予我权利来对那个作恶者施加相同的恶行,但这个绝对基本的道德真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有点难以接受。事实上,苏格拉底是仅有的一个把握并完全接受以下这个道德准则的希腊人:同态报复、复仇或无论我们选择如何称呼它,这种做法都是错误的,永远都不可以接受它或为它辩护。苏格拉底是第一个明确表述这个公理,并在对抗整个世界的情况下(contra mundum)坚持这个公理的人。
自从苏格拉底首次制定或发现这个新的道德法则(对立于人的法则的神的法则)以来,不仅政治家、将军与民主国家(更不用说独裁政权与君主专制国了)已经无数次地违反了这个法则,而且无数个别的男人与女人在他们的个人行为中也已经无数次地违反了这个法则。例如,倘若我们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会被迫承认,英国和美国这些自以为是的民主国家,在投身于它们合理地认为具有正义性的战争时,针对臭名昭著的敌人,它们有时—某些人或许会说经常—屈从于同态报复的诱惑。不过它们承认这是一种诱惑,它们愿意接受对它们的这种做法的批评。即便在当时,关于轰炸德国与日本以及使用原子弹的正确性的争论就接连不休,自此以后的许多场合下肯定也是如此。这些争辩之所以发生,是由于苏格拉底最初的道德启示以及它随后对普遍良知的启发。
——选自(英)保罗·约翰逊著,郝苑译《苏格拉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