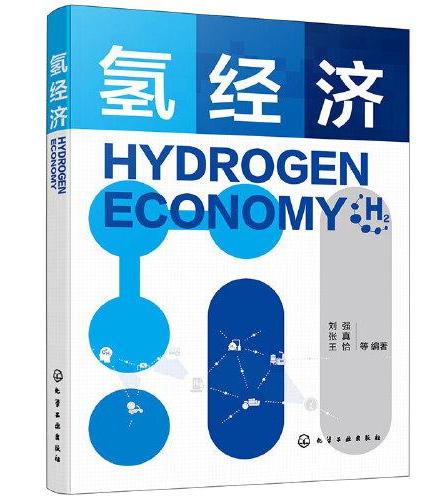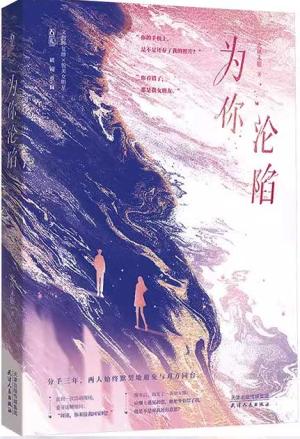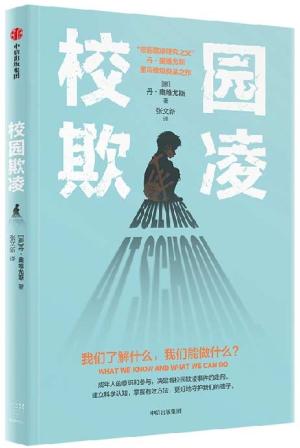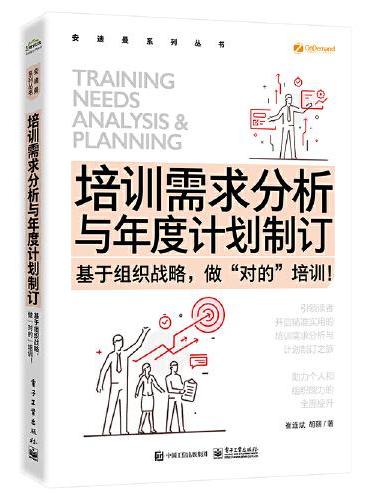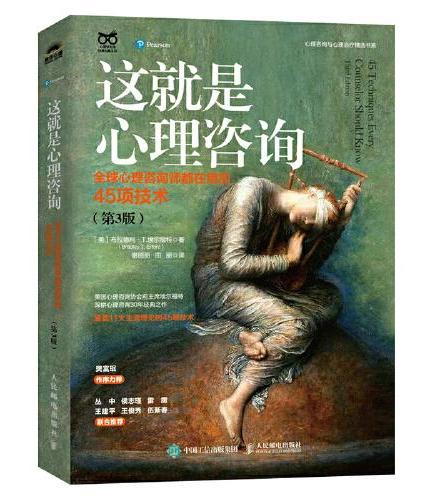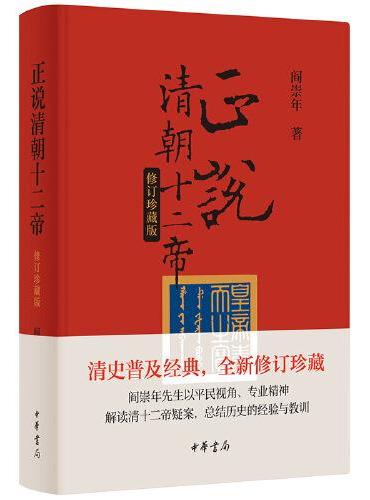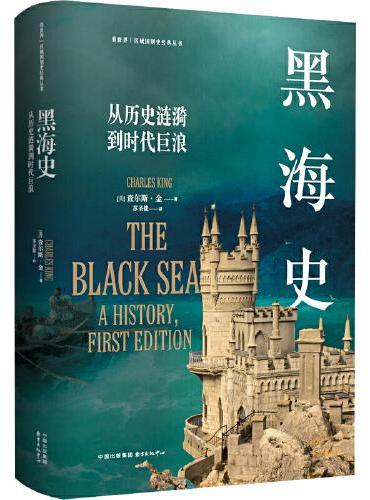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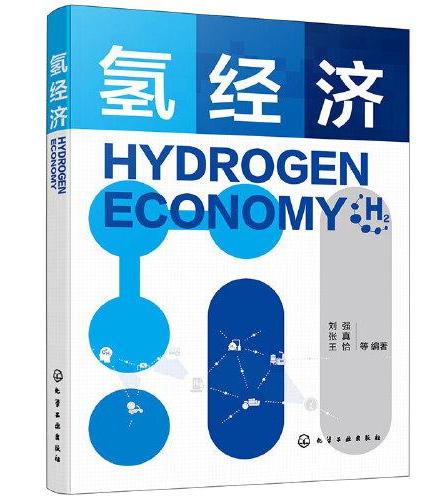
《
氢经济
》
售價:NT$
549.0

《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
售價:NT$
22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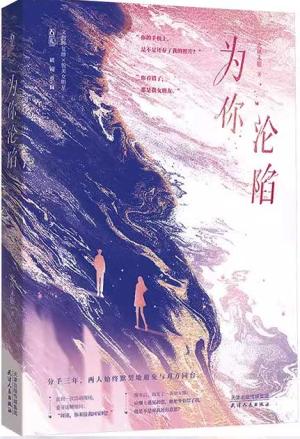
《
为你沦陷
》
售價:NT$
26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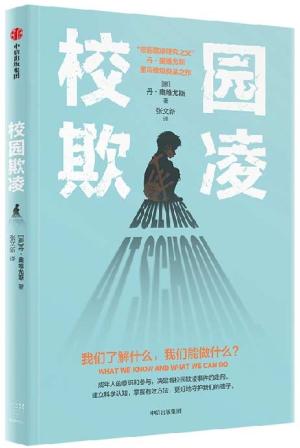
《
校园欺凌
》
售價:NT$
2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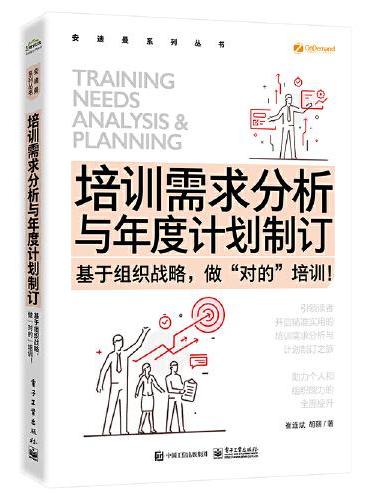
《
培训需求分析与年度计划制订——基于组织战略,做”对的”培训!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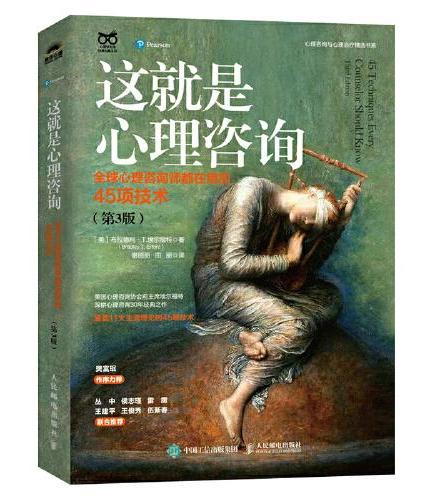
《
这就是心理咨询:全球心理咨询师都在用的45项技术(第3版)
》
售價:NT$
7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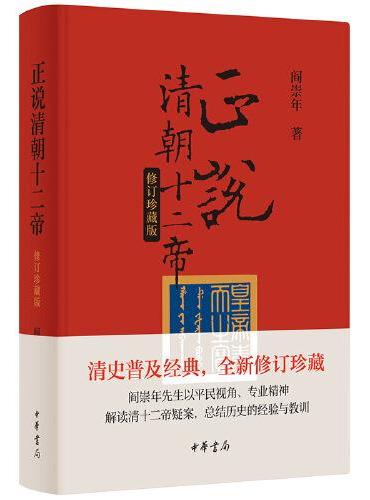
《
正说清朝十二帝(修订珍藏版)
》
售價:NT$
4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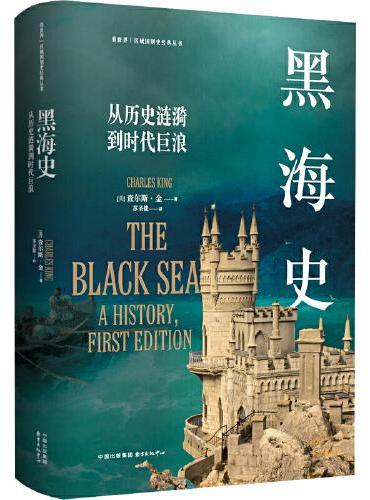
《
黑海史:从历史涟漪到时代巨浪
》
售價:NT$
538.0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收入当代作家系列访谈,对话双方均是当代文坛有相当知名度,在读者间有一定影响力与号召力的名作家、名诗人,其中包括81岁斩获茅盾文学奖,85岁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王蒙;当代著名作家、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奖“获得者、巴蜀五君子之一的欧阳江河;当代著名诗人、“第三代诗歌”标志性人物韩东;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获得者,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的刘亮程;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寻根文学”代表,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得者韩少功……对话双方都有着开阔的文学视野、丰厚的文学素养,对话涉及写书著说、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女性独立、理想乌托邦等,均是与当下、时代、日常有联系且备受大众关注的重要话题。对话内容既有文化、学术高度,又生动鲜活、性情沛然,具有引人入胜的阅读价值。
|
| 關於作者: |
梁鸿鹰,《文艺报》总编辑、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出版评论集《守望文学的天空》《文学:向着无尽的可能》等,散文集《岁月的颗粒》,译作《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等。发表小说、诗歌若干。
何向阳,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出版诗集《青衿》《锦瑟》《刹那》,理论集《朝圣的故事或在路上》,学术随笔《思远道》,长篇散文《自巴颜喀拉》《万古丹山》等。获鲁迅文学奖等二十余种文学奖项。
|
| 目錄:
|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王 蒙?? 何向阳
写作是一条不断拓宽的河流
张 炜?? 赵月斌
让理论的光芒照亮文学和生活
南 帆?? 张学昕
我的写作是有抱负的,它体现为一种阔视和深虑
欧阳江河?? 何 平
“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拨亮人类精神的微光”
陈 彦?? 杨 辉
何来今天的蔚为壮观—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
何建明?? 丁晓原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隐藏着文学的萌芽
范小青?? 子 川
一曲金、木、水、火、土的交响曲
赵丽宏?? 张 炜?? 李东华
“我坚持文学是有基本面的”
曹文轩?? 邵燕君
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与文学生活
汪 政?? 王 晖
北回归线上的“转身”
范 稳?? 李云雷
多棱镜下的文艺之光
欧阳黔森?? 颜同林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
莫 言?? 张清华
作家凭什么让人阅读
韩少功?? 南 翔
女性独立是乌托邦吗?
金仁顺?? 艾 伟
《心居》中都是好人,只是分寸的把握不同
滕肖澜?? 张 英
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永远需要保持求知欲
韩 东?? 魏思孝
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
理 由?? 李炳银
《本巴》:当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
刘亮程?? 杨庆祥
未来学与文学创作
张 炯?? 吴崇源
一切文本和想象都需要根植于大地
罗伟章?? 李 黎
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
白 烨?? 徐 刚
“90后”谢冕:不知老之将至
谢 冕?? 刘鹏波
后记
|
| 內容試閱:
|
序
李敬泽
《多棱镜下的文学之光》是一部对话集。在这里,46位作家、评论家以文学之名相遇。是对话,更是彼此成全。
大概在语言诞生之初,对话就出现了。社会学家讲,语言是人存在的基础,因而对话也是人的本质需求。但并不是只要有语言就有对话,真正的对话应该包含着交锋与碰撞,其间藏匿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往远了说,经由 《论语》,我们结识了孔子及其弟子,经由《理想国》,我们得见遥远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往近了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抵也可称为一个大型“对话”现场,启蒙主义、人文精神、日常生活、消费社会……在一次次的对话中,这些当代文学的关键词逐一浮出水面——《文艺报》曾见 证过这一历史,更深度参与了这一进程。
然而在今天,“对话”这一古老的传统正在遭遇危机。人们习惯了躲在屏幕后面,仿佛一人对抗全世界,研讨会上、批评集里,看似一团和气, 实则自说自话。对话精神的失却,人与人的孤立,或许是某种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局。但是,我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破圈”与“出圈”时,渴望的不正是更广泛、更深层的对话吗?文学的“破圈”,就是从自我走向他者,从小群体走向大多数,进而走向一个整体性的时代现实。
《多棱镜下的文学之光》即是力图恢复文学对话的传统与精神。在对话中,我们看到了对谈者的观点与锐见,但更有意思的是,通过一次次对话,那些躲在小说、诗歌乃至评论文章背后的声音变得清晰可感,那些通常隐于书后的写作者终究走向台前,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于是我们看到,耄耋之年的王蒙依旧豪情万丈地呼唤着“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何其巨大的生命能量;“讲故事”的莫言告诉我们,“每个故事都有一粒种子”,而种子本身更蕴藏着万千秘密;从海边出发的张炜,始终坚守自然大地,追逐纯粹的精神,其文学信念亦如河流般沉潜而宽广;知行合一的韩少功,在深切的个人经验中,重新感知与回应着时代的精神……
是为序。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王 蒙?? 何向阳
“同频共振”这个词我特别喜欢,也特别感动,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
何向阳:王蒙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9日从央视直播中看到习近平主席为您亲自颁发国家荣誉奖章时,我想这份荣誉固然是对您个人成就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是对您所代表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奖掖,以及对共和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作家的激励。作为一个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命运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其间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在您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您如何看待作家、艺术家个体创作与他所处的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王蒙:谢谢您!我们那时候习惯的说法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刚才您说到“共和国第一代作家”,这个词过去我还没听说过,对我也是一种使命和鞭策。新中国的建立跟文学界、文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49年10月1日以前,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老作家,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陶、丁玲、艾青、欧阳山、草明、赵树理、康濯、马烽等,作家的阵容特别强大,而且当时我们文化界、文学界的情况跟苏联还不一样。在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大量作家回归内地、回到大陆来写作,关于这件事情,舒乙讲过,他说老舍就说过,1949年中国有90%的写作者都是欢欣鼓舞地进到北京,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就说我自己吧,我的青年时期,甚至是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的。我入党很早,大概14岁的时候,只是达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入团年龄。我所处的那个时期正好赶上时代的大变迁,这给予了我们这一代人激励、激情,也为我们提供了亲眼为历史作证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作家的幸运,也在以后变成了我们写作中一个共同的文学主题或者说是母题。
何向阳: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单,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2019年我在中央党校第46期中青班学习,我们毕业前的一次会上还有一位老师高声朗诵这部作品中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当这首诗被朗诵出来时,我感觉身上的血都热了。对于《青春万岁》,不同年代的读者的阅读记忆是不同的,2018年在青岛,在“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发布会上,我们坐在台下聆听您和一群中小学生一起朗诵。那次倾听让我和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水。一部作品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青春万岁》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的确是一部跨越了许多岁月的不朽作品,从1957年这部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发表,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整小说,再到1983年黄蜀芹导演同名电影,后来2005年国家话剧院一度要把它改编成话剧,再到2019年《故事里的中国》节目中,它以舞台剧的演绎形式得以呈现,可以说它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而对于您来讲,它的意义更是不同,您个人的青春年代与共和国的青春是同频共振的,而且这种“同频共振”的关系在您的创作中一直贯穿始终。
王蒙:您刚才说的这个词——“同频共振”,我特别喜欢,也特别感动,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那些小至十三四岁、大至十八九岁的青少年,他们赶上了革命的胜利、国家命运再造的进程,这是多么难得。1947年,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当时都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然后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人们唱着新的歌,用的词也都不一样了,人的作风也都不一样了。我写的书恰恰就有这样一种想法,把这些记录下来,把它们挽留住。因为人不可能天天处在这样一种激奋状态,看什么都新鲜:听一次讲话就热泪盈眶,看一部苏联电影也热泪盈眶,你要当时不记录下来,可能以后就很难再体会那种心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后,每天都在发展,都有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北京刚一解放的时候垃圾堆特别多,当时整个东单广场全是高高的垃圾,臭得不行。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根本没人管,后来共产党来了,连夜用两三天时间清理干净。之后一年之内就开始在交道口建电影院,在新街口建电影院,在什刹海开辟游泳场,万事万物,百废俱兴。1953年11月我开始写《青春万岁》,确实也是一种勇敢的对于这个大时代的记录和应答,我想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青春万岁》现在仍然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在重版,2020年也有新版,不止一个版本,我很受鼓舞。因为《青春万岁》是1953年开始写的,1956年我获得了半年的创作假,基本写完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序诗,就是您刚刚讲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当时我特别崇拜的诗人是邵燕祥,我就把序诗寄给邵燕祥,后来他都忘了,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我是他的一个“粉丝”,当时他给我回了封信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这话很有师长的味道。诗一上来有两句话,为了整齐他给我改了,本来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最后他改成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何向阳:在自传、自述写作中,您多次提到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对您最初写作的影响,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您在《王蒙八十自述》中写道,“1952年的深秋与初冬我在阅读巴尔扎克中度过。”您还说,“超越一切的是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他能写出一代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青年人的灵魂,绝不教条,绝不老套,绝不投 合,然而它是最绚丽、最丰富,也最进步、最革命、最正确的。”能够以这样热情的文字写一位作家,足见《青年近卫军》对您写作初始时期的影响,少年时代对俄苏文学的阅读和接近,构成了您作品最初的理想主义底色。
一代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大的时代环境。1956年由中国作协与团中央联合召开的第一次青创会,汇聚了新中国的青年作家英才,听家父说你们当时住在新侨饭店,会议开得生机勃勃,周恩来总理专门到会上来看望你们,可以想见那次青创会的盛况。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与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写作同属一个时间段,它们之间也有主人公生活的连续性,一个即将走出校园,一个刚刚走进机关,主人公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但人们往往对林震这个“新人”的理解与对郑波、杨蔷云等“新人”的又有所不同。林震这个“新人”形象的确是与众不同的,小说似乎在批判向度上将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引入了深层,林震“这一个”人物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即在于他将信仰视为生命,并在工作中一以贯之,不懦弱,不妥协,他坚持坚守的东西真的是贵比千金。但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对“这一个”“新人”形象的研究仍是不够的。什么是您最希望在林震这位主人公身上得到表达的?
王蒙:法捷耶夫是一位长满了革命者的神经与浪漫的艺术细胞的作家,他的革命理想、艺术理想、文学激情融合在了一起。他写的苏联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成员,单纯而又丰富,勇敢而又坚忍,忘我而又个性化。16岁的队长奥列格,冷静周到,有着领导人的素质。净如水莲的乌丽娅,深沉矜持。而泼辣靓丽的柳巴,玩弄法西斯如入无人之境。险中取胜的丘列宁,是孤胆英雄。他们与另一种空虚的、颓废的、自私的哼哼唧唧的人生是怎样地不同啊。即使苏联最后解体了,法捷耶夫则早已自杀,他写青年英雄人物,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他的新生活与新人梦,他对于美好的青年、美好的人生的向往,仍然永在。我当时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人员,我们那时每天讨论的都是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至于林震,他不是英雄,他有追求,也有幼稚和困惑。即使是笃诚的现实主义写作,也因为作品的浪漫与激情而渲染着梦想与现实的碰撞,有火花,也有泪痕,有宏伟雄奇,也有天真烂漫和脆弱。现实而又梦想,生活而又文学,世俗而又升华,多情而又那么多成熟的人情世故:这也许正是文学的魅力吧。
第一次青创会,我们是在北京饭店与周总理见面的,女同志们排着队等着与总理一起跳舞。
在我已有的80多年人生历程里,一个始终有目标、有太多的热度与活计的人生是幸运的,它是光明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是一个足实与成功的人生
何向阳:我注意到您的创作有几次大的起伏,或者说是有过几次创作高峰期,比如20世纪50年代、80年代以及21世纪的今天,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新时代,您的创作均处于“突飞猛进”的爆发期,三个时期各有代表作,从《青春万岁》到《活动变人形》到《笑的风》,各个阶段的中、短篇也极为精彩,比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比如《蝴蝶》《布礼》《如歌的行板》《明年我将衰老》《生死恋》等。但同时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您的创作不惧低谷状态,文学创作能够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完成,比如《青春万岁》,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是在1979年,而那时已是完成它的25年之后了;而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这边风景》,写作于1974年,出版于2013年,从40岁到79岁,其间整整相隔39年。25年,39年,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您一直在以文字与岁月与时间博弈,当然最终您是胜者,同时也可以说这两部作品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也见证了您创作上两个最重要的人生阶段,我想知道的是,您是如何在时间或经历可能要拿走您的文字的时候,而紧紧地抓住它从不放手的?这样的状况好像在一个作家身上并不多见。对于早期作品的修订与创造,其实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是一项比原初的创作更艰难也更具挑战的工作,您是怎样在漫长的岁月中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特别昂扬的创造力的?
王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当然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青春万岁》不是1979年第一次出版,而是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当时获得的反应可能比后来还强烈很多。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安慰自己,这也算是对我的写作的一个考验,一部作品毕竟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历史的考验。《青春万岁》经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这边风景》大致经历了40年才出版,当代文学中有许许多多远比它们更重要的更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经过25年或者45年以后,您再看那些作品,它们可能会是重要的里程碑,但已经不在读者的书桌上,更不在青年的案头上了。这也是很遗憾的事。所以我觉得《青春万岁》近70年后还红火着,真是幸福啊。您记得吗?国庆70周年,国庆群众游行的一个方队就被命名为“青春万岁”,而方队的自行车队,是多么接近黄蜀芹导演的影片《青春万岁》的场面啊!这也是我的幸运,尤其我没想到,在邵燕祥的帮助下改出来的序诗,现在还有点家喻户晓的劲儿。您上网上查一查,有很多版本,有青年学生、著名演员、广播员、艺术大家朗诵并演绎的不同的视频版本,各有各的味道。
何向阳:这首诗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中都能引起共鸣。它跟您的许多作品一样,就是总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底色在里面,有一种乐观的、不顾一切而向前走的精神,我个人觉得您的作品一直有一种追光感,或者说是一种趋光性,一种向前的行动,它是追光而行的,哪怕在个人创作不是很顺畅的时期,或者是在坎坷、曲折的人生段落里,您的作品,包括您本人也一直给人以一种追光的感觉。
王蒙:我是觉得不管怎么说,在我已有的80多年人生历程里,一个始终有目标、有太多的热度与活计的人生是幸运的,它是光明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是一个足实与成功的人生。人一旦老了,往往有些遗憾和后悔,觉得这个事情想干没干,那个地方想去没去过,年轻的时候想唱歌也没唱好,后来想跳舞也不会跳……可我这样的遗憾比较少,我86岁了,没闲着,不必蹉跎踌躇,这绝对是一种真实的心情。我也觉得环境对我来说仍然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我开玩笑说,人这一辈子跟打篮球一样,上半场你输得比较多,15比68落后,可是下半场你打得优秀一点,反败为胜了,大比分超越,还发什么牢骚,还吭吭唧唧什么呢?
这是从个人角度,从社会、国家的角度来说,我这辈子经历了别人几辈子的事,原来咱们吃喝拉撒睡是什么样的,现在又是什么样?我小时候出生后的三年里,最大的事就是卢沟桥事变,日本占领了我们的国土,当时我是在沦陷区,也叫占领区。我们那儿离阜成门很近,到处都站着日军,男女老幼从他们面前经过都得鞠躬。小学里有个日本教官,一上课全体老师学生都得站起来先说日语,那是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太多事儿了,当然自己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我自己也参加了,也争取了,也冒险了,也奋斗了,付出了不可以不付出的代价。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有这么一个光明的底色。再说我虽然小,但党的政治生活参加得非常多,从最早在天安门广场参加腰鼓队,到后来“三反”“五反”的时候斗资本家,各种事见多了。当然我也会懊恼,也觉得自己肯定有错误,有缺点,有需要纠正的地方,但是少有遗憾。
何向阳:您经历了新中国的成立、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这样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作家,对这一完整的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您是最好的观察者、参与者,同时也是最有发言权的书写者。您的作品也的确忠实记录了共和国的发展历程,当然其中也有曲折和弯路,但您在作品中表达的情绪一直是昂扬的、乐观的、向前的,即使在面对困难时也毫不晦涩灰暗,您一直相信,一种对生活的信念在您作品中一直“活着”,就像《布礼》中凌雪对钟亦成所说的“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的法则”“人民的愿望、正义的信念、忠诚”,作为您作品中的底气,哪怕是在杂色的生活中,您的写作所传达出来的东西也总是光明、温暖而坚定的。
王蒙:对,非常坚定,尤其没有绝望的念头。我总是觉得,事情总会往好的方面发展,即便不发展也坏不到哪儿去。为什么呢?我去新疆从事了很多体力劳动,但是劳动不好吗?我父亲跟我说过俄罗斯的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话,原文我记不清了,大意是说——我爱劳动,我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但是我更爱体力劳动。您也可以说这是自我安慰,但是为什么人不可以自我安慰?你不自我安慰,自己折腾自己,自己折磨自己,我觉得不是好的选择。
何向阳:特别喜欢您这种乐观的态度,总是很欢乐地去拥抱生活,这其实体现了您的人生信念,包括对生活的信念,对文学的信念,对人的信念,这是一个底子。有这个底子,才能够坦然面对所经历的一切,才能够纵浪大化,不忧不惧。刚才您说到新疆,新疆之于您的创作与人生的重要性而言,是不可替代的。从1963年到1979年您在新疆度过了16个春秋。1963年您还不到30岁,这16年是您从29岁到45岁的岁月,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从青年到壮年的最好的时候。您的《你好,新疆》一书开篇一句就是:“我天天想着新疆!”您在回忆新疆时期的文字中写这16年对您的一生“极其重要”,您“受到了边疆巍巍天山、茫茫戈壁、锦绣绿洲、缤纷农舍的洗礼”,您“更开阔也更坚强了”,您对外国朋友说,您这16年“在修维吾尔学的博士后。预科两年,本科5年,实习3年,硕士研究生两年,博士研究生两年,博士后两年,共16年整”。您说,“越是年长,我越为我在新疆的经历,为我在新疆交出的答卷而骄傲。”70万字的《这边风景》作为一份长长的答卷,足见新疆在您生命中的分量,足见这段生活对您产生了怎样至关重要的影响。
王蒙:这里我要说明一点,我在新疆16年间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大概是8年,并不是全部的时间。因为我在伊犁,户口和家都安在伊犁,但我是在农村参加劳动,有6年时间在农村参加劳动,还在“五七干校”待了两年多。另外8年是在编辑部,当时叫创作研究室,帮助当地排话剧写稿子。我确实是喜欢新的事物,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我为什么愿意去新疆呢?原因之一就是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要经风雨,见世面。他说,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而且我认为毛主席特别关注中国的农民。所以我就去了新疆,我在北京待的时间太久了,那时候我已经快要30岁了。
何向阳:所以您29岁选择了去新疆。
王蒙:对啊,我已经快要30岁了,这里头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北京,除了3岁以前模模糊糊的记忆里是生活在河北南皮。一个人光在北京生活是绝对不够的。还有一个,我现在想起来也感到特别幸运,就是我当时在北京找不着感觉,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生活复杂多变,我也没办法预料和判断未来的生活和前景会怎样,一直到现在,我在回忆我这一生的时候,都认为当时自己做出了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智慧选择,那就是去新疆。去新疆我救了自己,也获得了更阔大的世界。
世界这么大,尤其新疆,不到新疆你能知道伟大祖国有多大吗?一到新疆,我立马就服了,那出一趟差到伊犁得三天三夜,到喀什得六天六夜,到和田需要九天九夜。在新疆,人对于空间和时间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此外当然还有文化观念的变化。新疆是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个民族各有各的特色,南疆和北疆也不同,即便同样是南疆,喀什噶尔跟阿克苏、和田也不一样,和北京当然是不一样的,就像俄罗斯思想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专门写过一本书《外省散记》,如今,一个写作人在首都与在“外省”也各有特色,各有长短。我觉得我的心胸、观念在当时有了很大的扩展,这扩展也不容易,这种可能性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国也是很难做到的。这也是我人生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且我还必须说明,在这个阶段我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我只能说,我的选择是一个自然的正面的选择。我没有因为去新疆而悲观失望,而是越来越有希望。
何向阳:新疆对于一位作家的滋养,是让您接了地气。原来是一个青年,回来就是一个壮年了,而且您是带着整个人生的新疆的大风景回来的。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1979年到1986年,您的创作呈现出一种“井喷”的状态,那时候一打开文学刊物全是王蒙的新作,而且风格各异,有现实主义的、有现代派的、有先锋的,让读者有“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蝴蝶》《春之声》《海的梦》,新作之多,真的是让评论家们追也追不上。这种创作的“井喷”状态,是不是也有新疆生活对您的激发?一下子就把您的这个气给提起来了。
王蒙:新疆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和我的城市生活互相参照的一个参照物。当我写到城市,特别是干部和知识分子,脑子里浮现的仍然是新疆农民的音容笑貌,当我写到新疆的这些事情,也有城市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以他们的存在来比较,这大概可以叫作比较地理学。刚才您提到一些作品,但是还有一个作品您没有提到,它对我个人的意义非常大,就是《夜的眼》。《夜的眼》写得非常早,那是1979年10月我写出来的,11月刊登在《光明日报》,而且《光明日报》发了一个整版。《夜的眼》的读者可能没从中看到新疆,但实际上有新疆。说到原来我待的这个地方去搭便车,手里头抓着一个羊腿,这种场面是属于新疆的,可爱,可悲。后来我写了一组收到《在伊犁》里,都是跟新疆有关系的作品,甚至其中某些还带有非虚构色彩,这些作品有的翻译成了日语,有些翻译成了英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