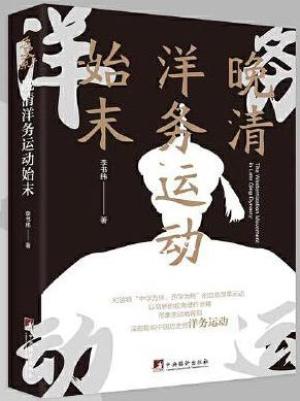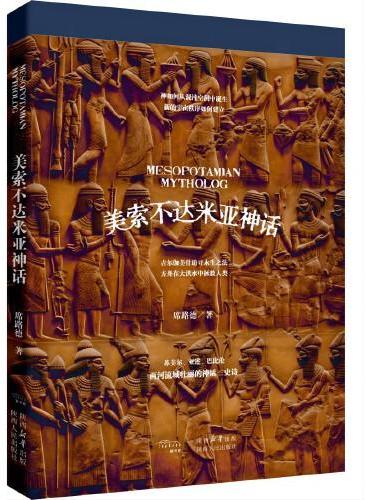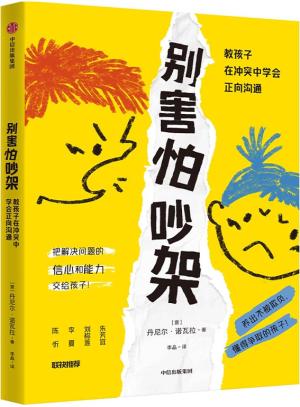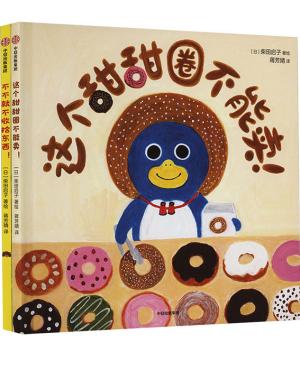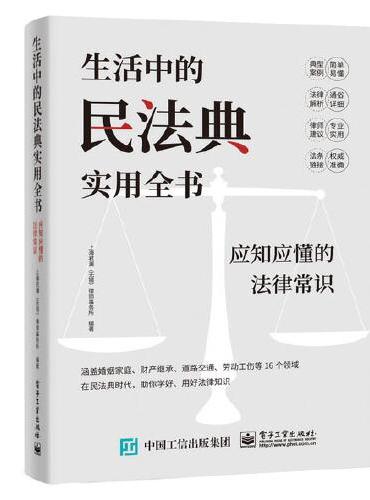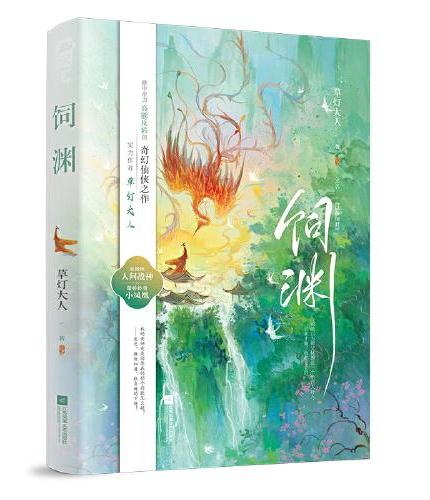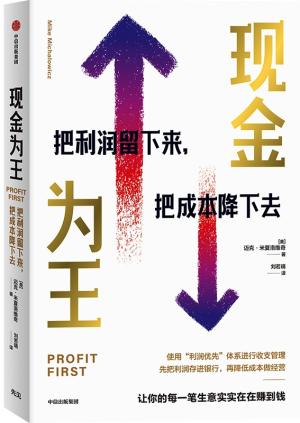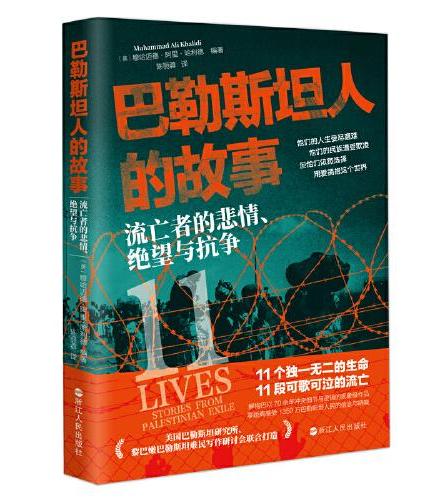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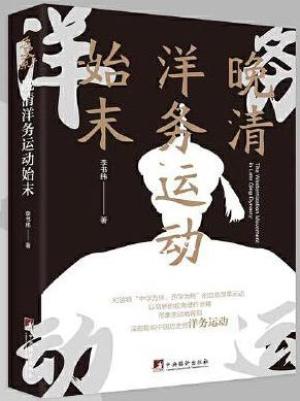
《
晚清洋务运动始末
》
售價:NT$
4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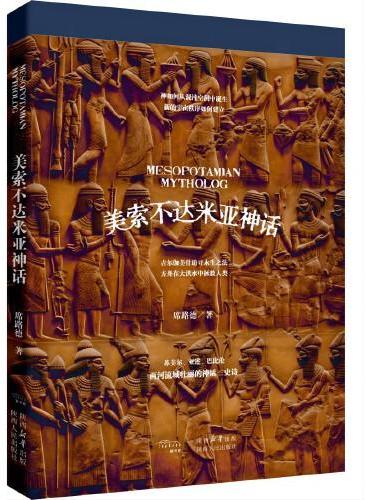
《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
》
售價:NT$
3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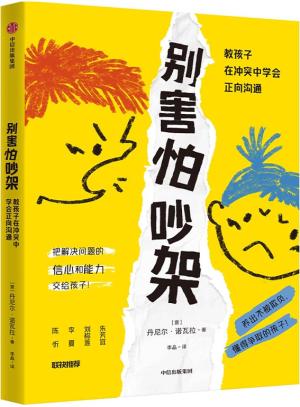
《
别害怕吵架:教孩子在冲突中学会正向沟通
》
售價:NT$
2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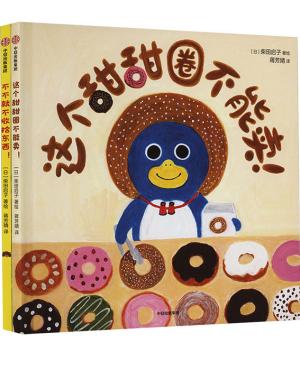
《
这个甜甜圈不能卖:奇思妙想爆笑绘本(全2册)
》
售價:NT$
4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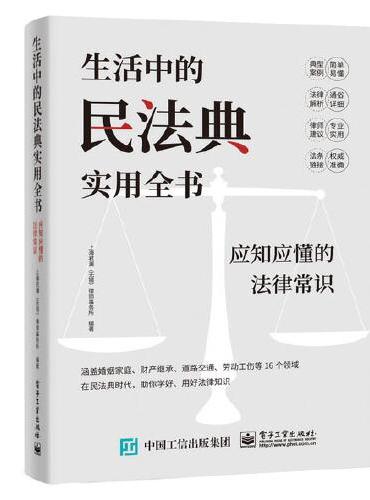
《
生活中的民法典实用全书:应知应懂的法律常识
》
售價:NT$
4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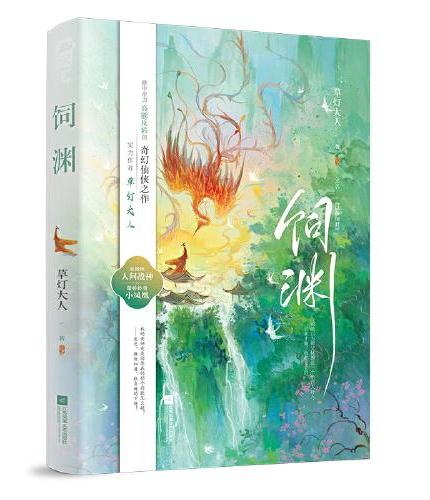
《
饲渊
》
售價:NT$
2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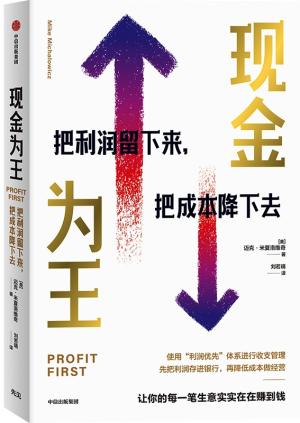
《
现金为王:把利润留下来,把成本降下去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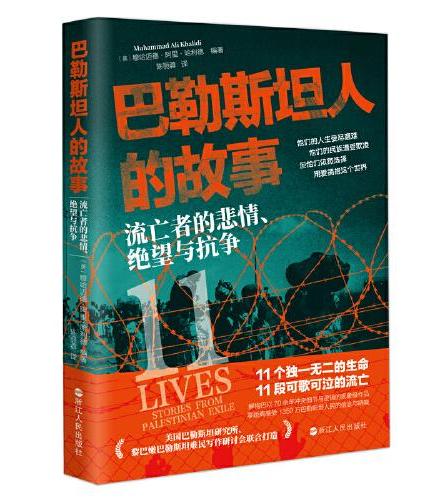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流亡者的悲情、绝望与抗争
》
售價:NT$
493.0
|
| 編輯推薦: |
★ 中小学生外国文学必读书目。
★ 村上春树阅读书单推荐。
★ 木心《文学回忆录》推荐书目。
★《如何阅读一本书》推荐书目。
★《一生的读书计划》推荐书目。
★ 习大大的阅读书单推荐。
★ 收录契诃夫短篇小说代表作。
★ 著名翻译家李辉凡倾心翻译。国内优质译本。
★ 本丛书由翻译名家柳鸣九主编,多位著名翻译家、学者编选,极具收藏价值。
|
| 內容簡介: |
|
《套中人——契诃夫短篇小说选》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选集,收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变色龙》、《一个官员之死》、《万卡》、《六号病房》、《套中人》等二十余篇作品。契诃夫被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其创作的短篇小说是十九世纪末俄罗斯乃至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本书所选的作品代表了契诃夫各个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其中很多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课本,可谓家喻户晓。
|
| 關於作者: |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俄罗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和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莫泊桑和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他坚持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描写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塑造具有典型性格的小人物,借此真实反映出当时俄国社会的状况。代表作有《套中人》、《六号病房》、《不安分的女人》、《樱桃园》等。
李辉凡,1933年生,广东兴宁人。1956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学院俄语系,1956年就读于哈尔滨外语学院研究生班,1959年进修于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1961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及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著有专著《文学·人学》、《二十世纪初俄苏文学思潮》、《苏联文学史》合作、《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译著长篇小说《复活》,短篇小说集《套中人》,编辑《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世界散文经典》、《契诃夫精选集》等。
|
| 目錄:
|
常读常新的契诃夫
迟开的花朵
坏孩子
一个官员之死
戴假面具的人
变色龙
牡蛎
苦恼
万卡
乞丐
六号病房
不安分的女人
文学教师
太太
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带阁楼的房子
关于爱情
套中人
醋栗
姚内奇
宝贝儿
烟草有害
新娘
附录契诃夫生平及创作年表
|
| 內容試閱:
|
套中人
打猎误了时的人们就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边普罗科菲村长的杂物房里歇宿了。他们只有两个人:兽医伊万·伊万内奇和中学教师布尔金。伊万·伊万内奇有一个相当奇怪的双姓—奇姆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对他很不合适。全省的人都只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他住在城郊一个养马场里,这次出来打猎,是为了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中学教师布尔金则是每年夏天都要到П伯爵家来做客的,对这个地方他早就很熟悉了。
他们都没有睡。伊万·伊万内奇是一个高高瘦瘦的老头,留着很长的唇髭,在门口脸朝外坐着,叼着烟斗,沐浴着月光。布尔金躺在里面的干草上,在黑暗中看不见他。
他们在聊天。顺便谈到了村长的老婆玛芙拉。她是一位健康的女人,也不笨,但她一辈子从来没有走出过自己的村子,从来没有见过城市,也没有见过铁路,近十年来总是守着炉灶,只有晚上才到外面走一走。
“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布尔金说,“生性孤独的人就像寄生蟹一样,竭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人还不少哩。也许这是一种返祖现象,想重新回到人类祖先那个还不是群居而是各自单独地穴居的动物时代,也可能这只是人类各种性格的一种类型吧—谁知道呢?我不是自然科学家,论及这类问题并不是我的事。我只想说,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不是罕见的现象。瞧,无须到远处去找,我们城里就有一个别里科夫,他是希腊语教师,我的一位同事,大约在两个月之前去世了。关于他的事,您当然也听说过。他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即使在非常好的天气里,外出时他也要穿上套鞋、带上雨伞,而且一定要穿上暖和的棉衣。他的雨伞也装在套子里,表也装在灰色麂皮的套子里。当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时,这小折刀也是装在小套子里的。他老是把他的脸躲在竖起的衣领里,因此他的脸也好像藏在套子里了。他戴一副黑眼镜,穿着绒衣,用棉花塞着耳朵。当他坐上马车时,就立即吩咐把车篷支起来。总而言之,在这个人身上可以看到一种一贯的、不可遏止的愿望:用一层外壳把自己包起来,为自己制作一个所谓的套子,把自己隔离起来,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使他害怕,他老是处在惶恐不安之中。也许是为自己的这种胆怯,为自己排斥现实世界作辩护吧,他老是赞扬过去,赞扬那从未有过的东西。就是他所教授的那些古代语言,对他来说,实际上也和他的套鞋和雨伞一样,是用以躲避现实生活的。
“‘啊,希腊语多么好听,多么优美!’他带着一种甜蜜蜜的表情说,并且好像要证明自己的话似的,眯起眼睛,伸出一只手指,念出一个词:‘安特罗波斯!’
“别里科夫甚至连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对于他来说,只有那些告示和有关禁令的报纸文章才是明白无疑的。当他看到禁止学生晚上九点钟以后上街的告示,或者是禁止性爱的文章时,他就觉得又清楚又明白:禁止就是了。而对于那些得到批准和许可的事情,他却觉得有些可疑的成分,觉得没有说透和模糊不清。每当城里获准成立一个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时,他总是摇摇头,并小声说:
“‘当然,这固然很好,只是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
“任何违反法令、偏离常规、不合规则的事都会使他精神沮丧,虽然这些事看来与他并不相干。如果同事中有谁参加祈祷迟到了,或者听到中学生调皮捣蛋的传闻,再不就是有人看到女子中学的女学监同军官玩得太晚,他都会非常激动,并且不停地说: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在各种教务会议上,他那种谨慎、神经过敏和纯粹套子式的意见,简直使我们感到难受。说什么不论是男子中学还是女子中学的青年品行都很坏,在教室里吵吵嚷嚷。唉,千万别让上司知道了!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还说什么,如果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那倒很好。后来呢,他用叹息、牢骚及其苍白的小脸(您知道吗,那脸就像是黄鼠狼的脸)上的黑眼镜,使我们大家都折服了。我们让步了,扣了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开除了。他有一种奇怪的习惯,经常到我们的住所来。他每到一个教师家,都是坐着,不说话,好像在观察什么似的。就这样默默地坐上个把小时,然后走掉。他把这称作‘与同事们保持良好的关系’。显然,他到我们这里来坐着,在他也是很难受的。他之所以来看我们,只是因为他觉得他对同事有这种义务罢了。我们教师们都怕他,连校长也怕他。您瞧,也难怪,我们这些教师都是有思想的、极正派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培育。但是,这个老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人却把整个中学禁锢了整整十五年!不光禁锢中学,还禁锢了全城。由于怕他知道,我们的太太们连星期日的家庭戏剧晚会也不举行了。他在的时候,牧师们不敢吃荤和玩牌。在别里科夫这种人的影响下,最近十至十五年来,我们城里人变得什么都害怕,不敢大声说话,不敢寄信,不敢与人相识,不敢读书,不敢帮助穷人,不敢教人知书识字……”
伊万·伊万内奇想说点什么,清了清喉咙,但先点燃了烟斗,看了看月亮,然后才从容不迫地说:
“是啊,有思想、正派,读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的作品,还读巴克尔等人的书,可是,他们却屈服、容忍这种事……问题就在这里。”
“别里科夫和我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布尔金接着说,“在同一层楼上,门对着门。我们常见面,我知道他家里的生活。在家里他也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一系列清规戒律,还有:唉,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素食有害,吃荤又不行,因为人家也许会说,别里科夫不坚持斋戒,于是他就吃奶油煎的鲈鱼,这既不是素食,但也不能说是荤菜。他不雇女佣,因为他怕别人对他有坏的想法,所以他雇了一个六十岁上下、神志不清、性情乖张的老头子阿法纳西做他的厨子。此人以前当过勤务兵,好歹能做点饭菜。阿法纳西总是双手交叉在胸前,站在门口,长叹一声,悄悄地重复着一句话:
“‘时下他们这样的人多得很哩!’
“别里科夫的卧室很小,就像一个箱子,床铺挂着蚊帐。他一上床就把头蒙上,又热又闷,风抽打着关闭着的门,炉子发出嗡嗡声,从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声……
“他躺在被窝里心里很害怕。他害怕会出什么乱子,害怕阿法纳西把他宰了,害怕小偷溜进来,然后是整夜做噩梦。早晨,我们一同到学校去的时候,他无精打采,脸色苍白。看得出来,他害怕他所去的那个有很多人的学校,非常厌恶。跟我走在一起,对他这个性情孤僻的人来说,也很难受。
“‘我们的班级里学生闹得很,’他说,好像是在尽力寻找说明他难受的理由似的,‘真不像话。’
“就是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您猜怎么着,还差点儿结了婚。”
伊万·伊万内奇很快地扫了一眼什物房,说:
“您在开玩笑!”
“真的,尽管您觉得很奇怪,但他的确差点儿结了婚。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新的史地教师,名叫米哈依尔·萨维奇·柯瓦连科,是乌克兰人,他不是一个人来,而是带着他的姐姐瓦莲卡一起来的。他年纪很轻,高个子,皮肤黝黑,一双手很大,从脸上就可以看出他是男低音。果然,他的嗓音像从大桶里发出来的:‘嘭,嘭,嘭!’……而她呢,可不算年轻了,大概有三十岁了,不过她个子很高,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两颊红润,总之,她已不是一位姑娘,而是一块水果软糖,伶俐活泼,爱说爱笑,老是哼着小俄罗斯的浪漫歌曲,并且高声大笑,动不动就‘哈哈哈!’笑起来。我记得,我们同柯瓦连科姐弟的初次相识是在校长命名日的宴会上。在那些拘谨的,甚至把赴命名日宴会也看作是尽义务的、紧张而又乏味的人中间,我们突然看见一位新的阿芙洛狄忒从泡沫里复活了:她双手叉腰地走着,又笑又唱,跳起舞来……她动情地唱着《风儿在吹》,然后又唱浪漫歌曲,接着又唱一支。她使我们所有的人,甚至连别里科夫,都迷住了。别里科夫靠近她坐下,甜蜜地笑着说:
“‘小俄罗斯语言柔美,响亮动听,使人想起古希腊语。’
“这些话使她感到很愉快,于是她便热情而恳切地对他讲起她们加嘉奇县有个庄子,她妈就住在这个庄子里。庄子里有多么好的梨,多么好的香瓜,多么好的卡巴克!乌克兰人把南瓜称为卡巴克,把酒馆称作什诺克。他们称红甜菜和茄子煮的红甜菜汤‘很好吃,很好吃,简直好吃极了!’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大家都想到一块儿了。
“‘让他们结成夫妻该多好啊。’校长夫人小声地对我说。
“不知何故,我们大家都想起来了: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有结婚。这时我也感到奇怪,他生活里的这件大事,我们以前怎么竟会没有注意,一直忽略了呢?他对女人一般会持什么态度呢?他又将如何解决这一迫切问题呢?以前我们全然没有关心这件事,也许连想也没有想过,这个不论什么天气都穿着套鞋、放下帐子睡觉的人也会恋爱。
“‘他早已过了四十岁,而她也三十了……’校长夫人说明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她肯嫁给他。’
“在我们省里,由于烦闷无聊,什么事没做出来呀,有过多少不必要的蠢事啊!这是因为,必要的事大家根本不做。瞧,就拿这个别里科夫来说吧,既然大家甚至不能想象他可以结婚,我们又何必突然要去撮合他们的婚事呢?校长夫人、副校长夫人以及我们中学的所有的太太们都活跃起来了,甚至比以前变得好看多了,好像突然间发现了自己的生活目标似的。校长夫人在戏院里租了一个包厢。我们一看,坐在包厢里的原来是瓦莲卡,她摇着那么一把小扇子,容光焕发,满面笑容。坐在她旁边的是别里科夫,矮小、驼背,就像人家用钳子把他从家里夹出来的。我在家里办了一个小小的晚会,而太太们却要求我一定要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莲卡参加。总之,机器开动起来了。看来,瓦莲卡并不反对出嫁,她在弟弟家里过得并不十分快活,他们整天都是又吵又骂的。您看看下面一个场面吧:柯瓦连科在大街上走着,他是一个又高又壮的大个子,穿一件绣花汗衫,帽子下面露出一绺长发耷拉在额门上,一只手提着一捆书,另一只手拿着一根带节疤的粗木棍。姐姐跟在他后面,也拿着书。
“‘你啊,米哈伊里克,这本书你绝对没有读过!’她大声争辩道,‘我跟你说,我敢发誓,这本书你根本没有读过!’
“‘我跟你说我读过!’柯瓦连科大声喊道,用木棍在人行道上敲得很响。
“‘唉,我的天呀,明契克!你干吗要发火?要知道,我们谈的是带原则性的问题。’
“‘我跟你说我读过!’柯瓦连科喊得更响了。
“在家里,有旁人在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大吵大嚷。大概这种生活使她厌烦了,因此想有一个自己的窝,而且也不能不考虑自己的年龄了。她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挑挑拣拣,嫁给谁都行!哪怕是那位希腊语教师也可以。原因是很明白的:对我们大多数的小姐来说,不管是嫁给谁,只要能嫁出去就行。不管怎么样,瓦莲卡对我们的别里科夫开始表示明显的好感了。
“而别里科夫呢?他也常到柯瓦连科家去串门了,就像常到我们这里来一样。进了他家就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而瓦莲卡就给他唱《风儿在吹》,或者用她那双黑眼睛若有所思地瞧着他,或者是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哈!’
“在恋爱的事情上,特别是在婚姻上,劝导往往能起很大的作用。不论是同事们和太太们,大家都劝说别里科夫应当结婚,对他来说,生活中除了结婚已没有别的缺憾了。我们全都向他道喜,用严肃的面孔向他说了各种俗套话,比方,婚姻是人生重要的一步等;何况,瓦莲卡长得不错,挺招人喜欢,她是五等文官的女儿,有田庄,更主要的是,她是第一个亲热而诚心地待他的女人。于是他有点飘飘然,拿定主意,真要结婚了。”
“那么,这时他的套鞋和雨伞就该收起来了。”伊万·伊万内奇说。
“您想象一下吧,这是不可能的。他虽然把瓦莲卡的照片摆在了桌子上,而且常到我这里来谈论瓦莲卡,谈家庭生活,谈婚姻是人生重要的一步,也常到柯瓦连科家去,但是他的生活方式却一点儿也没有变,甚至相反,结婚的决定好像使他染上了某种疾病似的,他变得更瘦了,脸色更苍白了,好像更深地躲进自己的套子里去了。
“‘我喜欢瓦尔瓦拉·萨维什娜,’他对我说,带一种微微的苦笑,‘我也知道,人人都要结婚,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切来得有点突然……需要好好想一想。’
“‘这有什么好想的呢?’我对他说,‘结了婚,就完事了。’
“‘不,婚姻是终身大事,首先得估量一下面临的义务和责任……以后可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才好。这一点使我十分不安,如今我整夜都睡不着。说老实话,我害怕,她和他的弟弟有一种奇怪的思维方式。知道吗,他们议论起事情来有点奇怪。她性格又很活泼,结婚以后恐怕难免会闹出点什么麻烦来。’
“于是他没有求婚,一拖再拖,弄得校长夫人和我们的所有的太太们非常懊丧。他老是在捉摸将来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他又差不多每天都同瓦莲卡出去散步。也许他认为,在他这样的处境下他应该这样做。他常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谈谈家庭生活。如果不是突然闹出一场大笑话的话,他后来可能就结婚了,从而也就作成一桩不必要的、愚蠢的婚事了。在我们这里,由于烦闷无聊,由于无所事事,像这样结婚的有成千上万的例子。应该说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从认识别里科夫的第一天起就恨他,受不了他。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告密者,这样卑鄙的家伙。哎呀,先生们,你们怎么能在这儿生活啊!你们这里的空气要窒息人,坏透了!你们难道是教育家,是教师吗?你们是官僚。你们这里不是学府,而是警察局,并且散发出一股警察岗亭里的酸臭味。不,诸位老兄,我在你们这儿再住一阵,就要回到我们庄子里去了,在那里我可以捞捞鱼虾,教教乌克兰的小孩子。我是要走的,而你们却要同你们的犹大留在这里。叫他倒霉去吧。’
“要不他就哈哈大笑,笑得流眼泪。他时而用男低音,时而又用尖细的声音,摊开双手问我:
“‘他干吗要上我这儿来坐着?他想干什么呢?坐着,两眼发直。’
“他甚至给别里科夫起了一个外号,叫‘蜘蛛’。当然,我们没有对他说他姐姐瓦莲卡打算跟‘蜘蛛’结婚的事。有一次,校长夫人暗示他说,要是他的姐姐跟别里科夫这么一个可靠的、受大家尊敬的人结婚,倒是一件好事。这时他皱起眉头说:
“‘这不关我的事。哪怕她跟毒蛇结婚也行。我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
“现在您听一听后来的事情吧。有一个捣蛋鬼画了一张漫画,画中的别里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正在走路。瓦莲卡挽着他的胳膊。下面的题名是:‘热恋中的人’。您明白吗,表情画得妙极了!想必画家不止画了一夜,因为所有男中和女中的教师们、宗教学校的教师们和官员们都接到了一份。别里科夫也接到了一份。这幅漫画给了他非常难受的印象。
“这天正好是5月1日,星期天,我们一起从家里出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员事先约好在学校里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城外的小树林里去。我们都来了,他却愁眉苦脸,脸色比乌云还要阴暗。
“‘竟有如此恶劣、歹毒的人!’他小声说道,嘴唇都颤抖了。
“我甚至同情他了。我们走着。忽然,您能想象到吗,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过来了,瓦莲卡也骑着自行车跟在他的后面。她满脸通红,消瘦了许多,可是开心,快活。”
“‘我们先到前面去了!’她大声喊道,‘咳,天气多好啊!多好啊,简直好极了!’
“他们俩一会儿就消失了。我们的别里科夫则从愁眉苦脸变成脸色苍白,好像是僵住了。他站住,望着我—
“‘对不起,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道,‘也许是我看错了?难道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
“‘这有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就让他们随便骑好了。’
“‘这怎么可以呢?’他叫喊起来,看见我满不在乎的样子,他很惊讶,‘你在说什么啊?!’
“他大为震惊,于是不想再往前走,回家去了。
“第二天,他老是神经质地搓手,打哆嗦,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身体欠佳。还没上完课他就走了,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这样做,也没有吃午饭。尽管外面已完全是夏天天气,傍晚时他还是穿得很多,慢慢地往柯瓦连科家里去。瓦莲卡不在家,他只见到了她的弟弟。
“‘您就请坐吧。’柯瓦连科皱着眉头冷冷地说。他的脸上睡意未散,午饭后他刚休息一会儿,心情很不好。
“别里科夫默默地坐了十分钟左右才开始说: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减轻我内心的痛苦,我心里非常非常难受。有一个卑鄙的人画了一张漫画,把我和另一个与我们俩都很亲近的女人画成可笑的样子。我认为我有责任让您相信,我与此事毫无关系……我没有做任何可以为这种讥讽做口实的事情,相反,我任何时候的行为举止都是一个完全正派的人。’
“柯瓦连科噘着嘴坐着,一言不发。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接着又用忧郁的声调小声地说:
“‘我还有一点事要对您说。我已经从教多年了,而您刚刚开始工作,作为一个老同事,我认为有责任对您提出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游戏对一个青年教育者来说,是很不体面的。’
“‘为什么呢?’柯瓦连科用男低音问道。
“‘这难道还要解释吗?米哈依尔·萨维奇,难道您不明白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学生会干出什么事来呢?他们就只有用头顶着地走路了!既然当局没有通令允许这样做,那就是不行。昨天我大吃一惊!当我看见您姐姐时,我眼前都发黑了。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这太可怕了!’
“‘说实在的,您到底想干什么呢?’
“‘我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警告您,米哈依尔·萨维奇。您是青年人,前途远大,您要十分谨慎小心才成,而您却如此马虎大意。哎呀,如此马虎大意。您穿绣花汗衫,经常在大街上提着书走来走去。而现在又骑自行车。您和您的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让校长知道的,然后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这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这不干任何人的事!’柯瓦连科说,涨红了脸,‘谁要是干涉我的家事和家属的事,我就叫他妈的滚蛋!’
“别里科夫脸色煞白,站了起来。
“‘要是您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说话,那我们就谈不下去了。’他说,‘我要求您永远不要在我面前这样地谈论上司,您应该尊敬当局才对。’
“‘难道我对当局说了什么坏话吗?’柯瓦连科问道,生气地看着他,‘请您不要打搅我。我是个正直人,我不想跟您这样的先生谈话,我不喜欢告密者。’
“别里科夫神经质地慌乱起来,急忙穿上大衣,脸上显出害怕的表情。要知道,他有生以来头一回听到如此不礼貌的话。
“‘您要说什么,随便吧,’他一面说,一面走出前堂,来到楼梯台阶上,‘我只是预先声明一下,说不定有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为了避免我们的谈话被曲解和闹出什么乱子来,我应该把我们谈话的内容……基本要点,向校长先生报告一下。我必须这样做。’
“‘报告?去吧,去报告吧!’
“柯瓦连科从后面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猛地一推,别里科夫就顺着楼梯滚下去了,他的套鞋啪啪地响。楼梯高而且陡,不过他滚到下面却平安无事。他站起来,摸摸鼻子,看眼镜碰碎没有。可是,正当他从楼梯上滚下来时,恰巧瓦莲卡回来了,还带了两位太太,她们站在下面并瞧着他—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比什么都可怕。看来,哪怕是摔断了脖子和两条腿,也比成为取笑的对象要好些,因为,这下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并将传到校长的耳朵里,传到督学的耳朵里。哎哟,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人家又会来一幅漫画,其结果就会命令他辞职……
“当他站起来时,瓦莲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可笑的脸,揉皱的外衣和套鞋,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还以为是他自己意外地摔下来的,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整所房子都听得见:
“‘哈哈哈!’
“这响亮的有节奏的‘哈哈’笑声把一切都结束了:做媒求亲的事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也结束了。他没有听见瓦莲卡说了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他回到家里,首先是把桌上放着的瓦莲卡的照片拿掉了,然后便躺下来,从此就再也没有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要不要派人去请医生,因为,据说他主人有点毛病。我便去看别里科夫。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不言语:不管你问什么,他都回答‘是’或者‘不是’,别的什么也不说。他躺着,阿法纳西则在他旁边走来走去,满脸忧郁,愁眉不展,深深地叹气,从他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像酒馆里的烈酒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大家都去给他送葬,就是说,两个中学和一个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如今他躺在棺材里,表情温顺、愉快,甚至高兴,好像他在庆幸自己终于被装进了套子里,永远也不用再从套子里出来了。是啊,他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天公好像也在对他表示敬意,他出殡的时候,天色变得阴暗,下起雨来了。我们全都穿着套鞋打着雨伞。瓦莲卡也参加了葬礼。当棺材放进墓穴时,她哭了几声。我发现,乌克兰女人总是不是哭就是笑,中间的心情她们是没有的。
“说实在话,埋葬别里科夫这种人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是我们谁也不愿意流露出这种快活感。我们从墓地回来时,大家的表情是谦逊而忧郁的。那种快活感就像我们许久以前做孩子的时候,当大人不在家,到花园里去跑一两个钟头,享受充分自由的那种感觉。哎呀,自由啊,自由!甚至哪怕只是一种暗示,一种可能得到自由的微弱的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后,心情很好。可是还没有过去一个星期,生活又和原先一样了:严峻、厌倦、乱七八糟。这样的生活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许可啊。情况并没有好转。事实上,人们虽然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样的套中人活着,将来又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说,又点燃了烟斗。
“将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人呢!”布尔金又说了一遍。
这个中学教师从什物房里走出来。他是一个敦实的矮胖子,头全秃了,黑胡子几乎齐腰长。有两条狗也跟着他跑了出来。
“月亮,月亮真好!”他抬起头说。
已经是午夜了。从右边可以看到整个村子。长长的街道延伸得很远,有五俄里长。一切都进入了恬静的深深的睡眠状态,没有一点儿动静,没有一丝儿声音,甚至让人不敢相信大自然竟会如此寂静。你在月夜看见宽阔的村街及其农舍、草垛和熟睡的柳树,心里就会变得宁静。在这个躲开了劳动、操心和悲伤而被夜色包藏起来的静寂里,村街显得那么温和、忧郁、美丽,似乎星星在亲热地、动情地瞧着它,似乎大地上已没有了恶,一切都非常美好。左边,村子的尽头,便是田野。这里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直到天边。在这一大片洒满月光的田野上,同样是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声音。
“问题就在这里。”伊万·伊万内奇又说一遍,“我们住在城里,又闷气又拥挤;我们写一些无用的文章、玩纸牌—这岂不也是套子吗?我们在懒汉、爱打官司的人和愚昧的浪荡女人中度过一生,自己说也听别人说各种废话—这岂不也是套子吗?喂,您如果愿意听,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
“不,现在到该睡觉的时候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他们俩都走进什物房,在干草上躺下来。他们俩盖上被子,刚要入睡,却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吧嗒、吧嗒……离什物房不远有人在走动,走了不远又停了下来。过了一分钟,又吧嗒、吧嗒响起来……狗叫起来了。
“这是玛芙拉在走动。”布尔金说。
脚步声停止了。
“你看着听着人家撒谎,”伊万·伊万内奇翻了个身说,“人家就会因为你容忍这种虚伪而说您是傻瓜。你忍受人家的欺负和侮辱,不敢公开宣布你站在正直和自由的人的一边,而且你自己也撒谎,还堆出笑容。这一切无非就是为了混一口饭吃,得到一个温暖的窝,谋到一个一文不值的官职罢了!不,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
“得了,您离题太远了,伊万·伊万内奇,”布尔金说,“我们睡觉吧!”
十分钟以后布尔金就睡着了。伊万·伊万内奇却翻来覆去,并且直叹气。后来他便起来,走出去,在门边坐下,点上了烟斗。
(1898年)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