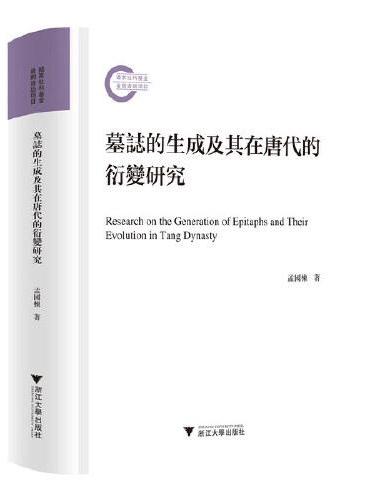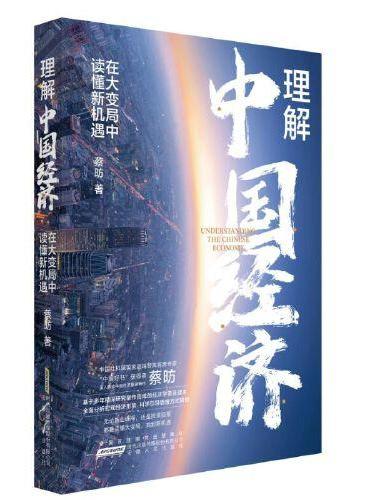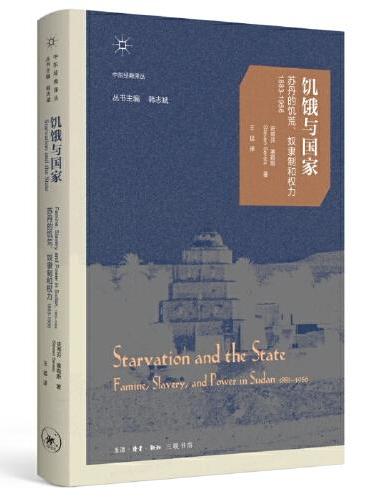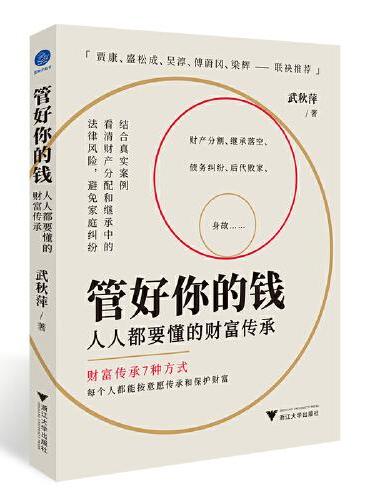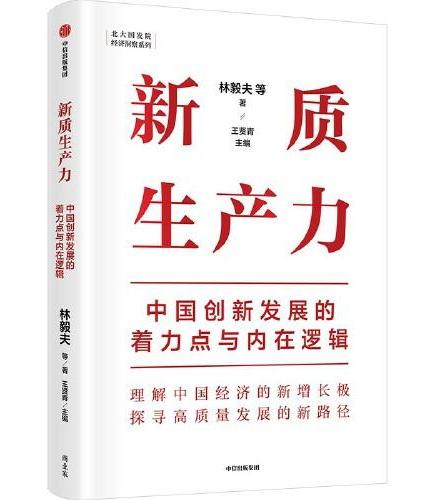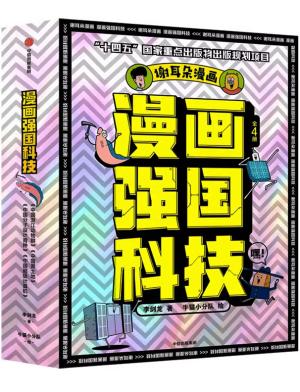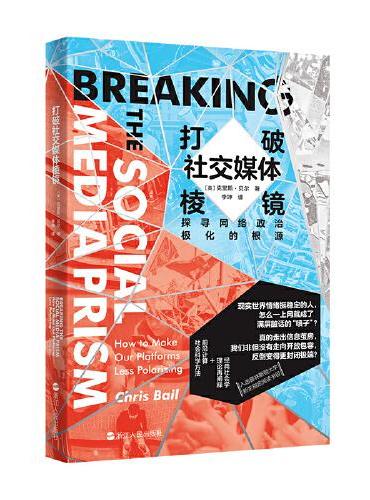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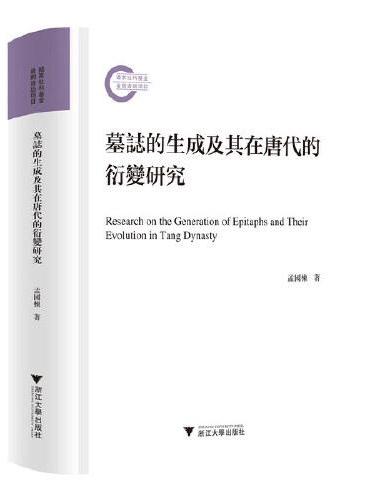
《
墓志的生成及其在唐代的衍变研究
》
售價:NT$
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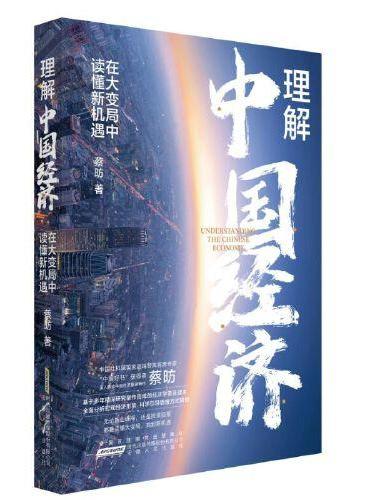
《
理解中国经济:在大变局中读懂新机遇
》
售價:NT$
2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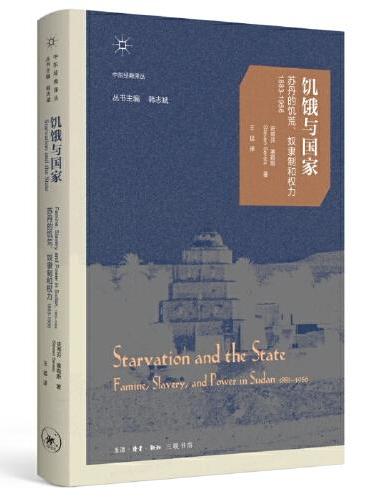
《
饥饿与国家:苏丹的饥荒、奴隶制和权力(1883~1956)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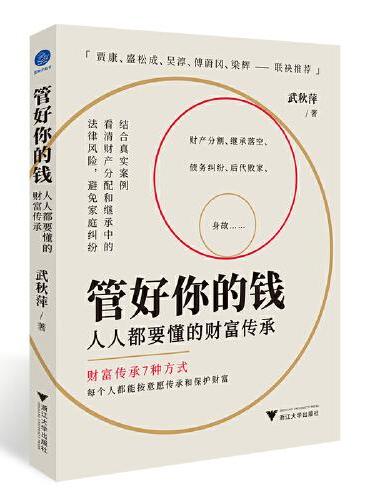
《
管好你的钱:人人都要懂的财富传承(一本书带你了解财富传承的7种方式)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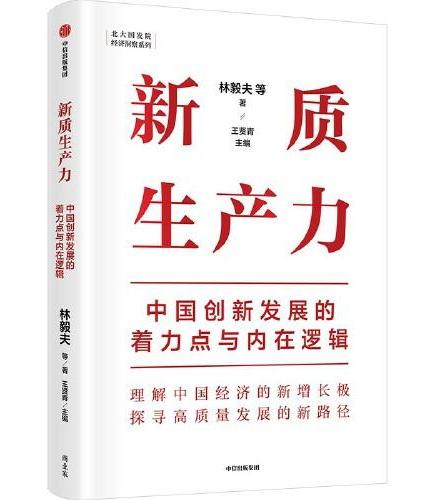
《
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
》
售價:NT$
4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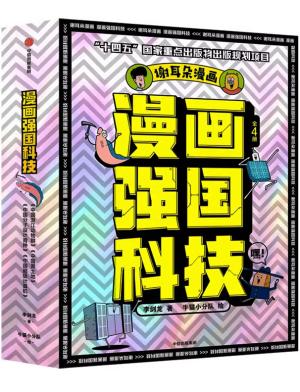
《
“漫画强国科技”系列(全4册)
》
售價:NT$
7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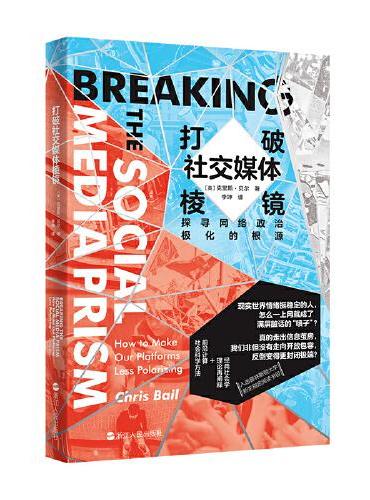
《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
售價:NT$
325.0

《
那一抹嫣红
》
售價:NT$
330.0
|
| 編輯推薦: |
《秋夜闲谈》系作家出版社“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丛书之一。
本书是著名学者孙郁先生的最新散文选本,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成果与思想见解,尽显文化之光,思想之美。
在百无聊赖的世界倘能开一绿洲,种着自己的园地,既不欺人,也不骗己,岂不是一种快慰?于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有益的事,从古老岁月的遗绪里打捞一点精神之火,照着昏暗的路,也是幸福吧?——《秋夜闲谈·从“度苦”到“顺生”》
从一个边远的群落,读到历史的脉息,那是大中华文化辐射的缘故。如果只是中原意象的描写,小说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此老镇与中原老镇的不同,在于声音的起落,旋律的强弱,我在此听到了久违的声音。比如方言的意象,就是我想寻找的东西。——《秋夜闲谈·老镇》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汇集了著名学者孙郁先生的三十八篇散文随笔,字里行间蕴含着浓厚的文化色彩,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成果与思想见解。
|
| 關於作者: |
孙郁,本名孙毅,1957年10月1日出生于大连。1988年毕业于沈阳师院中文系,文学硕士。曾任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鲁迅博物馆馆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鲁迅研究月刊》主编。
主要著作有《鲁迅与周作人》(1997年)、《百年苦梦》(1997年)、《鲁迅与胡适》(2000年)、《文字后的历史》(2001年)、《周作人和他的苦雨斋》(2003年)、《在民国》(2008年)、《鲁迅藏画录》(2008年)、《混血的时代》(2008年)、《鲁迅与陈独秀》(2009年)、《张中行别传》(2009年)、《走不出的门》(2011年)、《鲁迅忧思录》(2012年)、《写作的叛徒》(2013年)等。
|
| 目錄:
|
目录
古道西风1
穿越法兰西20
非洲的眼神42
复州拾遗60
杭州小记67
金寨72
徽州民居75
咸亨酒店78
越风80
老镇85
明末遗民申涵光88
诗人钱谦益96
无畏的文字99
身后的寂寞110
雪日读聂诗118
沉重的穿越122
从“度苦”到“顺生”129
志怪与录异140
谣俗谱147
顽皮之舞155
在德、俄版画之间165
画廊间的鲁迅175
游民图谱188
超人与禅191
回忆录195
又见坂东玉三郎198
尺牍之音201
关于苦雨斋群落205
谈曹禺212
谈沈从文227
谈张爱玲240
谈韦君宜256
木心之旅266
汪曾祺与黄裳273
忆周海婴先生281
看不见的诗文286
提问者史铁生294
莫言小记302
|
| 內容試閱:
|
雪日读聂诗
北京今日大雪,忽想起十七年前冬日的一个雪日,我去万寿寺参加聂绀弩的一个追思会。那次到会的老人很多,吴祖光、尹瘦石、舒芜、黄苗子等谈了许多北大荒时期的往事。印象是香港的罗孚先生也来了,会上给大家带来一册《北荒草》。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聂绀弩的诗,新鲜、冷峻、肃杀,一些句子过目难忘。读今人的旧体诗,一般不会生出这样的感觉。完全没有老气,如幽默的杂感,或是多趣的野狐禅,意外之音缭绕着。人在无聊的时候和这样的诗句相逢,麻木的神经似乎因之而有了痛感。旧体诗在今日还有这样的魔力,是少见的。
聂绀弩的文字一直以奇险、峻急诱世。散文与随笔都暗藏玄机,但唯有旧诗别开洞天。近六十年间,他的旧体诗大概是最好的。偶从一些读书人的文章里看到引用他的诗句,是新奇的感觉。酣畅、飘然、不拘礼俗,却妙意自成。他是个不为旧文体所囿的人,咏物吟人,任意东西,上下自如,一般琐事皆可为诗,染风尘却自洁如玉,谁能做到呢?阅读他的文字,才知道什么是天马行空的样子。死文字和死套路,因一种性灵而得以蠕活,近代以来大概只有鲁迅、郁达夫可以做到。
我后来才知道世间的聂迷不可胜数。常可以在一些沙龙文字里了解一些信息。有趣的是,去年初收到一位陌生的老人来信,夹着两册他编辑的注释聂诗的书。写信者是侯井天,才知道他是聂诗的研究者。书是自印的,朴素极了。一看注解,惊叹其爬疏之细,考释之详,都是学院中人没有做的。据说程千帆当年看到他自印的书,叹其功力不浅,以为有墨子的气象。此后他的注释本一直在民间默默流传。或许是他的虔诚感动了出版人,直到年底《聂绀弩旧体诗全编注释集评》得以正式出版,这部悄声流传的研究之作才浮出水面。
从民间读本到正式出版物,其间的故事一定是多的。侯井天为了印书,把全家的积蓄都用上了。几十年间他四处寻觅关于聂绀弩的墨迹,暗访诸多学子,史料背后的甘苦种种,而快慰是有的。他的注释聂诗,细致真切,互感的情思喷涌着,可谓诗人的知己。我有时候奇怪,像聂绀弩的诗,学院派的人为什么不去深究呢?一般学者不太去研究他的遗墨,是否是不中规矩的原因也未可知。民间的热与学界的冷,映照了今日的世态。聂绀弩写文章也好,做诗也罢,看似嬉戏笔法,实则大的哀怨于斯。读书人默然于此,实在也是积习所然,麻木的神经是不能触摸到圣洁的灵魂的。
我对聂绀弩的了解都是皮毛。读过他的文集,印象深深。他年轻的时候写下的作品,都有一点火气。文字是火爆的,而且很激进的样子。比如和曹聚仁的关系紧张,不喜欢非左翼文人的那些腔调。曹聚仁那时侯和鲁迅、周作人的关系都深,是自由人的身份,不喜欢单一的价值判断。而聂绀弩则有确信的东西,绝不骑墙,那就离自由主义者远了。他的文章都是爽快的声音,绝不伪饰自己。杂文风骨很硬朗,真有点鲁迅的意味。那篇《韩康的药店》,嬉笑怒骂之间,是忧思的闪烁,好玩与悲愤都有。读后真的让人喜欢。
五十年代后他命运多舛,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沦落之苦使其和旧体诗连在一起。右派与反革命的生涯,刺激了生命的体悟,遂有奇句飘来,血泪之迹里是飘忽的梦幻。好像是钟敬文曾说他是“人间地狱都历遍,成就人间一鬼才”,真是切中之言。聂绀弩不是悲观绝望的人,喜欢在日常中发现诗意,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入诗的句子都能神气地呈现出来,南社之后的诗人,大凡写旧诗,多没有这样的本领。
早就有人说,旧体诗已经难以翻出新意了。但聂绀弩却创造了奇迹。他随意翻动句子,许多俗语经由他的手而生出新意。在此方面有才华的还有启功、杨宪益等。启功是以幽默的口语入诗,白话的背后是雅的东西,多少有点士大夫的意味吧;杨宪益则洒脱磊落,是大的智慧,可谓独步文坛。聂绀弩比他们多的是底层的诸多受难的体验,他的旧体诗里没有旧式文人的那一套,词语都是现代的。借着古韵来说今人的思想,且反转摇曳,嘲人嘲己,明末文人的那些飘逸、放诞之举,我们在此都可以看到一二。
聂绀弩的不凡乃是其目光锐利,不为俗事所累。他在苦难里的自语,很有意思,大气得很。《北荒草》写劳动的诗句,真的妙如天音,如有神助。比如《搓草绳》描绘的场景本来枯燥得很,可是经由其笔,神乎其技,有天地气象:“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真乃绝唱。他在雅士们所说的不可入诗的地方,发现了诗意,我们看了只有佩服。他经常有些奇句入诗,都非生凑,而是随口涌出,水到渠成。《归程》有句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在世间流传传很广。“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有笑里的无奈,刺世之音暗藏其间。《无题柴韵诗八首》之八云:“也曾几度上吹台,张吻学吹吹不来。从此改途吾拍马,一躬到地为背柴。道逢醉汉花和尚,口唱猥歌倘秀才。我喊姐夫他不悦,贫僧尚未惹尘埃。”此诗诙谐多姿,反讽的地方和戏耍的因素都在,是作者真性情的刨示,不似市井的俚俗,却有智者的闪光。书斋中人,真的写不出这些诗来。
人在放逐里,倘还有自由的心绪,一旦写下什么,总要有些别样的意味的。我的父亲和聂绀弩有相似的经历,在农场的十几年的改造里,早年创作的灵感都淹没了,那原因是思想不能起飞的缘故。但聂绀弩却没有熄灭心灵的火,在逆境里还能笑对天下,自如往来在精神天地间。他的诗句是飞起来的,人被囚禁,而灵趣种种,万千心绪跳成彩色之舞,其诗见证了一个通达之人的心魂。有骨气和睿智的人,才能有此奇音。与六朝人的诗句比,聂诗绝不逊色。
历史真的巧合,十七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在雪日里读到聂诗,今日重温旧句,不禁生出感叹。现在我们总算有了一部详细的聂诗诗解。为这样的诗人作品作注,要有广博的学识才行。后代人接触这些,没有注释要费力气无疑。侯井天先生集多年之功,写下这本签注,可谓祥备已极。对人物地图,时代因缘,文化沿革,多有心得。如果不是他的辛勤搜求,考释探究,现代的年轻人大约不易理解这些诗句了。我们看这本诗集,会想起许多事情。历史的恩怨,沦落的烟尘,四散在这里,给我们久久的感怀。我有时看到一些雅士写下的旧体诗,觉得多是无病之吟。总是在想,把旧体诗搞死的正是他们,无病之音有什么意思呢?聂绀弩以喷血的声音写下的妙句,那才是艺术,而旧体诗也由于他,重新活起来了。只有精神飞起来的人,才会抵达思想的圣界。在我们疲劳的人生里,能飞翔起来的人,真的让人羡慕。
沉重的穿越
在大学读书时,看到赵园的《艰难的选择》,曾被深深地震动过。她对“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心态的把握,是很有特点的。那种忧患感和文中时常流露出的苦涩的自我意识,至今想来,仍使人心神为之一动。我想,在中青年学者中,像她那样富有诗人气质、带有沉郁的直觉特点的研究人员,是不多见的。她的这种非学院化的研究个性,对后来的一些青年学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近几日阅读她的新著《北京:城与人》,越发使我感到她的学术个性的魅力。《北京:城与人》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与方式,似乎与以往的赵园精神有着不小的差别。它已由内心的冲动、焦虑,转向一种沉静和肃穆的审美观照。她对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北京生活方式、文化风貌的细腻、独到的发现,可以看到她不衰竭的理论功力。但是,如果把她的这种选择的转换,看成价值尺度的更迭,那显然是一种误解。在这部描述城与人关系的论著里,何尝不会感到她已有的那种探索的孤独!与那些沉醉于京都文化的“绅士气”文人相比,赵园的《北京:城与人》是沉重的。
我在她那细致、冷峻的笔触里,感受到了这种沉重。关于北京的文化情趣,可以找出许多说不完的话题。赵园大约不喜欢名士化的情趣,面对北京这个极富诱惑力的文化都城,她选择的是另外一种角度:“经由城市文化性格而探索人”,这多少带有寻找中国知识者“心灵史”的意味吧。她好像没有完全摆脱中国知识者的那种自审意识,在理解对象世界时,时常把自我的困惑与自信,传染给读者。但赵园在这里还是尽力节制自己的情感,努力客观地审视客体。这使全书散发着较浓的文化学的气息。她的审美意识,较之过去更成熟和学沉了。
北京确实是一座颇有诱惑力的城市。元、明、清以来,各民族在这里汇聚、碰撞,产生了特殊的文化模式。和古都西安相比,北京既有浑厚、典雅的气派,又充盈着宏阔的威严,颇有“胡气”的风韵。清末与“五四”前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畸形的社会形态,使这儿的文化变得特别起来。“五四”以来的作家对古都风情的描摹,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赵园清楚地把握了这一文化特征,对古城的世态、人情是较熟悉的。但赵园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北京的礼仪文明、人文景观,而恰恰主要是作家作品中表现的人与城的复杂联系。在人与城多种形式的关联里,可以看出更深层的文化情结。国民的心理状态、行为方式等,都在这里被外化出来了。
吸引赵园的,首先是描写北京生活的小说里那种地域性特征,和内的在文化品位。她在“京味”小说里,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内容。我感到她对“京味”小说的把握是有分寸的。她说:“‘京味’是由人与城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赵园在北京文化与北京人之间,发现了这座古城的“内在于人生”的那种格调。由作家创作态度、风格、设计,推导并发掘“京味”内在的风韵,不失为一条好的研究途径。作者对老舍很有兴趣,她在以老舍为代表的“京味”小说里,发现了京城文人独有的风格特点。比如对京城人的“理性态度”、“自足心态”、“非激情状态”、“介于雅俗之间的平民趣味”、“幽默”等问题的总结,可以说是对“京味”小说所涵盖的文化哲学最好的注解。从文学形象折射的情感逻辑方式,寻找北京的市情风貌,赵园是下了苦功夫的。她以良好的悟性,捕捉到了“京味”小说所涵盖的文化哲学,使我们对“京味”小说某些零散的印象,排列组合成一个有序的系统。我觉得,作者对北京人的情趣和精神模式的概括是准确的。例如,她说:“老舍是太成熟的人,太成熟的中国人,太多经验,以至抑制了感觉,抑制了瓷肆的想象和热情。”刘心武笔下的胡同,汪曾祺的淡泊有味的文化神态,陈建功对京城人“找乐”的审视,在赵园看来,构成了“京味”小说多样化而又神情相近的总体风格。这里既有老舍式的“由经验、世故而来的宽容钝化了痛感”,又有古代文人那种“萧疏澹远”的精神。从这些作家以文学而与城市联系的方式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人与现象界的某种奇妙的沟通吧。
“京味”小说纯净优雅的美学风格,是北京特定文化的产物。由“京味”小说推及到北京文化,对作者是件饶有兴致的课题。正如作者所说,导致京味小说的原因,一方面是清末“贵族社会带有颓靡色彩的享乐气氛造成了文化的某种畸形繁荣”,另一方面是清朝覆灭后,“宫廷艺术、贵族文化大量流入民间”,加之“满汉文化的融合”,北京人在多元文化的包容下,形成了特殊的生活方式,将世俗生活审美化了。“小情趣寄寓朴素温暖的生活感情”,这是北京人精神乐天的一面。赵园对这一现象的分析是很有深度的,她在对家庭文化、商业文化、建筑文化以及人对痛苦与享乐的分析里,看到了中国人身上潜在的、某种原型的东西。作者以自己敏锐的嗅觉,体味到古都颇有代表性的文化风韵。北京文化既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又隐藏着国民精神某种畸形的东西。长久以来儒、道、释模式禁锢下的国民文化性格,在北京人身上的表现是典型的。胡同中的人生之梦虽然带有祥和之气,但在那些个性委顿、精神封闭的自我满足里,你会感到,这种过于节制的、人工化的世俗生活,把人的强烈的创造欲和生命意志,统统弱化了。难怪老舍在对北京风情进行有滋有味的审美打量时,时常表现出对市民的某种忧患。赵园将此理解为“理性与情感的剥离”。北京传统文化给人带来的兴奋与失望,不能不说具有悲剧的意味。
但北京人的这种生活的艺术化,并不单纯地显现着一种优雅与平和。在那些持重、圆熟、非冲动的生活情境里,的确有着更深刻的人生体验。赵园在“京味”小说中的棋迷、戏迷、遛鸟者的自我行为里,也看到了其中的郑重与人性的深。这种熟透了的文明,体现着人在自我限制中的适应性与自塑性。这使人想起中国的微雕和艺人的绝活。北京文化中的那种小玩艺中的奥秘,实际上正是人的精神的对象化的一种表现。这里不乏智慧与创造、悟性与体验。特别是在北京的方言文化里,你会感到,北京人实在是很有艺术情趣的。在声音意象与说唱的艺术里,融会了多少精巧、细致、富有声象特质的美的东西。北京人在有限之中,创造了无限,于平凡中体悟博大,从宁静中拥有永恒,这不能不说是“京味”的魅力所在。
北京文化精神的这一矛盾的特点,对当代知识者来说,是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的。中国国民的弱点与执著的生命力,在这里表现得极为完备。如果对此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文艺的更新是困难的。在经历了时光的磨砺后,人们越发感到超越这种文化品位的必要性。因为前工业社会所留下的中世纪式的封闭的艺术格调,与生活的、充满生命强力的人生状态是格格不入的。成熟就是衰落的开始,国民性的改造与文化的更新,对当代中国人来说,仍是多么艰难的任务。赵园深深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从她的怅然、悲慨的叙述里,我看到了这种忧患。
把北京城作为一个文化标本,来研究中国人的精神走向,对人的启示恐怕要超过本书题目自身。从城与人的多种形式的关联中,寻找人的意义,这在国内是不多见的。赵园把本书写作意图归结为“搜索城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表达式”,是很聪明的做法。因为这一方面避免了某种空泛的宏观大论,将文化问题具体化了;另一方面,找到了适合她个性特点的研究视角。研究对象必须加以限制,限制意味着具体化。可惜日前这种书还太少了。城与人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现代社会人的某种本质的东西。与乡土社会的文化形态不同,城市文明更清晰地跳动着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脉息。三十年代的上海与北京的不同风格,再典型不过地记下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足迹。赵园对北京的考察,或许是出于对现当代文化结构与人的心理结构深层体味的需要吧。实际上,从城与人的关系的文学表达式中,可以挖掘出更多的东西。限于资料和兴趣,赵园对北京生活的政治意识,和新派青年的现代式的心态,注意的还不够。不过,在限定的范围中,作者还是提供了许多有启示的观点。寻找城与人的对应性,也就是对意义与价值的寻找,和对人自身潜能的认识。赵园在后记中写道:
对于北京文化的兴趣,也仍然是由专业勾起的。清末民初的历史,北京特有的文化氛围,是“五四”一代人活动的时空条件。这条件中的有些方面却久被忽略了。我期待着由近代以来北京的文化变迁,北京学界的自身传统,去试着接近那一代人,说明为他们塑形的更具体的人文条件。我想,为了这个,包括北京胡同在内的北京的每一角隅都是值得细细搜集的。在上述可以堂而皇之的“缘起”之外,纯属个人的冲动,是探寻陌生,甚至寻求阻难,寻求对于思维能力、知识修养的挑战。北京,北京文化是这样的挑战。对此,我在刚刚开始进入本书课题时就已感觉到了。
不管作者写作时充满了怎样的艰辛与困惑,从《北京:城与人》中,我们还是高兴地感受到作者顽强地接近“斯芬克斯之谜”的努力。本书最有分量的地方,正是体现在“我在哪里”这一现代人文主义主题的独到的把握上。
不能不佩服作者对北京文化与北京人的领悟。在对北京人的“礼仪文明”、“理性态度”、“散淡人情”、“旗人现象”等方面的考察里,她的目光是深沉、尖锐的。赵园习惯于对苍凉人生的体验,很少稚气的理想主义。她的文章单刀直入,没有迂回婉转的踌躇。她往往直观地抓住事物外在的特征,将其形态形象地概括出来。比之周作人、汪曾祺等人,赵园的笔锋更多的还是含着冷静的反省。即使面对最精湛的艺术样式,你仍然无法寻到沉湎于世俗文化的那种价值趋向。这与以往人们谈到京派艺术时的那种津津乐道之情相比,的确是太严肃了。赵园似乎一直保持着对现象界的某种警惕,在对文学以及文化现象的梳理、分析时,常常带有感情凝重的批判意识。这种批判意识不是建立在对理论的形而上的演绎上的,而是深深地植根在自己的体味之中。凭着女性缜密、精灵的触觉,她在琐碎的、司空见惯的艺术细节中,总能把握住常人忽略的东西。在这部专著里,我感受到了她来自内心深处的那种冷气和热力。选择这个颇有文化学意味的选题,对她的确是一个挑战。这种近于古玩式的品评赏析,与她内心的孤苦和冷酷的清醒,有着怎样的反差!我感到《北京:城与人》交织着她内心某种不和谐的颤音。在文化眷恋与文化批判之间,她的心在惶悚不安地飘泊着。传统文化的引力是巨大的,多少文人未能抵住它的诱惑。当人们反顾过去审视尘迹的时候,会不会因依恋而停住脚步?赵园深味历史轮回的可怕,她急速地穿过历史的旧路,好像走得很累,丝毫没有停下歇息的轻松。在对北京文化的反刍里,她始终被复杂的情感折磨着。在这里,仍可以找到她在《艰难的选择》中所表露出的情绪,它不断纠缠着我们的作者,以至使全书蒙上了郁闷之情。这使我想起闻一多从创作转向古文化研究时那种心境地。当他从激情冲动的状态转向平静、单调的沉思时,内心何尝不想踏破这种平静!鲁迅当年抄古碑的苦寂,难道不也是内心角斗的外露吗?写北京,写文化学色彩很深的文章,大概也隐含着赵园的一种苦衷吧?一杯苦酒喝下去,是痛苦的,但却换来了一种清醒、一种自慰。赵园的尝试,是值得的。
从“度苦”到“顺生”
四十年代后期的北平,京派文化日渐式微。但《世间解》的问世,似乎像京派文人最后的余晖,留住了那个时期精神的碎片。该杂志的发起人是张中行,地点在广化寺。现在无法了解杂志酝酿的具体过程,只知道事情由他新认识的续可法师张罗、废名等人曾到寺里热烈的讨论过办刊思路。至于资金的筹划等细节,据说是天津的一位居士赞助,在张中行后来的回忆里谈得简略,我们也无从知晓。《世间解》在沉闷的旧都出现,想来也没有多少读者关顾的。总计出版了十一期,发行量并不太多,知识界后来很少提及于此,似乎并不存在过。可是我读过这本杂志后,还是颇有兴趣。因为无论学识的深还是文笔的好,都是颇让人感念的。
《世间解》第一期出版于1947年7月15日,是以佛教文化为题旨的杂志。张中行是唯一的编辑。从初版的情况看,很有雄心壮志。他在创刊号编后记中明确地说:“本刊是一个讨论人生之道的刊物,其目的与其说是致知,无宁说是致用。所谓致用尤着重普遍。以是,我们希望由下期起,谈人生之道和生活经验的文章能够比本期多。”张中行后来回忆说,办这个杂志时,对学术的兴趣是超出对宗教的兴趣的,即通过人生的思考去解决心灵的问题。那时他对佛学的兴趣旨在对苦楚的超越上,想借此开一个园地,聚来同道,阐佛学之幽微,释玄学之广大。第一期的作者都不错,有来自印度的师觉月《佛教在印度人民生活中之地位》,废名的《孟子的性善与程子的格物》,顾随的《揣龠录》,俞平伯的《今世如何需要佛教》等。第二期的作者增加了任继愈、吴晓玲、慧清等,任继愈写的是《理学探源序》,吴晓玲则是《奈都妇人画像》。后来熊十力、朱自清、金克木、赵景深、丁文雋、王恩洋、南星等都成了他的作者。文字都很温润儒雅,学识和趣味交织着,在精神的深和文采的平实上,都高于一些人文杂志。文章都很好读,即便是熊十力的《读智论抄》,也仍然亮光闪闪。泰戈尔的诗,禅宗的语录等,都在流动着心绪的亮色,照着人间的灰色。我相信编出第一期时,张中行是暗自高兴的,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设计出一种思想的平台,可以说,京派的意绪和学院里的高妙汇聚在一起了。
当时的佛学杂志很多。浙江《海音潮》,汉口《正信》,上海《觉群》《弘化》《觉讯》《觉有情》,镇江《中流》,湖北沙市《佛海灯》,广州《圆音》,新加坡《人间佛教》,台湾《台湾佛教》等,在佛学界都有影响,是专门化的杂志。不过张中行办刊,有一点杂色的意味,也将非佛教的学说引进来。比如文学作品,译介与佛教文化有关的诗与散文。还有谈科学与宗教及社会关怀的杂感之类。像吴晓玲对甘地的介绍,南星对文化理论的翻译,王恩洋《知识与文化评论》,丁文雋《自由平等新解》等文字,加进了现代的感受,科学理念的随感也夹杂其间,显然是有些生气的。哲学与佛学的理念,还有诗人的内觉,悠然而岑寂地流在字里行间,比文学的期刊多了理性,比理论杂志又多了趣味。文章呢,有冷有热,可作美文来读。顾随的高远辽阔,熊十力的玄奥深思,废名的苦涩和灵动,朱自清的清澈隽永,俞平伯的古拙老成,对读者的吸引是不必说的。
在第二期,张中行发表了一篇文章《度苦》,述说着他喜欢谈佛的原因。那是十一年前与杨沫婚姻失败后,他在绝境里与佛学的一次意外的相逢。而这,改变了他的生活,思维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在极度绝望和灰色里,佛的语录像微弱而亮亮的火,把他死去的心温热了:
大约十一年前,正当我的生活经历一次变动以后,我开始看到心经。那是同学李君给我送来的。那时我借住在大学宿舍的楼上。正如同学李君所言,我当时是有烦恼,所以他送来心经,他说心经可以去障。那是一个红红的小褶本,字印得清楚而大。我第一次念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菠萝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里竟觉得大受感动。但对五蕴皆空的事毫无所知,度苦厄云云自然就更谈不到了——但这也是比较而言,李君是信佛法甚笃的人,他是怀着度苦的大心愿常到我屋里来。那时我的心情正在寂寞动摇的时候,他走来,穿着蓝布长衫,坐在窗对面的小凳上,看我一会,于是又重复一次:“打破那个烦恼障吧!”我也看看他,也看看放在床头的心经,心里感到一些温暖。这温暖一部分从友情来,一部分由佛法来,我觉得这个世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
开篇的寥寥几句颇为动人。他的佛学因缘就是由此所得的吧?在张中行看来,人的苦有两类,一类来自本性,一类来自社会。社会之苦遮蔽了本性之苦。那是更大的苦。而要灭这个苦,就要有安身立命之道。这个道是什么呢,那就是宗教。在他心的深处,宗教的力量似乎可以观照到内心之苦。从死灭和绝境里走出,佛的力量也许是最重要的。不知为什么,喜欢西洋哲学的他,没有走向基督教的世界,而是从东方的哲学里找到慰藉。他快慰于这一慰藉,因为思想的乐趣,是可以驱走悲凉的心绪的。
有趣的是,编者对己身的体验,只是个案地处理,并不特意搜求类似的文章,对别的作者写什么是不强求的。这一本杂志的问世,对废名这样的人来说是个新的平台。自周作人入狱后,京派文人的阵地是萎缩的,他的寂寞也自不必言。不仅帮助设计内容,还对编辑理念出了诸多思路。他给张中行的信里,多是鼓励的话,显然还带有二十年代时的热情,似乎回到了与周作人、俞平伯讨论问题时的兴致。废名对佛学的看法很怪,与熊十力的观点还每每相反。他在《世间解》发表的《佛教有宗说因果》《〈佛教有宗说因果〉书后》《体与用》等文,偶尔与熊十力开点玩笑,锋芒是可见的。废名的文字里流出的思想渺乎如林中云烟,冷彻的凝视里不乏诗情的闪动。对俗世的冷嘲也含着周作人的风骨。他研究佛学,不是张中行那种从己身的苦出发的诘问,纯粹是精神的静观,讨论问题是有点神秘的色彩的,玄学的东西颇多。他甚至把孔孟、程朱的思想也放入佛学的语境里讨论,把哲学与宗教的话题一体化了。废名在文章上的特异与这种玄学的低语有关,他在对存在的因果问题的思考上走得很远,与当时读书人的兴奋点是大为有别的。连张中行也颇觉奇怪,孟子不知佛,程子反佛,放在一起讨论真会拓展思维的空间么?
《世间解》的作者里,顾随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按辈份,顾随是张中行的老师,张中行认识他,却是大学毕业后。因为那时需要谈佛的文章,谈佛,就不能不涉及到禅宗,而在张氏接触的学者范围里,还没有这类的人物。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前海北岸南关口。张中行第一眼看见他,就有了良好的印象:
顾先生身材较高,秀而雅,虽然年已半百,却一点没有老练世故的样子。我说明来意,他客气接待。稍微谈一会话,我深受感动。他待人,几乎是意外的厚,处处为别人设想,还惟恐别人不满足,受到委屈。关于写稿的事,他谦虚,却完全照请求地答应下来。这之后连续一年多,他写了十二章,成为谈禅的大著《揣龠录》。许多人都知道,中国的子部中,禅宗的著作是最难读的,有关禅的种种是最难索解的。我又是这样比喻,子部许多著述同是高妙,可是性质有别:就说《庄子》《荀子》吧,像似四大名旦演出,虽然高部科技,却都有个规矩;禅就不然,像是变戏法(新称呼是魔术),看了也觉得高不可及,却莫名其妙。莫明要使之明,先要自己能明,然后是用文字来表明。在这方面,顾先生的笔下真是神乎其计矣,他是用散文,用杂文,用谈家常的形式说了难明之理,难见之境。
这个评价确不为过。顾随的学生周汝昌、叶嘉莹也有类似的描述,对老师的印象几乎一致的。学识高又有善良的心,自然是很有引力的。由于他的催促,顾随写出了惊世之作。他催稿是热而急的,两人的交往留下了许多故事,成了《世间解》背后的最让人怀念的一页。顾随在那篇大作的结尾篇里就这样说:
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大约民十顷发表于《北京晨报》之副刊。而副刊的编者则是孙伏园。后来,鲁迅追纪当时的情形曰:“那时伏园虽然没有现在这么胖,然而已经笑嘻嘻地颇善于催稿子了”。看其语气,颇若有憾于孙公者然。《正传》尚没有登完,这之间,孙公不知为了什么事而告假回南了。代理编辑的一位某公,史无明文,其胖与瘦虽不可得而知,我想定是不那么笑嘻嘻地善于催稿子,于是鲁迅就将阿Q枪决了,而《正传》也就以“大团圆”收场。鲁迅于此曾说:倘若伏园不离开北京(那时当然还没有“北平”这个名称),他一定不让阿Q被正法。现在,我们感谢孙公之善于催稿,同时,我们也憾于其告假,以致阿Q竟在《正传》之第九章绑上了法场;如其不然,阿Q底寿命一定更为长些,而《正传》也将有第十章或第十七章了。然而过去底事究竟是过去底事,说什么也挽救不回来,正如人死之不可复生。如今且说苦水之写《揣龠录》,自其开端之“小引”,一直到现在写着底“末后句”,没有一篇不曾受过中行道兄之督促,就是道兄自己也说苦水写此录是“逼上了梁山”。于此我必须声明:中行道兄永远瘦,过去是,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一定是,虽然苦水并不懂得麻衣相法。在编辑的途中,道兄积劳成疾,还生了一次不轻底病:肺炎。记得我去看他的时节,虽已十愈八九,但他仍须躺在床上和我说法,看其面貌较之平时也并不算瘦;其时我想道兄大概平时早已瘦到不能再瘦的程度了罢。至于道兄之善于催稿子则绝不弱于孙公伏园,即使苦水并非鲁迅,而且他也并不笑嘻嘻。他底面貌永远那么静穆,语音永远是那么平和,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永远不着急,不起火。这使我想:道兄真不愧有道之士也。其静穆底面貌与平和底气语却有一种“逼人力”,即是说:他让你写稿子,你便不能不写,不好意思不写;即使是挤(鲁迅所谓挤牛奶之挤)也罢。多谢道兄:以苦水之无恒与无学,拙录竟托了谈禅之名出现于佛学月刊底《世间解》上,得与天下看官相见;而且一年有半的期限之中,竟写出了十有二篇。
顾随是出色的鉴赏家,在三十年代已颇有些名气。他长年生病,写的文章不多。可偶一为之,便有不俗的气象。因为是外语专业,对域外文化的了解较深。可是无缘出国,兴趣也渐渐向国学转移。他谈旧诗词,灵思闪闪,冷观深切,道他人未道之言,比王静庵毫不逊色。言佛理与儒学,亦深思洒脱,目光如炬。他本来能写很好的小说,旧体诗词亦佳。可是后来退到书舍,以教书为业,遂放弃创作,埋头到教案的写作了。不过他似乎不怎么看重自己的文字,动笔渐少,许多思想都消失于精神的空洞里了。张中行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也很深。自己也多少受到顾随的影响。多年后写那本《禅外说禅》时,多少还是能看到《揣龠录》的影子的。
同是出身于北大,顾随喜欢鲁迅,张中行偏爱知堂。两人对周氏兄弟的看法有同的一面,也有异的地方。顾随文字婉转清俊,亦热气腾腾,似乎学鲁迅;张中行平淡幽微,乃知堂笔法。不过在对传统的看法和诗词的鉴赏方面,两人相近的地方多。前者对宋词有精妙的体悟,后者浸于唐人的清幽流畅的意蕴里,可谓古风习习。他们都在传统文化里用力,却又没有方巾气,意识里是现代人的洒脱。对国民的批评和反省,是异乎寻常的。顾随热的一面,是张中行少的地方。所以一个忧愤过深,以至伤体。一个不温不火,就岑寂得很,竟得高寿。张中行回忆自己的友人时,常常惦念的是这位高雅而热心肠的人,因为彼此在对精神的幽怨存在的看法,毕竟还是有诸多相近的地方。这就是人生来大苦,唯有艺术能超凡入圣。他们对旧的诗文的敏感和有趣的阐释,现在能与之比肩的不是很多。
《揣龠录》是难得的奇文,张中行对此评价很高。我一直觉得它对张氏的影响是内在的。或者彼此在对佛的看法上心有戚戚焉。比如书中对怀疑问题的感受,就非禅似禅,似哲非哲。说,“大疑,大悟;小疑,小悟。学佛要信;参禅须疑。”真是悟道之言。而且也认为,一切归创造:“佛佛不同,祖祖各异。则亦以其为是创作故,非模拟故,非剿袭故。”这就把佛学的存在流动化了,绝无教条的痕迹。他看经典,思绪是动的,乃智者的内省,时见耀世之灵光。如:“窃为凡一切为学,必须有两种精神:一曰取,一曰舍。而且取了舍,舍了取。舍舍取取,如滚珠然;取取舍舍,如循环然。”至于如何取舍,顾随回答得大气淋漓,即倜傥分明也,往来自如也,不为物所累也。《揣龠录》是哲人的独思,意蕴仅在周氏兄弟之下,有时亦多奇思,翻滚摇荡于江河之上。他从佛的意蕴里,看见的不是静止的遗存,而是动的精神。“一种语言中,倘若没有了否,则便只剩下是;而只有是的语言只有印玺和保守,而更不会有革新与创造了。”此种观点,张中行都心以为然。你看他的文章,不也多是类似的意识么?
虽然是佛学类的杂志,但后来有关佛学的文字却被文学与人生哲学的话语代替了。因为作者群中,信仰佛教的人太少,只是把此作为话题而已。而张中行的兴奋点也渐渐向罗素那类哲学家的路径靠拢,文章的编辑就与周作人式的趣味接近了。其实在编辑该杂志时,他对佛学的一些基本理论也生出怀疑来,《心经》所云“不生不灭”、“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用逻辑学的观点看,前者违反排中律,后者违反矛盾律。他觉得,重要的也许不在于对与错,而是引起对生死问题的冥想。佛学大而深,接近它而非迷信之,能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在那些人眼里是理应如此的。人生是个漫长的度苦之旅,但那力量有时不在外力,而多在自己,回到自身才是悟佛的一个归程。
废名谈佛有禅宗的意味,不妨说带着神秘的期许。顾随则有点禅外的哲思,偶能窥到内心的清寂与冲荡。俞平伯讲佛的时候,内心却有孔老夫子的中和之音,自己还在佛门之外的。以顾随为例,在内心深处是最有悲苦意识的,其诗词里就多有空漠的意象。可是偏偏以非正襟危坐的语气面对禅学,未被禅意所累。众人谈佛却不入佛门,乃是对人生有别样的看法,儒者的智慧也是有的。佛学的吸引张氏,是因为意识到了内心的苦,是有动因的。所以他既没有神灵飞动的一面,也没有安详如梦的心绪。看到了佛说的苦的根源,自然有大的欣喜。但人的生命源于欲,竟然以消灭欲望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也是有自身的问题吧。他在与佛学深入地接触之后,发现只用释迦牟尼的思路是不能解决所有的困惑的。于是思路又回到罗素的怀疑主义那里,从笛卡尔式的沉思里直面悖反的难题。他后来写《顺生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即从佛学出来后,怎样对待“逆”和“顺”的问题,这时候他与佛家的距离就很远了:
从人生哲学的角度看,有三点很值得注意。以佛家的轻视私爱之情,可是不舍“大悲”,修菩萨行,要普度众生,这即使应该算作空想吧,如果所想多多少少可以影响所行,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想总不比不想为好。二,逆常人之道以灭苦的办法,如果真能够信受奉行,精进不息,禅悟而心安理得,这种可能还是有的;修持而确实有所得,这条路一定不如常人么?似乎也不容易这样说。三,定名的网罗,疏而不漏,跳出去,大难,不幸有疑而问其所以然,又常常感到迷蒙而冷酷。对这样冷酷的现实,道家的办法近于玩世不恭,只是不闻不问地混下去。佛家则不然,他们认真,想人定胜天,沙上筑塔,其精神是“抗”。胜利自然很难,不过,正如叔本华所推崇的,逆自然盲目之命而行之,可以当作人对自然的一种挑战。这用佛家的话说是“大雄”,结果是螳臂当车也好,这种坚忍的愿力,就是我们常人,想到人生,自然这类大问题的时候,也不能淡漠置之吧?
上述的思想能看出他的关于信念与否的核心。前人的信仰,是对外在理念的执著,信他。张中行起初也是这样的。至少办《世间解》的时候还残留着这种期盼。可是读来读去,发现有许多理论和自己的体验有别。就是说,再好的理论都有一些盲点的。不过这一发现,并不能让他走向无信的虚无主义之路,或者尼采那样的孤独自行的险境,即也隐隐地相信生命能够自己支撑自己。读他的文章,总觉得背后是有一种奇异的信念在。几乎感受不到极度空无的那种存在主义的惊悸。这使他既没有走鲁迅的路,也没有走胡适的路。和周作人那样完全书斋化的选择也是有别的。天底下什么是可信什么是不可信呢?用胡适的观念,采用实验主义的方法,什么也得经过检验才能理会的。张中行在理论的层面,早就解决了价值论的问题,一生都没有变。可是生命的爱与苦,哲学里没有解决,佛学也没有解决。怎么办呢?庄子的逍遥?陶渊明的归隐?尼采的流浪?他都没有选择。因为他自知不是大哲,没有庄子的洒脱;也不是陶渊明,没有明暗之间起落的反差。那是一个小民的独思与独乐,困苦而能于衣食住行间消解之,无奈可麻醉于诗文的吟哦间。生是“无常”,而艺术却可以使人抵达永恒之路,即“常”。他自己是深以为然的。在“无常”与“常”之间,他以旧式文人的情怀和怀疑主义哲学渐渐去解决它了。
小民,也就是布衣之族的信念是什么呢?衣食之无忧,儿女之无患之外,是爱欲的表达与诗意的栖息。诗意的却不是俗态的,在他是个闪光的地方。比如玩玩古董,做做旧诗,谈谈哲学,都是。一切为了己身之乐和他人共乐。在百无聊赖的世界倘能开一绿洲,种着自己的园地,既不欺人,也不骗己,岂不是一种快慰?于是在力所能及的时候,做一点有益的事,从古老岁月的遗绪里打捞一点精神之火,照着昏暗的路,也是幸福吧?回到自己,顺生而行,这个信念,后来就从没有变过。
顺生,其实就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小民的生存,一般的情况,要么顺从奴态,要么叛逆而行。张中行自己,不选择这样的路,而是清醒地顺人生的路走。顺生,不是奴性,而是寻找自然的状态。根据自己的心绪理性而从容地设计自己。流行的存在不能吸引自己,卑琐的享乐也不能占据内心。逆人生的路走是不好的,放荡的日子自然也该放弃的。关键是充分地显示个人的价值。一个甘于边缘的人,生活的简单却无法制止其精神的高远,他从“无常”的世界里,展示了自己的“常”,小而渐大,旧而弥新。在存在的方式上,他其实和废名、顾随、俞平伯等走着相似的路。不同的是,他把此意从人生哲学里突现出来,说“顺生论”是那一代人的一种体悟,也是对的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