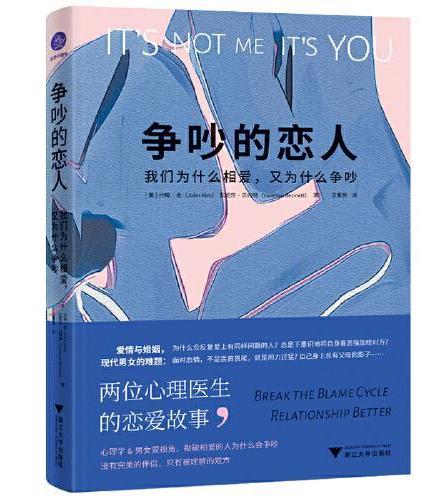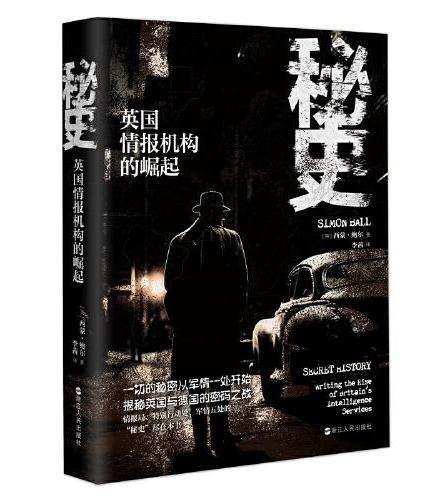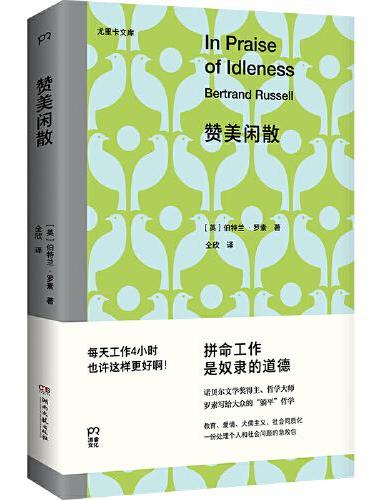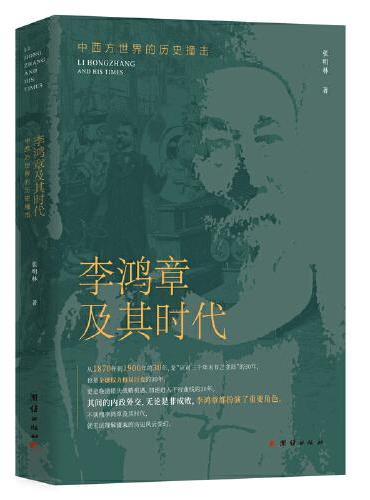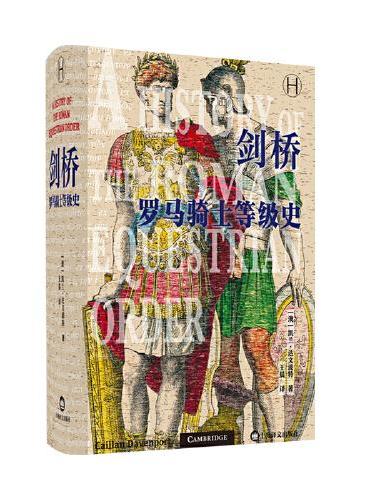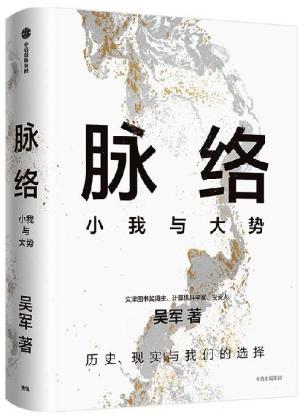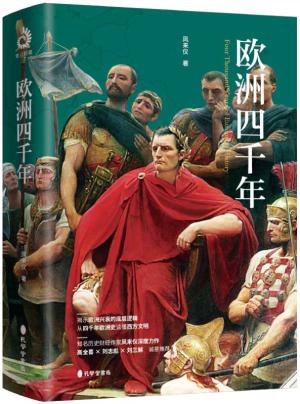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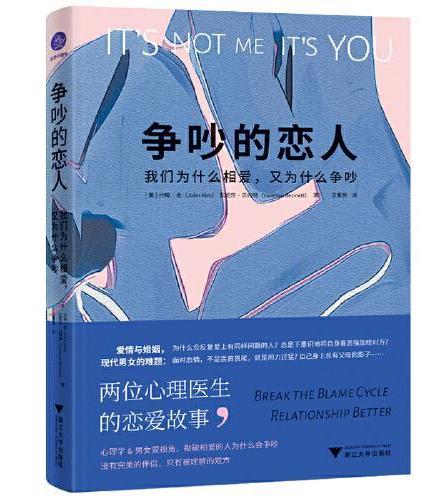
《
争吵的恋人:我们为什么相爱,又为什么争吵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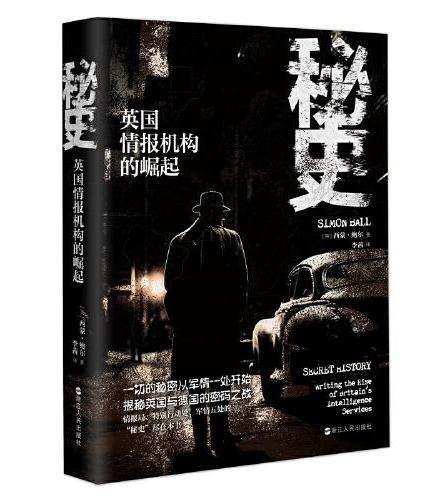
《
秘史:英国情报机构的崛起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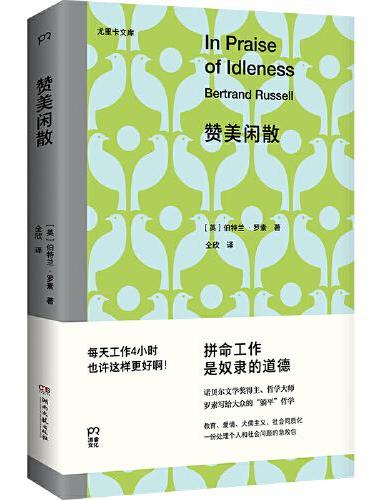
《
赞美闲散(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哲学大师罗素写给大众的躺平哲学)
》
售價:NT$
3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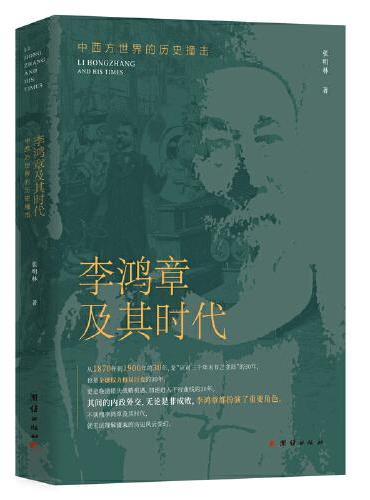
《
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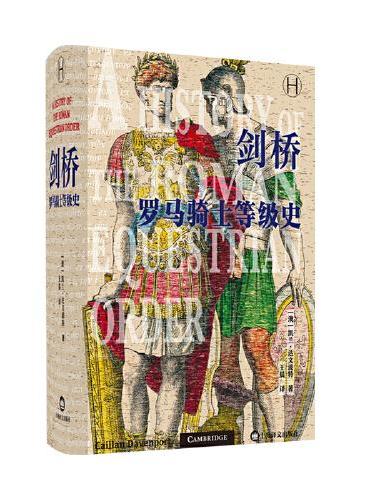
《
剑桥罗马骑士等级史(历史学堂)
》
售價:NT$
12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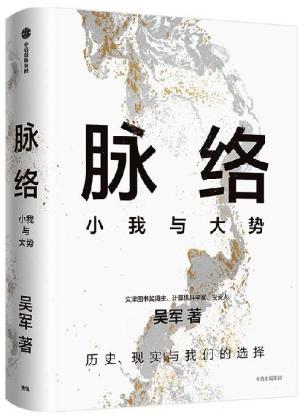
《
脉络:小我与大势
》
售價:NT$
484.0

《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
》
售價:NT$
4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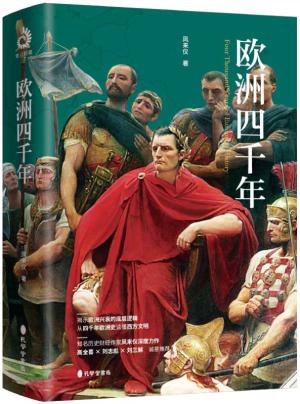
《
欧洲四千年
》
售價:NT$
435.0
|
| 編輯推薦: |
20世纪文学带来了什么,又教会我们什么跨越种族、国界、信仰、文化的人类情谊是什么样子的互联网时代,我们读书的的意义在哪里?
20世纪文学千帆荡漾,本书将带你登上涉渡之舟,发现文学作品背后的思想观念和创作脉络。
无论你是文学专业的学生、写作者或文学爱好者,还是仅仅是一个爱书之人,都将受益无穷。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涉及一百位影响当代中国文学潮流的作家及翻译界大家:莫言、贾平凹、汪曾祺、阿来、余华、迟子建、马原、王安忆、托尔斯泰、彼得·汉德克、陈平原、戴锦华钱谷融……重点介绍了他们的主要经历、思想和代表作。读者循着文章给出的线索,可以对20世纪的文学图景有全景式的了解。这些文章意在深入浅出地刻绘出作家思想的肖像,艺术的肖像,精神的肖像。有助于读者拓展文学视野并提升文学趣味。而对于希望“遇见”这些作家的读者而言,循着文章给出的线索,或许就能对这些作家,乃至整体的现当代外国文学“了然于心”。
|
| 關於作者: |
|
傅小平,祖籍浙江磐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报业集团文学报评论部主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兼职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著有《四分之三的沉默》《时代的低语》《普鲁斯特的凝视》《角度与风景》《一米寂静》《夜莺复调》等作品。获文学类、新闻类奖项若干。
|
| 目錄:
|
自 序/ 1
海外篇
辑 一
列夫·托尔斯泰:他竭力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寻求绝对的真理/ 4
安德烈·别雷:融合多种艺术技巧,使小说如复杂的交响乐/ 12
瓦西里·阿克肖诺夫:俄罗斯是他眷顾的心灵之乡,更是故事的源泉/ 18
伊利亚·爱伦堡:在任何时代,作家的重要使命都在于发现人的心灵/ 23
辑 二
若泽·萨拉马戈:重新学会“看见”,并让世界尽可能变得好些/ 30
塞尔玛·拉格洛夫:她天马行空的想象,让“教科书”成了文学经典/ 40
克努特·汉姆生:文学选择了我,却让我如此纠结/ 43
约恩·福瑟:我探入未知,并带回了某种曾经未知的东西/ 48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应该相信碎片,因为碎片“创造”了星群/ 60
彼得·汉德克: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勇于探索歧异的观察方式/ 68
安妮·埃尔诺:找到最合适的词和句子,让来自回忆的感受都被看见/ 77
吕西安·博达尔:小说是解释世界,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唯一方式/ 88
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好吧,让我们来谈谈怎样构建自己的避难所/ 92
伊夫林·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创造一个自己的系统/ 101
D.M.托马斯:以元小说叙述,揭示人生失落和孤寂的本质/ 106
哈尼夫·库雷西:看到我作品深处,才能看清反讽背后无言的悲伤/ 109
阿娜伊斯·宁:她用写延续性日记的形式来创作“小说”/ 113
弗雷德里克·福赛斯:我只是用小说来描绘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 116
马克斯·弗里施:我通过写作展示在写作之外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121
伊塔诺·斯维沃:带着打开的“头颅”,写时代的复杂诗篇
/ 126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他以写作一网打尽社会污浊底层的暗流/ 131
辑 三
约翰·厄普代克:赋予庸常生活以其应有之美/ 138
阿瑟·米勒:悲剧让观众对人类前景抱有最光明的看法/ 144
露易丝·格丽克:“诗人”命名的是渴望,而非一种职业/ 153
史景迁:他所有的作品都可以理解为一个或多个人物的传记/ 160
彼得·海斯勒:通过对普通人的观察和描写,透视深远的中国背景/ 164
辑 四
肖洛姆·阿莱汉姆:他在伤心故事里,把悲剧描画成了喜剧/ 172
伊斯梅尔·卡达莱:在知道自由时,我对文学已经很熟悉了/ 178
约瑟夫·罗特:他从不写诗,但他的每一本书都极富于诗意/ 186
卡勒德·胡赛尼:小说有一种将人们团结起来的特殊能力/ 195
辑 五
胡安·鲁尔福:写作是他与孤独对抗的唯一方式/ 200
埃内斯托·萨瓦托:艺术可以挽救社会不发疯/ 209
辑 六
纳丁·戈迪默:写作时不要考虑后果,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218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以新的眼光回望故乡/ 226
辑 七
三岛由纪夫:超越道德界限,展示纯美的存在/ 234
远藤周作:我写小说、讲故事,是为了传达神学思考/ 248
新井一二三:旅行在她笔下,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意义世界/ 259
渡海篇
辑 八
傅雷:文学翻译必须是有文学性、有艺术性的再创造/ 266
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271
许渊冲:文学翻译,让一个国家的美成为全世界的美/ 279
草婴:我所做的只是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 288
钱春绮:多读多写是提高翻译水平的唯一途径/ 295
高莽:他把翻译当成比写作更重要的事情/ 299
傅惟慈:生活好比一场牌戏,就看你怎么打好这手牌/ 303
李文俊:真正的译者必须要有“手段”,还原出完美的原图/ 307
叶廷芳:文学翻译有着太多的艰辛和奥秘/ 311
周克希:在翻译里,追寻逝去的时光/ 315
蓝英年:只有永恒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 320
江枫:只要汉语不变,译诗自然流传/ 325
任溶溶: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 330
郭宏安:传达原作风格,才是最高境界/ 338
马振骋:生活是独一无二的“原著”,有阅历才能如哲人般思考/ 342
余中先:等待贝克特的路上,遇见萨冈的“忧愁”/ 346
袁筱一:翻译是全心的交付与投入,对原作,也是对自己/ 350
万之:高难度的翻译,是挑战,是诱惑,也是探险/ 353
辑 九
哈金:难就难在写作“成功”之后仍能不断地写下去/ 358
张翎:理性的审美距离,让我完成“文学救赎”/ 365
陈河:能远离喧嚣,只按自己的冲动写作,感觉真好!/ 370
张北海:“侠”是个快意恩仇的美梦/ 374
黎紫书:我不愿意让读者看出我在书写过程中的挣扎/ 380
张彤禾:只有从个人发展中,才能看到国家的真实面貌/ 391
张惠雯:原地起飞,呈现丰富宽阔的生活/ 398
海内篇
辑 十
汪曾祺:我必须用笔写,这样我可以触摸每一个字/ 406
黄永玉:世界因为有了我,可能会变得好玩一点/ 421
王蒙:他不曾告别的“青春”写作,始终有着温暖的色调/ 429
冯骥才:当下知识分子应该有充分的文化自觉/ 437
张贤亮:自言“最有争议的作家”,不落俗套,也不曾落伍/ 450
陈忠实:创作是最孤苦伶仃也是最诚实的劳动/ 454
辑 十 一
莫言:作家即使写的别处,实际上也是在写故乡/ 462
贾平凹:所谓现代意识,也是从真实的生活中长出来的/ 471
王安忆:写作就是给那些无可命名的事物一个准确的表现/ 479
阿来:文学写作理当对语言有追求,对现实世界有超越/ 484
余华:不要想着超越自己,需要做的是不重复自己/ 494
张炜:唯有诗与真合成的力量才能抵达人性深处/ 511
韩少功:思想能力怎么会是个贬义词?/ 517
迟子建:写下文字,让沉默的生灵发出声音/ 523
毕飞宇:任何时候,离开世态人情,小说必死无疑/ 531
辑 十 二
马原:不是“小说已死”,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已经死了/ 536
王朔:我从来不认为这世上存在高级知识分子/ 545
刘震云:文学界的阿基米德?这也不在话下/ 555
刘庆邦:最大的技巧是真诚/ 562
欧阳江河:写作不仅仅是修辞,还要包含更深的呈现,更深的聆听/ 572
雪漠:“我”只是一个出口,流出了比现实更巨大的世界/ 579
辑 十 三
徐则臣:在海拔以下写作,眼光就没法高过地平线/ 584
李修文:我写散文的本意,是想促使自己更加贴近周边人事/ 591
冯唐:我所求不过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自在境界/ 596
赵本夫:写作有时就像在一片大雾里行走,走到哪算哪/ 599
阎真:“与真实零距离”中,追问人的生存困境/ 606
辑 十 四
吴兴华:游荡在中西文学之间,指示给他人奇异的梦/ 612
陈平原:文学教育切忌太功利,它是“润物细无声”的/ 619
戴锦华:向下看,向下流,向下走,我会比较踏实/ 628
余秋雨:要建立起对文化的信念/ 639
夏坚勇:坚守,行走,抒写“湮没的辉煌”/ 650
王尧: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感性与知性的融合/ 663
徐风:他的写作让我们看到地方文化的源头和流向/ 676
辑 十 五
曹文轩:我宁要“浅显”的审美,也不要做作的“深刻”/ 690
赵丽宏:我还可以非常真实地,用少年的眼光观察世界/ 695
黄蓓佳:以孩子的视角,表达对这个世界温柔的批判/ 701
毛尖:你说,他说,看看“我”会怎么说/ 705
周云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带我去远方流浪/ 711
|
| 內容試閱:
|
自序
五年前,我出过一本《普鲁斯特的凝视》,是我“刻绘”的100位外国作家“肖像”的结集。实际上,我不止写了这些,只是当时因为超篇幅,还有其他缘由割爱了。没收入集子的,加上后来新写的,就构成了这本书里的“海外篇”。我之所以把它放在前面,是因为以我的理解,自1897年林纾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以来,尤其是自1917年新文学肇始,中国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便是外国文学。如果说,百余年的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获得新生,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中国读者正是在对外国文学的阅读和学习中获得了世界性视野。
何尝不是那些不同语种的翻译家为我们打开了视野?王小波在《我的师承》里感叹,到了将近四十岁时,读到了王道乾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但即便是这样的大翻译家,也并不为世人关注。2009年初,我任职的《文学报》开设“走近翻译家”栏目,初衷即是让他们更多进入读者视野。我进入他们的居所或办公室,和他们近距离交流,也可谓是真正“走近”了,只是遗憾那时写文字,偏重于诠释他们的翻译生涯,没能更多记录现场,如今就是想复原也不可能了。而就在这短短十几年里,已经先后有多位翻译家离开了我们。如此,我到底还是欣慰于以无声的文字留存了他们的“印迹”。
我曾在一次会上听王安忆说,他们这一代作家与文学有关的训练,都来自于翻译小说,好在还算幸运,那些翻译家都是大文豪。这大概是作家所能给予翻译家的最高礼赞。莫言在《我与译文》里写道:“好的翻译家,也是熟练使用汉语的高级技师,他们为了准确传达原著的语言神韵挖空心思在汉语的宝库里所进行的艰难飞翔,是创造性的劳动。”如此,我总觉得翻译家其实也可以说是作家,他们不过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创作”罢了。
如果是给这些翻译家刻绘肖像呢?我竟然想到了前些年上映的电影《编舟记》,里面的辞典编辑们苦心孤诣搜集词汇,耗费十六年才得以编成《大渡海》。翻译家们也常常是为了找到最准确的词语,或是最恰当的表达反复推敲,以至于翻译一本薄薄的小书,都要消耗许多时光。因为语言并不是沙滩上的鹅卵石,只需旅者带它回家,它是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呀,把它转换成另一种文字,还能保持鲜活生动的面貌,仿佛获得了第二次生命,谈何容易。倘是改一下里面的人物荒木的话,那便是,外国文学的海洋浩瀚无边,那一本本翻译书是这片大海中的一叶叶扁舟,我们靠着它们渡海,找寻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言语,便是找到了独一无二的言语的奇迹。我总觉得那些海外华文作家也像是摆渡人,他们带着母语远渡重洋,又带着打上了异质文化印记的母语回家,这来来往往之间,便丰富了我们的中文世界。如此,这两辑似乎可以称之为“渡海篇”。
这便是影响的力量。这种影响来自于生活,也来自于阅读。余华说,对那些伟大的作品的每一次阅读,都会被他们带走,以至于自己就像是个胆怯的孩子,小心翼翼地抓住他们的衣角,模仿着他们的步伐,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走去,那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对同时代优秀作品的阅读,也是美好和富有启发的旅程。就像余华说的,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好比是阳光对树木的影响,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时,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许许多多的树木都在阳光雨露下以各自的方式茁壮成长,才得以长成一片莽莽苍苍的大森林。我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是抱着这样的期望的。我们期望读到更多好的作品,也期望在打开书页的瞬间,开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收录于最后三辑的中国作家——其实也不尽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而我总喜欢保留一两个例外,分明没有谁规定作家就得长成什么样子嘛——,也就构成了这本书的“海内篇”。
古今中外的作家们汇聚的文学大森林,又何尝不是一座避难所。走进森林,找一片阴凉之地,或是攀到树上,坐定后,欣欣然沉浸到阅读的世界里,足以让我们忘却人世间的烦扰。这大约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区别只在于如今阅读的方式有了变化,但无论是带上一本书,还是用手机或阅读器阅读,阅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不同。恰如毛姆所说,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你自己构建一座避难所,让你得以逃离人世间几乎所有的痛苦与不幸。果真能如此吗?其实未必,但即便是不那么愉快的阅读也让人躲开现实的重击,有了片刻的喘息。为世界读者构建避难所的托尔斯泰,晚年仓促离家时,也没忘带上《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书就成了他随身携带的避难所,他应是从中得到些许慰藉的吧。
如此,这本集子便叫了《去托尔斯泰的避难所》。我想起乔治·斯坦纳的感叹,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马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但倘是没有那些敏锐的敲打,又怎么体认我们得以奔赴的避难所的浩瀚与伟大,而敲打于我是力所不及的,我只是发出呼唤罢了。最初是我的老同学、出版人万骏问我能不能再整理一本像《普鲁斯特的凝视》这样的集子,要是再有个100位是再好不过了。好是好,数字就听着好,百尺竿头、百米冲刺、百花齐放、百川归海,能说不好?百位作家?我听了也还是觉得好,但心里是没底的,毕竟平时只管埋头写,从来没统计过写了多少,但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整理,却发现真是写了不少——我不能不感叹,职责驱使,加上一些媒体的邀约,居然写了不少!饶是如此,我也觉得写得不够,因为总还有一些作家值得“刻绘”,好在没有一个作家是孤立的,他总是和其他作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也在一些文章里留下了线索,循着它们,你或许可以描绘出更为完整的文学图景。
书稿辗转到了李黎手上,他编辑了《普鲁斯特的凝视》嘛。何况这本书稿虽在写法上有所不同,看上去却像是姐妹篇。幸得李珊珊编辑,也有幸得到范红升和孙茜老师的关照,终于出成了这本集子。有道是文学史上是流行三姐妹组合的,契诃夫就写了叫《三姐妹》的四幕剧本,写的是一个俄罗斯外省的小城里住着姐妹仨:奥尔加、玛莎和伊林娜,她们11年前随父亲从莫斯科迁居而来,又幻想着重新回到莫斯科去。她们能回得去吗?契诃夫这一问,我是解答不了的。我只是从阅读世界里召唤出了奥尔加和玛莎,但伊林娜不会再有。好在姐妹俩终究是相聚了,她们是要携手开启新的旅程的吧,将去往何处呢?且看着吧。
余华
不要想着超越自己,需要做的是不重复自己
1
1993年底,余华在《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活着》,他那时大概不会想到这部不到12万字的小长篇,会被看成是他创作水准的标杆,以致他于2021年初出版《文城》,不少读者也是惊呼,写《活着》的那个余华又回来了!
言下之意,这次“回来”的不是写《兄弟》和《第七天》的那个余华。《文城》也确实如评论家潘凯雄所说,与余华早年创作的《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叙事风格上更具一致性,但这样的类比或许还因为两者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刚读到这部小说节选文字的时候,我脑子里就闪过一个问题:余华为何写这样一部小说?说来这不算什么问题,没有一个作家会无缘无故写一部长篇小说,像余华这样暌违八年才捧出一部,就更得找到非写不可的理由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一晃而过了。等到要写推荐语,到豆瓣上看了看,却看到有网友也有类似的疑惑: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结束了,中国城镇化突破50%都已经过去十年了,再去写民国时期的村镇和乡贤又有什么意思呢?于是,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就回来了。
像余华这样的作家,似乎更应该把有限的笔力用在写当代上,或者说他更正确的路是在《兄弟》《第七天》没完结处继续往前,而不是像这本新作从《活着》故事开始的时候回退。退一步说,即便他要写民国时期的故事,也得如《白鹿原》一般从十九世纪末写起,一直延伸到当代,那样漫长的叙述,才会给人以史诗般的震撼。
无奈余华并没有出来做任何说明,《文城》也是简洁到除正文外,不见前言、后记,扉页上也不见引语,我也就只能推想,我就想到他曾在《兄弟》后记里写,在21世纪到来前,他开始写作一部望不到尽头的小说,那是一个世纪的叙述。我当时并不确定这部小说是《文城》,只是觉得有了这部,单从小说序列看,他已经完成,或接近于完成了自己的叙述抱负。好在这个推想,终于得到了证实。在“余华和他的《文城》”新书分享会上,余华谈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他确实是想写《活着》以前的故事。他们这一代作家有挥之不去的抱负,总是想写一百年的,哪怕不是在一部作品写完,也要分成几部作品写完。所以在1998年或者1999年,眼看着20世纪快要过去了,他就想着从《活着》故事开始的年代往回写,因为《活着》是从1940年代开始,结果他写了20多万字以后,感觉到往下写越来越困难,就马上停了下来。他在《兄弟》出版以后重新写,《第七天》出版以后又重新写,一直到疫情期间,他才把这部小说最后写完,所以确实是写了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追问,余华为何前前后后写了21年,其中原因在于他自己说的,在很长时间里,他都没能把握人物最终的走向,他对他们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了解过程。要理解这个说法,我们就得看看小说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余华简言之写了两段旅程,小说主体部分主要写了林祥福南下寻找纪小美的旅程,后半部《文城:补》写了沈阿强携纪小美北上逃亡或冒险的旅程。
话说——,我们用“话说”这两个字切入来转述小说故事是合适的。第一节写主人公林祥福背着个大包袱经过溪镇,碰到镇上人就问:“这里是文城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他又走出了溪镇。说白了这是个引子,是引我们进入故事情境的。从第二节开始,小说才算是步入了正题,而余华在某种意义上用的就是说书人的口吻,只是这个说书人实在是无比有耐心,从来不耍“说时迟那时快”的把戏。也就是说,余华叙述的速度,和小说故事发生的速度,是完全相匹配,甚至是前者还要略慢于后者的,但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慢,这实在很考验叙事功力。
有网友称,林祥福是那个时代朴素的理想主义者。照我看,林祥福确实是够朴素的,也确实是有理想的,虽然他出生在北方一户富裕人家。但正因为他朴素,有理想,到了二十四岁都还没能成亲。话说那一年那一天的黄昏时刻,他听到宅院外有一对年轻男女——也就是读后我们知道的,自称来自文城的阿强和小美,用他从来没听过的,“仿佛每个字都在飞”的语速说话。他打开门把他们迎了进来,同时也是把小说真正要讲的故事迎了进来。说来也是投缘,林祥福因为刚死了母亲,渴望和人交谈,而小美在留宿一宿后又偏偏病倒了,如此谎称急于赶去京城的阿强,只能留下她独自“北上”。于是我们看到林祥福在照顾小美的过程中,喜欢上了她,两人在一个冰雹之夜发生了关系。但没过多久,小美拿着林祥福家从祖上开始积攒下来的七根大金条和一根小金条离开,这使得林祥福伤心欲绝,只是时间一长就慢慢平复了,但小美后来居然又回来了,她回来是因为她怀了林祥福的孩子,也因为她知道林祥福为人朴素,会善待她。问题是小美生下孩子后又走了。林祥福就此开启了带着嗷嗷待哺的女儿南下寻找纪小美的漫漫长路。
2
老实说转述故事是没什么意思的,越是好的小说越是不适合转述。毕竟一经转述,小说就被缩略成了故事。有网友说,《文城》前半部的前面部分,讲的是“一个媒婆引发的惨案”,虽有戏谑成分,却不无道理。林祥福在相亲过程中看上一个叫刘凤美的千金小姐,偏偏见面时这个姑娘一声不吭,让媒婆误以为是个哑巴,使得林祥福按惯例留下一块彩缎就走了,一段本来可能有的美好姻缘,由此烟消云散。等到很多年后,已经长大的女儿林百家问他她妈妈是谁时,他没法说小美,就假托那个已经故去的刘凤美是她妈妈。反正按这个逻辑推理,要不是因为那个媒婆搅和,林祥福娶了刘凤美,就用不着他这么凄惨地南下寻找了。
讲到这里,即使不知道小说后面写了什么,读者也能猜到,林祥福多半是找不到小美的,他根据那么一点线索,能找到才怪呢。实际上,余华是想过让林祥福到南方,也就是到溪镇后就找到小美的,但这样写的话,那个时代就没法展开,所以他就放弃了。也正是因为要写那个时代,他干脆让林祥福融入溪镇,亦即进入到那个时代里生活。他这么处理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即使林祥福还在北方,他也可能不会过上安稳的日子,因为时代已经乱了,“那是一个乱世,乱世不止是在溪镇乱,在北方也一样乱。所以田家四个兄弟拉着死去的大哥和林祥福回家的路上还在说钱庄的老爷也被土匪绑票了,所以那时候全中国都是这样的”。
不过,小说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余华虽然没让林祥福找到小美,但实际上已经无限接近于找到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不管怎样,能不能找到纪小美,对于林祥福生死攸关,对于我们来说,却不是那么重要。我们要看的是他寻找的过程,这个过程套用余华一篇随笔的题目,即是“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两个人直到纪小美长眠十七年之后才重新有了“交集”,更是让这个旅程百感交集。
而这个旅程实在是不好转述的。我只能说,余华写得饶有意思,很是精彩。尤其是他写林祥福一次次背着孩子敲开一家家门讨奶水喝的过程,是能让人读出一种地老天荒的史诗感的。而写他初次抵达溪镇时在万亩荡遭遇的那场离奇的龙卷风,和他回到溪镇后经历的那场长达十五天的大雪,要我看也是直追施耐庵在《水浒传》里写林冲夜奔的神韵和劲道了。余华写这个过程的篇幅,也大抵是施耐庵写林冲夜奔前前后后的那些篇幅。那接下来林祥福怎么样?他在当地商会会长顾益民的关照下,在溪镇这个有缘之地住下来了,并且和同样是外来户的陈永良合作成立了木器社,他的生意也是越做越大,以至于把万亩荡都买了下来。
再后来就如网友说的那样,发生了一场“一群土匪引发的惨案”。余华写这个“惨案”真是写得巨细无遗、惨烈无比,在篇幅上大约都超过了林祥福寻找的过程,而且在这部分里,与其说余华主要写的林祥福,倒不如说写了那个荒蛮年代里溪镇人的群像。我看到有评论说,《文城》是一部更加丰富立体的群像小说,放在这部分——亦即小说前半部的后半部分里讲是成立的。而余华这么写,往好处讲是突破,是对围绕一个主要人物或家庭展开的叙事模式的突破,往不好处讲就是离题,而且离题离得那么远,是会落入凑戏份或不善于驾驭长篇的口实的。
但我想余华这么写,应该有他的道理。从写历史的角度,如果单看林祥福寻找的前半部分,除龙卷风和雪灾以外,甚至让人觉出祥和、温暖,也只是后半部分写到的匪乱才写出了真正的荒蛮、残酷,或者说正因为前半部分的祥和,更让我们觉得后半部分荒蛮的无以复加。再则,这部小说虽然我们能辨认出余华写的是清末民初,但我们很难找到具体的历史时间,也就这段匪乱最是能让我们明显联想到军阀混战的背景了。但余华应该无意于写历史,他是把历史当布景,写那个极端年代里人的生存经验。而他把历史背景写得扎实,说到底是为了把人写得真切。事实上,就文学而言,真正触动我们心灵深处的,往往不是历史本身,而是那种不为时间、地域拘囿的,为人类共同拥有的经验,这里面包含了文学所具有的神秘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腰封上引了余华的话,“我们总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作家那里,读到自己的感受,甚至是自己的生活。假如文学中真的存在某些神秘的力量,我想可能就是这些”显然是有所指的。
3
说回到小说写匪乱的部分,评论家杨庆祥在他的《余华〈文城〉: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一文里,可谓做了精到的分析。他谈及的“信”,与“信”相关的是“义”,也正是在小说这部分里得到了集中体现。如杨庆祥所说,小说中的次要人物甚至是反面人物,都遵循这一行动的原则,比如土匪,有情有义的土匪最后得到了善终和尊敬,而无情无义的土匪则只能曝尸街头,受众人唾弃。如此,当有网友问余华为何放着当下不写,去写民国时期的村镇和乡贤时,或许这里隐含着答案。用杨庆祥的话说,《文城》写的并非固态静止的历史演义,而是以镜像和幽灵的形式活在我们身边的故事。而以我的理解,当一部小说提醒我们当下缺失了什么,或许就已经把当代性,或者它之于当下的意义包含其中了。
接下来故事就推进到了堪为北上版《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文城:补》部分。有网友说这部分写的是“一串铜钱引发的惨案”。这么讲也讲得通,要不是在沈家作为童养媳的纪小美同情多年未见的弟弟,给了他那串铜钱,就不会导致纪小美被休,要不是纪小美被休,也就没有了沈阿强后来带纪小美北上的故事。但余华这么写也在情理之中,但凡有一定的阅历后,我们回头看很多事,就会明白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偶然会怎样改变人的一生。而从叙事上看,这部分实则对小说前半部留下的谜团做了解释,我们由此知道沈阿强和纪小美怎么就阴差阳错到了林祥福家,林祥福当年离开溪镇时为何半路杀出个女人送他孩子穿的衣服,纪小美在溪镇时又是怎样不和林祥福相见。当然他们之所以没能在生前相见,就是因为小美和阿强说冻死就冻死了。不能不说,这是让我读了百感交集的场景之一,我为这样的虔诚而动容,也为这样的愚昧而痛心,但往深处想,余华或许是让小美以死来赎罪的,如果是这样,又不能不让人感叹备至了。这就应了王安忆说的,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纪小美如是,溪镇那些在乱世中相互扶持,甚至慷慨赴死的百姓亦如是,林祥福就更是善良到了极致。
按余华自己的说法,他和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朋友关系,他是在一步步往下写的过程中,越来越了解林祥福是怎样一个善良到了极致的人。他说道:“林祥福刚出现的时候,对我来说还只是一个概念,他在雪冻的时节抱着婴儿来寻找一个人,寻找的那个人是谁,他谁都不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在寻找小美,同时他还要保护小美,他不能伤害她,他需要所有人不知道,只有在小说里陈永良离开溪镇要搬到齐家村的时候,他才告诉他到这来是干什么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林祥福也没有告诉他,他其实已经知道小美和阿强是夫妻,并不是兄妹。”
而余华也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写一个善良到极致的人,他曾经想重写《圣经》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个有上千头羊的富翁,他突然过腻了眼下的生活,就把财产交给他最信任的仆人打理,他自己则带着他的家人和其他仆人到外面去。过了好几年以后,他突然想回家了,他让一个仆人先回去,告诉帮他看家里财产的那个仆人说,他要回来了,让他准备一下。结果派去的仆人回去以后被杀了,消息传回来后,那个人认为是自己不应该派一个笨嘴笨舌的仆人去,他就派了他最喜爱的,一个非常灵活又很聪明的仆人去,结果这个人又被杀了,这时他还是认为自己错了,他说我不应该派仆人去,应该派我最爱的小儿子去,他看到我的小儿子就会知道我真的回来了,结果他的小儿子还是被杀了。他最后终于明白那个仆人变节了。余华感慨道:“当一个极其纯洁的人开始愤怒的时候,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他最后打回去了。但在这之前,他真是纯洁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种纯洁的力量,真是让我极其感动。我一直在想,我的文学作品笔下应该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曾经有段时间我想重写《圣经》的这个故事,因为《圣经》已经没有版权了,是可以改编的。我终于在林祥福身上完成了这个愿望。”
但严格说来,余华此前已经在《兄弟》里的宋钢和他的父亲宋凡平身上做过这样的试验。就像评论家李敬泽在他那篇题为《警惕被宽阔的大门所迷惑》的评论文章批评的那样,这两个人物被塑造成了善的化身,几乎具备凡人所能具有的善的品质,与此相对照,李光头一出场时就是个小流氓、小无赖,后来更是成了欲望和罪恶的化身。而且,这欲望和罪恶在人物身上焕发出的是一种神话般的力量,几乎被神化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到最后,我们发现李光头在社会上如鱼得水,宋钢则得了悲凉的下场。
应该说,《兄弟》出版后招致批评很大原因就在于,在很多读者和批评家看来,人物塑造不够有说服力。李敬泽由此直言,《兄弟》在更大的尺度上模糊了世界的真相:“据说余华立志要‘正面强攻’我们的时代,但结果却是,过去四十年来中国人百感交集的复杂经验被简化成了一场善与恶的斗争、一套人性的迷失与复归的庞大隐喻。”评论家邵燕君所说,宋钢和李光头兄弟二人与其说各自是善与恶的代表,不如说是强与弱的代表。我们看到的不是善恶对抗,而是强弱对比,其结果不是善恶有报,而是弱肉强食——这或许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同的时代逻辑。也正因为此,有人质疑《兄弟》的热销不在于它以小说品质取胜,而更在于小说扣准了大众心中隐藏的密码,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就是对强势者的崇拜。以我的看法,余华这样写是可以找到现实根据的,问题只在于,作家本人应该持怎样的立场,还有怎样让笔下的人物更有说服力。
4
不管怎样,在《文城》里,林祥福的善良是合乎情理的。余华在林祥福身上又一次践行了他在《活着》中文版序言中所说的“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和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余华在故事已经基本完整的前提下,还要写《文城:补》,也是进一步展示了高尚,虽然以他自己的说法,他主要是想给自己的叙述制造困难。在分享会上,余华说,以小美在小说出场时的设定,他要把她写成坏人很容易,要想再把她写成一个好人,难度就会大一点,“我为什么要写补?就是要告诉读者,小美的所有选择都不是她主动这么去做的,而是命运驱使她去做的,同时她也被命运撕裂了。余华举例说,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面于连准备向德瑞那尔夫人表达他的爱,因为他们互相有意,这在别的作家写起来并不难,因为伯爵的庄园很大,让于连找个没人的地方悄悄表达一下情意,是再方便不过了。但司汤达偏偏不这样写,他写了这样一个场景,伯爵家草坪上有一张桌子,德雷纳夫人和她的闺蜜坐在一起,于连坐在那用脚勾夫人,那种紧张、害怕就来了,夫人的闺蜜更是觉得莫名其妙,她发现她跟德雷纳夫人说话都是答非所问,司汤达把这个场景写得像一场战争一样。我就觉得作家写作,应该像司汤达教育我们的那样,永远是找困难的写,不找容易的写。因为把小美塑造成一个好人,要比把她塑造成坏人难得多,所以我就这样写了。”
和把小美塑造成好人一样困难的是,或许是怎样安排小美的结局。余华坦言,他写的时候觉得,林祥福到南方以后找不到小美很正常,中国那么大,找不到一个人很正常,何况文城也确实是不存在的。他说:“我当时为什么听从妻子的建议选择《文城》这个书名,就是因为这个城是不存在的,但正是因为有文城,所有故事都好像跟它有关系。我也不是要用伟大作品给自己贴金,但有些作品像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读了两遍,百年我读到了,就是没有读到孤独,里面所有人还都是热热闹闹的,哪有孤独?而且马尔克斯还做过一个演讲‘拉丁美洲的孤独’。毫无疑问,他是把‘孤独’原来的意义和概念完全扩充到开放式的,大家可以随便去理解。所以最后之所以选择《文城》这个书名,也是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书名。”但文城可以作为大的留白,就写人物而言,余华却是觉得虽然要留白,但不是给读者留一个大白,大的地方他是要完整写完的,所以他觉得有责任交代一下小美的生活历程。
前面已经交代,小美和阿强是在祈雪时被冻死的,虽说这也是情有可原,但我们读了还是觉得挺无辜的,也或许唯有无辜,才更让我们久久不能释怀。
要不像小说里悍匪张一斧那样的死法,就只会让我们觉得痛快了。据说,余华把这个人物写死,是尊了夫人的命。既然夫人说这个人不能不死,他就花三天时间把他给写死了。但让林祥福死,应该是余华自己的意愿,他也让他死得非常无辜。林祥福为赎回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带去土匪强要的枪支意图交换时,被尖刀从左耳根处戳进去戳死,他的死也并没有换回顾益民,顾益民事实上是被陈永良营救出来的。而林祥福死后,他的尸体是被曾万福从齐家村弄回来的。他南下到了万亩荡时,又是这个人划着船把他带到溪镇。余华说,他这样写,而且把曾万福背尸体的过程写得特别详细,就是为了给读者一个缓冲,让他们慢慢接受林祥福的突然死去。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余华式的温情。
而我在这里强调余华怎么设定情节,是想说明故事本身是有规定性的,未必是作家事先给定了框架。譬如不少评论都说到,《文城》在地域空间上有所突破。这么说自有其道理,因为余华的小说总体上是写南方的,具体来说是写南方小镇的,他写的所有故事笼而统之可以称之为“南方往事”——而据余华自己说,这部小说原先的书名也是《南方往事》,可见他写这部小说,本意还是写南方,但阿强和小美却是真正意义上“北上”了。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活着》里,福贵也曾被抓了壮丁“北上”,但只是渡过了长江,不久后又被战争裹挟着回到了南方。在《文城》里,林祥福就不必费这个周折了,他本就生活在黄河北边,他南下寻找小美,可是实打实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南下”。
当然,无论是林祥福,还是阿强和小美,他们要去的地方——阿强、小美虚拟的“文城”,和阿强只是听母亲说有姨夫曾在恭亲王府上做事就欲投奔的京城,都可以说是虚无缥缈的所在。这使得他们的“北上”或“南下”在缺少指向性的同时,也多了纯粹性。从寓言意义上讲,因为目标是虚无的,他们也就一直是“在路上”。这么说是因为,阿强和小美不是在“在路上”的时候就被冻死了,而林祥福虽然暂时在溪镇定居下来,却总想着有一天回到家乡,他死后,老家的佃农就遵照他的遗嘱来溪镇接他“回家”了,也就是说他还是“在路上”,小说到这里接近尾声,可想而知如果继续写下去,将会是一部余华版的《我弥留之际》。
无论如何,小说人物的南来北往,勾画出了一片广阔的地域空间,这在余华的小说里是前所未见的。虽然《兄弟》里李光头和宋钢也“走”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去了日本,或是去了海南,但与其说他们是“走”出来的,不如说是“闯”出来的。但话说回来,如果说写一个世纪体现了余华的写作抱负。写宽阔的地域空间或许并非他刻意为之,而是由故事本身自然而然带出来的。
5
其实不管对《文城》是赞许还是批评,读者大都认为它讲了一个好故事。先搁置好故事是否就是好小说不谈,我们有必要先问问怎样才算文学意义上的好故事。在这一点上,我赞同潘凯雄说的,一般意义上的“好故事”,不能简单等同于小说层面上的“好故事”。前者更多地诉之以“讲”,热热闹闹地讲,后者的要义更在于“写”,它要求作家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就我的阅读而言,体现在《文城》里,余华的语言是颇具诗性和张力的,但诗性在很多作家笔下往往会导致模糊,余华却让它走向了准确。而张力会让阅读的弦绷得太紧,余华却用幽默让这种紧绷舒缓了下来,并有了弹性。以我看,余华写纪小美再度回来躺进被窝后,林祥福感受着她在他手掌里倾诉般的哆嗦,这“倾诉般的哆嗦”六个字胜过千言万语,而余华也通过他富于想象力的笔触,把这种“哆嗦”倾诉般地传达给了我们。
所以说,余华至少是用好的语言讲了好的故事。而故事的好,也不只是在于它跌宕起伏、悬念丛生,恰恰在于它同时让我觉得明白如画。以我看,写一个百年前的故事——那时的时代环境、风物人情都与现在相去甚远,远到足以让人生出隔世之感——能写得明白,就像裁剪一件饶有古韵的衣裳,让人穿着熨帖自然,是需要作家下功夫的。看余华写乡绅文化,我们也能看出他是做足了功课。在分享会上,余华回忆说,他刚开始写《文城》的时候已经有网络,但需要连电话线,那时上网主要是发Email,没有别的功能。所以他主要是去书店买书准备材料。他写林祥福做木匠活,还罗列了橱子、柜子,以及各种家具的一些做法,其中有些就是从他查找的资料里来的,当然他也有这方面的记忆,“我小的时候,木匠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家的家具都是请木匠到家里来做的。所以,我对他们是很熟悉的,我记忆很深的是,有一次木匠刨东西,那上面有一个钉子没有拔出来,他就把刀刃刨折了,这可不是小事,把刀刃磨好是需要花很大力气的。小说里还涉及写中医,包括写顾益民怎么把他身上的腐肉去掉,我都是在中医书上去摘抄一些内容下来的,我知道什么地方有用”。在余华看来,了解这些资料是必要的,它会给你写作的一个基础,你不一定用它,但是你了解了心里有底。
也只有“心里有底”,余华才有足够的信心往下写。小说前面部分写林祥福到溪镇以后,遭遇了一场连下了18天的大雪,小美和阿强也正是在祈雪时冻死的。有读者就质疑南方哪里下过这么大的雪?余华回应道:“他这么质疑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反问,你忘了几年前那场大雪了吗?其实你去看中国一些大事记,就会发现不少这样的事。我查资料的时候就记得有一本书里写,清朝顺治年间,在无锡太湖区域,连下了40余天大雪。我在这本书里面只写18天,因为写到第18天时,我就觉得已经写不动了,假如我能写到40多天,我肯定是大诗人了。”
话虽如此,余华写一场大雪能写18天,就像他写这部小说写了21年一样,足以显示他叙事的耐心了。当然,我必须得说作家有耐心写,读者却未必有耐心读,所以最最重要的是,他能让我们有耐心读下去。这样我要问的问题是,这种叙事效果从何而来?这实在是很难说清楚的问题,但我隐约觉得,这是一部一直“在路上”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一直在“行动”的小说,余华自始至终都很少让人物静止下来,我们在读小说的同时,是跟着人物的“行动”,在不断移步换景,这使得我们总是觉得故事的转角有什么东西在等着我们,不至于失去了耐心。那人物一直在行动,余华又是怎么写他们的心理呢?他是通过写行动写心理的。或许很多人都读过他的那篇《内心之死》,他在里面直言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他进而写道:“威廉· 福克纳解放了我,当人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余华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写的。他是不多见的有独到的阅读感悟后,能把这种感悟彻底贯穿到写作实践中去的作家,也是那种写小说能写得和创作谈或读后感——在他这里,主要体现为随笔——一样好的作家。
以此看,作为现象级作家的余华在写作上取得如此成功,未必只是出于如他谦称的“幸运”。“当时这部小说发表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这部作品对我来说是如此重要,起码是在中国,它差不多是我所有的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了我其他的作品,由此才开始慢慢了解我。这确实是我的一本‘幸运之书’。”他说道。
6
但显然,《活着》不应该成为判断余华写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我们也不能过度吹捧这部“转型之作”,忽视余华此前充满先锋色彩的创作。余华自言,《活着》之前的长篇,他的第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从写作角度来说,对他也有着重大的意义。而《活着》则告诉他,面对一个题材要寻找最适合它的叙述方式。“作家写作和做其他行业一样,当你用这样一种方式取得成功以后,你会一直依赖于它。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作家一生都在用一种方式写小说。但是另外还有一些作家,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去处理不同的题材。我自己也是这样,当一个题材吸引我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是去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一种表现方式,前提是努力把自己已经很熟悉的那种叙述手段给忘掉,用一种空白之心去面对一个新的题材。”
而他所说的题材,或许并不包括短篇小说题材。分享会上,余华感叹他已经二十多年没有写短篇了,现在谈短篇就感觉在回忆往事一样。以他写作的感受,写短篇基本是按照构思来的,写长篇有时候会离开构思,“像《许三观卖血记》,我根本没想过会写成长篇。当年我跟程永新说一年在《收获》发六个短篇,他说我们没有这个规矩,我说没有这个规矩可以创造这个规矩,他说跟李小林商量一下,李小林说我们破一下例,给你一期三个行不行?我说我就要一期一个,一年六个。李小林也同意了。这样第一期发一个,第二期又发一个,第三个就是《许三观卖血记》,结果到第三期快发稿的时候程永新打电话说,余华,写完没有?我说,这可能是中篇小说。程永新说好好,我想他心里是想终于摆脱你了,每期发一个,以后别的作家怎么办。等到第四期快要发稿,他又打电话说,余华,中篇小说怎么样了?我说可能是长篇小说。他说长篇更好。第六期发了”。由此,余华得出一个结论,写短篇是一个工作,写长篇是一种生活,“短篇小说一般你构思好了把它写完就是。长篇小说写着写着,你的生活在变化,小说也在变化。所以我现在还是更喜欢写长篇,虽然长篇写起来很累”。
余华“累并快乐着”,也未尝不是因为他对写长篇“心里有底”,而所谓“心里有底”,或许主要是在小说和生活一起变化中,他对人物走向越来越有底。就《文城》而言,余华说,其中的一些人物像顾益民、陈永良,还有和尚,包括林百家、陈耀武、陈耀文,以及顾家四个男孩、两个女孩等都还活着,他们后来的故事其实也都在他的脑子里了。虽然当他把《文城》的稿子交给出版商的时候,他已经决定不写续集了,但很多读者都想知道后来怎么样,所以我希望能写续集,但条件是他体力允许。他说:“这部小说历时21年才写完,如果再写21年,我已经82岁了,实在是拖太长时间了。何况我还有好几部没写完,我现在正在写另外一部,已经写了一半多的小说。《文城》是我最接近完成,可是又最难完成的作品,我终于把它完成了,这让我信心倍增,我觉得另外一部也能完成。”
但余华一般只有真正心里有底了,才会把小说拿出来出版。
他会为自己的作品拉出一条平均值,感到一部作品能达到之前小说的平均值了,他才愿意出版:“我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作家,这是事实。我也希望一年能写七部八部,但写不出来。不过,我对自己的要求很高,可能是一个优点。我的手头有好几部长篇,这部《文城》1998年、1999年就写了20多万字。去年疫情待在家,我删掉了10来万字,又重写了10来万字。”
这可算是余华对自己所说“一个作家必须要挑战自己”的身体力行。以他长期以来养成的写作习惯,当他觉得往前写越来越困难时,他会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容易就会有点担忧。但这并不是说,他希望每部作品都比过去写得更好。在他看来,一个作家想超越自己是不可能的,他也不用总是想着超越自己,他需要做的是不重复自己。他也常常是有一个新的想法,就去写一个新的小说。但随着年纪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留给自己写作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少了,坦言:“我会集中精力把没写完的那几个写完,下一部小说可能不需要八年了,争取四年内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