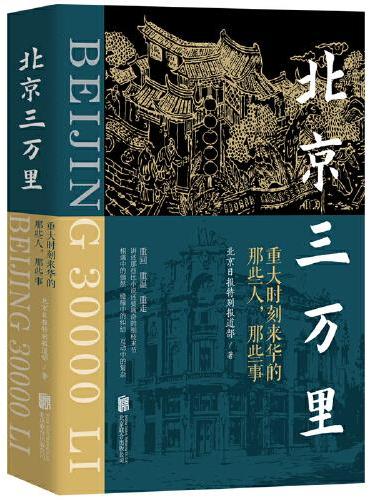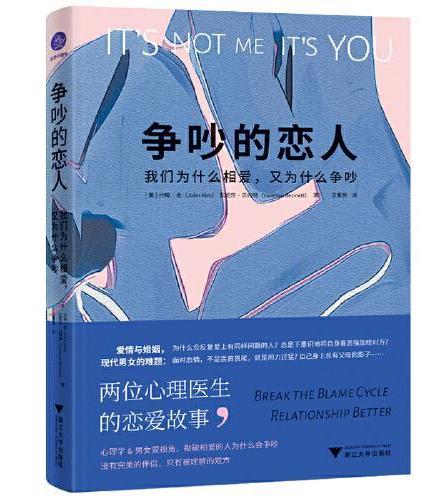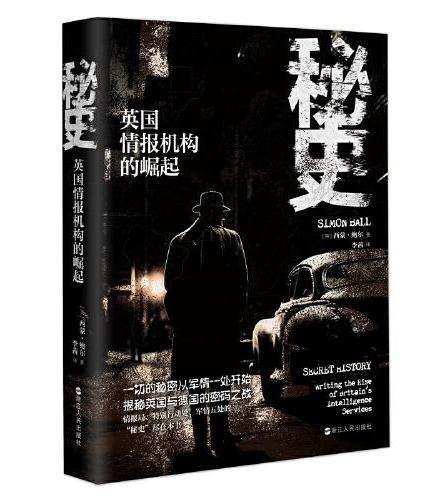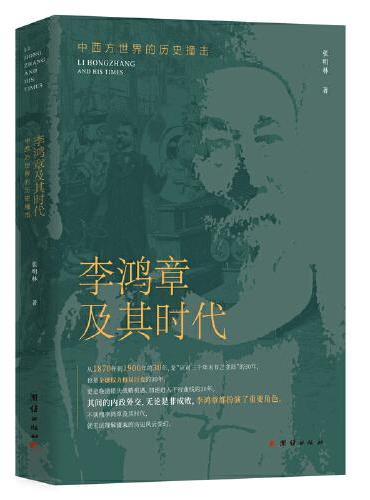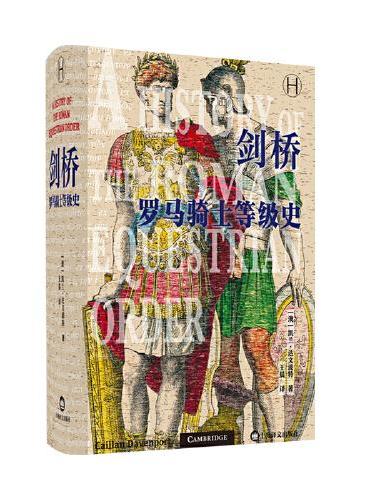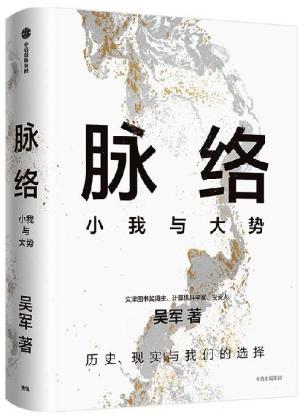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假努力:方向不对,一切白费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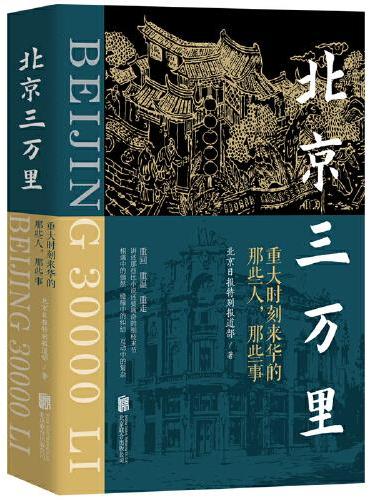
《
北京三万里
》
售價:NT$
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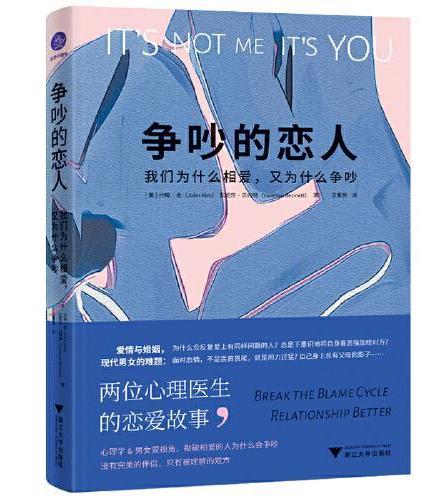
《
争吵的恋人:我们为什么相爱,又为什么争吵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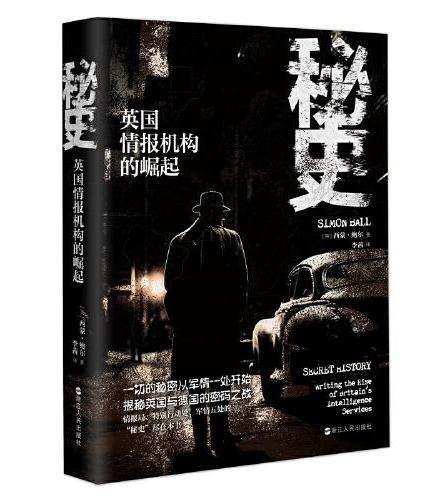
《
秘史:英国情报机构的崛起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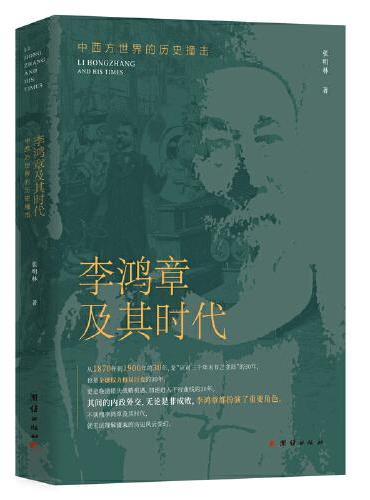
《
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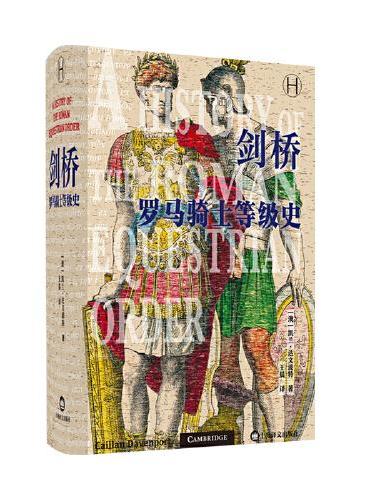
《
剑桥罗马骑士等级史(历史学堂)
》
售價:NT$
12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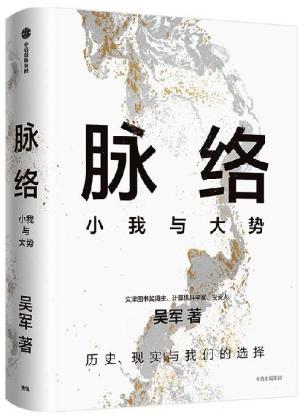
《
脉络:小我与大势
》
售價:NT$
484.0

《
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
》
售價:NT$
435.0
|
| 編輯推薦: |
1.《鼠疫》全新未删节全译本,生死边缘,是人性的考验与重生
2.《鼠疫》借助对苦难、死亡与存在的思考,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3.一座孤城,一场鼠疫,看瘟疫下的人生百态
4.精心整理作者生平事迹 珍贵照片 精美书签
5.《鼠疫》是1957年诺贝尔奖得主代表作之一,二十世纪西方文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作品!
6.《鼠疫》出版三个月就加印4次,印数达10万册。
7.1947年,《鼠疫》获得了法国批评奖,被译成了28种文字,在全世界拥有无数读者
8.法语直译,无删减,语言精湛,将加缪作品中所揭示的荒谬体现得淋漓尽致,精准还原了作品原貌。
9.内外双封面设计,内文采用高品质纯质纸,版式疏朗,阅读舒适
|
| 內容簡介: |
|
《鼠疫》是加缪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描写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以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那些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拥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的真正勇者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伟大的自由人道主义精神。
|
| 關於作者: |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大师,“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1957年,加缪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加缪是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具有影响,具有哲思的文学大家。代表作有小说《鼠疫》《局外人》,剧本《正义者》《卡里古拉》,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等。
译者简介:
李玉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教学之余,从事法国纯文学翻译三十余年。主要译作有小说《鼠疫》《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漂亮朋友》《羊脂球》等;戏剧有《缪塞戏剧选》《加缪全集?戏剧卷》等;诗歌有《艾吕雅诗选》、阿波利奈尔诗选《烧酒与爱情》等六种。此外,编选并翻译《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纪德精选集》;主编《纪德文集》(五卷)、《法国大诗人传记丛书》(十卷)。
|
| 目錄:
|
目录
第一部001
第二部055
第三部137
第四部153
第五部219
译后记 真理原本的面目 255
|
| 內容試閱:
|
译后记
真理原本的面目
这部《鼠疫》,通常论来是象征小说、哲理小说。不过,作者在文中界定得更为具体——“这部纪事体小说”,他强调指出,采用“历史学家的笔法”。生怕读者误解似的,叙述者(最后里厄承认是他本人,作者的替身)特意说明了这一点。不妨原话引用,像路标一样立在这里,指引我们阅读:
因此,由塔鲁倡导而组建起来的卫生防疫队,应给予充分客观的评价。这也就是为什么,叙述者不会高歌称颂人的意愿和英雄主义,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也就够了。但是,他还要继续以历史学家的笔法,记述当时鼠疫肆虐,给我们所有同胞造成怎样破碎而又苛求的心灵创伤。
所谓“给以客观的评价”“适当地重视英雄主义”,粗看也许是虚笔谦抑,泛泛承让,恐非作者真实的意图。历史学家的笔法,也并不意味不能颂扬英雄主义,尤其像塔鲁这样一批志愿者,协助里厄这样一些尽职的大夫,一起抗击鼠疫,坚持十个月,随时随地都有被感染的生命之虞,他们的行为怎么就不能被歌颂呢?事关对这部小说整体的理解,我不免半信半疑,仍怀着一般人的阅读心理,期待着在这场大灾大难中,看到可歌可泣的故事,却又迎头浇来一盆冷水,只见叙述者进一步解释:
不错,如果人真的非要为自己树立起榜样和楷模,即所谓的英雄,如果在这个故事中非得有个英雄不可,那么叙述者恰恰要推荐这个微不足道、不显山不露水的英雄:他只有那么一点善良之心,还有一种看似可笑的理想。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来的面目,确认二加二就是等于四,并且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紧随幸福的豪放欲求之后,从来就没有被超越过。同样,这也将赋予这部纪事体小说应有的特点,即叙述性过程怀着真情实感,也就是说,不以一场演出的那种恶劣手法,既不恶意地大张挞伐,也不极尽夸饰之能事。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不树立英雄的楷模也就罢了,如若树立,怎么也轮不到格朗这个窝囊废呀,总该是顶天立地的硬汉塔鲁。这还是次要的。经过仔细琢磨,我觉得这段话分量相当重,以加缪严谨的文风,不会是戏言妄语,看来郑重其事,似乎在宣告这部小说的宗旨和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首先,小说就不该是约定俗成的英雄颂歌。这部小说的所有人物,包括表现突出的里厄大夫和塔鲁等,无不是群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哪个也没有被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这就颠覆了“乱世出英雄”的传统,也颠覆了所谓“英雄”的概念。英雄主义何以该回到次要地位,作者一句话就道破了:英雄主义从来就没有超越寻求幸福的豪放欲求。换言之,这是其固有的功利性使然。那么谁来占主要地位呢?当然就是所有普通人物了。说到底,《鼠疫》通篇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其次,“这就将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这句话值得好好掂量,疑似更为重大的颠覆,而且颠覆到真理的头上。“原本的面目”,莫非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并没有见到本相?这里又不是确指哪一条真理而是泛指一切真理。简短一句话,好大的口气。言下之意,虽未得其详,但是我们凭借经验,不妨揣度一下:一提起真理,自然联想到“放之四海而皆准”,何其高远,何其圣洁!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表明,至少在我的心中,真理已经神圣化了,偶像化了。那么,怎么才是“原本的面目”呢?且看书中这样一段话:
必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斗争,绝不能跪下求饶。问题全在于控制局面,尽量少死人,少造成亲人永别。为此也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同鼠疫搏斗。这个真理并不值得赞扬,这只是顺理成章的事。
面对肆虐的鼠疫,决不能跪下求饶,任其摆布,不管以什么方式,必须与之搏斗,这就是《鼠疫》通篇彰显的真理。而这个真理在作者看来,“只是顺理成章的事,并不值得赞扬”。
以上两点——“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去伪存真;去其神圣性,去其偶像色彩,存留本真,将这种高不可攀的大词宏旨,降低到常人理解的水平“顺理成章”,也就合乎了常情常理。
这是本书的两大关目,关联着人与世界的方方面面:以鼠疫为象征的命运、苦难、上帝、信仰、生与死、爱情与亲情、社会道德、善恶、怜悯、良心、责任、抗争等等,这一切,不再是抽象的思想概念,而与书中人物一一相关。须天天面对,时刻处理问题。
奥兰,一座几十万居民的城市,本来生活正常,各自忙碌,互不相干,却突然闹起鼠疫,全城封闭,一切就全变了。全城演绎着集体的历史,个人命运不复存在了。
鼠疫这个象征物,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小说写作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泛滥的法西斯主义。不过,这种象征显然预留了很大空间,大大淡化了具体所指。罗兰·巴特发出批评的声音,对此就有微词,加缪在答复中有这样一段话:
《鼠疫》本意是希望读出多重含义,但是从内容上看很明显是欧洲抵抗纳粹的斗争。证据就是这个敌人没有指明,而在欧洲各国,人人都能指认出来……《鼠疫》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一部抵抗的纪事体小说。但是可以肯定,它还不失为这样一部作品。
加缪一方面强调鼠疫的多重含义,另一方面又坚持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和抵抗纳粹的斗争。这并不矛盾,具体所指,这是不言而喻的,倒是“读出多重含义”更为难能可贵。象征过分贴近时代背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象征意义就萎缩褪色了。加缪创作《鼠疫》时,想必有意模糊了象征的确指和泛指的界限,结果预留的空间与日俱增,能和读者的想象互动。因此,将近七十年过后,那段历史虽然不会被忘记,但是这种多重意义的象征,则由时间和纷扰的世界增添新的内容。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鼠疫》历经大半个世纪,非但没有被人遗忘,反而越传越广,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读者的喜爱,单在法国本土,销量就高达五百万册,成为不可多得的长销的畅销书。
作为一部哲理小说,这真是个奇迹,须知从哪方面看,《鼠疫》都不具备一般畅销书所具备的要素。正如叙述者所坦言:“这场鼠疫运行良好,如同一种谨慎而无可挑剔的行政管理,根本没有任何引人入胜的东西可以报道,没有类似老故事中的那种鼓舞人心的英雄,或者不同凡响的行为;不像大火那样壮观而又残酷,就连瘟疫初起时,萦绕在里厄大夫头脑的那种激情澎湃的壮观景象,也荡然无存了;尤其这场灾难持续时间长,单调到了极点,人所遭受的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
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就承认,鼠疫期间发生的故事单调得很,既不壮观也不感人,那么这部小说凭什么进入畅销的经典行列呢?我们还需要从文本中寻求答案:
叙述者的态度倾向于客观,以求杜绝歪曲事实,尤其杜绝昧良心的话。他几乎不肯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仅仅照顾到叙述大体连贯的基本需要。正是这种客观性本身知道他现在要说,那个时期的巨大痛苦,最普遍又最深重的痛苦,如果说是生离死别的话,重新描绘鼠疫的那个阶段,如果说在思想上责无旁贷的话,那么这种痛苦本身当时就丧失其感人的特点,也同样是千真万确的。
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家的笔法,特别强调客观性,不为追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事实。作者重申的这种写作态度,足以保证本书的宗旨和原则一以贯之,即我所说的通篇彰显的两大关目:普通人物唱主角,恢复真理原本的面目。这种创作理念,在《西绪福斯神话》这样的哲学著作中无法实践,于是加缪说:“你要想成为哲学家,那就写小说吧。”讲这话是有背景的,与其说是劝告别人,不如说是自勉。
我们知道,加缪的三部“荒诞”作品,即中篇小说《局外人》、剧本《卡里古拉》和哲学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相继发表,自成荒诞理论的体系。按说,哲学论述与文学形式这样相互支撑和印证,效果已经相当可观了。然而,这个体系总括来说,论述演绎了荒诞性,尚缺乏与之相制衡的反抗,于是有了第二个作品系列:长篇小说《鼠疫》(1946)、剧本《正义者》(1950)和厚重的理论力作《反抗者》(1951)。这就是以反抗为主题的另一个“三位一体”系列。
然而,第一系列以“荒诞”为主题,还缺少一个鲜明生动的、震慑人心的荒诞象征。荒诞的象征,在《西绪福斯神话》中流于抽象,在《局外人》中流于模糊,在《卡里古拉》中流于单弱,因而需要一个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的长篇复杂故事,需要创造一种刺激人神经,强迫人思考的创巨痛深的特殊氛围。《鼠疫》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鼠疫”这个瘟神,在人类历史上多次行妖作怪,大范围肆虐制造的恐怖惨景,史书多有详细记载,给人类留下不可磨灭的恐怖印象。单单“鼠疫”这两个字,就能先声夺人,一旦作为荒诞的象征出现,就成为不二之选。
在《鼠疫》中,这个瘟神不减当日威风,果然有惊人之举,要独霸几十万居民的奥兰城,就先发制人,放出成千上万只疫鼠,满街头楼道乱窜,发出吱吱哀叫,猝死在行人脚下。恐怖气氛与日俱增,老鼠在城中逐渐灭绝,便轮到人应征充当疫兵了。围城中的一切都听瘟神的调遣,都围着瘟神运转,这便是典型的荒诞世界了。
人一旦意识到荒诞世界,没有感染上疫症,也平添了心病,这就是身陷围城、心陷绝境的征兆。人什么都不能自主了,完全丧失了自我,那么人还剩下什么,还能做什么呢?
在此之前,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绝不肯将自己的苦难跟集体的不幸混为一谈,可是现在,他们都接受了这种混淆。他们没了记忆,也没了希望,就立足于现实中了。其实,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变为现实了。实话实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剥夺了友爱的能力。因为,爱要求一点儿未来,而我们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
是的,头几个星期,大家还很激愤,还盼望这种集体受难早些结束。然而,鼠疫猖獗日甚一日,无休无止,瘟神的战车来回碾压,什么情爱友爱,什么记忆希望,什么社会、道德、信仰、怜悯心、责任感,一切都被碾得粉碎。普遍的沮丧情绪,安于绝望的心态,比绝望本身还要糟糕。“只剩下一些当下的瞬间了”,这不就等于坐以待毙吗?
坐以待毙是大部分人的倾向,就连“新派伦理学家”都宣扬只能跪下求饶,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帕纳卢神父则表明基督教的观点,阐明鼠疫“发自天意”,是对世人的惩罚。“永恒之光通过死亡、惶恐和呼号的途径,引导我们走向本原的沉寂和生命的前提”。换言之,基督教徒只能表达笃信,余下的事上帝自有安排。
其实,这种倾向只是表面现象,谁也不甘心等待上帝的安排,任何人都没有听天由命,甚至自以为相信上帝的帕纳卢也不相信。奥兰城的秩序既然由死亡来节制,这就迫使人思考,是否还有别种选择。就连组织祈祷周的帕纳卢神父,在布道时也明确指出,“反思”的时刻到了:
进行劝导,伸出友爱之手,靠这种办法督促你们向善已经过时了。今天,真实情况就是一道命令。而救赎之路,现在就由红色长矛向你们证明,并且推动你们上路。我的弟兄们,上帝的仁慈最终就表现在这方面,即赋予一切事物以两面:善与恶、愤怒与怜悯、鼠疫与救助。就连危害你们的这场灾难,也是对你们的教育,给你们指明道路。
帕纳卢神父这段话,无意中提出一个荒诞的问题:鼠疫就是救赎,就是对世人的教育。我们可以抛开他讲这话的动机、前提和结论,拿来比较一下书中有识者的思想和行为,却是一个很有趣的殊途同归的事例。
同帕纳卢神父相对应的两个不信上帝的人,则是两个极有见识、极清醒的人物:一个是干劲十足,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里厄大夫,一个是极力反对死刑的社会活动家,全身心投入抗击鼠疫的斗士塔鲁。全城人落入鼠疫的围墙里,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人心大崩溃的时候,塔鲁和里厄却心有灵犀,很快就走到一起,为了同一种斗争。
抗击鼠疫的这两个灵魂人物也是殊途同归,各有各的反抗史,因鼠疫而走到一起。两个人的几次谈话,越谈越深入,由里厄的叙述和塔鲁的纪事铺衍缀补,无一不剀切荒诞这个主题意旨。同样,帕纳卢的两场布道,则从侧面乃至反面衬托了荒诞主题。这些表现荒诞-反抗主题的大脉络贯穿全书,串联起众多人物的命运:殊途同归,最终都投入这场斗争中。
书中最不可思议的,又最顺理成章的事,就是社会上各色人等,原本不是一路人,甚至是敌对者,却都陆陆续续汇聚到里厄和塔鲁的反抗旗帜下了。这正是荒诞的象征——鼠疫所起到的教育作用。但是教育的结果,却与帕纳卢神父布道所期望的恰恰相反,不是抽象的弃恶向善,而是奋起同死亡做斗争。
鼠疫这个荒诞象征,其示范效应产生了奇迹,如影传行,如镜示相,幻化了魔之形、恶之相,肆虐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挤压掉人生的空间,使得所有人无论所谓的“善人”还是“恶人”,都无路可逃,不想死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场斗争越惨烈,就越能激发人抗争,就连有案底的社会不安定分子——鼠疫期间走私发财的科塔尔,就连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总以审视的目光看别人的初审法官奥通,乃至传统宗教的代表人物帕纳卢神父,都纷纷投入这场战斗中。正如里厄那样,“在同现实世界进行斗争,自认为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
让人人都“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这就是加缪讲的“想成为哲学家就写小说”这句话的初衷吧。同样,这也正应了上文提到的两大关目:“赋予真理其原本的面目,归还英雄主义其应有的次要地位。”作者却是没有为求艺术效果而改变什么,结果顺理成章,原本面目的真理更容易被理解和掌握,而不贴英雄标签的人物事迹也更贴近现实生活。正是基于这些品质,小说《鼠疫》拓展了并且形象生动地演示了荒诞-反抗的主题,在荒诞的现实世界的多层面上,全方位地给人以启发。
加缪创作了两部荒诞推理小说,出版时间相隔仅四年,虽然命题相同,粗略比较一下,跨度还是相当大的。《局外人》唯一的主人公默尔索,在荒诞现实中是个独醒者;而《鼠疫》中的里厄、塔鲁等人物,则构成了一个反抗的群体,代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局外人》讲的是一个小职员因过失杀人,最终被判处死刑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是逐渐式的:默尔索还不以为然,不料却一点一点被绞进荒诞的司法程序中,没有他辩白的机会,一旦判决,就成为铁案了。默尔索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局外人”。《鼠疫》则讲述了一个席卷几十万居民的特大事件,是突发式的:一场持续十个月的大瘟疫,倾覆了一座城市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人心情感、道德良心、责任担当等社会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谁都不能置身这种荒诞现实之外,哪怕是偶来的局外人和社会的边缘人物。从气氛的角度来说,前者主人公一贯冷漠超脱,情节也相应进展徐缓,除了结尾爆发一下,通篇基本上平铺直叙,直到行刑前夕也是平静地迎接死亡。后者则截然相反,鼠疫突袭,一下子就把所有人置于紧张而惶惶不安的氛围中,疫城危难,与外界隔绝,死亡的数量和恐怖日益激增,人人性命不保,面对死亡的威胁,纷纷起来抗争,情节起伏跌宕,交织着极度伤悲和义愤的场景。
不过,比较起来,最值得注意的还是《局外人》所无暇顾及,或者说《鼠疫》所增益的内容,即给人以极大启示、直叩道德人心的部分。这部分内容在文中分量很重,探索了人的幽微的心曲,揭示了荒诞绝非纯粹的外境,内患与外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看作者如何阐微。
首先,如何看待把他们聚拢到一起的鼠疫,自然是他们实际行为的前提。这个群体的灵魂人物,里厄和塔鲁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们不赞同帕纳卢神父所谓的“集体惩罚”的观点,但是认为“鼠疫有其裨益,能让人睁开眼睛,逼人思考,尤其有利于一些人的思想升华”。鼠疫所象征的荒诞现实,还有其“裨益”,甚至利于“思想升华”。正是因为荒诞的现实,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能促使人脱离浑浑噩噩的状态,睁开眼睛看世界,认认真真思考所面临的残酷现实。作者的这种观点是一贯的,与《局外人》同时创作的剧本《卡利古拉》,整出戏只表现一件事:皇帝卡利古拉接连的疯狂举动,就是要逼使他周围的人睁开眼睛,看清这个荒诞世界。至于“思想升华”,其实也不难理解:古今中外,有多少杰出人物都经历了苦难,在文学领域经常被提起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个鲜明有力的例证。加缪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出身贫寒:“我是穷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产者。”也正是这种困苦的环境,磨砺出他那伸张正义的性情和坚持真理的勇气。
思想升华与反抗密不可分,可以说互为因果。《鼠疫》中的这些人物,首先要确认自己是否身陷鼠疫的危害之中,是否应该冒着生命危险与之斗争。里厄和塔鲁身世职业不同,但各自一直同现实世界做斗争,清醒地感到自己走在通往真理的路上。在组建志愿卫生队,填补行政管理空缺的问题上,二人一拍即合:“看到鼠疫给人带来的灾难和痛苦,除非是疯子、瞎子或者懦夫,才会任其摆布。”里厄这样回答塔鲁的问题,表明他不欣赏帕纳卢的“集体惩罚”的观点,治病救人才是他行医的理念。这里不妨节选二人的对话,我认为大有深意:
里厄:不相信沉默的上帝,竭力同死亡做斗争,这样对上帝也许更好些。
塔鲁: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不过如此。
里厄:这不成其为停止斗争的理由。
塔鲁:我不免想象,这场鼠疫可能对您意味着什么。
里厄:意味连续不断地失败。
塔鲁:这一切是谁教会您的?
里厄:是苦难。
塔鲁:还有一句话,大夫,哪怕您觉得可笑——您完全正确。
里厄:对此我不甚了了。那么您呢,您了解什么呢?
塔鲁:我要了解的事情不多了。
里厄:您认为自己全部了解生活了吗?
塔鲁:不错。
里厄:在进入这段经历之前,再确定一下,您能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幸免于难。
塔鲁:一百年前,一场鼠疫大流行,夺走波斯一座城市的全部性命,唯独那个一直忠于洗尸体的人得以幸免。
里厄:您管这件事,出于什么动机?
塔鲁: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里厄:什么道德观?
塔鲁:理解。
二人十分平静地谈论着人生中这么多天大的问题,以极平常的语气讲出生活的这些真理。顺便提一句,全书凡是这类真知灼见,从不激昂高阔,始终保持这种家常的语气。下面仅就这段谈话所提及的几点,看一看在“荒诞”这个主题上,作者如何阐明道德人心的真实情况。
面临大灾难,信仰问题就会凸显。里厄和帕纳卢,一个医生、一个神父,道不同,最终还是走到一起。神父宣称“应该热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医生则答以“誓死也不会爱这个让孩子受折磨的世界”,但是他们都在尽心尽力“为拯救人而工作”。唯独这一点才重要,表明他们能超越信仰,超越渎神和祈祷的事,一起同病痛和死亡做斗争。二人达到心灵的契合,里厄握住帕纳卢的手,平静地讲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现在,就连上帝也不可能将我们分开。”
不用大词阐述宏旨,这是加缪的创作特点。里厄和帕纳卢终生坚守的,一个是职业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信仰,而真正信仰的前提,作者并没有用大爱的字眼来表达。唯有大爱,才能超越信仰的争衡,在大灾大难中,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里厄这样评价帕纳卢——“心里要比表象优越”“他讲得好,做得更好”。帕纳卢自从参加了卫生防疫组织,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和鼠疫传染的地方,在击退鼠疫的前夕以身殉难。
鼠疫猖獗时期,消除了人的价值判断。所有出路都关闭了,人很容易就全盘接受眼前的一切,无论做什么都不再有所选择,这就是丧失了信仰。当然,真正坚定的信仰是不会因外境而丧失的,就像里厄、塔鲁、帕纳卢等人这样,而在特定的境况,反抗就成为他们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吸引来有案底的边缘人物科塔尔、自认为疫城局外人的巴黎记者朗贝尔、主张判决的威力胜过法律的初审法官奥通先生等一干人。同样,在鼠疫这种特定的境况,反抗也成为不同价值观的唯一去向。这就是上面那段对话的基本内涵。
反抗成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但是个人的动机却不尽相同,毕竟心怀大爱的人在世间属凤毛麟角。就连塔鲁也直言,他的动机出于“理解”的道德观。“理解”一词词义明确,又很广泛,出自塔鲁之口,必有其特殊的含义,如果不联系他的身世,就很难抓准意思。塔鲁的父亲是法官,在塔鲁看来,父亲一上法庭和刑场,就变了一个人,那种表现“正应该称为最卑鄙的谋杀”。于是,他十八岁那年离开优裕的家庭,体验了贫困的滋味,为谋生干过各种行业,不想成为“鼠疫患者”,便成为社会活动家。他认为他所生活的社会是建立在死刑基础之上的,就同社会做斗争,极力反对死刑。为了达到一个不再杀人的世界,他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投入欧洲各国的斗争中,自以为走在正确的路上,尽心尽力在同鼠疫做斗争,最终才醒悟,自己一直是鼠疫患者,即使抱着良好愿望,即使好人也难免杀人,“因为他们就生活在这种逻辑中”,一举一动都可能致人死亡。塔鲁说道:
即使拯救不了人,起码也尽量少给他们造成伤害,有时甚至给他们做点好事儿。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拒绝一切直接或间接的、有理或无理的杀人行为,也不为杀人的行为辩解。
同样,这也是为什么,这场瘟疫没有教会我什么,只让我明白必须和你们一起同瘟疫斗争。我基于可靠的知识了解,鼠疫,每人身上都携带,因为任何人,是的,世上任何人都不能免受其害……一个正派人,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但是现在,我心甘情愿,原原本本做人,我学会了谦虚。我只想说,大地上还有灾难和受难者,一定得尽可能拒绝,不要跟灾难同流合污……我听到过那么多高谈阔论,脑袋几乎被弄晕乎了,那些高谈阔论也足以使其他一些人晕头转向,结果同意去杀人了。从而也使我明白了,人的不幸缘于他们没有使用一种清晰的语言。于是我决定讲话和行动都要明明白白,以便走在正道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