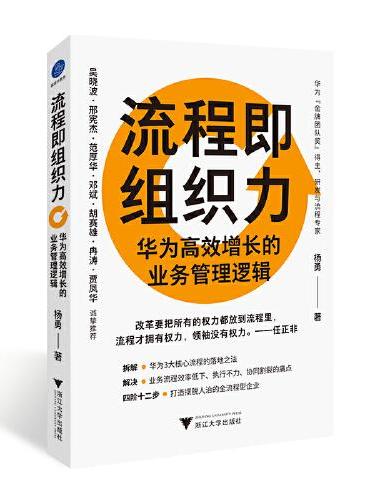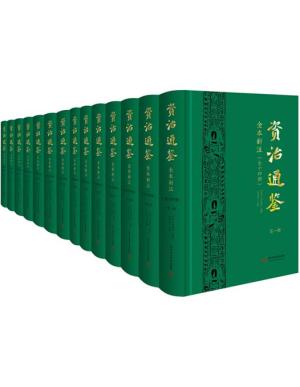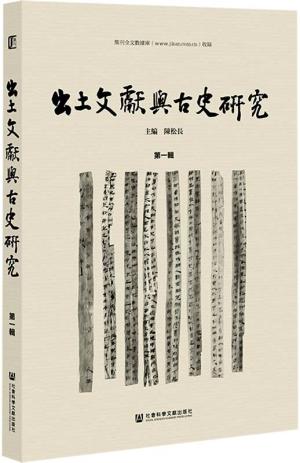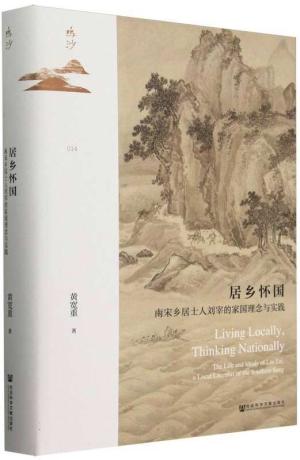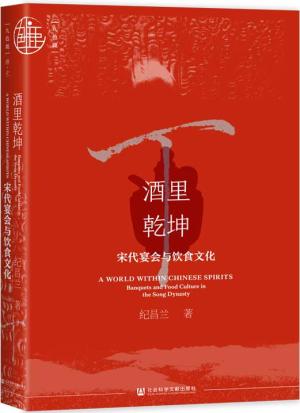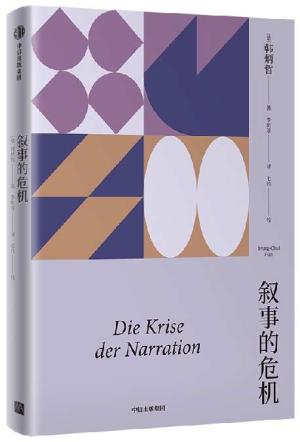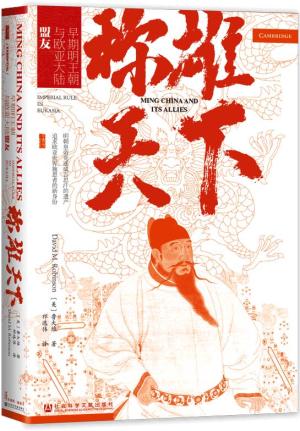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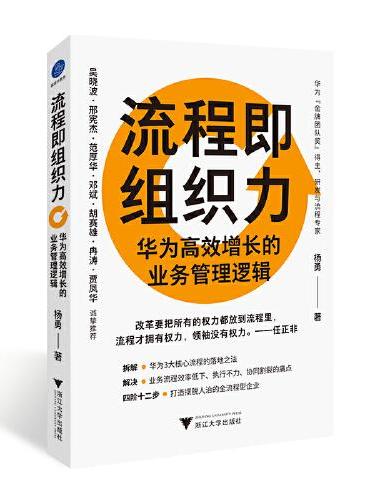
《
流程即组织力:华为高效增长的业务管理逻辑
》
售價:NT$
3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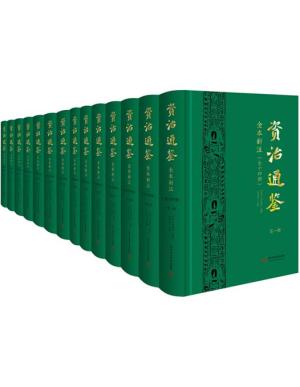
《
资治通鉴全本新注(全十四册)
》
售價:NT$
873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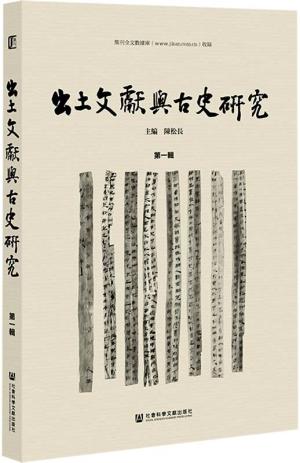
《
出土文献与古史研究(第一辑)
》
售價:NT$
704.0

《
九色鹿·镇守与共荣:唐代的太原尹
》
售價:NT$
4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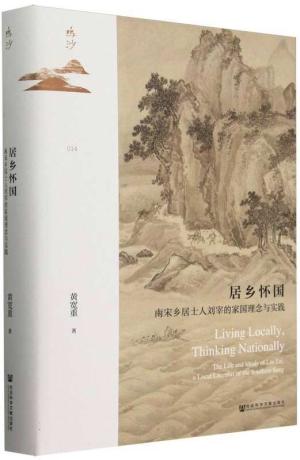
《
鸣沙丛书·居乡怀国:南宋乡居士人刘宰的家国理念与实践
》
售價:NT$
49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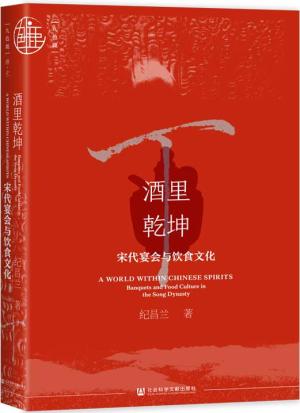
《
九色鹿·酒里乾坤:宋代宴会与饮食文化
》
售價:NT$
49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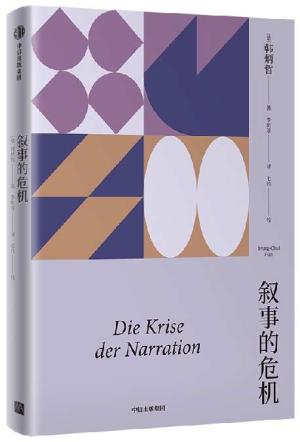
《
叙事的危机
》
售價:NT$
26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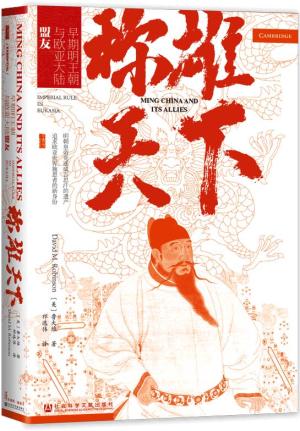
《
称雄天下:早期明王朝与欧亚大陆盟友
》
售價:NT$
380.0
|
| 編輯推薦: |
高校教授、学者钱虹首部个人散文集
卢新华、严歌苓、张翎、巴金、贾植芳、余光中、徐中玉、钱谷融……19篇精选散文,带
你领略学人之风
心中自有文池书海,往来皆是雅人韵士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为作者近年来在教书、学术研究之余,陆续写下的有关忆人散文中挑选出来的散文结集。其中绝大多数都曾为各种报刊刊载过。全书分为“同道中人”“名人忆旧”和“师恩难忘”三辑。“同道中人”多为作者对多年来相知相熟的世界华文文学领域的著名作家的印象与侧记,如卢新华、严歌苓、张翎、陈若曦、尤今、吕大明、吴玲瑶等,凸显其作品与文字背后的故事与魅力。“名人风范”收入作者与文坛名宿,如巴金、贾植芳、余光中、刘以鬯等人的接触或交往故事。“师恩难忘”所收则为怀念或回忆作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期间几位授业恩师的文章。
|
| 關於作者: |
|
钱虹 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及同济大学女教授联谊会副会长。现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员,并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监事长、上海市钱镠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著有《女人·女权·女性文学》《缪斯的魅力》《文学与性别研究》《灯火阑珊:女性美学烛照》等多部作品,出版编著2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
| 目錄:
|
/? 辑一 同道中人 /
003 吐丝心 须,锯齿叶剪棱
? ? —— 卢新华及其文学创作
012 “小说是作者的一个个梦”
? ? —— 我看严歌苓及其小说
025 “曲”中情意结,“恋”时人婵娟
? ? —— 我与张翎的文学交往
040 至情至性的人事风景
? ? —— 陈若曦其人及其散文
048 “放只萤火虫在心里”
? ? —— 我所认识的新加坡女作家尤今
057 “艺术家只能听命于美神”
? ? —— 旅法女作家吕大明及其散文
065 缪斯赐予的典雅与睿智
? ? —— 我与菲律宾华文女诗人谢馨的诗缘
077 幽默是人生的“润滑剂”
? ? —— 美华女作家吴玲瑶及其散文
091 非鱼非石,是景是灵
? ? —— 记香港的“宋公明”彦火先生
/? 辑二 名人忆旧 /
101 那年春节,巴金给我签了名
? ? —— 巴老辞世五周年祭
106 贾作真时真亦“贾”
? ? —— 纪念贾植芳先生辞世一周年
110 凭一首《乡愁》
? ? —— 忆诗人余光中先生
117 “所有的记忆都是潮湿的”
? ? —— 我与刘以鬯先生的海上文学缘
129 “真的猛士”真性情
? ? —— 我所知道的钱玄同
140 “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
? ? —— 记钱法成与昆曲《十五贯》
/? 辑三 师恩难忘 /
159 铮铮风骨,国士无双
? ? —— 忆恩师徐中玉先生
169 魏晋风度,坚守“人学”
? ? —— 记导师钱谷融先生
185 先生风范,山高水长
? ? —— 忆施蛰存老师
203 仙风道骨,春风化雨
? ? —— 忆许杰先生
210 跋
|
| 內容試閱:
|
代? 序
我从 1977 年高考走来
我对历史常常一知半解,看了美籍华文女作家李黎女士的《我的一九六八》,犹如突然打开了心灵深处尘封已久的历史抽屉。就我有限的记忆而言,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年份应是 1977。因为正是这一年,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成千上万像我这样失学十年的中国青年的命运。
人的一生,往往会有许多偶然。有时候,人的命运,就是因为某些偶然事件而发生改变和转折的。
席卷神州大地的一场文化浩劫,它无情地掐灭了中国青少年叩开人类文明宝藏大门的求知梦想;而后者,却像阿里巴巴用暗语打开了意想不到的藏金秘窟之门,像我一样的幸运者得到了泛舟学海、攀登书山的机遇,圆了曾经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学之梦。
1966 年夏天,虚报年龄早上一年学堂的我,刚读到小学六年级。我万万没想到,此一脚跨出小学校门,等到再踏进学校大门,竟会相隔整整 11 年的光阴,并且还是直接迈入大学门槛。1977 年 10 月下旬的一天,报纸上、广播里突然传来了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在当时,简直不亚于引爆了一颗原子弹,霎时震撼了整个中国。从车间到田头,从兵团到农场,从北大荒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天山南北,多少原本大学梦早已破灭的知识青年,仿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听到这一消息,失学多年的我,自然也是兴奋不已。当时我正在皖南山区的一家发电厂当汽车电工。已经 11 年没进过课堂的我,文化程度填的是初中毕业,可实际上自 1966 那个夏天之后,我就没摸过一本教科书。我上山下乡去的是位于苏北如东县海边的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一团。三十年后,2009 年冬天我与许多当年的知青结伴重003返故地,欣喜地看到那里已成了深水港开发区,真正应了伟人的诗句:“三十二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想起我们当年抵达这里时正值大雪过后,天寒地冻,几千名知青很快就被分到营、连、排、班,变成了农垦战士。去后不久,团里宣传股要成立一个团报道组,负责全团广播站的新闻通讯稿的采写和对外宣传报道,决定每个营抽调一名知青作为记者。冥冥之中似乎有幸运之神在眷顾我,一个偶然的机会,还不满 16 岁的我竟然被选上了。我挎起书包,书包里是笔记本和钢笔,白天到各连队去采访,晚上在煤油灯下赶稿。记得印象最深的是1970 年 4 月的一天,我国的“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消息传来,我倍感兴奋。那天晚上在团部收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便立即独自一人摸着黑(连手电筒都没带)奔走在田埂上,连夜赶到各连队去传播“喜讯”。这就是当时最原始但也是最直接的传播手段。后来每每想起来都很害怕:万一遇上歹人或是掉下沟渠,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当时就是那么毫无顾虑地胆子特别大。我担任团通讯组记者的时间不长,一年之后就按照政策调去地处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当了工人。这一段知青岁月,虽然短暂而又艰苦,但对我而言却是难忘而又宝贵的经历。它大大地锻炼了我的胆量和自信,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与反应速度,并且培养了我不怕困难的毅力和独立思考的勇气。这是我后来报名参加 1977 年首届高考时才意识到的。
我进了地处皖南的上海后方基地“小三线”某发电厂后,整天与“解放”牌、“交通”牌大卡车的发电机、点火塞、电瓶、大灯小灯打交道,再也没碰过纸和笔。后来大学开始招“工农兵学员”,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组织推荐”。我反正轮不上,所以也就不再做上大学的梦了。谁也想不到,就在 1977 年 12 月,中断了 11 年的高考,在全国各省市一个个简陋的考场内,竟然恢复了。我进了大学后才知道:那年,有 570 万年龄不一的考生参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次设在冬日的全国高考,那一届录取人数为 27.3 万;那年,印制高考试卷的纸张严重匮乏,是邓小平伯伯拍板用准备印制《毛选》第五卷的纸张解了赶印试卷的燃眉之急。
那时,由于上海后方基地各家厂报考的人数众多,路途遥远,不能赶回上海参加高考,于是后方基地与安徽省协商后做出决定:后方基地的考生一律在当地参加安徽省自行命题的高考,但不能占安徽省的报考名额。这个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后方基地的考生只能填报上海市和安徽省的大学。这也是当年的一项“特殊规定”。我心想,权当是像当年在生产建设兵团当知青记者那样“练练笔”,就勇敢地报了名。考试还没开始,就要填志愿,当时上海只有两所文科大学,我就懵里懵懂填了一下:第一志愿填的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三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历史系”,反正是瞎填。高考那天,我清晨从山沟里坐厂车赶到贵池县城池州师范专科学校的高考考场时,手脚已冻得僵硬。我不停地搓着手,跺着脚,进了考场。第一门考试是语文。作文题目有两题,由考生任选一题。作文占 70 分。我选的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这是从叶剑英元帅的一首五言绝句中选出来的一句诗。我当时具体写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了。另有一题是“谈谈‘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刻含义”,占 30 分。这是鲁迅先生的诗,我读过。至于怎么分析其中的“深刻含义”,也全忘了。还有两题是加试题,分别是古文标点和古文翻译,各占 10 分。这样,语文满分为120 分。我进了考场后已顾不上冻僵了的手脚,只是不停地挥笔,心想无论如何要把考卷写满。真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我的语文成绩居然获得了 99.5 分,成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1977 级新生中语文单科的最高分。可是,其他几门考试科目,就没语文这么幸运了。虽然我报的是文科,免考物理化学,且 1977、1978 级高考因历史原因而免考外语,但数学和历史地理,对根本就没摸过中学教科书的我而言,哪一门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尤其要命的是,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考场,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身处皖南山沟里的我,不但找不到一本 1966 年前出版的中学数学、历史和地理课本,而且根本不知道该从何处入手进行系统复习。我想请探亲假回家,以便向念过高中的弟弟和他的老师求教,可是当时厂里的车辆正面临“年检”,另一位汽车电工生病休养,剩我一个不但没法走,还得经常加班加点。我只好在上下班的路上“喃喃自语”,把一些数学公式背得滚瓜烂熟。好不容易熬到通过了车辆“年检”,我才请了十天探亲假,回家将数学和历史地理临时抱佛脚地恶补一番。所以,这两门课,我自觉考得不好。考完高考,我对被录取不敢抱什么奢望。1978 年春节,我留守皖南的厂里继续加班。谁知春节后某一天,突然接到了厂组织科的通知,说我已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是全厂唯一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组织科要我尽快交接工作,赶在 2 月 28 日这天去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我起先以为是搞错了:厂里与我一起参加高考的有 30 多人,其中不少以前念过完整高中,怎么会轮得到录取我这个初中都没念过的人?但组织科交给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我的名字。离开组织科,我攥着录取通知书,一路跳着笑着,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那个人。
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后,我就像一条欢快的小鱼,无比酣畅地游进了知识的海洋;又像一块干涸的海绵,如饥似渴地吸吮着书本里的营养。当年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有不少国宝级的名师,如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钱谷融等先生。我何其幸运,能够成为他们亲自执教的学生。在我的人生之路上,他们的人格魅力、精深学问、学术品格和高风亮节深深影响着我,他们是我进入学术圈的人生楷模。在他们中间,许杰先生年纪最长,资格也最老,他是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建系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四时期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会员。他是我考取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最早认识的作家。入学不久,我在图书馆看到 1935 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系大系:小说一集》,其中收有他的小说《惨雾》《赌徒吉顺》等。茅盾先生赞许他是当时“成绩最多的描写农民生活的作家”,我十分钦佩这位以表现浙东乡村悲剧见长的名作家。我研究生毕业后与他成了同一教研室的同事。不久,教研室搞活动,年近九旬的他也拄着拐杖来了。我的影夹里珍藏着教研室同人与许杰先生的唯一一张合影,弥足珍贵。作为教研室秘书,我曾数次去许先生家登门请教。施蛰存先生被誉为一生同时开启四扇窗户 —— 现代派小说创作的“东窗”、西方文学翻译的“西窗”、古典文学研究的“南窗”、金石碑版考据的“北窗”的学界泰斗与文学大师。我念大二时有幸成为他亲自授课的唯一一届本科生之一,那年他 75 岁。一学期下来,这位年龄与我们整整相差半个多世纪的老教授,在我们那届“小”学生中人缘颇佳,我们既钦佩他的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更喜欢他的平易近人、幽默风趣,丝毫没有一丁点儿著名教授的脾气和架子。从他的言行举止中,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位曾经长期遭受人生种种磨难和不公的老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毕业留校,后来有幸成为施先生的同事,多次登门拜访,与他面对面交谈。在我所认识的那些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中,除导师钱谷融先生外,我最喜欢跟施老这位乐观、机敏、充满生命活力和生活情趣的老师用方言交谈。他操一口乡音很重的普通话,无论说话还是聊天,风趣生动,睿智幽默,妙语如珠,让人如沐春风。钱谷融先生是我读研究生时的导师,也是教会我懂得什么是文学、怎样做人做学问的学术引路人。记得先生给我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文学是人学”。他说,文学是人写的,文学也是写人的,文学又是写给人看的,因此,研究文学必须首先学做人,做一个文品高尚、人品磊落的人,这是人的立身之本。先生严肃地指出,他喜欢踏踏实实做学问的老实人,讨厌东钻西营搞关系的投机家,对自己的学生更是如此要求。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要把主要的精力最大限度地放在做学问上,而不要放在人际关系的斡旋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品比文品更要紧,人格比才学更宝贵。1957 年先生写了那篇《论〈文学是人学〉》的著名理论文章,此后被批判多年,其间 4 次胃和十二指肠大出血,讲师一做就是 38 年,可他却从没有后悔过,晚年的他对我说:“因为我相信我的观点没有错。”徐中玉先生是我进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时的系主任。他比以上这几位年逾九旬的老先生更为长寿。在超过百年的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地坚守知识分子的良知与中国文论和文学的标杆,历经磨难而以民族、国家大义为重,以传承与发扬光大中国文化传统为己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身处逆境而沉静,面临危局而敢言;兢兢业业俯首工作,甘于清贫埋首学问 —— 这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他的一生,端端正正地写好了一个大写的“人”字,成为我们后学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
我之所以会选择文学研究为终身职业,是和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施蛰存先生、许杰先生等老一辈先生们的言传身教和鼓励支持分不开的。比如我大二时发表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其实是交给徐中玉先生的一篇课堂作业,他鼓励我拿去投稿,于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我就投给了《上海文学》,没想到竟然发表在该刊 1979 年第 4 期上。虽然至今我已经在国内外各种刊物上发表了 300 多篇学术论文,但受到徐中玉先生鼓励而投稿发表第一篇文章时的激动之情仍难以忘怀。还有读研究生时,钱谷融先生为我的论文发表写推荐信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我此后的任何一点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栽培与教诲。从一个只学过一句英语的无知少女,到站上高校讲台主讲多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大学教授,我想,发生在我身上的命运变化,也许只是一个偶然;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在四十年前作出恢复高考决策的伟人邓小平伯伯的缅怀,却又是一种必然。因为,如果没有他当年的高瞻远瞩和巨大魄力,就没有千千万万 1977年后踏入大学之门的中国青年的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大学生,没有我们,就无法体现 1977 年恢复高考的意义和录取标准的公正;没有我们的“大学梦圆”,中国的各行各业,尤其是教育科技文化领域“人才断层”危机就将变得“不可救药”(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先生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77,大学梦圆,就不仅仅是“我们”的,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2018 年 6 月 1 日写于上海
2020 年 10 月修改
(原载 2018 年 12 月 24 日《解放日报》“朝花时文”公众号,并
获华东师范大学纪念 77、78 级校友入学 40 周年主题征文特等奖,有
删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