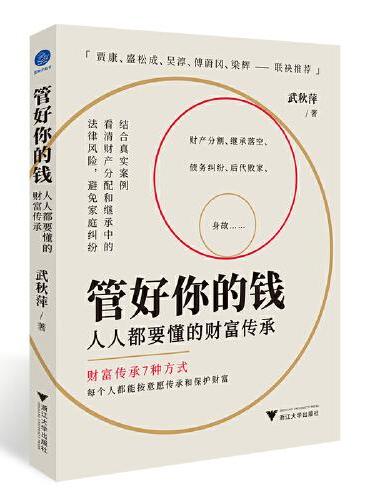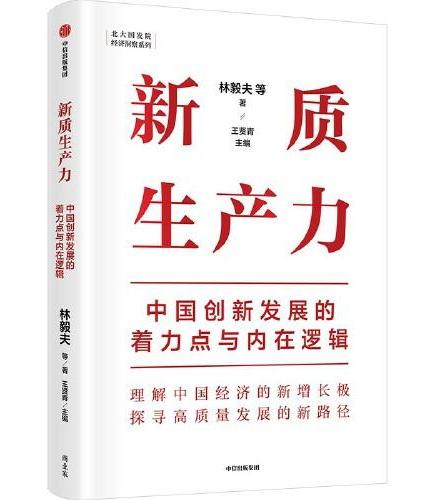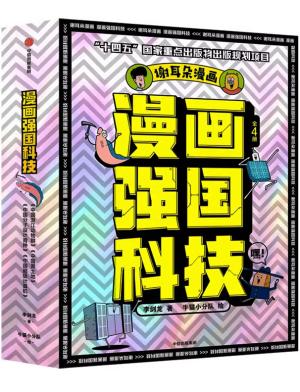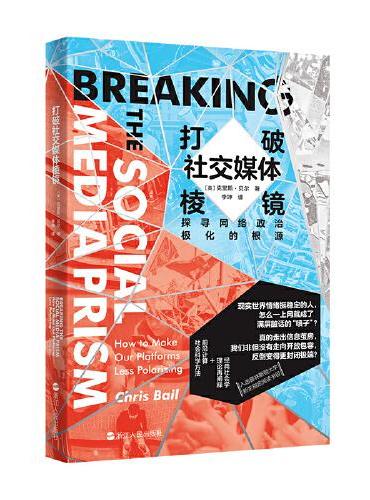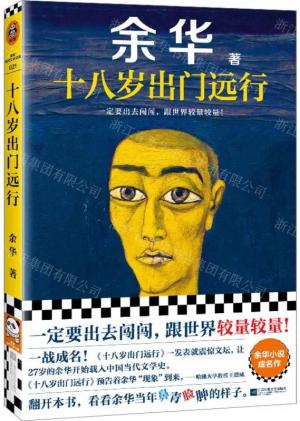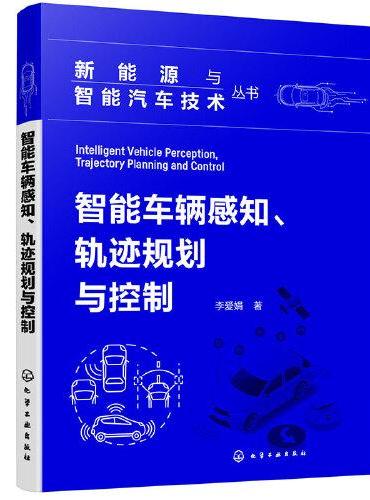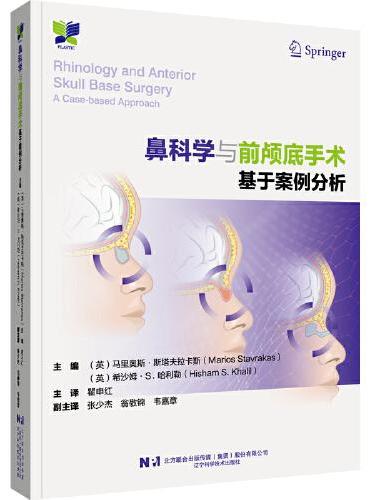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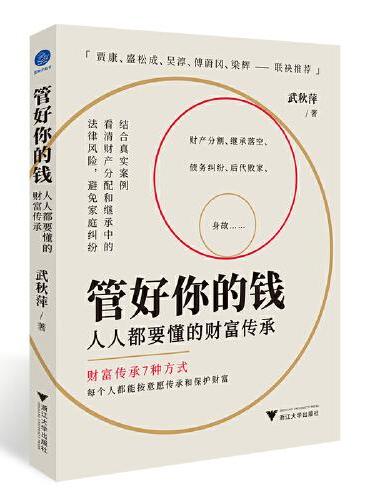
《
管好你的钱:人人都要懂的财富传承(一本书带你了解财富传承的7种方式)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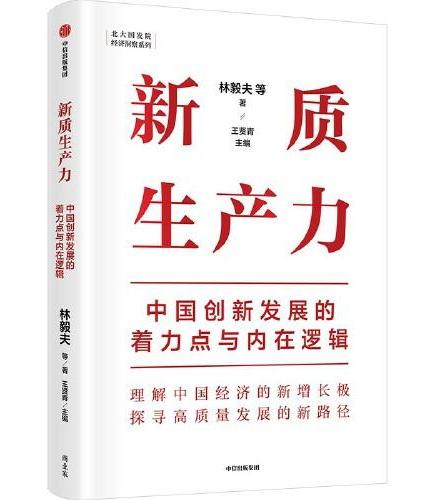
《
新质生产力:中国创新发展的着力点与内在逻辑
》
售價:NT$
4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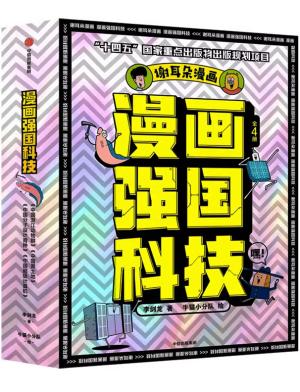
《
“漫画强国科技”系列(全4册)
》
售價:NT$
7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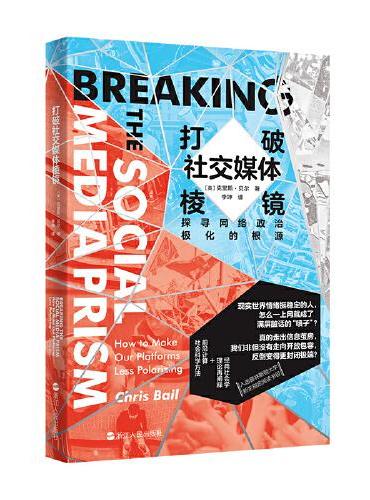
《
打破社交媒体棱镜:探寻网络政治极化的根源
》
售價:NT$
325.0

《
那一抹嫣红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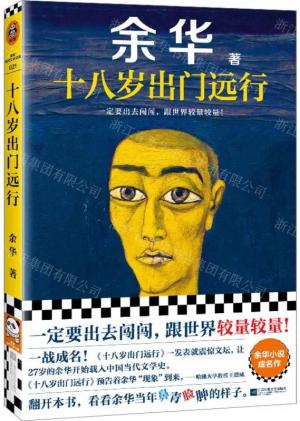
《
十八岁出门远行
》
售價:NT$
2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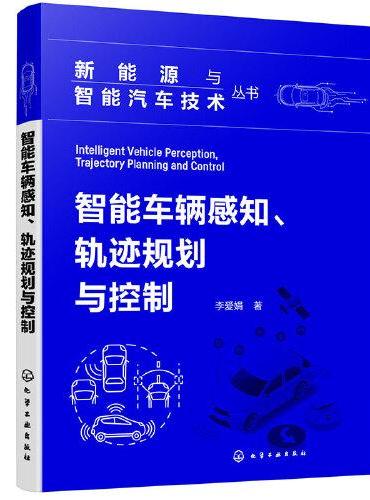
《
新能源与智能汽车技术丛书——智能车辆感知、轨迹规划与控制
》
售價:NT$
6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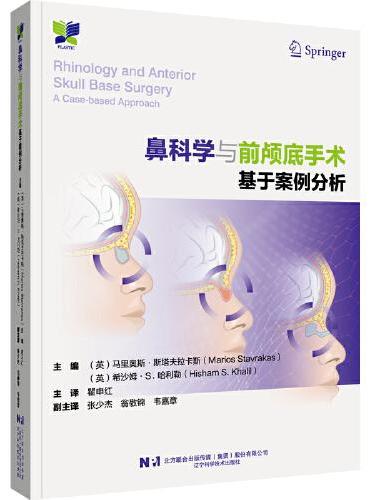
《
鼻科学与前颅底手术——基于案例分析
》
售價:NT$
1669.0
|
| 編輯推薦: |
恋人就是可以将几十年浓缩到一个下午的人。而人间那些夫妻,不过是将一个下午稀释成了几十年的人。
万事皆有理可循,唯爱情可以毫无道理。——杨典
|
| 內容簡介: |
《恋人与铁》收录了杨典39篇短篇小说,整体而言除了延续《恶魔师》《鹅笼记》的部分气息外,本书的写作倾向主要来自对生命流逝或爱的焦虑,以及探究什么才是文学“推动”的问题。
“恋人”通常指的是人性中的罗生门、棱镜或移动的变压器,这个概念是私人的、隐秘的,同时也是反抗的,是属于大历史的名词。万事皆有理可循,唯爱情(恋人及对恋人的幻想)可以毫无道理——无端的爱,先验的爱,隐秘的爱,变态、畸恋、恶趣、绝望与毁灭的爱,乃至不分男女、不分动植物与时空异化的爱。在智力游戏与纯叙事化小说甚嚣尘上的时代,“爱”是个已腐烂的字。
《恋人与铁》恰恰是为了能降解这种失败与误解。
|
| 關於作者: |
|
杨典(1972—),作家、古琴家、画家,代表作有小说集《恶魔师》《鹅笼记》《懒慢抄》《鬼斧集》;随笔集《随身卷子》《孤绝花》《琴殉》《肉体的文学史》;诗集《女史》《麻醉抄》等。
|
| 目錄:
|
序 盐与蜂的文学 ·001·
恋人与铁 ·001·
且介亭之花 ·003·
洗墙
——“且介亭之花”续编 ·008·
寒暄
——或“崭新的野蛮”(阴阳本) ·023·
草窗雨霁 ·029·
叛军时代的绣花针 ·048·
点心 ·069·
一 ·071·
筋斗云
——或“群魔的玩笑” ·073·
隐形 ·079·
一窝猩红的蛇 ·085·
停止简史 ·090·
圣兵解
——或“烧尾宴”中的《龙龛手镜》 ·096·
就义 ·117·
棍棒梦 ·120·
藩王的刺青 ·123·
单驮记 ·129·
坐腊 ·133·
巨匠(Demiurge) ·136·
中国斗笠 ·141·
敌人絮语
——十二世纪一位黑契丹军师的幻术、兵法、畸恋与哲学手稿 ·145·
狮子楼客话
——作为诡辩、色相与哲学困境下的“微狂人日记” ·163·
新笼中豹 ·181·
壁虎 ·187·
一点不斜去 ·189·
吾友拉迪盖 ·191·
冲刺 ·195·
焊枪 ·200·
谁是博物馆中的血腥少女? ·203·
肉嶲 ·210·
麻袋
——或“一个现实问题” ·213·
指南车上的崔豹 ·221·
倒影与狗 ·225·
快 ·229·
发小 ·230·
金叉 ·231·
澜 ·245·
狮吼九千赫 ·269·
切梦刀笔记(七十则) ·274·
一、髓焰之肉 ·274·
二、占婆图书馆 ·275·
三、哥德巴赫的飞翔姿势 ·275·
四、叱咤女首艳本 ·276·
五、独轮车之帆 ·276·
六、土耳其定向仪(突厥罗盘) ·277·
七、掌心雷 ·277·
八、切梦刀 ·278·
九、黑火 ·278·
十、青蚨与赵鹊 ·278·
十一、天厕之疑 ·279·
十二、机械女轱辘头 ·280·
十三、人肉炮弹与占星术 ·280·
十四、悲乔叶哭 ·281·
十五、煮宫 ·281·
十六、过庭鳅 ·282·
十七、毛发的数量 ·282·
十八、罗眄的事 ·282·
十九、筷子猪 ·283·
二十、人 ·283·
二十一、左臂 ·284·
二十二、肺鱼之象征 ·285·
二十三、鬼敲钟与郭子仪 ·285·
二十四、晋砖中的阿Q正史 ·286·
二十五、有物混成 ·287·
二十六、纸楼祭 ·288·
二十七、仙人弹琴 ·288·
二十八、Steam-punk话本人物造型 ·289·
二十九、罗袜 ·289·
三十、雨的朝代 ·289·
三十一、吞象奴 ·290·
三十二、阿拉伯移动光轨仪 ·290·
三十三、藏画与纳肝 ·290·
三十四、明月 ·293·
三十五、窄门、矮扉与悬关 ·293·
三十六、内经:宏大叙事小说 ·294·
三十七、名古屋泳骨 ·294·
三十八、衡功 ·294·
三十九、鸽叔 ·295·
四十、没踪迹处莫藏身 ·295·
四十一、镜卜 ·297·
四十二、选择派教义 ·297·
四十三、赤翼黑鳍 ·297·
四十四、鲁迅号导弹 ·298·
四十五、蛋糕的日子 ·298·
四十六、六维与机器 ·300·
四十七、螃蟹 ·301·
四十八、海豹 ·301·
四十九、霍屯督阴唇 ·301·
五十、瘿 ·302·
五十一、元儒 ·303·
五十二、黑能量 ·303·
五十三、云阶 ·304·
五十四、乳房缓刑 ·304·
五十五、秃顶 ·304·
五十六、火柴占 ·305·
五十七、蛇入后庭 ·305·
五十八、哑兔 ·305·
五十九、提头行者 ·305·
六十、巨型河童 ·306·
六十一、火地岛“女食” ·306·
六十二、撒尿庙(或江绍原爱经九种) ·306·
六十三、讲话 ·309·
六十四、王旷怀 ·309·
六十五、肩神 ·309·
六十六、肉胎 ·310·
六十七、雾大人 ·310·
六十八、独目小僧与食睛 ·311·
六十九、海粮记 ·312·
七十、阳明土 ·313·
|
| 內容試閱:
|
序
盐与蜂的文学
万家禁足期间,寂寞京城又下了雪。自凌晨至午后,鳞甲纷纷,江山尽瘦。已忘了这是今冬第几场雪了。寒气逼人下,潜心写作以御寒,自然又馋起酒来。可旋即便想起陆务观之句“中年畏病杯行浅,晚岁修真食禁多。谢客杜门殊省事,一盂香饭养天和”之类,倒句句都是过来人的话,只得写字佯醉而已。窗前静观鹅毛时,为聊补遗憾,便学乾坤一腐儒之穷酸,小赋半阕曰:“佚诗难觅追病国,馋酒不得赛相思。鹊剪寒林分疏密,雪掩群魅未舞时。”写旧诗,真算是没有用之事。恰若庄南华山木与鸣雁,普鲁斯特躲在家里叙述他那些隐秘的、本无人会关心的少女与韶光。文学或诗大概本来就是“没有用的”。就像这窗外要风景何用?房子够住就行了。爱情何用?能繁殖就行了。美食何用?能吃饱就行了。尊严何用?能活着就行了。可那种看上去没什么实际之用,而又从生命本身中静水流深,或剧烈迸发出来的东西,或许又是人所必需之物。
传说1187年,埃及苏丹萨拉丁在攻占十字军占据的耶路撒冷后,两边军队都死人无数,城市也千疮百孔,断壁残垣,只剩下一堆石头。人问萨拉丁,牺牲这么大,你要这么一座破城空城到底有什么用,有何价值?萨拉丁摊开双手笑道:“一文不值。”然后忽然又交叉双手道:“无价之宝。”耶路撒冷,便是文学。
据说,只有六十二岁的海明威曾拿着自己的一摞小说对人道:“什么文学,这就是一堆字而已,一堆字,对于真生活来说毫无意义。”然后放声大笑,走回屋里,用脚丫扳动了塞在嘴里的猎枪。鲨鱼与海没有消灭老人,巴黎的流动盛宴、两次飞机坠落、拳击、斗牛、乞力马扎罗雪山上的豹子或战场上的武器与丧钟,毫无功绩的前克格勃间谍身份等,也没有消灭这位故作强者的爱达荷州第五纵队“老兵油子”,他每天太阳照常升起,喝酒钓鱼。但终的才思枯竭、负伤引起性功能问题(有争议)、父亲的影响与晚年的疾病、电疗、抑郁症与记忆力衰退等,却提前要了他的命。他曾说过:“死在幸福之前光荣。”海明威生前早已闻名天下,荣誉、金钱与地位全都享有,可文学虽然对现实生活没意义,那没有文学的现实生活,却更没意义。幻想与健康,便是文学。
对太宰治而言,无数次地重复殉情于绝望,便是文学。
对川端康成而言,打开煤气阀后仍然沉默无语,不留一个字而去,便是文学。
对萨德而言,在监狱与大革命的封闭中,秘密地去虚构那些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其实根本无用的色情行为,便是文学。
对自幼与兄长一起抄遍中外群书的周知堂而言,“我一生著作不足挂齿,唯晚年所译之希腊对话录勉强可读”,这著作等身却又无牵挂之精神,便是文学。
宋人蔡绦《西清诗话》曾载杜少陵之言:“作诗用事,要如释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盐有用,水更有用,而那无用的,却不能单独拿出来的咸味,便是文学。
《景德传灯录》曾载神赞禅师,一日见其师于灯下读经,忽然有一只蜂急触窗纸,满室求飞,乃云:“世界如此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得。”又偈云:“空门不肯出,投窗也大痴。百年钻故纸,何日出头时?”此蜂、此驴、此钻,便是文学。
文学并不一定是已出版之书,更非文学之盛名。即便成王败寇论合理,也不能完全抵消心性之所求。文学对于爱文学者而言,只是某种与身俱存亡的本能,拿出来说,或一钱不值,放在心里则又瞬息万变。故见近日有人在谈什么“当代文学无革命”,还顺便把我也划到“文学革命”或“文学不革命”的任何范畴里,这都是错误的。我跟整体性写作倾向、代际划分、流派、风格或批评家们所设定的各种山头都毫无关系。我的写作纯属家教失误与个人行为:大多固执、渺小、独立地写了很多傲慢与荒唐的字,基本上又全是些偏见、恶趣与怪癖。我写的书都是些闲书,没什么用,故我是可以被大众忽略的,唯愿不会被大时间遗忘,就算万幸了。
不知不觉,又到今年新书付梓时刻。祖佛共杀,唯留天地敬畏;纵浪大化,仍须小心翼翼。文学上的道理也差不多吧,即凡事不做便都简单,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之。真做起来才知道前人之辛苦伟大处。人都有局限。即便不高山仰止,也会对创造者的某种困境、局限与不得已心领神会。
当代汉语写作,类型化的东西太多。现在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对那种智力游戏式的,靠机巧构思、科学幻想或错觉陷阱等编织的长短篇小说,皆驾轻就熟。譬如用量子力学来杜撰复杂的推理故事,用星际穿越来反观人类的渺小等。此类小说出现时也会引人入胜,因汉语此类作品过去不多。但不知为何,我总是觉得,这种对纯粹智力与技术的偏好终也不会太长久。当然,此类小说我也写,不过本质却有所不同。我相信,好的小说,除了智力与技术等之外,重要的还是作者骨子里必须要有一种元初的本能,一种不可抑止的叛逆劲头,一种从心中迸发出来的内在激情,才能真正抵达。生命状态不仅是文学护身符,我也视此为一切伟大文学之“推动”。若没这个东西,恐怕再聪明狡猾的写作,终仍会沦为机械的公式与麻木的叙述,化为某个时代语言形式的过眼烟云吧。
惭愧,我也并非想在此作什么“文学批评”。窃以为很多对当代汉语写作作批评者,也习惯性地喜欢指点江山。此历代通病,毋庸赘言。群体争鸣的意义再大,也会小于一部真正的好作品出现。四十年来,乃至一百多年来,此类泛泛之批评亦太多。而文学本是必须“小中见大”的私人心中的秘密宇宙观。我是那种相信用一本好书(包括闲书或未完成之书),就足可代表一个时代,乃至一种文化模式的人。文学本不需要搞成铺天盖地的社会思潮与普遍观点(当然,若实在有此嗜好,也有其自由,但并不是重要)。譬如,一本始终没有作者真相的《金瓶梅》,也可以代表明人写宋人,乃至写整个中国人之历史景观了。再譬如,若只能选一位二十世纪的西方作家,那卡夫卡便几乎可以代表整个二十世纪之作家。因他的作品(其日记书信也是小说)就是他这个人,而被他写到的那些小说人物倒是次要的。这并不是说,同代就没有别的伟大作家。二十世纪的好作家多如牛毛。但于文学性本身,则不需要拉大旗作虎皮式地全都罗列出来,所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否则加缪或马尔克斯也很好,索尔仁尼琴或科塔萨尔也可以,冯内古特、卡尔维诺或川端康成的掌小说当然无可挑剔,乔伊斯、赫胥黎、乔治·奥威尔、塞林格、舍伍德·安德森、贝克特、鲁尔福、纳博科夫、拉什迪、卡达莱、帕维奇、库切、聚斯金德或波拉尼奥等等也都叹为观止,那就没完没了了。各国文学都是群峰,而越全面,就越有明显的缺陷,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如从博尔赫斯到埃科的很多作品,在我看来也只能算是“第二经验”之写作。只有完全从个体冲决网罗而出之文学,因内心感受达到沸点而突然发明之文学,以及文学对个体生命之“无用性”,才接近我所认定的高度。那是根本恶的高度,怀疑一切的高度,平常心的高度,同时也是透彻爱、性、梦与死的高度。这就像恋人的痛苦作为现象很普遍,作为概念也人人都懂,但唯有每个人自己那些不可替代的,即纯粹属于私人恋爱经验里的痛苦,才是真实的。
文学必须是个人的,所以才会各有所好。简而言之:“文学就是我,我就是文学。”唯有个人才是包容的,集体则往往会是一致排外的。写作,无论颠覆传统与否,创新、解构或将某种观念推到极致与否,具有现代性或批判性与否,便一定要作用于社会与世界吗?就不能是冷僻的、私人的,甚至关于一颗被封闭之内心的反映吗?文学可以包括社会学,但不一定或根本就不是任何社会学。它们可能会同时存在,但互相之间又毫无关系。很多作家,生前何曾引起过什么社会思潮或集体效应?他们苟活于他们的时代表象下,本都是些毫无用处、潦倒、污名化,甚至是卑贱如尘土的边缘人。他们的写作完全是出自私人的嗜好,就像被语言霸占了血汗的赌徒。的确,写作就像宗教,或一场不切实际的奇异爱情,是一种成熟到已经不思悔改的赌博。输赢全无所谓了,只剩上瘾,且很难戒掉。文学家瘾发时无救,还会代入各种新发明的理由,他会破罐破摔,终变成一个败家子。
好的文学正是从这悲惨的失败、无奈的被忽略里才得来的。
这本小说集名为“恋人与铁”,乃因其中部分篇章,皆是以一位虚构(或以某个真人作镜像)的少女或恋人为符号而写。《说文》云:“孌,慕也。”即除了爱恋,还有景仰与羡慕之本义。恋,也许是某种难以言说的标准,即便是想象的标准。繁体的“孌”,从。在《说文》中,“”之本义为乱、治以及不绝等。故“恋”字足可以表达一种类似治乱交叠,起伏绵延的心情。《玉篇》云:“,理也。”可见混乱的内部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现代汉语的“恋人”一词其实来自日语。特意用了这个词,也是为了避免与诸如情人、爱人等在现代汉语中因诸多历史语境之多义性而产生的误读。因日本文学也尤其重视女性的意义。“恋人”作为一个隐喻,一个独立的修辞,过去也散见在我的很多作品中,无论诗还是小说。这并非仅仅是因我们八十年代都曾受到过罗兰·巴尔特《恋人絮语》、克尔凯郭尔《诱惑者日记》或谷崎润一郎《痴人之爱》等书的影响,更非因对张、胡、二周或喻血轮、姚灵犀等那一代作家的情感观有什么新的理解;也非如夏济安先生在日记中说的那样:“我对自然不大有兴趣,我认为除女人以外,没有美(Kierkegaard也有此感)。我要离脱了人世后,才会欣赏自然。我喜欢一个人住在荒山古庙里,这不是为了自然之美,而是对人生的反抗。在此世界上,只有女人是美的。”(见夏志清《鸡窗集·亡兄济安杂忆》)写作或有起因,但任何具象又都不是我写作的目的。因这恋人也不仅仅指女人(亦非任何性别),而是观念。我的“恋人”也可以是反抗人生或世界的。
写这本书纯是从我本身的观念出发而作的一种尝试。
记得早年次读中国伟大的那本堪称“恋人百科全书”即《石头记》时,我也完全不懂为何这样一本无聊、絮叨、脂粉气,靠摔盆砸碗、喝茶写诗、婆婆妈妈和唉声叹气的书,会被称为“中国古代小说成就”。三十岁以前都读不下去。四十岁以后才渐渐明白,所谓成就,并非红学或索隐派的论证史多么绵长,也不是脂本与其他诸版本等的差异,而大概是指中国人在这里,次有了“大旨谈情”的勇气。当年如果没有《石头记》,中国也照样是中国。事实上就算有了这本书,中国也还是中国,中国人也还是那副黑色的样子,永远也不会变。但正如白先勇先生所言:“一个人在读过《红楼梦》之后,他的人和世界就会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我觉得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之前数千年的经史子集里,都没有正式谈过爱的问题、恋人的问题。虽也有西厢牡丹桃花白蛇,老衲机锋,列女悲苦,但还只是“临去秋波那一转”,托志于幽魂而已。甚至有了《金瓶梅》那样伟大的“具有现代性的小说景观”,大胆地写了性与死,也仍缺了点什么。是作为“恋人”的小说人物贾宝玉的出场告诉了我们,原来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充满经学文字与训诂的准野蛮部落。原来我们不是只会帝王将相、打打杀杀、经学科举、仙山侠隐。原来我们也有爱,且可以是无端端的爱,先验的爱,隐秘的爱,变态、畸恋、恶趣、绝望与毁灭的爱,乃至不分男女,不分动植物与时空异化的爱。且中国人的爱、慕、恋、情、义等,也是一个连续性的,不一定会因情感关系结束便消失的情感逻辑关系。原来我们的文明与性欲并不只是为了一个只会传宗接代、繁殖仕途匹夫的酋长国;原来我们的生命中有权表达对这个荒谬世界的理解,有权相信梦、敬畏美,为青涩幼稚的爱情说话,怀念大于整个人生的青春,维护弱小者或恋人的尊严与自由,反对既定的秩序与假设的伦理社会体系,并有权选择对“无”的崇拜。原来“情不情”也可以是天经地义的。原来女性伟大。原来我们也是人。
前几年,我也是因此才写了《鹅笼记》里的那篇《沁芳闸》。
“恋人”通常是人性中的罗生门、棱镜或移动的变压器。正如爱从没有定义,甚至大部分时候是反的、偏的甚至恶的,故“恋人”这个概念在我的叙事中是私人的、隐秘的,同时也可以是反抗的,属于大历史的名词。人本是缺陷与遗憾的产物。只有在恋爱中的人,哪怕是虐恋或失恋,才能明确感受到这种与生俱来的缺陷与遗憾,并有效地反抗它的压迫。事实上历代有一大部分暴乱、政变、屠杀乃至革命的秘密,都不过是为了爱情,或消解爱情的失败。甚至很多哲学的出现,初也是哲学家为了给本人失败的爱情“复仇”,便寻求用理性战胜感性的宁静。因万事皆有理可循,唯爱情(恋人及对恋人的幻想)可以毫无道理。恋人是一枚不可理喻的反逻辑晶体。这也是性欲、革命与宗教都解决不了的。文学也是勉为其难,充其量只能算一种用来缓冲痛苦的替代品。
当然,写小说本就是一件自讨苦吃的事。
譬如,事实上历来就有相当一部分读者(甚至作家)都只看得懂,或只愿意去看得懂写写“现实”的作品。稍微超前或抽象一点,能量大一点,语言升级一点,就会被看作是制造“阅读障碍”或“不说人话”了。事实上写作的重要性,从来就不是看写作者能否熟练地表达现实或抽象、具体或荒诞、对爱与恨怎么看、通俗社会问题与晦涩历史观念如何运用到故事里、东西方语言传统功底是否扎实、形式结构是否足够先锋,以及作品是否进入了现代性等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文学主要就是看写作者自己是否有平地而起,凌空创造一种思维方式的勇气。文学可以独立存在,所谓“千载已还不必有知己”。中国的大多数问题,都出在是否能创造、能理解与能包容不同的思维方式上。而中国文学的阻力,恐怕也并非来自“大众不读书”,而恰恰是一般读者及自以为读过点儿书,其实早已被某种传统阅读习惯洗脑的各类人里。对文学广度与深度的认知全凭天赋。比作家的天赋更重要的,是读者的天赋。这个问题不是读书多少能决定的。好在我是那种敢于冒犯读者的写作者。说到底,几十年来,有没有读者都无所谓,何况还有一些。甚至对我的书全都是负面评论也没关系。负面也是一种对创造性发生的兴观群怨。文学若形不成某种悖论,也没意思。
再譬如,这个世界还需要长篇小说吗?不是我给大家泼冷水,长篇我也在写,也会出,但我真心觉得这世界大概已不需要长篇小说了。尤其是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很可能以后连中短篇小说都不需要。超短的笔记体,因与信息化同步,估计还能坚持一阵,看运气吧。埃科当年说得有理:即便对那些历史上的名著,以后的人也可能想要看故事梗概,或看缩写本就行了,不需要再看完整的作品。写得越厚,越是无用功,尤其汉语小说。对未来而言,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编织得再复杂,形式再奇异,实验性文本再先锋或再具颠覆性,本质也已无真正的创造性。越长往往就越显得土气老套,就像被注水稀释后的酒。长篇小说除非重新发明,否则长篇小说可以休矣。
好在《恋人与铁》仍是短篇集,且在短篇集里也只算是一本小书,很多篇幅很短。其中重要的篇章,大多来自今年上半年的写作,另有二三篇修订自过去从未出版过的旧稿。笔记体志怪“切梦刀”,则算是对《懒慢抄》的某种补充。整体而言,除了延续《恶魔师》《鹅笼记》的部分气息外,本书的写作倾向,主要还是来自对生命流逝或爱的焦虑,以及探究前文所说的,究竟什么才是文学“推动”的问题。我们这一代,从小也都受过某种“仇恨教育”,并在暴力、冷漠与麻木中成长。习惯了丛林的残酷与谋生的卑鄙之后,那陌生难学的东西,莫过于爱。中国人一般都不愿意承认,爱的艰难远胜于一切哲学或科学。即便承认,在文学里,也都喜欢运用现实主义的形式,譬如写写具体的婚姻、外遇、禁忌或滥情等。但爱(恋人哲学)却不一定是具体的。因爱会以其极度的快乐而抵达一种不快乐,就像教徒以宗教般的压抑抵达一种痛苦的狂喜。而且,这秘密的喜悦再波澜壮阔,也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不足为外人道。西诗所谓“苦难没有认清,爱也没有学成”。在现代生活中,“爱”字同时也代表着俗气与浅薄的表达。在智力游戏与纯叙事化小说甚嚣尘上的时代,“爱”是个已腐烂的字。只是每个人又都会不断遭遇爱或被爱的袭击,并常常惨遭失败。中国历代大多数现实的苦难、犯罪、沉冤、冲突与无奈,追根溯源也是来源于爱的失败及对爱的误解。只是因汉语传统从来就没有这个表达习惯,故只好用别的那些话语系统来诠释而已。写“恋人”也是为了能降解这种失败与误解。不过,无论我是假借眉间尺前传、且介亭、契丹军师、少年玄奘、棋手、拉迪盖、笼中豹、博物馆还是狮子楼,无论我写的是古代志怪还是现实记忆,这广义上的“恋人”之喻,都不该被任何概念所坐实。拟向即乖,这也是常识。人生在世,即便无写作、无解释,乃至没有一句话可说,也会有一种巨大之激情,如水中盐、窗内蜂,令每一位饮者自知,并从背后狠狠地推动着我们去感知存在与虚无的悖论,试图从蒙昧的窗纸中钻出去,哪怕是以头撞墙。不是吗?观念先行时,词语亦毁灭,是不是被称作“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2021年1月—6月
恋人与铁
我昔日的恋人生下了一块铁,巴掌大小,楚国为之震惊。①此事她也没告诉我。铁就放在她宫殿的门槛上。每一个进出之人,都能看见,且必须从铁上迈过去。铁没有父亲。铁是有形状的。我因无法私下与她谈论这一痛苦的形状,故只能公开变成快乐的话痨,或偶尔靠践踏山林,否定金属取乐。往事肥遁后,我与恋人已很久没说话了。恋人的沉默是正的,我的寂静则是反的。这沉默与寂静,就如把一双用脏的手套从里到外翻过来,形状不变,左右互换,也还能戴。现在的人,都厌倦了喧嚣。我记得前朝之猛士唐俟曾言:“我还期待着新的东西到来,无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无非是死的寂静。”那摆在门槛上的意外的铁,便算是新东西吗?喧嚣与寂静是一样的吗?这只有手套里的手清楚。
恋人太年轻了,必须蛮横无理。她与铁紧密相连。她青春的恶与美,常泥沙俱下,对我的抽打狠如壮丽的鞭刑,其实根本没法写。如今勉强能写,乃因我自己早已没有了青春。虽说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也算一种安慰,但较之我对她与铁的敬畏而言,仍是太难过、太抑郁,并隔着一层痛失寂寞后的大时间中的伤心。
写作只是为了聊胜于无铁,为了免于崩溃。
亡国弑君之前,我常听闻,恋人无事时,便会拿着那沉重的铁,四处向人展示它有伟大的锈、迷人的尖。她可以白天把铁吞进肚子里,午夜再吐出来。她可以当街用铁投掷她厌恶的人,非死即伤。只是她从不对我展示。独处时,她还会伸出少女的粉舌,尝一尝那铁。铁是甜的。一块残酷的硬糖。铁的出现,即便楚王也不理解。楚王从不知有我,正如我从不认为这人间有任何的王。恋人的沉默也是实心的无,高密度的无,因她从不解释为何自己会产下这门疯狂的玄学。作为她过去的一位秘密知己,我对铁的逻辑,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只是无法对恋人说。楚国就是个罐头,里面四分之三是肉馅,只有四分之一是空气,且是三十年前的空气。不对她说,尚有文学。若说了,不仅文学会消失,恐怕连恋人都看不见了。尽管玄铁后来会被玉玺、梦、冶金技术、铁屋建筑与武器等所霸占,足以倾倒天下,但我依然爱着这恋人的异化。出于对她与铁的尊重,我宁愿在这漆黑的罐头里像秒针一样疯狂旋转,令时间不增不减,始终都像初次见到她时那样。
那天,我戴着一副肮脏的手套,正在制造火,撰写一本传世韬略。可她忽然来了。刚看到她眼时,我便不禁暗自低头流泪。我可以为她去做一切荒谬的事、残忍的事甚至卑鄙的事。我根本不能理解我自己,故从头至尾与她说话时,都是冷冰冰的。
2021年4月
且介亭之花
她已很久没想起过那个留连鬓络腮胡须的中国人了。他现在胡子都该白了吧?对她的少女时代而言,那是一段充满歧视的偏见,是多年来被密封的壮烈遗憾。
十几年前,就坐在那间举世闻名却荒草萋萋的破亭子里,他便对她说过:“我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意思了,都麻木了。粮食、城市与猪也都是死的。”
她仰起头又问:“怎么会,爱情呢?”
“当然也是。”
“我倒不这么觉得。”
“你年轻。你是圈外人。”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
“你可以回家,可以继续写诗。”
“你呢?”
“我事太多,你就别费心了。”
“这算是你的决定了?”
“谈不上什么决定,我们从来也没真正在一起过。”
“可我刚才还挽着你的胳膊,在路上散步呢。”
“你多虑了,据我所知,这条街也是早就死了的。就算还有几个活人,恐怕也没有谁会注意我们的胳膊吧?”
中国人说着,低头看了看少女的手。她的手便握成了拳,像一头沮丧小鹿,离开了他胳膊修长的悬崖,朝衣袖的山洞中缩了回去。然后他又抬起头看了看这破败亭子的卯榫穹顶,以及挂在歪斜木柱上的斑驳对联。可对联写的什么,恐怕他一辈子也想不起来。
他只记得,且介亭漆黑瘦小,就立在马路边,像一个因多年站街而佝偻的苍老娼妓。取这样的亭名,大约也是因中国人都很熟悉吧。他们约到这里见面,本是想避嫌。按照目前整座城市的疯狂与危险,无论是兄妹、恋人或夫妻,都是不能见面的,也不必见面。他知道过去不过是一个时间圈套,是疯子手中的黄金,很难面对。一面对就成了此刻,过去就被熔断了,化了。唯有故意“不见面”和“近距离地回避”,可以勉强抵达这无限含蓄的深度。未来是肤浅的,只配拿来虚度;只有过去值得探索,而且深不见底,总是与此刻并行。况且恋人见面,都需要极其强大的、残忍的克制力。见面还会毁了没见面时的一切。搞不好见面之时,便是这整条街乃至城市被炸掉之时。好在且介亭是一座被忽略的废墟,除了附近腌臜的野猫与浑身污泥的流浪狗,谁也不会进来打扰这不得已的见面。
“你送我的那几本书怎么办?”她又问。
“可以转送给李元,或者你的什么同窗好友。”
“李元,你不是恨他吗?”
“哪有的事。”
“我记得你这么说过。”
“太准确的表达方式总会引起一些误读。友谊也是一种
误读。”
“那我们的那些信呢?”
“都烧掉吧。”
“烧?我舍不得。”
“又不是你的诗,有什么舍不得?”
“就是舍不得。不想。”
“你是想得太多了。身外之物。”
“但这次真的不想。”
“难道你还要把那些信随身携带吗?”
“也可以寄存在李元那里呀。”
“那更麻烦。谁知道那家伙会做出什么来。”
“你还是不信他。”
“他倒不足挂齿。信会毁了你。”
“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
“我可以把信寄回我老家去。”
“路上寄丢怎么办?现在发生什么都有可能。”
“真丢失了,不也正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中国人听到这里,倒也不知怎么回答了。他伸手看了看手表。
黄昏,一只翅膀被弹弓打残了的燕子,这时正好落在且介亭的匾额上扑腾。它好像把巢筑在了匾额的后面,隐约能听见群燕叽叽喳喳之声。
那些年,作为一位傲慢的、固执的少女,她始终在中国黑暗的地方为恋人写诗。她那尖尖的、小小的脑袋,不知道为何总是会模仿性地写出一些冷酷的大意象,如:“我尖锐的亲吻是粉色的装甲舰,闯入中国恋人腐烂的前额。”可惜,当年那位连鬓胡须尚黑的中国男子,暮气太重,从来都不读她的诗。她甚至都不能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恋人。在且介亭幽会,他们后的对话是那么平淡、无聊。他甚至还带着些微的不耐烦。为了掩饰这中国式的尴尬,她只好从兜里拿出一粒棕色发亮的硬糖,剥开印着中世纪蓝色云纹图案的糖纸,放到嘴里慢慢吮着。吃糖也是他们过去常在一起时的嗜好。他从不抽烟,此刻则时不时地拿出手帕来轻轻擤一下鼻涕,或擦一擦鬓角的细汗。少女知道,中国人根本没有感冒,不过就是想为这无言的恋人时光增加一些根本不值得怀念的动作。
直到后,当马路尽头已出现黑压压的人群与武器,他们才打起精神来。他握了握少女的手,示意她离开。情急之下他们有没有拥抱,对此两个人完全不记得了。
“那些人是冲你来的吗?”她着急地问。
“应该是。”他并不着急,似乎早已等得够了。
“那你快走吧。”
“我们朝相反方向走,分头离开。”
“再也见不到了吗?”
“不好说。”
“如果活着,你还会回家吗?”
“也不好说。你别去找我。”
“以后……我是说以后,我怎样做才能记得起你的脸?”
“也可以不记得。”
“怎么会?”
“不记得是好事。对我的记忆越多,你越危险。”
“以后什么都没了,总得有记忆吧?”
“记忆坏。你别自讨苦吃。”
“就算我记不得你,你也会记得我。”
“真是小孩子话。我一生孤苦,不需要记得任何人。”
“或许我对你不一样。”
“不一样?”
“我是对你全部记忆的否定。”
“你说什么?”
中国人刚有些诧异,可话音未落,写诗的少女便如一头洁白的幼兽般,伸出爪子忽然捧起他的脸,将口中的硬糖用柔软的舌头强行送到了他的嘴里,像是要以此堵住他想继续说的那句话。然后她便转身,冲着人群疾驰而去。她穿过肉墙的人群,并消失在肉墙里。中国人感到嘴唇有点发疼,像是被这幼兽猛地扑上来时的虎牙撞出了血。那粒泯灭在少女芳唾中的硬糖,此刻早被她舔得化了一半,棱角也变成了滋润的椭圆,唯滚烫、潮湿而甜丝丝的唾液能让他对她后那一滴凶猛的眼泪记忆犹新,如饮烧酒。
含着剩下的糖,中国人侧目看着街角人群。肉墙中有一个穿长衫的、皮肤白皙的腼腆后生,手里拿着一把他从未见过的手枪,还背着一根带紫檀鱼线轱辘与锡坠的钓鱼竿。后生朝中国人喊道:“嘿,我看你就别跑了。都这把年纪了,何必再折腾呢?”说着,便远远地朝他猛地抛来了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或许是且介亭前的落日太炫目,少女的糖还在嘴里,也令他走神,故他完全看不清那空中飞来的是一枚子弹,还是鱼竿上的锡坠。
2021年2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