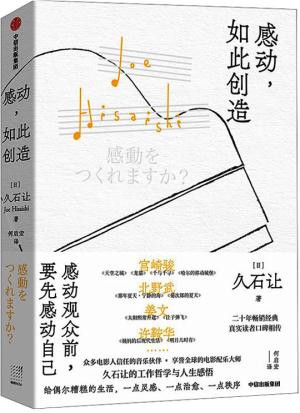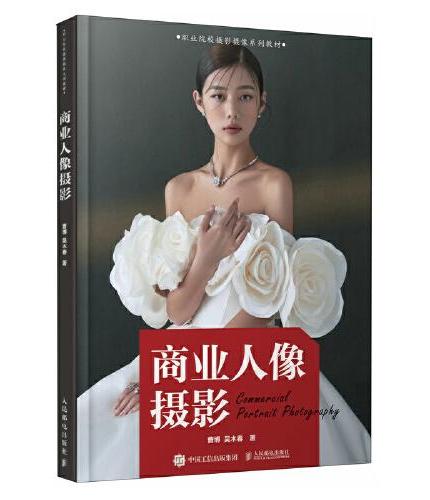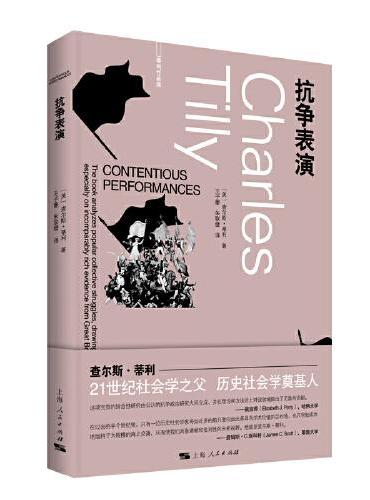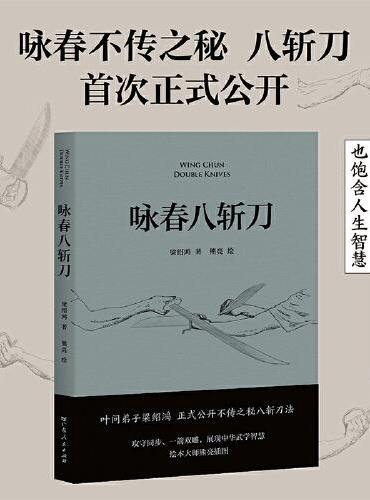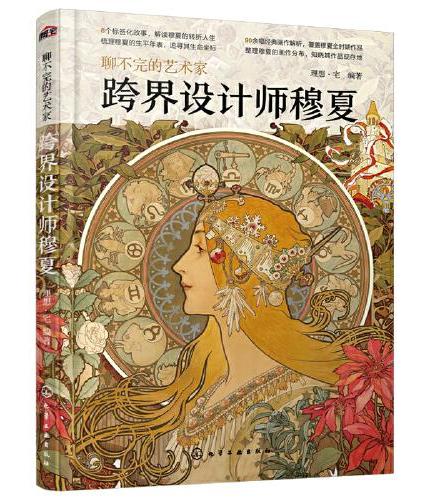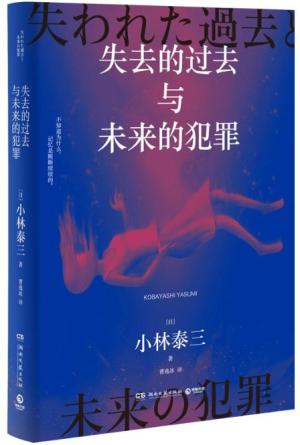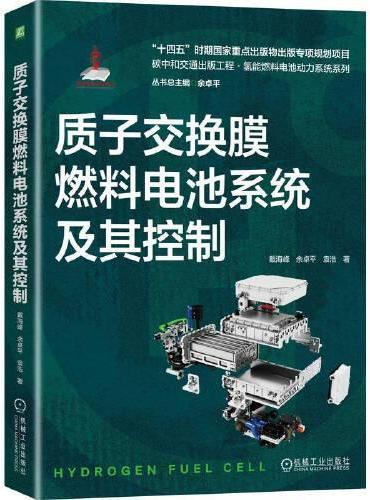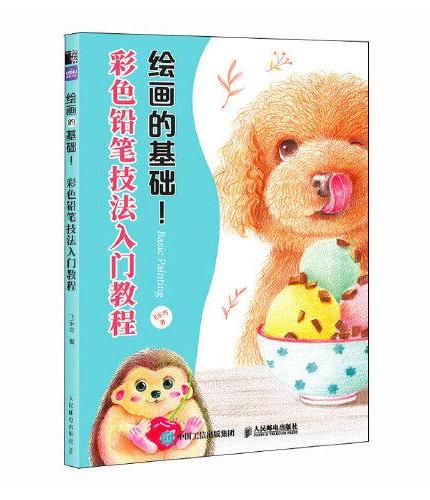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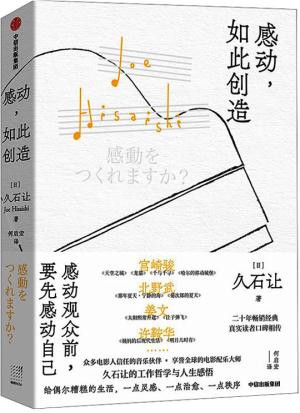
《
感动,如此创造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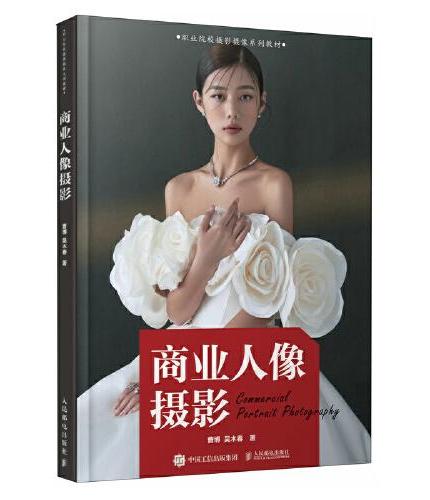
《
商业人像摄影
》
售價:NT$
4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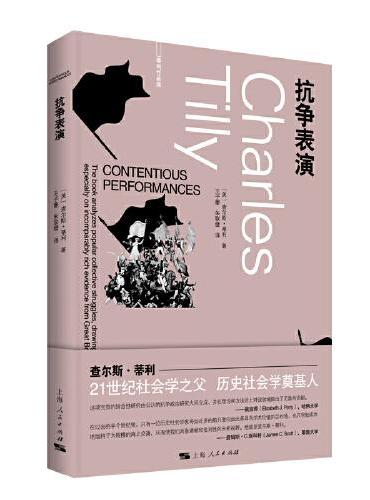
《
抗争表演
》
售價:NT$
3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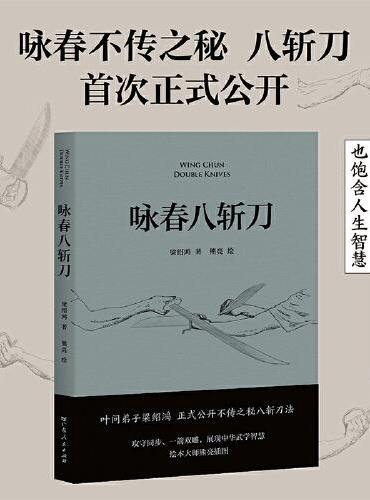
《
咏春八斩刀
》
售價:NT$
3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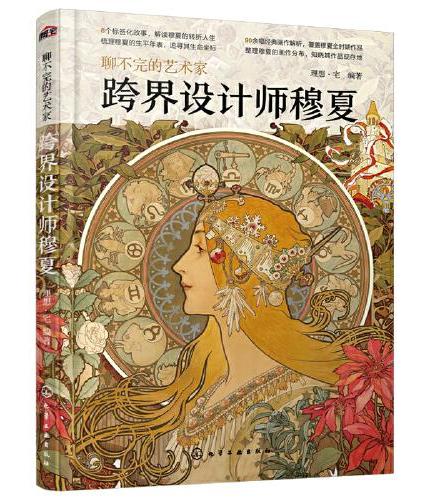
《
聊不完的艺术家:跨界设计师穆夏
》
售價:NT$
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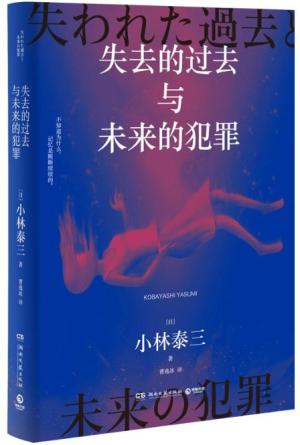
《
失去的过去与未来的犯罪
》
售價:NT$
2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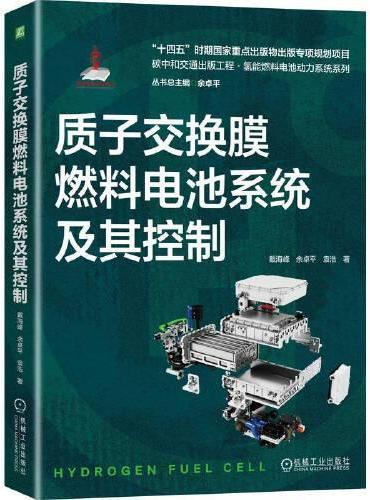
《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及其控制 戴海峰,余卓平,袁浩 著
》
售價:NT$
11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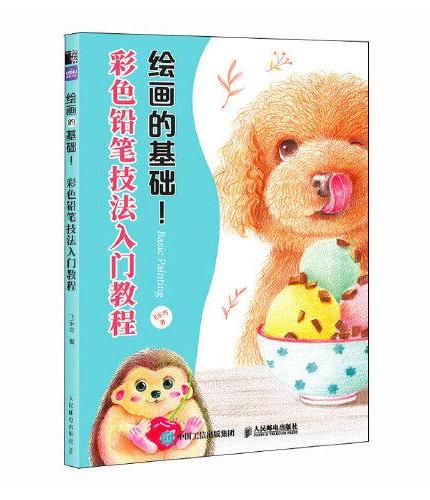
《
绘画的基础 彩色铅笔技法入门教程
》
售價:NT$
279.0
|
| 編輯推薦: |
1.典型类型小说,历史悬疑故事,多线叙事,情节环环相扣:小说以江湖逃亡和朝堂权谋两条主线并行,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使得故事充满了变数,精彩纷呈。
2.影视版权受多家影视公司看中,作品上市宣传期,可进行同步宣传。
3.小说将造纸、医药、雕版印刷、香绸扇等传统文化元素合理融入到人物和情节中,弘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展现了唐朝的文化生活:滇蜀风貌、江南风情、长江河畔,九个月的逃亡之路,踏遍九州风土人情;造纸、雕版印刷、医药、香绸扇,人间百工,继古开今。
4.一个造纸小匠人,把南衙北司搅了个遍,差点颠覆一个王朝。同类作品《长安十二时辰》《风起洛阳》《两京十五日》为市场证明该类题材的受众广泛,《长安纸墨录》同样从史料罅隙中,构建出一个遵从史实的历史悬疑故事,内容扎实,也将获得读者们的喜爱。
|
| 內容簡介: |
《长安纸墨录》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晚唐时期,泾县少年以宣纸洞悉惊天秘密,被迫参与皇权争夺的故事。
安史之乱后,唐盛极而衰,至文宗时,南衙北司之争愈演愈烈,江山、皇权岌岌可危。
太和九年,西南纸业联盟不堪刊印重负,大批造纸、印刷工匠北上,似有暴动之危。
以造纸天赋扬名万里的宣州少年沈元白,本是个知足享乐的逍遥公子,却因一个雕版而洞悉了动乱背后的秘密,亦招致京城内外各方觊觎,历尽几番生死。劫后余生的他发现自己注定要做大唐历史的中间物,而为了阻止朝廷出兵镇压匠人,血流漂杵,他毅然入局,却没想到,长安城终究掀起了腥风血雨……
|
| 關於作者: |
辛昕新,历史爱好者,尤以唐宋明三朝历史见长。
写过数篇中短篇小说,发表在《烧脑X》《脑洞W》《一本正经的脑洞名画》《超好看》《山海琳琅书》等合集中。
2021年创作长篇历史悬疑小说《长安纸墨录》。
|
| 目錄:
|
楔子
章 两个逃犯
第二章 冷雨与墨宝
第三章 纸铺初见
第四章 司马第
第五章 佳酿,琴音,过往
第六章 初九午时
第七章 书阁
第八章 横刀出鞘,无人生还
第九章 馆驿冲杀
第十章 故人重逢
第十一章 绮罗轩
第十二章 制扇者
第十三章 夜宴杀局
第十四章 默契
第十五章 十年前
第十六章 心思各异
第十七章 是故人,亦是敌人
第十八章 造纸
第十九章 暗流涌动
第二十章 劫杀
第二十一章 痛心疾首
第二十二章 节外生枝
第二十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十四章 生死难料
第二十五章 长安城
第二十六章 终究不是对手
第二十七章 谋事在人
第二十八章 石榴花开满城哀
尾声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章 两个逃犯
太和九年二月,长安,大理寺狱。
阳光透过狭小的囚窗斜射进来,浮动的尘埃在光束中清晰可见。
“喂,有人吗?”沈元白扒着牢门向外呼喊,“老孙,你死哪儿去了?”
老孙是狱卒,真实年纪不详,满头白发,一脸褶子,看起来非常苍老。沈元白刚被关进来的时候,大理寺狱没有这人,三天之后一名狱卒酒后猝死,老孙取代了他。据他自己说,他初是京兆府监牢的狱卒,有了儿子以后,想去更大的地方当差多挣些钱,就给时任御史台狱丞的同乡送了几坛子好酒,被调到了御史台监牢,大理寺狱缺人,他又求那个同乡从中斡旋,终如愿以偿地来到此处。可惜,大理寺狱和御史台监牢的月钱相差无几,他等于是白折腾了一场。
“喊什么啊?”老孙踏着满地水迹走过来,“都关三个月了,你就不能安分些吗?”
“老孙!”沈元白试图从牢门的空隙中探出头来,可惜太窄,他只塞进去半边脸,目光中满是兴奋,眉飞色舞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屁事儿没有,别瞎打听。”老孙并未直视他,转而进了他对面的一间空囚室,将里面的一套肮脏被褥叠了起来。
“不可能。”沈元白撇嘴道,“从日光射进来的角度判断,现在应该巳时末,快到午时。刚才有三个狱卒进来,挨个牢房送饭,还给了每人一壶酒。这是监牢,平日两餐都难以保证,今天中午却加了一顿,还给酒喝,这正常吗?三个月以来,除了我和对面那个人,囚犯里有谁喝过酒?更离奇的是,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了,要说全都喝醉,反正我是不信。你告诉我,是不是在酒里下毒了?”
老孙闻言身子一僵,深吸口气,放下手中的活儿,从那间囚室出来,站在了沈元白的面前,隔着牢门盯着他,冷声道:“这是什么地方?大理寺狱。关押的可不是普通人,除了京畿重犯,就是等候发落的朝廷官员。下毒?哼,你可真敢想啊!”
“那为何没我的份儿?”沈元白不依不饶。
“你的饭菜不一样,没那么快。”老孙转身欲走。
沈元白又道:“对面那人去哪儿了?”
“与你无关。”老孙从他视线中消失了。
沈元白气急败坏地猛踢了一下牢门,这一脚的力度不小,牢门完好无损,他却因为脚趾受创发出一声惨叫,然后瘫倒在地,用手揉着脚,阵阵剧痛令他不停地倒吸凉气。
对面囚室的那个人,是在沈元白入狱五天后关进来的,不知所犯何罪,平日沉默不语,不论沈元白用什么方式与其搭话,那人皆不回应。
正如老孙刚才所言,沈元白的饮食与别人不同,几乎每顿饭都有酒有肉。问其原因,老孙三缄其口,怎么都不说。起初他还害怕得要死,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了,便也吃了,吃了之后既没中毒也没有被拉出去处死,之后便习以为常。让他意外的是,对面那个男人吃的竟然与他一模一样。而现在,那个男人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四周的人又安静得像死了一样,怎么看都不太对劲儿。老孙的搪塞之语显然是在欲盖弥彰,这让沈元白更加确信,今日大理寺狱必然有事发生,而且一定不是好事。
这时,老孙又回来了,端着一盘美味佳肴,比沈元白平时吃的还要丰盛。他先将饭菜放到地上,掏出钥匙打开牢门,然后端起托盘走进来,放好之后才说:“你不是说有毒吗?尝尝便知。”
“老孙,咱俩交情可不错啊!”沈元白凑近,几乎与老孙贴在一起,“你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别跟我套近乎!”老孙一把推开他,翻了个白眼,“谁跟你有交情?你是囚犯,我是狱卒,这话要是让狱丞听到,还以为我是你同伙呢!”
“你个老不死的,忘恩负义。”沈元白没好气地说,“上个月你儿子生病,是我帮你找的大夫,现在病好了,全然不记得了?”
“你只说宣州泾县有个姓吴的女医或许可以医治我儿的病,既没带路,又未引荐,诊金也不是你出的,何以是你的功劳?”老孙转身往外走,在囚室外继续说,“那名医者确实厉害,价格公道,人也善良,是个好姑娘,但好像与你没什么关系吧?”
“怎么没关系?她是我……”沈元白脱口而出,意识到目前的处境不宜节外生枝,便将后边的话吞了回去。
“你夫人?”老孙斜睨着他,似笑非笑。
沈元白不予回答。
“我不信。”老孙鄙夷地望着他,“你这样的人,不说一事无成,肯定也不会干好事儿,怎么可能娶到那样的贤妻。”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沈元白不服气地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反正不是好人,好人怎会来这儿?”老孙笑了起来,但不是嘲笑,他的笑容温和且慈祥,像极了长辈在捉弄了孩子以后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开心。
“我是被冤枉的!”沈元白争辩道,“迟早真相大白,到时候你会知道我是……”
“行了,你快吃吧!”老孙打断了他,转过身说,“我走了。如无意外的话,你我就此别过,永远不会再见了。”
“永别?”沈元白惊恐地问,“什么意思?”
老孙没有回应,整理了一下衣衫,快步离去。
他听到了大门开启又关闭的声音,看来老孙是真的走了。
沈元白烦躁地在囚室中来回踱步,本来地方就不大,还摆着一些酒菜,不论他怎么走,都是绕着那个盛满佳肴的托盘。当然,他的视线始终没离开过那壶酒。
“再也不会见面?”他眉头紧蹙,嘀咕道,“你是狱卒,我是囚犯,为何不会再见?难道说,你我之间今天有人会死?”
一念及此,他的心突然紧张起来。
“不可能。”他摇了摇头,“已经关了三个月,要杀我也不用等到今天。”而后,他拿起那壶酒,稍加犹豫,还是倒在了碗里,“我不信你敢下毒。”由于手在颤抖,酒水洒出来不少。
他端起酒碗,一咬牙,猛地一饮而尽,可是还未等咽下去,目光瞥到了牢门,满口的酒全都喷了出来。并非察觉到酒有异常,而是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老孙出去后,并没有锁上牢门。
他的心跳骤然加快,仿佛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他很恐慌,同时又很兴奋,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三个月不见天日,又没有任何处置的结果,无休止的等待让他备受折磨,虽然还未曾绝望,但也知道被释放的可能微乎其微,毕竟背负的罪名太大了。可是现在,转机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对自由的渴望犹如洪水猛兽一般不断地冲击着他的心灵,使其不受控制地走过去,伸出手,抓住牢门……
然而,理智终占了上风,回过神来的他被吓了一跳,急忙缩回了手。
“不对劲。”沈元白眉头紧蹙,喃喃自语,“长安一共三座监牢,老孙都待过,显然不是疏忽之人,忘记锁门这种致命错误他绝不会犯。今天本就反常,他又来了这么一手,到底是何用意呢?”
他思索着,目光再次落到了那壶酒上,继而发出一声苦笑:“如果是陷阱,踏出牢门便是死路一条,如果酒里有毒,同样活不成,反正我是俎上鱼肉,想杀我易如反掌,那还不如来个痛快!”言罢,他一把抓起酒壶,这次连碗都不用了,仰头便往嘴里倒,一口气全喝光了。
一般来说,杀人基本只用烈性毒药,入口见效,迟不过一炷香的时间。
沈元白将酒壶摔碎,默默地等待着死神降临。
很快,他的表情开始扭曲,一副极其痛苦的样子,捂着腹部冲出了牢门,然后倒了下去,躺在地上不停地翻滚,咬牙切齿地喊道:“救命,有没有人啊?”
鸦雀无声,没有任何人回应他。
沈元白闭着眼睛聆听周围动静,确认真的没人,这才长吁口气,从地上站起来,表情与刚才截然不同,什么事都没有。酒里没毒,他之所以装出中毒的样子,只是为了走出牢门,看看外边有什么,如果是陷阱,他便可以用喝酒之后身体不适搪塞过去。从结果来看,他多虑了,甚至有些自欺欺人的意味。
他在狐疑中向牢狱的大门走去,沿途路过一些囚室,透过牢门向里面观望,发现此间关着的犯人已经睡着了。他又看了看另外几间,里边的情况皆是如此。
“原来如此。”沈元白恍然大悟,“他们的酒里确实有药,却非毒药,只是让他们睡觉而已。”
有人赶走了狱卒,迷晕了犯人,还让老孙不锁牢门,这是有意来救他。可是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来什么人会来救他,即便有,也不可能做到这个地步。那要多大的权力才可以?不过,联想到在狱中的特殊待遇,或许真的有个位高权重的人暗中庇护。
前方有一张木桌,上面摆着一盏油灯,火舌跳动,忽明忽暗。
在油灯的旁边,放着一件崭新的米白色圆领缺胯袍,还配了一顶极其常见的幞头,这是大唐庶民的常服。沈元白非常确定,这套袍冠是给他准备的,因为在折叠整齐的衣服上,放着一个只属于他的物件。
那是一个雕花白玉牌,雕的是兰花,白玉的品质一般,雕工也算不上精良,拿到典当行恐怕连一件衣服的钱都换不来。不过,对于此时的沈元白来说,这块失而复得的玉牌等同于一粒定心丸,让他那颗从走出牢门便一直悬着的心彻底落了地,因为真的有人在救他。
这块玉牌原本只有一半,现在却是完整无缺,用的还是嵌丝拼接工艺,修复的人技艺精湛,断痕被金丝覆盖,丝细如发,还用黄金加了个边框,应是出自将作监擅长金银玉器的大师之手。这说明,他入狱以后,朝廷里有位可以驱使大理寺狱卒和将作监的大人物见到了他的半块玉牌,此人的手里有他缺失的那半块,从而认定他是自己人。
沈元白只能想到这些,至于那人是谁,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一无所知,因为他所拥有的那半块玉牌,原本也不是他的。
沈元白换上新衣服,带好幞头,深呼吸几下镇定心神,然后拉开了牢狱的大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微胖的背影。
当眼睛完全适应了外边的光线后,沈元白看清了此人的衣着,丝绸很贵重,颜色与样式很像官服,只有帽子不太一样,以他的阅历不曾见过,但从其鬓白无须的特点来看,应该是内侍省的宦官。
“沈元白?”那人微微侧身,并未直视他。
沈元白木讷地点了点头。
那人不再多言,回身向前走去。
沈元白明白他的意思,紧紧跟在他的身后,不时左右观望,发现院子里竟然没有一兵一卒,那些看守大理寺狱的卫士全都消失了。看来之前的猜想没错,今日大理寺狱确实有事发生,而且与他有关。
很快,沈元白跟着宦官来到了前院。这边是大理寺臣僚办公的地方,偶尔有官员出入,宦官却像没看到一样,如入无人之境似的直奔衙署正门。沈元白头也不抬,恨不得贴在宦官身上。那些擦身而过的官员偶尔侧目相望,似乎有些好奇,但都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从大理寺出来,宦官继续向西走去,一直将沈元白带出了顺义门,彻底离开了衙署林立的皇城。繁华的长安街道让沈元白有种重返人间的感觉,他沐浴着正午的暖阳,感受着二月的春意,沉浸在自由带来的舒适与惬意之中,甚至忘了身边还有一个人。
那个宦官瞥了他一眼,而后将目光投向街上那些来往的行人,用不带任何温度的语气说:“仲夏之前回报结果,否者死路一条。”
沈元白怔住,下意识地反问:“什么结果?”
宦官没有回应,扔给他一袋钱,然后向停靠在街边的一辆朴素的马车走去。沈元白还要跟随,可是接钱的动作迟滞了他的行动,未等靠近,宦官已经上了车,车夫似已等候多时,待宦官上来后立刻驾车向北驶去,很快淹没于人流之中。
此人将沈元白从大理寺狱带出来,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便仓促离去,其用意为何,他暂时还搞不清楚。但不管怎么说,现在他已经脱离了囹圄桎梏,等回宣州见了雕花白玉牌的真正主人,所有疑问都将迎刃而解。
沈元白心情大好地沿着皇城边的街道向南走,刚过布政坊,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骚动,他远远地望着,原来是一队从北边来的金吾卫,那些人手持沈元白的画像,在各个坊门处排查询问。沈元白意识到情况不妙,急忙躲了起来。金吾卫没有得到结果,便四散而去。紧接着,长安、万年两县的捕贼吏也倾巢出动,他们查得更细,不仅联合坊内的武侯铺地毯式搜寻,还将抓捕告示贴得到处都是。
“什么情况?”沈元白既惊愕又困惑。
买通狱卒,撤走卫士,让宦官亲自引送,这位幕后之人必然手眼通天。可是,既然此人大费周章地把他救出来,又为何会放任金吾卫大张旗鼓地追捕?倘若他在长安被抓,之前所做的一切全都功亏一篑,如此致命的纰漏,老谋深算之人不可能想不到。所以,沈元白猜测,解救他的人与指派金吾卫抓捕的人,应该是两伙人。而且,金吾卫来得也太快了,这种速度,不说事先知情,至少在老孙离开以后便得到了消息。
想到老孙,沈元白竟有种陌生之感,越发觉得此人神秘莫测,老孙出现在大理寺狱的时机是他入狱三天后,从后那句“不会再见”可以断定,老孙是今日之事的知情者之一,这便产生了一种可能,老孙来大理寺狱乃是受人指使。不过,目前无法确定他真正效命于谁,也许只是听命一人,也许背后还有一人。
这些事从里到外透着古怪,却也由不得沈元白多想,箭已在弦上,若是此时被抓回去,他就再也别想出来了。的活路,只有逃出长安。
近的城门是西边的金光门,午时将至,西市坊门已开,中外商贩接踵入市,载着货物的牛车和骆驼挤满长街,人潮涌动,浩浩荡荡一眼看不到尽头,正是混入其中的大好时机。那个宦官选择这个时辰将他带出大理寺狱,或许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沈元白在衣着各异的人流中穿行,竟然真的避开了那些搜捕他的官差。前方不远便是逃出长安的城门,却也是一道不容易蒙混过去的关隘,因为之前那些金吾卫散去之后,并没有放弃追捕,而是分头去了各个城门,此处也不例外。
城中百姓排着长队出门,外面的人则排着长队进城,所有经过金光门的人都要经过卫士的查验。沈元白排在出城队伍的中段,门洞的墙上贴着抓捕他的告示,与之并列的还有一些别的逃犯,城门卫士的查验非常仔细,想从这边出去似乎不太可能。他回头往后方看了看,赫然发现长安县的捕贼吏正带人往这边来。这就非常难受了,前有拦截后有追兵,他要是贸然脱离出城队伍,便是不打自招,所以只能装出一副坦然自若的样子,跟随人流缓缓向前行进。
前边的行人经过查验没有异常,被卫士放出了城,轮到沈元白的时候,卫士看了一眼他那身崭新的缺胯袍,摆手示意他过去。沈元白大气都没敢喘,僵硬地笑了笑,然后快步往外走,可是没等走出几步,身后传来了卫士的惊疑,紧接着便是一声厉喝:“站住!”
沈元白神经一紧,脑海中瞬间闪过了无数可能。如果拔腿就跑,会怎样?卫士一定会骑马来追,跑不了,此乃下下策。当做没听见,坦然向前走呢?卫士还是会追过来。万一他喊的不是自己,站住岂不是做贼心虚?当然,胡思乱想并不能改变现状,城门卫士已经和捕贼吏汇合,从不同方向把他围住了。
终究还是功亏一篑,沈元白面如死灰。
就在这时,城门外尘土飞扬,一辆马车疯了似的向这边冲来,眨眼之时便到了近前,在城门下的人群里打了个转儿,不论是百姓还是卫士,全都为了躲避这突如其来的冲击而四散逃窜。不过,围着沈元白的这些人没有动,因为马车正好停在他们身前。
“什么人?”卫士和捕贼吏纷纷抽出腰刀,全神戒备地盯着驾驶马车的那个男人。
那人站起来,却没有下车,用尚未出鞘的横刀指了指那些海捕告示的其中一张,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那个是我。”
卫士侧目望去,确认此人身份之后脸色骤变,大声喊道:“此人是在逃钦犯,给我拿下!”
那人也不多言,抽刀应战。
此人武艺超群,一人战数人居然还占上风。
抓捕沈元白的人全都参入了战斗,他便趁机偷偷溜出了城门,然后不顾一切地往西跑去。大约跑出一里的路程,一个穿着男式翻领胡服、骑着驴的年轻女子与他擦肩而过,在他身侧勒住缰绳,毫不客气地问道:“喂,看到一辆发疯的马车没有?”
沈元白觉得此人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此时他没闲心思考这些,于是回身一指:“金光门。”
“胆子太大了,敢往长安跑,我看你这次怎么脱身。”女人也没道谢,气冲冲地追了过去。
金光门的战斗结果如何?那个驾车而来的男人究竟是谁?这个追赶的女人又是谁?这些都不在沈元白的考虑之内,他现在只想尽可能地离长安远一些。不过,他还是很感激那个男人的出现,若非此人公开闯门,这会儿他有五成几率被押回大理寺狱,另外五成是直接处死,不论哪一种,对他来说都是末日。所以他在夺路狂奔的同时,也在心中为那个男人暗暗祈祷,希望他能顺利逃脱。
夜幕深沉,一轮皓月在云层中若隐若现。
奔逃许久的沈元白终于在一片树林里停下脚步,他汗流浃背,精疲力尽,打算倚靠树干休息片刻,由于无力支撑滑落下去。他就这样瘫坐在树下,大口喘着粗气,直到体力稍微恢复一些,才重新站起来,在昏暗的光线下环视四周。
周遭尽是高耸的树影,一眼看不到头。
别说路了,连方向都分不清。
沈元白缓步前行,可惜没走多远又倒了下去。腹中饥饿尚能忍受,然而口渴却非意志力能够压制,从大理寺狱出来之前,他也只是喝了一壶酒,之后便滴水未进,长途奔袭这么久,不断流汗消耗了大量水分,让他极其虚弱。
这时,一个东西从树上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沈元白的身上。他被吓了一跳,抬头看了看,由于光线太暗,什么都没看到。他将视线移回到那个东西上,赫然发现,此物竟是一个羊皮水袋,他亟需补充水分,因此也顾不上是何处而来,拔开塞子便大口喝了起来。
“不怕有毒吗?”一个略带轻蔑的声音从树上传来。
“何人?”沈元白戒备地抬头观望,“不要装神弄鬼,有什么话下来说!”
树上的人跳了下来,轻盈的身姿宛如落叶。
来者穿着一身斜领素衫,外罩半臂长袍,一把黑鞘横刀被他环抱在胸前。沈元白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人正是之前驾车闯入金光门,间接救了他的那个逃犯。
沈元白好奇地问:“你究竟是谁?”
“陆珏。”那人微笑道,“与你一样,都是朝廷钦犯。”
“幸会。”沈元白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然后继续喝水,直到把水袋喝光,他才畅快地长吁口气,在一棵树下席地而坐,打了个哈欠,把空水袋扔回给那人,“多谢出手相救!”
陆珏单手接住水袋,真的一滴不剩,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而后走近些,似笑非笑地说:“这片林子有猛兽出没,你若夜宿于此,怕是要以肉身投馁虎。”
“既如此,你为何还来?”沈元白倚在树干上,为了使自己更舒服一些,他尽可能地倾斜身体,几近躺平。
“我能自保。”陆珏在他身侧坐下。
“那你顺便保一下我吧!”沈元白疲惫不堪,可是不想再逃了。
“可以。”陆珏微笑道,“但你要告诉我,你在大理寺狱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太正常的神秘人暗中见过你?”
“好几个呢!”沈元白闭着眼睛说,“有个年轻人,也就十几岁,身旁跟着一个看起来比他爹岁数还大的仆人。相较于年轻人而言,这位仆人展露出来的气势更像大官。”
“他问了你什么?”陆珏又道。
“与大理寺卿差不多,询问我杀人的原因和过程。”沈元白一声冷笑,“可惜啊,他们连那人是不是我杀的都没搞清楚,能问出什么来?”
“除了他们,还有什么人?”
沈元白道:“其余的人都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个一直没有让我看到正脸的人,他不问我杀人始末,只是让我……”
“为何不说了?”陆珏眉头微蹙,“让你干什么?”
沈元白缓缓坐直了身体,斜睨着他:“你不对劲!你我萍水相逢,何以对我在狱中所见如此在意?你到底是什么人?”
陆珏微怔,而后笑了起来:“不瞒你说,我是一个杀手,专门刺杀朝廷命官。去年我在长安当街刺杀弘文馆学士,不幸失手被擒,而后以一人之力逃出了大理寺狱,本以为我是越狱之人,没想到你一个文弱之人也跑了出来,这不合理,定然有人暗中相助,所以才会好奇地打听一下是谁在帮你。”
沈元白疑惑道:“你为何要刺杀官员?”
“行侠仗义。”陆珏道,“我杀的没有一个是好人。”
沈元白不太相信,却也没兴趣刨根问底。
“你呢?”陆珏又问。
“与你差不多。”沈元白淡淡地说,“我被抓,是因为杀了开州司马宋申锡。此人远离长安多年,你应该不曾听过。”
“此人官至尚书左丞、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年前被贬为开州司马。”陆珏一语道破,笑着说,“不过,我听说宋申锡乃是病死,何以是被你所杀?”
“你从哪儿听说的?”沈元白愕然。
“这不是秘密。”陆珏道,“因为他的病故,皇帝给了他儿子宋慎微一个县尉官职,两个月前便举家搬离了开州。”
沈元白大惊失色:“既然知道他是病死,为何还关着我?”他的这句质问没有目标,不知道是在问谁。
“虽然朝廷声称他是病死,却也未必可信。”陆珏斜睨着他,“你到底杀没杀他?”
“没有。”沈元白郑重地说,“宋申锡病逝那晚,开州司马第确实有人被杀,但不是宋申锡本人,而且也不是我干的。”
“你没杀人,更没杀宋申锡,却被以杀害宋申锡之罪关了起来,这件事怎么看都不太正常。”陆珏来了兴趣,“长夜漫漫,猛兽潜伏,你也别睡了,不如把开州的前因后果告诉我,如果你真是冤枉,我可以帮你。”
“你为何要帮我?”沈元白谨慎地问。
“行侠仗义。”陆珏脱口而出,“好人不该蒙受冤屈。”
“那行,你先给我找些吃的。”沈元白重新靠在树干上,“饿着肚子没力气说话。”
“荒山野岭我去哪里给你找吃的?”陆珏语带不悦,沉声威胁道,“我可是杀人如麻之人,你不要太得寸进尺!”
“陆兄,你是否太小瞧我了?”沈元白不以为然地笑着,“你以为我真的会相信‘行侠仗义’这种鬼话吗?我从金光门出来的时候,你还在与卫士打斗,我一刻未停地奔逃至此,你何以会事先等候?而且,你是在逃钦犯,没事儿去闯金光门,难道嫌命长吗?你对我在狱中见过何人非常在意,如今又询问开州一事,所以你不是偶然路过出手相救,乃是从一开始便冲我而来。我不管你效命于谁,找我有何目的,反正我光明坦荡,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可以说,但你不要把我看成好欺之人。”
“我虽是冲你而来,却也是行侠仗义,二者并不冲突。你身上发生的事如此怪异,莫非你不好奇?”陆珏并未动怒,“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你有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我们不妨拼凑一下,看看能否得出某种结果。既能满足我的好奇,又可以寻找为你脱罪的契机,互利互惠,何乐不为?”
“可以啊!”沈元白道,“先给我找些吃的。”
“我真不该救你。”陆珏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去寻找食物了。
这里是树林,以他的身手找些肉类并不难。
过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陆珏回来了,手里拎着一只野兔,皮毛和内脏已被去掉,似乎还用水清洗过。羊皮水袋也被他重新灌满,随意地扔给沈元白。
“你在哪儿灌的水?”沈元白诧异地问。
“三里之外有条小溪。”陆珏说着,点燃了一堆篝火。
“三里?”沈元白瞠目结舌,不禁赞叹道,“这么短的时间,不仅抓了只兔子,还往返了六里路,你这身手确实不错!不如这样,我给你钱,你一路把我护送回家,如何?”
“我拒绝。”陆珏捡起一根笔直的木棍,把兔子串起来,头也不抬地说,“如果你我目标一致,我自然会保护你。但是,你必须信任我。”
“那你必须让我信任。”沈元白道。
陆珏仅是淡然一笑,并未做出任何承诺。
然后,他把兔子架在火上烤,很快便冒出油来,香气扑鼻。
沈元白越发饥饿,不断吞咽口水。
陆珏往篝火里添了些木头:“还需再烤一会儿,你可以先说着。”
“不急,吃完再说。”沈元白直勾勾地盯着烤兔。
又过了一会儿,陆珏从树上摘下一片巴掌大的树叶,包着兔腿一把扯下,递给沈元白:“应该熟了,你尝尝。”
沈元白几乎是抢过去的,猛地咬了一大口,被烫得龇牙咧嘴倒抽凉气,仍然满嘴流油地说:“熟了,你也趁热吃。”
陆珏忍俊不禁:“你这样子,像极了饿死鬼投胎。”
沈元白没空说话。
不多时,那只兔子便被他吃没了一大半。
“别光吃,说话。”陆珏催促道。
“我是饿死鬼,你便是催命鬼。”沈元白拔出羊皮水袋的木塞子,猛灌了一口,舒爽地长吁口气,“你烤兔的手艺不错,只是兔肉本身未经腌制,少了一些滋味。回头你准备些油盐豉椒之类的东西带在身上,以后便可以烤得更好一些了。”
陆珏脸色铁青,目光阴冷得仿佛要杀人。
沈元白赫然一惊,急忙将视线移开。
烈焰熊熊,木柴被烧得噼啪作响。
“三个月前,山南西道连续下雨,道路泥泞……”
他望着那堆篝火,仿佛从火光中看到了一辆在暴雨中艰难行进的马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