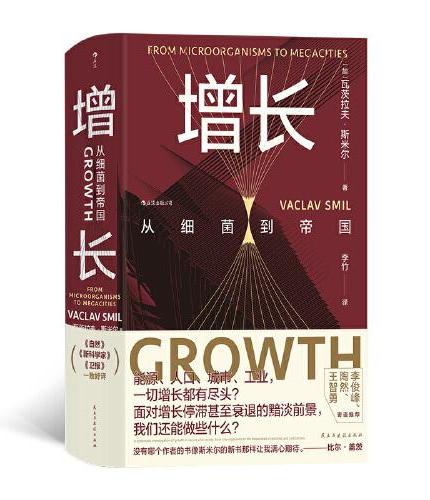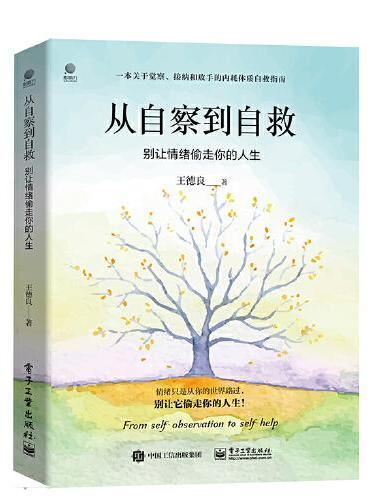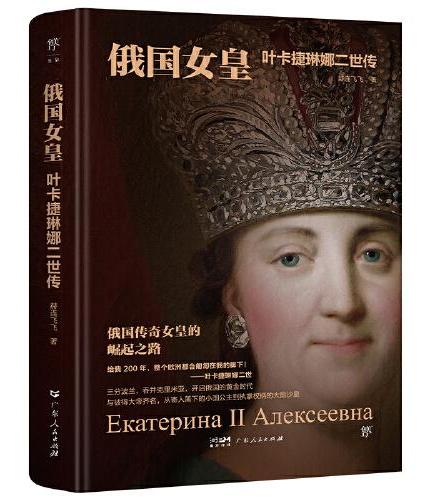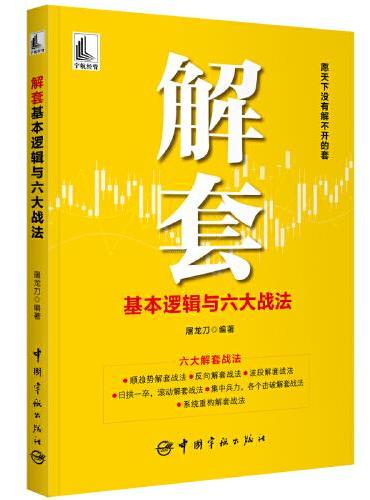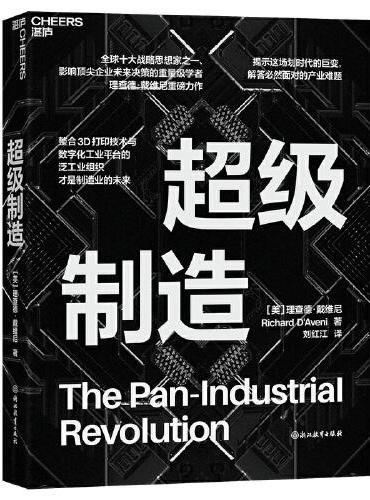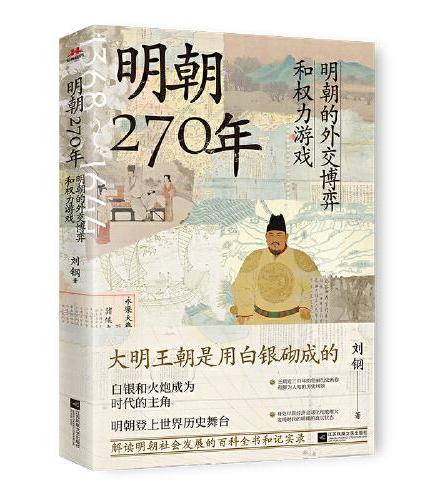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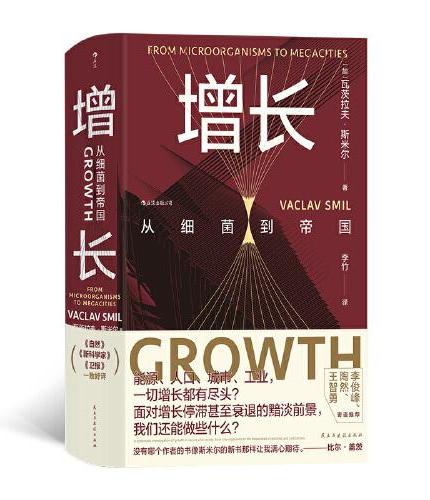
《
智慧宫丛书026·增长:从细菌到帝国
》
售價:NT$
8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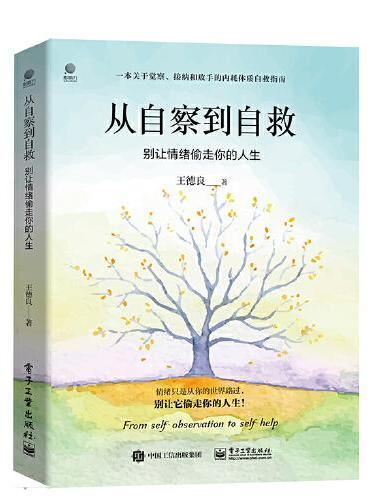
《
从自察到自救:别让情绪偷走你的人生
》
售價:NT$
420.0

《
晚明的崩溃:人心亡了,一切就都亡了!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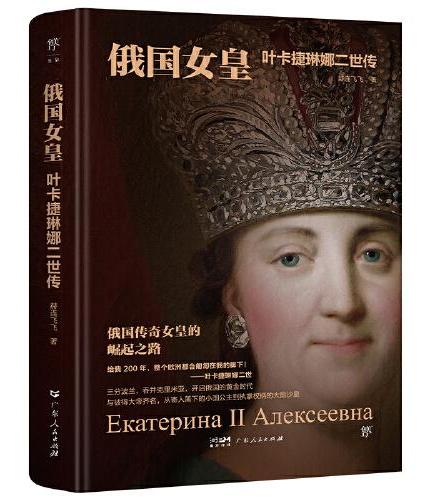
《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精装插图版)
》
售價:NT$
381.0

《
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
》
售價:NT$
2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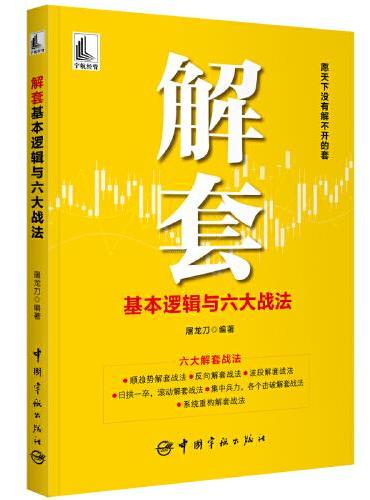
《
解套基本逻辑与六大战法
》
售價:NT$
2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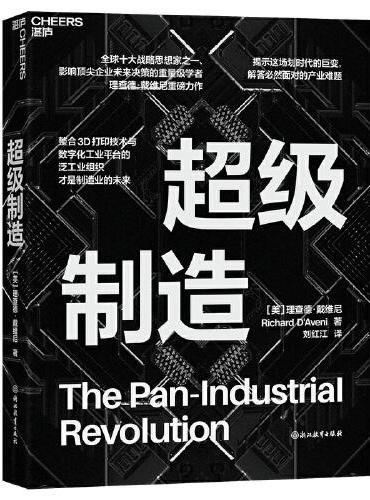
《
超级制造
》
售價:NT$
6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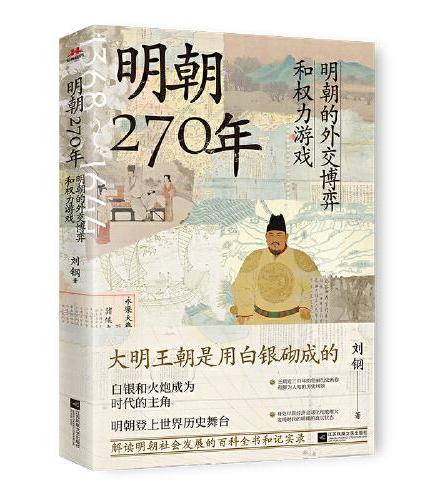
《
明朝270年:明朝的外交博弈和权力游戏
》
售價:NT$
325.0
|
| 編輯推薦: |
《徐坤文集》(八卷本)精选了当代著名作家徐坤进入文坛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野草根》四部、中篇小说集《热狗》、中短篇小说集《厨房》、散文随笔集《春上明月山》和文学评论集《双调夜行船》。这是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徐坤作品收集多、权威的选本,极富文学价值与出版价值。
徐坤是以女性作家与年轻学者的双重身份登上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其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是极具女性人文主义色彩的代表性和较强影响力的作家,也是安徽文艺出版社一直锁定的精品战略中的重要作家。其作品情感丰沛,收放自如,大气磅礴,接地气,语言幽默诙谐,部部精彩,堪称精品。
|
| 內容簡介: |
|
文学评论集《双调夜行船》,20世纪9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整体格局给女性写作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通过大量详尽的文本分析,本书探讨了以上诸种女性写作现象的背景渊源,并概括和梳理出女性写作在90年代的基本脉络走向和特点,是部系统论述20世纪90年代大陆女作家写作的论著。
|
| 關於作者: |
徐坤,女,1965年3月出生于沈阳。作家,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曾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主要从事小说、文学批评及舞台剧创作。已经发表各类文体作品500多万字。代表作有《八月狂想曲》《先锋》《厨房》《狗日的足球》《午夜广场后的探戈》《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等。话剧《性情男女》2006年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
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长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30 余次。长篇小说《野草根》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7年十大中文好书”。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韩、日、西班牙语。
|
| 目錄:
|
序 / 1
上部
双调夜行船
——90年代的女性写作
章 绪论:双调夜行船
——90年代的女性写作 /
一、尴尬与自由 /
二、断裂与接合 /
三、颠覆与皈依 /
第二章 母亲谱系的梳理与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 /
一、空白之页 /
二、玫瑰门——通向母亲之路 /
三、母性女儿 /
四、“纪实与虚构”的母性史 /
五、母性姐妹 /
第三章 女性私语与个性化写作 /
一、作为女性写作的一般性概念梳理 /
二、话语背景 /
三、传记与风俗 /
四、私人生活:女性内心生活与外在生存境况的断裂 /
五、智者心语 /
第四章 女人书写自己——身体的忧郁 /
一、身体叙事 /
二、一个人的战争 /
三、文本 /
四、从自慰自恋开始自我认知的女性躯体 /
五、飞翔 /
六、语言的再设 /
第五章 迷宫与镜像 /
一、人间遭际与梦中情怀 /
二、女巫咒语与迷宫逃离 /
三、宗教情境与女性密码妄猜 /
四、突围与困守或绝处逢生 /
第六章 孤独的叙说——女性个人与历史对话 /
一、长恨挽歌:一部“被叙述”的女性史 /
二、孤独行吟:山水寄情 /
三、家园回望:梦魇无皈 /
第七章 颠覆:作为一种文本策略 /
一、突围:作为一种表演 /
二、杀夫场景:恶之花的重现 /
三、牺牲与献祭:含情脉脉水悠悠 /
第八章:现实一种 /
一、穿越城市 /
二、异化与成长 /
第九章:男性视域下女性形象的默变 /
一、阉割恐惧与废置之野 /
二、并非纯粹感觉的抚摸 /
结语:从边缘到中心 /
下部
因为沉默太久
因为沉默太久
因为沉默太久 /
文学中的疯女人 /
英雄浴火重生
——当代女作家笔下男性形象的演变 /
在传统和现实之间
——20世纪60年代出生女作家的创作 /
堂吉诃德与莎乐美——女性文学中的“抹脖子”事件 /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女性主义美学原则 /
三八节有感
三八节有感 /
叛逆的骚扰 /
廊桥遗梦还是男权梦遗 /
20·30·40 /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
性别之累 /
知识女性:上下都很艰难 /
一间自己的屋子
一间自己的屋子 /
回家,回家,听鸟唱歌,同驴说话 /
抚摸的纯粹感觉 /
亮出你的肌肉块儿 /
缝纫机哪里去了 /
一唱三叹 /
女球迷 /
女足像条龙,男足像堆虫 /
两次演讲
鳄鱼与母老虎
——首届“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
当我们在谈论门罗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第二届“中国——西班牙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
|
| 內容試閱:
|
序
年轻时爱马致远的《双调夜行船·秋思》 :“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甫一开头,便如一壶醇酒,直直浇透胸臆。及至末段,“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更是令人击节赞叹,仿佛写的就是自古文人骚客应当过的一种生活。其实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活动半径没超出过校园,羞谈老庄,遑论儒佛,懂得什么兴亡之叹,又有过多少人生遭际呢?
某种无缘无故的喜欢就这样一直伴随着我,十几年的日月穿梭,导致我竟将自己的部文学评论著作也命名为《双调夜行船》,副题是“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由山西教育出版社于1999年3月出版。那时我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该书纳入杨匡汉先生主编的“九十年代文学观察丛书”之中。这是我的本,也是国内本研究九十年代女性主义文学的理论著作。丛书的作者还有楼肇明、陈晓明、李洁非、张志忠、王绯、周政保、贺桂梅等社科院文学所和北大中文系的批评家同人。那会儿,20世纪90年代还没有结束,新的21世纪如天际雷声还在遥远处轰鸣。批评家们先行了一步,开始总结旧世纪,迎接新千年。因为动手早,也因为这支队伍人员的权威性,这套丛书,后来成为新世纪的研究者们综述90年代文学现象时绕不过去的书。
写作这本书时,我的身份虽属社科院的青年学者,同时,却也正活跃在文坛上当一名青年女作家。因而,与丛书队伍中其他专家学者不同,我是属于双调、双重身份的“在场”写作:在着手创作时,心中暗藏着一层女性主义理论的指引;在进行批评时,又多了一层对于女性文学作品肌理、脉络的切肤体会和深切共鸣。至于“夜行船”,其形状跟当时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状态很贴切。那时候说起女性主义理论来还是闪闪烁烁,比较边缘化,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远没有登堂入室成为一门学科,国内除了北大教授戴锦华和孟悦等几个女学者曾经在80年代末时进行过理论引进和宣传之外,还没有人大张旗鼓为其正名,甚至一些女性作家书写私人生活的作品还被指斥为“准黄色”。形势看起来非常险峻。我的这本书,来得正当其时,是一本为女性作家作品“正名”之作。这也是本通过大量详尽的文本分析,来阐释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著作,诸如当时流行的女性身体写作、私人写作、杀夫情结、游戏与解构等等,都一一做了分析,梳理其产生的背景渊源,从理论上为其找到了创作依据。故而,这本贴近文本的批评,出版之后很受欢迎。尤其是新世纪到来以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几乎成为高校里的一门显学,女博士女硕士人数大量增多,来索书讨要资料的人源源不断,初印的几千本很快不够用了。紧接着就是看到孔夫子旧书网上的各种高价叫卖。
当这些后来的文学女英雄风起云涌掀起女性主义批评热潮时,我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生涯却已告一段落,新世纪的黎明业已降临,我的写作激情又疯狂转向创作中去了。
如今回想,二十多年前,纯粹由于职业使然,我随波逐流成为一个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始作俑者之一。今天,回过头去审视我们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其价值体系、文学审美谱系、躯体修辞学体系实际上充满矛盾困惑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它必须要颠覆和破开,确立自己的坚固理论平台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处于多变的不断发展的现实情境中,它又时刻想校正自己,达到跟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生活的和解,因而它自身总是处于不适和悖论中。我自己也同样受过蛊惑,女性主义理论一度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大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我写过一些比较好看的女性主义作品,像《厨房》《狗日的足球》等,同时也写过一些刻意的“女性主义”作品,类似于《相聚梁山泊》《爱人同志》之类,羞于提起。但是,也不要忘了,任何一种文学反抗和实践,一开始都是新鲜的、蓬勃的、有生机的,都必须给它时间,让它完成标榜和检验自己的过程,直至走完困顿和无望的全境,才能真正有效地验证出其价值,而不是要一味地硬性扼杀。
正如写作《影响的焦虑》和《西方正典》的美国批评家布鲁姆所说,类似女性主义批评、拉康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当代一些流行批评理论,难免要以颠覆以往的文学经典为代价,并特别重视社会文化问题。中国当代女性主义研究和写作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困境,当我们用十几年时间走完了步,也就是对传统的打碎和颠覆阶段以后,却不知道下面该怎么走,打碎以后,我们却并没有能力重建。所以,我自己努力不再为性别问题所扰,希望自己变回那个初出茅庐时的热情有理想的、满怀正义的文学青年,从《鸟粪》《白话》《先锋》那种高难度的歌唱开始,绕过《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午夜广场后的探戈》的低回婉转,重新走回了《野草根》的关注底层苦难与《八月狂想曲》的标高炫技的意气风发正路,关注现实,回归经典,回归正统的文化价值观。
借本书重新出版之机,特在书后附录笔者近些年来发表在报章杂志上的零散短评与随笔,皆与女性主义有关,以记录二十年来身为女性作家与研究者所走过的心路历程,亦为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普及立此存照。
“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生如白驹过隙,沧海桑田,如今再读这些词句,已能满满地品出其中味了。
是以为序。
徐坤
2021年3月21日于北京以北
章 绪论:双调夜行船
——90年代的女性写作
毋庸讳言,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突出的文学现象之一,就是“女性写作”命名的突起。笔者指的是对这样一种现象的“命名”,而非女性作家的写作本身。因为女性作家并非从90年代才开始写作,历史上自从有了文学这门关于语言文字的艺术那天起,女性就已投身其中,为建立这门艺术的规范而效力,并已取得骄人的成绩。只是,一部男权文明史极力将她们排斥于历史之外,轻描淡写,使她们在历史的景框上淡出。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在以往的文学史中,一直被归在其他诸种文学潮流之下予以论述,因而它的特殊部分,它对一部公有的男性文明的别一份性别体验就被压抑在历史地表之下,不得尽情凸显。实际上在各个历史阶段,在各种文学态势中,女性都以她们卓越的艺术才华和深刻的思想而走在时代创作的前列,独领一代风骚。仅就20世纪的小说领域而言,从老一代的冰心、丁玲、卢隐、萧红、张爱玲起,到中年的张洁、谌容、宗璞,再到青年的王安忆、铁凝、刘索拉、残雪、池莉、蒋子丹、徐小斌、毕淑敏、张欣及至更年轻的迟子建、陈染、林白、海男等不可尽数的女作家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绩表明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同样具有卓尔不群的力度,并且在某些关于人性本质描写的优美细腻方面令男性作家稍逊一筹。只是,没人愿意就她们的性别为“女”而发表看法,她们迫于外在的文化压力以及内在的文化忧惧,或许也以被当成无性别或准男性的“中性”作家解析而引以为荣。
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以来,情形有了微妙变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国的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有了更深一层的自觉。女作家们对自己的“女性”不再采取回护姿态,无论是在写作观念上,还是更深一层的艺术处理上,较以前都有了显著变化。女作家们以女性视角直面人生的书写更有力度,直抒胸臆时更加直白大胆,对商业化社会“游戏规则”的把握也更有穿透力;女性个人与历史对话的姿态更加孤独也更为执着;商业视阈下的女性写作有了更为自由广阔的空间;一些女作家则将女性的性别体验以一种执拗的“私语”化方式描绘出来,渐渐形成一股新的女性写作态势。这些,都构成了对90年代女性写作加以专题研究的基点。
女性写作在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已成为一道颇为亮丽的景观。它的深度理论根源承系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而它的高潮迸发却是借于90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的召开。90年代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整体格局,也给女性写作提供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女性之私与个性化写作,女性躯体对于反抗男权文明的执着与迷失、细语与呼喊,空白之页上一部女性史的开掘,女性对于商业化社会中男权游戏规则的颠覆与反判……这一切都使得90年代的女性写作变得迷乱而纷杂。本书旨在通过大量详尽的文本分析,探讨女性写作的实践意义,并概括和梳理出诸种现象表层之后的背景渊源及女性写作在90年代的基本脉络走向和特点。
一、尴尬与自由
要想给女性主义及女性写作下一个明确和完整的定义极其困难,几乎在每一次有关女性问题的研讨会上都能看到对这个问题的无休无止的争讨,后结果往往是以各说各话而告终。女智者们在面临“主义”这一重大历史命题时往往不能够达成共识,这与几十年来女权主义在西方的普遍境遇很有些相似。按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女性主义”是永远不能够下定义的,一旦定义以后,它便失去了意义。不可言说的言说,必然紧跟着歧义、歪曲、误读和误解。要给女性的写作实践“下定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女性写作“这种实践永远不可能被理论化、被封闭起来、被规范化——而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然而它总会胜过那种控制调节菲勒斯中心体系的话语。它正在而且还将在那些从属于哲学理论统治之外的领域中产生。它将只能由潜意识行为的破坏者来构思,由任何权威都无法制伏的边缘人物来构思。”理论的模糊和不可言说一方面给创作带来无法遏制的混乱和犹疑,另一方面,却也正好给创作实践提供了程度的自由。有多少个女性,便会有多少种关于女性写作的解说,便会有多少种关于女性作品的实际创作。若将“女性写作”简单地定义为凡是性别为“女”的女性自然人的写作,那么,女性写作“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实践”的意义也就无从凸显,它就仍将遮蔽于菲勒斯机制观念传统之下,关于它的种种批评分析就会容易堕入既定的男权话语里,其反叛意义及性别特质也就无形之中遭到忽略。如若我们再简单地强调其“性别立场”,将“女性写作”限定为只是“女”性作者书写其与外部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相疏离的一己之私生活,那么整个当代文学史上能够提供给我们解析的女性作品少而又少,或许只有90年代的部分女性私小说才能进入这个批评视域,而绝大多数女性作家的作品就要被排斥在“女性写作”的范畴之外,这样一来就如例行的男权文化当道一样,女性主义批评者也有陷入女性“性别本质主义”的危险。
并且,由此所言的“女性立场”也大可值得怀疑。当整个社会的价值坐标和审美体系都是一个,或说是千百年来由男权所规定的那一个时,属于女性自己的这一个话语规范又如何确立?或者,它只是一个大系统中的子目录?如此,它相对于“总目录”的意义又何在?当女性没有建立起来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实际上也不可能独立于社会整体价值形态之外去另立)时,那么,她的话语形态,她的思考方式,都是借助于男权既已定好的那些规范,多是在其中以不再对性别回护的姿态和眼光进行与他们同样的思考。当哲学命题一样,生存困境一样,是非道德标准一样,宗教情境、幽闭途径,及其肉身厌世自我割裂撕碎的方式都没有什么超出“被允许”的程度之外时,女性的“自视”实际上仍旧等同于“他窥”,女性的“自我”实际上还是“他我”。女性陷进了自我设计的思维之障。究其根本原因,是女人没有自己的语言。而人类,正是借着语言来进行思考的。
这就是女性在男权统治中的文化宿命。要突破这种两难的文化处境,就必须找到女人表达自己的语言,从而加速建立起女性自己的诗学。
因此,在考察女性写作实践时,强调其“文化立场”而非“性别立场”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文化立场”的女性主义,“是以女性的独特体验、独特视点去反观男权文化”戴锦华:《女性主义是什么》,《北京青年报》,1996年1 月16日。。它期冀着在一系列的女性话语的颠覆、反抗过程中,赢得女性在历史中言说的权利,建立起平等的男女文化关系,进而建构女性主义自己的诗学规范。不管是在既定的男权话语内部,还是游离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之处,女性或不惮于冒对整个菲勒斯机制忤逆的危险,从文字的游戏和喧哗之中呈现自己的精神反叛,或踽踽独行,于无声处书写沉默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所有这些或许都不失为一种机智的女性文化策略,所有的书写文本或许都不失为是“女性”的。
在对于“女性写作”的认定上,笔者赞同女性主义批评家戴锦华教授的观点,她认为在女性写作当中,“实践”的意义尤为重要,她说:“我自己不太喜欢用‘女性文学’‘女性诗歌’这样的字眼……我自己更喜欢用‘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来谈所有关于女性的文化事件、文学事件。在女性写作中,我非常强调实践的意义。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作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涵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女性写作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特殊的可以进行界定的文学现象。”暂且,在我们所处的90年代的当下,在它所被认定和接纳的初期,“女性写作”在中国的文学发展史上还不失为一个“事件”,一个重要的或者还蔚为壮观的“事件”。显在的事实是,女性的自我性别意识一经确立后,其文化地位便有了与以往大不相同的改观。性别之于女性书写者来说,可能会是一把双刃匕首,它可以合理运用成为一种文化身份上的“僭越”,同时又是其攻守进退时的护身甲胄。无论是在性/政治的颠覆策略上,还是女性性别书写/文化反叛的格局中,抑或是在迷宫/镜像的反讽架构上,女性文本以其美学及其诗意上的巨大而鲜明的隐喻性,能动地穿透了当下的生活,仿佛是在明处,又仿佛是在暗中,在90年代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形成一幅“双调夜行船”的迷人图景。女性文本既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又在人们的言说之外,破译或说解这份图景,既是“我们”的一份自由自愿,间或又是“我们”的一种责无旁贷。
二、断裂与接合
1995年在中国女性的记忆中应该永远被记取。1995年既是中国女性写作的狂欢之年,同时也是反思之年。本年度,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北京隆重召开。借此春风吹助,中国女性与世界各国妇女姐妹联手,在亿万世人瞩目之下经历了一次的女性集体狂欢,中国的女性写作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体验。1995年的中国女性创作、研究和女性作品出版真可谓异彩纷呈、热闹非凡。各种专题妇女国际研讨会不断举行,女作家个人作品的研讨会接连召开,文学期刊上陆续推出女性文学创作专号,论述女性写作的学术著作竞相在这一年出版,女作家文集、丛书一批又一批大规模集束性问世,女性生活大众性读物成批涌现……所有这一切,似乎标示着一个空前喧闹、纷繁的女性写作新时代的到来。
回溯之一:女性主义代表作异彩纷呈。本年度对女性文学创作影响的事件就是四套女性文学丛书的出版。按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辣椒文丛”,主编陈骏涛,内收有斯妤、蒋子丹、唐敏等非常有创作实力的女作家的代表作;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的“风头正健才女书”丛书,主编陈晓明、王朔,内收有王安忆、徐小斌、林白、张欣等七人的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红罂粟”丛书,主编王蒙,这是一套规模、收得齐全的丛书,共收入了全国二十二位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女作家,从陈祖芬、叶文玲到池莉、迟子建等的小说集;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她们文学丛书”,主编程志方、刘存沛,内收有海男、陈染、林白、赵玫等十二人的作品。
这四套丛书的共同特点:主编挂帅者均为男性。
河北教育出版社在推出“红罂粟”丛书的同时,又推出了“蓝袜子”外国女作家丛书以及“金蜘蛛”海外华人女作家丛书,每套丛书都有二十本左右。与此同时,各文学期刊也借此机会纷纷推出女性文学创作专号,影响较大的有:中国作家协会所属机关刊物《中国作家》和《人民文学》杂志,分别在9月份世妇会召开之际推出女作家作品专号;甘肃省的《飞天》与云南的《大家》杂志也分别于世妇会召开前期
刊出女作家专号;北京作协的机关刊物《北京文学》也刊出海外华人女作家散文专号。
同年,女性大众文化杂志热销。冠以“女性”名称的通俗读物在街头巷尾的书摊上到处都可以见到。陕西的《女友》杂志与北京的《女性研究》杂志,都以其文化品位高、视角新颖而赢得众多读者,在销售量上名列各女性杂志榜首。此前,中国的文学刊物,尤其是正宗的纯文学刊物几乎很少为女性专门出一个特刊,出版社也很少会如此大规模集束性推出女性文学作品,除了一些纯粹为商业设计的时装、发型、汽车、挂历等品种的杂志常拿女性做装饰外,很难看见有谁会将“女性”这一话语作为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提出。此次人们对于女性问题关注热情之高,有史以来十分罕见。“阴盛阳衰”一时成为文化界纷纷议论的话题。
回溯之二:女性研究方兴未艾。遮蔽于阳刚历史之下的女性写作得到挖掘和整理。与女性文学创作丛书风起云涌大规模面世相伴的,是有关女性写作研究专著的积极出版以及各种旗号下的女性写作研讨会的召开。中国直到80年代中后期,才有学者率先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运用于批论中国的女性文学实践。先期的女性主义文学评论著作有:李小江的《女性审美意识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它们在将西方理论与国内实践结合方面具有成功的示范意义。但当时这种文学批评方法并没有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和反响。直至1995年,女性写作业已成为一种大趋势时,几位女学者的率先垂范意义才得以真正凸显。从京城到外省,许多此专题的学术研究著作都在这一年里如雨后春笋般大量问世,其中可以做出索引记录的有: 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和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任一鸣的《女性文学与美学》(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年),王春荣的《新女性文学论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
林树明(男)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年),王绯、孙郁(男)主编“莱曼女性文化书系”(作家出版社,1995 年 ),其中关于女性写作的著作有王绯的《睁着眼睛的梦——中国女性文学书写之召唤》,戴锦华的《镜城突围——女性·电影·文学》,鲍小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 ),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
除了后两种著作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专门译介之外,前几种专著都侧重于女性理论在评介具体文学作品时的操作实践。它们紧随李小江、孟悦、戴锦华的著述之后,在其研究基础上都把问题的探讨向前推进了一步。几本著作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著名篇章、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电影等等都进行了一次女性视角下的重新梳理和审视,得出了与以往男性编撰的文学史和男性视域下的评论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审美机制进行无畏的诘问和挑战。后两种著作中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全面译介,其工作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零星开始,只不过在经过十余年的艰苦努力后,在世妇会于中国召开的1995年,整个女性问题研究已经或多或少成为一种共识时,这种劳作的意义才被烘托得更为明显。
本年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有:天津社科院主持召开的“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女性文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河北《女子文学》杂志社联合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讨会”;河北教育出版社召开的“红罂粟丛书”首发式暨作品研讨会;作家出版社在北京召开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研讨会。
同期,各杂志社、出版社纷纷为女作家召开个人作品研讨会,对她们的个人创作经验进行研究和总结。这些人都是当时中国文坛上相当有实力且非常活跃的作家。一方面,她们的创作实绩为严肃文学评论界所首肯和认可;另一方面,她们的作品在大众读者群中也非常热销。从她们的作品中能了解到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概貌。1995年召开的大陆女作家个人作品研讨会有:徐小斌《敦煌遗梦》研讨会(《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林白《守望空心岁月》研讨会(《花城》杂志社主办);王安忆《长恨歌》研讨会(《钟山》杂志社主办);陈染《私人生活》研讨会(《花城》杂志社与作家出版社合办);赵玫作品研讨会(天津文联主办),叶文玲《秋瑾》研讨会(浙江文联主办)。
简单的事实回溯之后,不难看出这一年度女性写作(包括创作与评论)的繁荣景观,且先不论这“繁荣”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从性别歧视、压抑到浮出水面的事实隐含。
1995年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出版和评论表面上的繁荣并没能掩盖它背后所掩藏的深深的矛盾。这样一种完全是外来的、以性别为基准来划分写作类型的趋向,在中国国内的文学视域内份额究竟能占几何?包括女性主义批评家在内的女学者、女作家和女诗人们,她们是否情愿自己所从事的写作活动仅仅被视为一种“女性写作”?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男权传统的国度里,偏离了中心话语(父权审美机制)的女性写作理论和实践,其意义和价值又应该如何判断?对于中国所有从事写作的女性来说,这些问题并未随着世妇会的幕揭幕落而得到具体解决,问题的实质也并未因此而显得清晰。相反,女性写作整体与菲勒斯中心主义批评机制的分裂,女性集团内部对于“女性写作”这一问题认识的纷杂不一,每个女性个体内心体验与外在现实之间存有的裂隙,等等,这一切都给世纪末的中国女性写作罩上了重重的焦虑与疑惑。尽管许多有识之士(男士)一直不停地在为女性写作的定位与意义而竭力地鼓与呼,但这种呼吁有时却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他们”看“我们”的窠臼,其实质仍旧是站在中心话语上发言的巨大的“男人”,在对边缘状态细语的纤小的“女人”放送着启蒙与提携的犹犹疑疑的目光。并且,少数智者的认同和肯定,仍旧不能够扭转绝大多数评论者与读者对女性写作持有的一贯偏见。而当换成由女性自己来为她们的写作进行伸张与辩护时,情形也未显出太大的乐观。绝大多数的女性写作者又会因循起教化的传统,“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自己的写作是“女性写作”。至少,她们是不甘心自己的写作仅仅被归入“女性写作”名下的。
90年代的女作家们一直十分忌讳或者说惧怕自己的女性性别被人特地提起。对她们来说,只要能以无性别的“作家”这一面目出现就已经足够了。任何一种多余的定语尤其是“女”作家这等性别标号,肯定会在她们心里引起强烈的焦虑和不安,对女性性别的刻意强调,不但不会给她们自身带来任何益处,相反,还会惹出一些麻烦。张扬女性写作的障碍恰恰来自女性写作者本身;将一个女作家的作品划分到“女性写作”名下时,先招致的反对将会来自女作家本人。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花木兰”范式是中国女性写作的版本。绝大多数的中国女作家登场出演时都披挂着这千篇一律的行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要归于长期以来男权社会的经久教化之功,完全是她们被迫坚持模拟男性文学大师和崇拜父系英雄神话的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是她们虽已意识到自己的“第二性”归属,期望有所表达,但却小心翼翼地对自己的性别采取规避和回护的姿态。因为在一个大环境不具备的条件下,任何一种孤军奋战的女性抒写方式,其结果,要么是文章不得见天日,要么是作品发表以后遭受冷遇或中伤,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落得个自生自灭的下场。
在当代中国文学长廊上,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出类拔萃、独领风骚的女性作家,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次大的思潮波动都可以看到她们奔跑在前的矫健身影。可是,一旦要将她们的作品归入严格的女性主义理论下来解读时,便显得有些牵强附会,理论和实践互相为彼此制造出诸多的麻烦和障碍(姑且不论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迄今为止是否认同“女性写作”这种说法,也姑且不论她们在创作中是否故意对自己的性别予以回避,已穿上一层有效保护自身不受伤害的“中性”或“无性”铠甲或干脆就是“男性”盔甲)。有时能在某位女作家的篇章中不期然解读出一些带有女性意味的因素,但很快作者就迅速地将自己的性别遮饰住,那个“女性”如惊弓之鸟一般慌忙远遁,剩下的全是合乎一般“中性”审美规律的文字表达。在通读女作家的作品时,总能让人感觉到,有一个强大的、作为道德坐标的“中性”或是“仿男性”的作者,一个“他者”在窥视、挑唆和审判着一切,女作家们常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这种男权视域下的写作模式。比方说一些女作家笔下的三角恋爱故事,无不是两个女人为争一个男人而打得头破血流非死即伤,而引起祸端夹在中间的那位男人,除了象征性地受一点良心的谴责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损失。这种典型的男权社会对于妇女“出位”的惩戒模式,如今已被女作家自觉运用,且屡试不爽了。
如此一来,女性写作与女性主义——这样一种新型的对写作进行区分和判定的话语,在其一开始被正规引入中国时便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要消除男权文化强加给女性的忧惧,还要靠全体女性写作从业人员的共同努力。拂掉假面上的化妆油彩,探视一下女性作家们的真正脸孔,正是90年代的女性研究者们所要精心去做的有意义的工作。
三、颠覆与皈依
在试图对90年代的女性写作进行评说总结时,我们不能不回想起80年代那些让我们心灵和肉体共同产生震颤的名篇: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和《方舟》,王安忆的《雨,沙沙沙》《小鲍庄》和“三恋”,铁凝的《玫瑰门》和“三垛”(后一垛《青草垛》完成于80年代,却发表于1996年的《钟山》杂志),池莉的《烦恼人生》系列……那些作品曾经带给我们如许的清新和靓丽,如许的沉重和悲哀,如许无奈的叹息和感慨。当80年代女性写作不甘于被遮蔽在阳刚的历史之下,正在奋勇奔突,既成一股特别激情的力量而即将抽离于“他们”的写作之时,90年代这时却以一种令人无法预想的方式降临到中国的历史之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剧烈嬗变,都促使了中国作家对前途命运的思考和对自己写作位置的调整。一些作家沉入了历史,一些作家疏离了现实;一些作家倾泻着自我,一些作家拆解着游戏。80年代的光荣化作了90年代的梦想。光荣与梦想之间,却奇异地托浮出了女性作家在90年代创作的坚韧与执着。
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动荡、中期的狂欢以及随之而来的沉寂这些如火如荼的时代变幻考验后,20世纪末的大陆女性写作,则完全是以女性成熟的个性化姿态出现并展现魅力。纷争多义的“个性化写作”命题借此女性写作得到了良好的诠释。无论是池莉、铁凝的《云破处》《午后悬崖》式的基于女性获救之路描画的性/政治文本的双重策略,还是张洁、王安忆、徐小斌、须兰、斯妤等人的《梦当好处成乌有》《长恨歌》《双鱼星座》《宋朝故事》《浴室》等等对历史的诠释及女性迷宫/镜像式写作,抑或是迟子建、张欣、毕淑敏的《雾月牛栏》《伴你到黎明》《女人之约》等“现实一种”的书写,还有陈染、林白、海男的《私人生活》《一个人的战争》《私奔者》等个人自传体的女性生存经验描述,以及何玉茹、叶弥、周洁茹的《四孩儿和大琴》《成长如蜕》《熄灯做伴》等关于“成长”的小说,女作家们都将笔触进一步逼向人性的本质,在实施尖利的质问和无望的叩询中,执意寻找一丝审慎的爱意和自我获救的温暖。其间不乏惨淡,不乏壮烈,而更多的则是悲悯和忧怀。在90年代频繁迭起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晚生代”创作的雾瘴喧嚣声中,女作家们的创作独立于各种公众传媒和理论评说之外,沿着一条边缘的路径潜心行走,并进而向文化的中心地带迂曲徐缓渗透,执拗揭秘解说着一部人性的或说是女性的心灵史。
在肯定90年代取得如许业绩之时,也不能不注意到90年代的女性写作的另一种“趋时”: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确立,女性的“性别”不再是一个避讳,没有人再谈“女”色变, 90年代女作家公开打出的口号是:“作家还是女作家。”随着女性主义的渐进发展,至90年代中后期时,言明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不但成为女作家、女学者们之间群体呼应的一种简明暗号,而且成为她们彼此间进入女性文本和话语范畴、在同一基准上展开对话的“入围”资格和资历。甚至,矫枉过正,9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主义”,业已成为某种“时尚”和一种新的时髦。
例如在为惹人注目的90年代出现的女性自传或准自传方式的“躯体写作”趋向而言,90年代后期女性私人写作泛化热潮中已是夹杂了大众传媒和商业炒作因素,在一哄而起书写女性私人生活的母题下隐含了题材上的投机与风格上的彼此模仿。女性躯体叙事学的兴起源自西方女性主义的观念,“以血代墨”的女性书写定义得自埃莱娜·西苏以及玛丽·伊格尔顿的理论。批评家南帆在借用它来论述内地女性主义创作时说:“女性的躯体呈现为女性写作的一个醒目主题。在这个方面,男性话语的封锁圈被粉碎,以往,文学的男性手腕,诞生于这些手腕之下的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为自己的欲望所设计出来的模特儿。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同样是男性役使女性的意识形态。女性占领文学的目的之一即通过写作放纵躯体生命,冲破传统女性躯体修辞学的种种枷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充当写作所依循的逻辑。”南帆:《躯体修辞学:肖像与性》,《文艺争鸣》,1996年第4 期。中国女性对于自己的身体有过三次解放,次是五四时期争得男女平等的解放,那是借助思想解放运动,欲从长期的封建专制压迫下将自己的身体从被役使中解脱出来,争得自由支配的权利。无疑,女性的这种性别意义上的抗争,当时被遮蔽和划归在“民主”“平等”“个性解放”等等社会启蒙宏大的历史主题下,“娜拉出走”只在思想意识上进行了一番搏斗和抗争,而并没有顾及解决“身体”这一问题。第二次的解放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靠政府机制和行政律令强制执行的男女平等,在“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照样能办得到”之口号下,男女的性别差异被刻意泯灭,挑泥担担、开河挖山的“铁姑娘”“女英雄”成了这种模式下的身体受害者。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之中,女人柔弱的身体,不得不承受家庭和职业的双重劳役,身体的解放根本无从谈起。第三次解放,即90年代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放,一个相对平等、进步的社会机制和相对发达的电脑信息化网络的建立,使女性有权利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无论是选择婚姻、独居还是离异,也无论是出外做工还是选择滞留家里,不会有体制上的压力和公共道德舆论上的指涉。只有在这个时候,“身体”的问题才会被提到认识层面上来,遭受泯灭的性别才得以复苏,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欲望于是格外强烈。她们不必再如以往一样借男权之眼为镜,在那面哈哈镜中反观自己,而是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 在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等等90年代新一批女作家的作品《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双鱼星座》《我的情人们》当中,常常可以看到女性揽镜自窥的躯体描述,其间也不乏自恋以及自慰的描写。她们从母辈和祖母辈的记忆里得出结论,在千百年来动荡不定的存在中,一切都是靠不住的,灵魂的驻所不在天堂,天堂里由男性上帝把持着,它虚无缥缈,不肯接收也承载不起女性灵魂的重负;也不能把灵魂归附在俗世的男人身上。灵魂的驻所只能在躯体之内,珍藏于我们自己的肉身。只有这一具躯体才归属于我们个人。由此,她们便怀着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格外爱恋和珍惜自己。
这些具有自传性或准自传性的女性“私小说”形态,都是在以男性为对手、以男人为对立面的情形下出现的,女性视角的展现给她们的写作带来空前的自由和文体上的舒展。
这种超出传统意义上的、以女人之眼来关照打量自己、直接描述自己躯体欲望形态的作品,对于整个菲勒斯机制都构成了挑战。一方面这种作品提供了女性“私人化”写作的可能和现实,另一方面也显露出,当女性以一个庞大的男权文化为作战对手,将其当成挑战的把柄和颠覆的目标时,女性并没有显现出快乐,相反却显出忧伤、孤独,以及失望以后的悲愤与绝望。“以血代墨”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然而在这之后,当其成为女性书写的一个“群体特征”时,一个庞大芜杂的女子自传写作“症候群”不期然出现了。女性准自传性产品以丛书或套书方式大批量制作生产出笼,其“私人性”和“个性”都因其写作内容上的盲目复制(自我复制或复制他人)而显得贫血而失色,同时也使得刚刚提到认识层面上的女性私人化写作,在类型化的集体狂欢中,面临又一次失去审美独立性的可能。大众传媒的炒作和商业的庸俗以致恶俗包装,某些不怀善意的“窥阴”操纵及个别书写者内在的迎合,也使女性私人写作反而变成对女性性别的一种亵渎和玷污。所有这些都极有可能断送女性写作及写作着的女性们的前程,使她们的颠覆成为变相的献媚或皈依,“逃脱”或“突围”之处再一次成为“落网”,女性的“第二性”命运又一次在劫难逃。
作为对世界范围内女权主义思潮在中国之回应的女性写作,能够发展出今日之成绩颇为不易。唯愿业内人士尤其是女性写作者能对自己的奋斗成果特别珍惜。对这一写作趋势的研究整理,不仅能为我们研究90年代的整体中国社会文化提供一个参照,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探讨关于文化的一元与多元、边缘与中心的极好视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