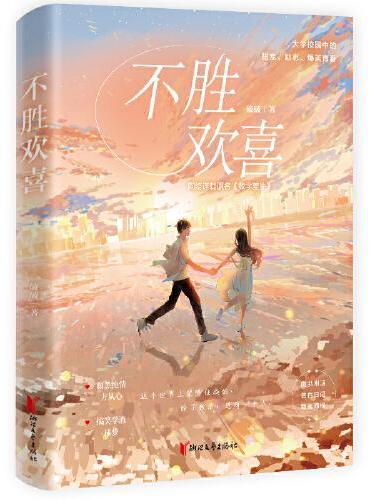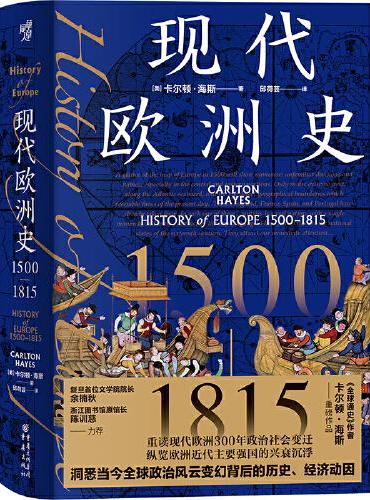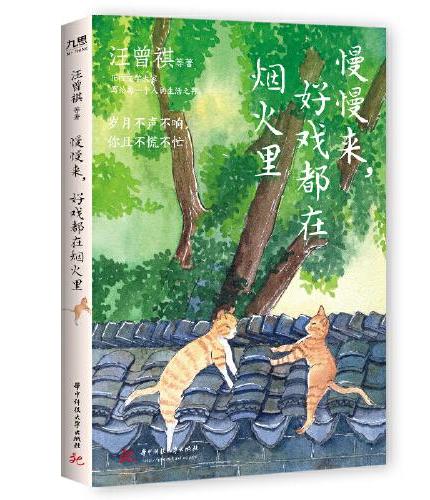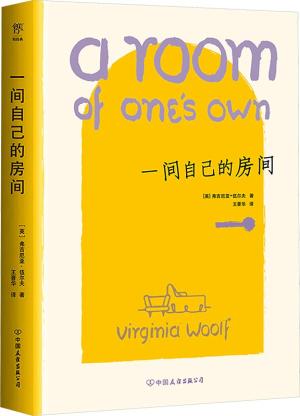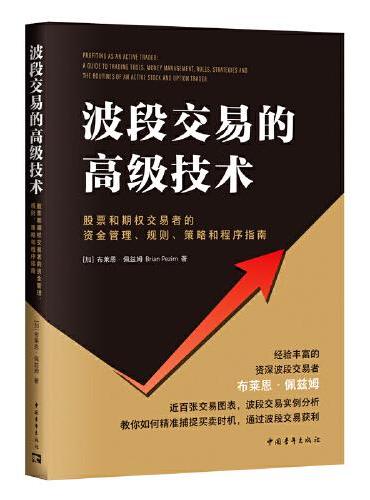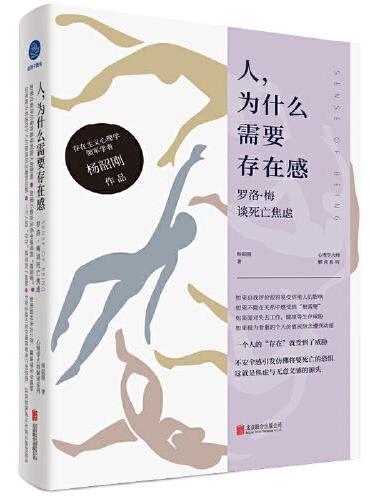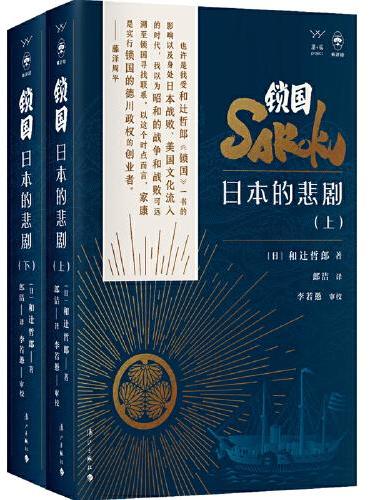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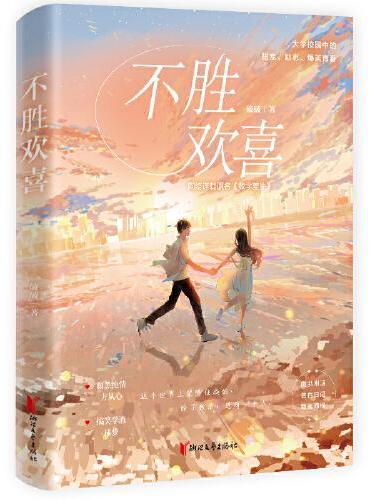
《
不胜欢喜
》
售價:NT$
29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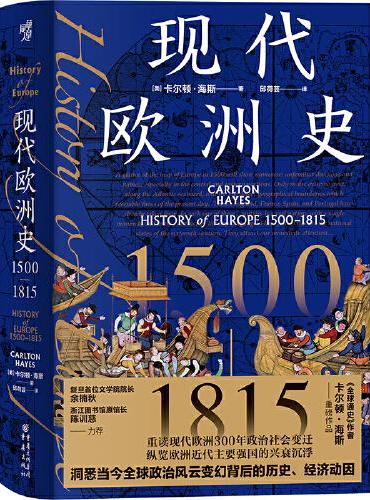
《
现代欧洲史:1500—1815
》
售價:NT$
493.0

《
高颜值创意饮品:咖啡 茶饮 鸡尾酒 气泡水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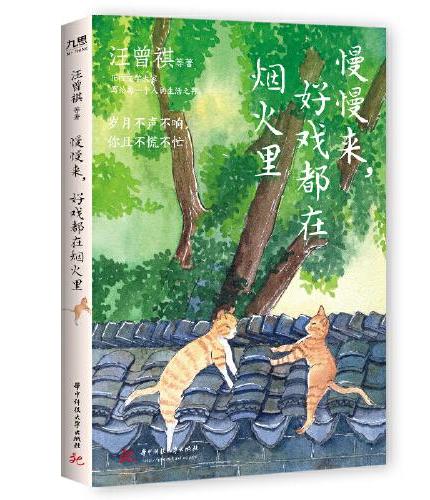
《
慢慢来,好戏都在烟火里
》
售價:NT$
2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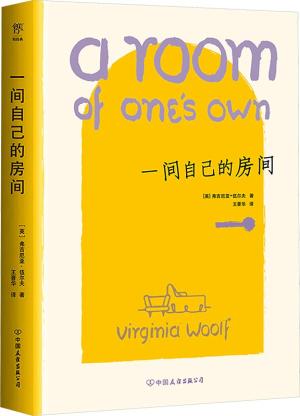
《
一间自己的房间
》
售價:NT$
2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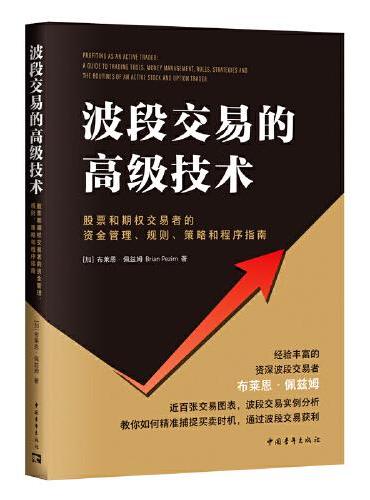
《
波段交易的高级技术:股票和期权交易者的资金管理、规则、策略和程序指南
》
售價:NT$
4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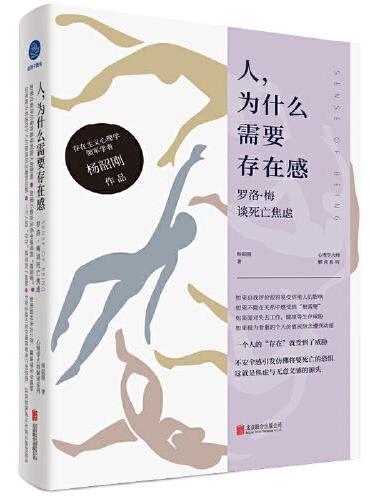
《
人,为什么需要存在感:罗洛·梅谈死亡焦虑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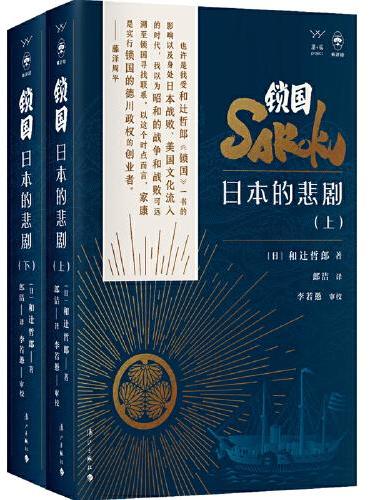
《
锁国:日本的悲剧
》
售價:NT$
437.0
|
| 編輯推薦: |
|
《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汇聚了蔡锺翔、陈良运、涂光社、袁济喜等诸多知名学者,对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作了一次全面深入的研究。作者在遵循基本撰写体例的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性与观点,彰显和而不同的学术自由精神,融会中西,将中国美学范畴与西方美学与文化相比较,提出了诸多学术锐见。该套丛书的出版,将为中国美学和中国文论史的研究及体系构建打下坚实基础。
|
| 內容簡介: |
|
《兴:艺术生命的激活》是《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中的一种。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具有多重含义的范畴,它将文艺创作中的一些基本范畴加以融会,具有以一总万的意义。作者深入研究了兴之诞生和历史发展进程,着重探讨了兴的内涵,以及它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价值和影响;作者既充分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
|
| 關於作者: |
|
袁济喜,198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杰出人文学者特聘教授。代表作有《六朝美学》《中国古代文论精神》《汉末三国两晋文学批评编年》等。
|
| 目錄:
|
绪 言/1
第一章 先秦两汉诗学之兴/5
第一节 《诗经》与比兴/5
第二节 孔子论兴/18
第三节 汉代经学家论兴/24
第二章 魏晋六朝之兴/34
第一节 兴与人生的觉醒/34
第二节 兴与文学创作/42
第三节 兴与审美理论/47
第三章 唐宋诗学与兴/56
第一节 尚兴重情的唐代诗学/56
第二节 平淡入兴的宋代诗学/78
第四章明清诗学之兴/94
第一节 格调说与比兴/94
第二节 性灵说与兴会论/101
第三节 陈子龙、王夫之论兴/106
第四节 王士禛的兴会神到说/115
第五章 兴的文化溯源/119
第一节 兴与原始生命/119
第二节 兴与原始艺术/130
第三节 兴与原始思维/136
第六章 兴的内涵/147
第一节 比兴与托喻/147
第二节 比兴的分道/152
第三节兴与意蕴/158
第四节 兴与文艺鉴赏/167
第七章 兴的审美心理/177
第一节 兴与心物活动/177
第二节 兴与灵感思维/182
第三节 兴与情景交融/188
第八章 兴的组合/195
第一节 兴趣/195
第二节 兴会/201
第三节 兴象/206
|
| 內容試閱:
|
绪 言
兴是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具有关键性质的范畴,它将审美与文艺创作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如心物、情景、情志等关系加以融会,作为沟通这些对立关系的桥梁,使审美与文艺创作成为既涵括情与志、情与景、心与物,又具有独立性质的精神文化创造活动。它包含的范围如此之广,涉猎的问题如此之多,具备海纳百川、以一总万的意义。这是中国审美文化理念与体验相融合特征的典型显现,是西方与其他各国的美学与文艺学所不曾有的。叶嘉莹教授曾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关系例说》一文中指出:至于兴之一词,则在英文的批评术语中,根本就找不到一个相当的字可以翻译。因此,不从整个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去了解兴的内涵与外延,就难以全面把握这一范畴的真实面目。
作为审美范畴的兴的出现,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先秦时代。在《诗经》的创作过程中,即已萌发了用比兴来作诗的自觉意识,孔子提出了诗可以兴兴于诗的命题,正式启用了兴的美学范畴。秦汉间的《周礼》最早提出比兴概念,后来汉儒在注《周礼》时对比兴作了诠释。《毛诗序》对比兴在诗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与功能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最初的时候,人们讨论兴的问题,一种是如孔子那样,当作用诗的概念,强调对《诗经》的欣赏是感发志意的美感心理;另一种是将它作为赋比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诗法来看待,其基本含义有两点,即感发与托喻的功能,它是与比相提并论,然而更具隐喻意义的一个范畴。汉魏之际,随着人性的觉醒与文学的独立,兴从托喻之辞向着自然感兴发展,其内涵逐渐延伸拓展,演化为超越政教思理、用以感兴寄托与、意在言外的审美范畴。唐宋以来,诸多的文论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从而使兴范畴的内涵不断得到充实与拓展,变成具有多重含义的古典美学范畴。兴从创作对象的角度来说,倡导缘物而感;从作者主观方面来说,提倡寓情写意;从主客观合一的作品层面来说,则倡举意在言外、回味无穷的审美境界。这三重意义,浑然融化成中国美学关于文艺创作的基本范畴,是中国文化特质在美学上的汇聚。
原夫兴之诞生,源自华夏民族自然生命与艺术生命融合而成的宗教之舞中。在后来中国美学的发展演变中,随着人的独立与觉醒,兴开始逐渐摆脱巫术文化的浸染,越来越走上审美之途,同时又汲取了原始之兴中深厚的人文蕴涵,用以寄寓动荡年代中的人生感喟,激活人生,使人生与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艺。其高风遗韵,至今仍使今人慨然感怀。它昭示我们,艺术之中没有生命之兴,就根本无法臻于至境,而只是文本制作,过眼烟云。兴是现实人生向艺术人生跃升的津梁,是使艺术生命得到激活的中介。由于中国文化浓重的遗传性,使得兴还保留着中国远古时代就形成的天人感应、观物取象、托物寓意等文化价值观念痕迹。这种从原始生命冲动与人格独立出发的艺术观念,虽然有神秘直观的成分在内,但是,在人类越来越受理性制约,审美生命日渐萎缩的今天,这种生命之兴具有激活平庸人生的积极意义,是中国古典美学有价值的传统之一。
从中国文化的整体特质来说,它是一种世俗乐天的文化,其特点是以情感与直观的方式去感知世界、认识外物。中国虽有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但是它不能替代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精神,中国人的宇宙意识与对信仰的铸造,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诗性文化的桥梁来沟通的。兴作为融合客观与主观、感知与情感、必然与偶然的美感心理,是中国人构建自己精神家园的津梁。林语堂曾在他的《中国人》一书中,对诗歌之兴在中国人精神世界中的作用与地位作了深刻的阐明: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是黑暗的生活之上点缀着的漂亮补钉,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死亡。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的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了人们心灵的创痛。其实,在齐梁时的钟嵘《诗品序》中就谈到: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钱钟书先生曾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指出,钟嵘的这一诗学主张是止痛安神剂。而诗的这种功能,是通过孔子说的诗可以兴兴于诗的美感方式来达到的。对兴的审美能力的培养,与后来蔡元培先生所倡的以美育代宗教说,确有殊途同归之妙。兴作为审美范畴,折射出中国诗性文化的光彩。在今日中国,对传统兴的审美精神的承传与弘扬,一如王夫之当年对兴的倡导一样,对于国民精神的濡涵与提升,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兴具有如此丰赡而又繁复的意蕴,因而自古至今,对它的解释如陆机《文赋》所说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许多人将此视为畏途。平心而论,以笔者的学识,要在文本的研究上超过前人的水平,是很难做到的,因而这种研究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不过我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在当前众多的研究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路子中,我只能选择自己的路子,这就是将材料的整理与观点的注入融合起来,借鉴清人所倡的义理、考据、辞章相结合的方法,既充分吸纳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以前研究中国古典美学范畴和的方法作了一些拓展,比如在材料的选择上,不仅注重文献学的材料,而且对于文化人类学的材料及他人的研究成果,亦充分吸收,并尽量在出处中标明。我个人认为,对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研究,不应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还原与整合的层面上,而应将她的内在精神与我们今日美学与文化的建设相融合,这是古人美学理论的精髓,也是五四以来中国美学精神得以承传的动力,正是本于此,本书在写作中力图做到从承续与超越上来追求这种境界。至于究竟能达到多少,则有赖于读者的批评与鉴定。
第一章 先秦两汉诗学之兴
作为审美范畴的兴的形成,是在有文字记载的先秦时代。然而,兴作为原始生命活动的表现形态,却是在原始社会中即已萌发了详见本书第五章《兴的文化溯源》。随着远古生民艺术生命的延伸,原始歌舞的形态从本能性的宣泄向着文字思维形态的艺术发展凝缩,歌、乐、舞合为一体的艺术形态逐渐朝着偏重语言形式的诗歌伸展,从而使得兴的内涵更加凝聚着社会历史与人生百态的意味,成为艺术使情成体的创作中介。在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中,兴的审美范畴得到奠定与确认。
第一节 《诗经》与比兴
比兴作为诗歌审美创作的方法,最早出现在《诗经》之中,这是有其文化与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古代的诗歌起源于何处,迄今仍是难以确定的课题。史前留下的原始资料难见其迹,而目前被称作肇开声诗的《康衢》、《击壤》,由于艺术形式与语言的相对成熟,使人难以相信它们是五帝时代的诗歌。倒是一些见之于考古资料的甲骨文上的卜辞,可以见出最早的诗歌的雏形,如癸卯,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第375片其中不乏有对称的五言,还有三言,二言,参差错落,和而不同,颇具民间谣谚的意味。其它《易经》中的卦辞与爻辞中也有一些简短而意味隽永,留传后世的名言,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虎视耽耽,其欲逐逐《颐卦》六四从这些句子来看,它们类似于谣谚,只是一种简单的心理的表达,而真正能够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形式抒写先民的喜怒哀乐,达到相当艺术水平的,是《诗经》。
《诗经》中的《风》《雅》《颂》三部分在孔子之前即已形成了。唐代经学家孔颖达说过:《风》《雅》《颂》,诗篇之异辞。《毛诗正义》卷一对于它们之间的划分依据,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毛诗序》为代表的经学家认为是依据诗的表现对象与功能来划分;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是按诗的作者身份及《诗经》中的内容来确定;而以郑樵《六经奥论》为代表的意见则主张应按《诗经》音乐属性的地域方面来认定。但一般说来,《风》《雅》《颂》的区分是应该从作者身份和表现内容两方面来判定的。《风》是十五国民间歌诗的汇集与整理;《雅》是贵族官吏们的作品,而《颂》则是商周御用文人所作的庙堂之作。由这三部分的作者身份与表现内容所决定,三者的思想与艺术也各具特色。一般说来,《风》诗具有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雅》诗属于贵族及其官吏的作品,它们的艺术水平相对高一些,感情细腻深沉;而《颂》诗的祭祀味道浓郁,格调沉闷繁复。但从这些经过整理的诗歌总集的内容与艺术手法来看,作者的创作主体思想是明显地增强了。从我们现在所见的作品考察,可知《诗经》中直接言及作诗动机的有16处,其中《风》诗中约有3处,74篇《小雅》中约有7处,3l篇《大雅》中约有6处。这也可以说明:《雅》诗中由于作者多为文化教养较高的贵族与官吏,他们的审美自觉意识更强一些;而《风》诗由于民间歌诗的特色,呈现出率兴而为的特点,故而自觉为诗的意识弱一些。但无论是《风》诗还是《雅》诗,抑或是《颂》诗,其中言及作诗之目的,大要不出歌颂与诉悲,也就是两汉儒生论《诗经》时常说的美刺两端:
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屦》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
夫也不良,歌以讯之。《陈风墓门》
家父作诵,以究王凶。《小雅节南山》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大雅民劳》
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大雅烝民》
关于这些诗作具体内容所指,迄今为止,还很难确定。但透过这些言及作诗动机的诗句,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见到《诗经》中有着明显的诗言志的传统。志者,止也,也就是原先积累的人生怀抱与志向,是自我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主体性,标志着《诗经》的作者们已经从远古时代人类观物取象、被动感应外物的朦胧意识,变为积极主动地去表现对象、抒发情感。外界的事物经过主观情感的熏染后,变成人化的自然。作者能够跳出远古时代的直抒其感、感性压过理性的思维方式,注重理性与感性的融合。在《诗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萌发的中华民族情理合一、温和含蓄的审美心态。比兴的运用,正是缘此而生的。《周礼春官大师》条载有大师教国子六诗之事:
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约成于东汉年间的《毛诗序》则称之为六义: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然而关于六诗或六义的解说,《周礼春官》与《毛诗序》中并没有作出解释,先秦时代也没有具体的资料可以佐证。不过,不管是《周礼》还是《毛诗序》,它们在言及六诗六义时,排列的顺序却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风、雅、颂与赋、比、兴应属两组不同的范畴。最早为六诗与六义作出解说的是东汉经学家郑玄:风,言圣贤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取善类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周礼注》唐代经学家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明确地将风、雅、颂和赋、比、兴作为《诗经》中两组不同的范畴,从体用两方面加以区别:诗各有体,体各有声。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后来南宋朱熹赞同此说,提出:且诗有六义,先儒更不曾说得明。盖所谓六义者,风、雅、颂乃是乐章之腔调,如言仲吕调、大石调、越调之类,至比、兴、赋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赋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两句颂起,因而接续云者,兴也;引物为况,比者也。立此六义,非使人知其声音之所当,又欲使歌者知作诗之法度也。朱鉴《诗传遗说》引朱熹是力图从音乐与诗义的结合去说明六义与六诗的区别,但是近代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中却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郑玄注《周礼》六诗,是重义时代的解释。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诗大序》为六义,便是以义为用了。当代有的学者也认为《周礼》中言及的大师教六诗其实是乐教的一种,是将《诗经》作为音乐教育中的歌辞来对待的,但是周代贵族教育中重视乐教,却也并不排除将《诗经》中的音乐与歌辞并重用以教育贵族子弟,不然,我们就不好理解,为什么继承周代教育体系的孔子会转而以《诗经》之义来教诲子弟,并辅之以音乐教育。歌辞是内容,音乐是形式,二者的相得益彰,可以使人在欣赏时深入人心。季札观乐,知音赞叹;孔子在齐国闻《韶》,如醉如痴,就绝不只是单向的音乐与歌辞所能奏效的,而是音乐与歌辞互相配合产生的审美效果。
然而,后人对《诗经》比兴的解说是一回事,而《诗经》中呈现出来的赋、比、兴创作手法又是另一回事。作品中呈现出来的美学范畴是以隐形的审美意识表现出来的,而诗论家与美学家对作品中蕴含的美学范畴的总结,有时候是符合文本的,有时候则明显地属大衍发微,两汉经学家对《诗经》中赋、比、兴问题的探讨许就是属于这种情况。依据我们今天对兴的理解,《诗经》中运用兴的手法应该是很自觉的一种创作手段与修辞手法。兴在《诗经》中的出现有二十例。根据当代学者陆晓光在《论孔子可以兴命题的历史意蕴》一文的统计,大约可以分成三大类。其一,为起身、起床之意。如: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卫风氓》言念君子,载寝载兴。《秦风小戎》子兴视夜,明星有烂。《郑风鸡鸣》及寝乃兴,乃占我梦。《小雅斯干》其二,意为兴盛,如: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大雅大明》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林。《小雅天保》其三,是兴发引发之意,如:天降滔德,女兴是力。《大雅荡》百堵皆兴,鼛鼓弗兴。《大雅帛系》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在稍后于《诗经》的《左传》之中,兴字也用得很多,但意思大要不出这几类。《诗经》与《左传》是先秦典籍中较为可信的作品,其中兴的用意同甲骨文、金文中众手同举之意是一致的,也就是发起、兴起、引发之意。在其他的先秦典籍如《墨子》、《庄子》、《荀子》、《孟子》、《韩非子》等稍后的书中,兴字的用义也基本一致。
对于兴作为《诗经》中创作手法的解说,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引东汉郑众释兴之意义时指出:司农指郑众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这一说法,大致说出了作为《诗经》创作方法之兴的基本意思,它与比相比,是一种先言他物以切入主题的创作手法,就这一点来言,它与朱熹《诗集传》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朱熹又说: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至于先言他事与所咏之辞即前句与后句之间有没有意义之间的联系,朱熹则说: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认为二者之间多无联系。朱熹的说法与汉儒论兴时强调兴与后咏之辞有着意义联系的观点大相径庭,因而明代郝经的《诗经原始》与清代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中对之作出了反驳。陈启源说:诗人兴体,凡托兴在是,则或美或刺,皆见于兴中。这实际上是将兴与比都视为蕴涵政教大义的创作手法,比与兴的差别只是所谓比显兴隐,或者如郑玄所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取善类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比与兴是因承担美刺政教任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今天看来,《诗经》中的兴基本上是指一种创作手法与修辞手段,其中所兴之物有的与后面的内容有着一定的联系,有的只是烘托气氛,与后面的内容并无必然之关联,汉儒强调兴的微言大义,比刺兴美之类,大可不必作为我们今天研究《诗经》中比兴的羁绊。
《诗经》中的起兴,有的是不取其义的发端,是远古生民观物取象,由此及彼的习惯性思维,二者之间没有意义的联系。如《秦风黄鸟》:
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交交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维此仲行,百夫之防。
交交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左钅右咸)虎。维此(左钅右咸)虎,百夫之御。
诗中起兴的黄鸟与下文的意义并无意思上的关系,只是发端起情,三章中分别写黄鸟落在棘桑楚之上,只是虚写,不是实写,所以有这样的虚写,显然是起定韵的作用。其它如《秦风车邻》,《王风黍离》也有类似的情况。
《诗经》中兴的运用第二类,是起兴与后咏之情有着一定的比喻作用。如《诗经》中著名的《周南关雎》: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诗中一开始由一对水鸟在河中沙洲求偶鸣叫想到自己爱慕的姑娘,渴望同她结成伴侣。诗的开头两句起兴与后面两句的意思显然有着联系,所以有人又称作比而兴,这也可以说明比兴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截然分开。后世有人千方百计想从前人夹缠不清的比与兴之中厘定二者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是建立在一种直感形的模糊思维之上的,不可能像研究西方美学那样条分缕析。
再如《周南》中的《桃天》: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子之于归,宜其室家。
诗的开头以桃花起兴,比喻新妇美丽的容颜,祈祝新妇婚姻幸福美满。桃花与新妇之间,也就是起兴与所咏之辞之间存在着比喻的关系。还有的起兴比较隐晦。如《邶风柏舟》中有: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
诗一开始用任水漂泊、无依无靠的小船起兴,以隐喻被遗弃女性的悲惨命运。类似的起兴与比喻在《邶风谷风》中也有: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诗的起兴用山中之风和乍晴乍阴的天气形容丈夫喜怒无常,让她提心吊胆。兴句采用阴晴不测的天气与暴风骤雨来比喻丈夫的脾气暴戾不定,是非常贴切而生动的。
《诗经》中兴的运用第三类,只是烘托气氛,起兴与后面的咏叹之辞并没有意思的联接,但是气氛的烘托成功,能够起到反衬的作用,有时候这种修辞效果比诸直接的意义联系更为动人。如《郑风风雨》中的起兴,渲染了一种凄清悲凉的气氛,很好地烘托出女子对相思中人的苦恋之情: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这首诗三章之首都用风雨中鸡鸣起兴,写出了一位女子在风雨中苦等男子的凄楚与想像相见后的快乐。开始的两句起兴虽与后面的内容没有直接的比喻作用,但是创造出来的悲凄气氛强烈地衬托出苦恋的情调,读之令人感动。也正因为开头二句起兴烘托出的气氛不同凡响,故而后世的人们常常将此单独剥离出来,用来形容在风雨如晦的黑暗社会中坚持素志,决不随波逐流的人格精神,南朝时的刘峻在《辨命论》中就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形容仁人志士在黑暗年代中的不屈志向。《诗经》中的起兴与传统诗学中所说的赋、比、兴原则有着很深的联系。赋是直言其事,比是比方言事,也容易理解;而兴则比较复杂,故较早解释《诗经》的毛传对赋比两种手法不标,而独标兴体,是知兴之难言。但兴与比、兴与赋实在是不好分的,有时候是借助于二者的桥梁构建而成。日本著名学者铃木虎雄在其《中国诗论史》中谈到《诗经》中的赋与兴关系时指出:由《诗经》中的甲句来看,是赋的直言其事的手法;而将其与后面的乙句联结起来,则发挥出兴的作用,即眼前所见之景成为后面之情的衬托。如《关雎》中的前面两句单独来看是赋,而将其与后面的男女相爱之情联系起来,则构成了兴。比兴的运用主要是服从于《诗经》作者强烈的创作主体意识,即通过特定的表现手法来抒发情志,传达出或怨或喜的情感:
如果说用赋的方法,其言率直而露骨,那么,运用比、兴的方法,即所谓比方于物,以事物为媒介寓托自己的心情,则其言婉曲。由于怨或刺的主题往往借助此法而婉曲表达,因而后世在解释时,即使在当时是最易明了的诗意,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作者的本意。
铃木虎雄的话可谓说出了兴在《诗经》中的意义与在后世传释时的遭际。他认为《诗经》中的比兴用法来自于怨与刺的主观情志需借助于婉曲的表达,故造成了比兴手法的运用。其中比兴并不存在着郑玄所说的比刺兴美对号入座的问题,比与兴都可以用来作为刺与美两种情志的表达。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说,《诗经》中积淀了远古生民对自然和社会进行观物取象与引譬连类的思维习惯,将兴作为客观外物与主观情感之间的触发点,由此即彼,由物及我,从而使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宇宙观得到了艺术的表现。中华民族艺术生命的激活,在兴之中获得了升华。
从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先秦典籍中,如《左传》、《论语》、《周礼》等等,有关兴的范畴与概念的表述,基本是停留在用诗的层面,而从创作论的角度去揭示的,是在东汉的《诗大序》及郑玄、郑众等经学家的注释中,真正从文学创作与文学欣赏方面去加以系统论述的,则是在魏晋南北朝的陆机、刘勰与钟嵘等人的诗论与文论之中。这是有着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的。
在先秦时代,《诗经》由于保留了上古时代的祭祀与宗教的典礼文化传统,其中有着自然与人文诸方面的丰厚的精华,因而成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元典,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推崇,早已步出了艺术的殿堂,与当时贵族的各项社会活动相结合。在《左传》中所记载的各种军事与外交场合,以及各种社会生活情境之中,赋诗言志成了普遍的风尚。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这些话说明了《诗经》是当时社交场合贵族修养的标志与共同语言,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兴义溯源》中曾详细统计了《左传》中赋诗引用的今本《诗经》之《风》、《雅》、《颂》各部分的比率,其中《大雅》利用率最高,占61%;《小雅》为55%;《颂》为42%;最低的《风》也占20.8%。由此可见当时赋诗言志的时尚,同时也见出《大雅》与《小雅》由于与赋诗言志的主体贵族身份相吻合,故较之《风》诗更受青睐。
这种赋诗言志与兴的运用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在特定的场合与情境中,赋诗者往往断章取义,对《诗经》中作品大衍发微。晋代杜预曾注曰: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赋六月注在赋诗时,或取首章首句,或取某章数句,借古诗婉曲地表达赋诗者的意愿。赋诗言志所以能够在当时通行,显然与创作者在诗中广泛运用了兴的手法,造成意思的委婉曲致相关,使得赋诗者可以以意逆志,加以发挥。当然,这并不妨害彼此之间对于《诗经》原意的理解。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兴义溯源》中说:看《左传》的记载,那时卿大夫对于诗三百大约都熟悉,各篇诗的本义,在他们原是明白易晓,正和我们对于皮黄戏一般。他们听赋诗,听引诗,只注重赋诗的人引诗的人用意所在;他们对于原诗的了解是不会跟了赋诗引诗的人而歪曲的。好像后世诗文用典,但求旧典新用,不必与原意尽合;读者欣赏作者的技巧,可并不会因此误解原典的意义。从美学上来说,创作论中的兴与鉴赏论中的兴本是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不同的环节,前者是第一性,后者是第二性,二者之间是一种审美传递的过程,鉴赏过程中的审美传递较之于创造活动,往往具有更大的发挥余力,也就是当代西方接受美学强调的第二创造的过程。在春秋时代,人们对《诗经》的解读,感兴趣的不是第一性的原创之兴,而是作为鉴赏过程中的第二性的兴,因为第二性的兴可以见仁见智,使原创性的兴获得更大的发挥与价值实现。明乎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孔、孟对《诗经》的解读,特别感兴趣的不是创作论问题,而是诗可以兴兴于诗与以意逆志的问题。
其实,兴从作为《诗经》中的创作手法与修辞手法延伸至鉴赏论,进而与人格培养相融合,其美学意义早已超出一般的创作论与鉴赏论范围,它对于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化的贡献,比起比兴意义的范畴大得多,而过去人们对于兴范畴的此种含义是重视相当不够的,在我们今天讨论兴的时候,这种倾向应当得到纠正。兴作为以诗乐舞的艺术教育与美育的途径,在传说中的周代贵族教育中已经存在。《周礼》中的《春官大司乐》中指出: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悦远人,以作动物。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掌管教育的教官与掌管礼仪的礼官都负有实行乐教的职责,而乐教又具有道德教育乐德、语言教育乐语和艺术教育乐舞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一种系统的美育工程。这种乐教与强制性的道德与法制教育相比,具有潜移默化、沦肌浃髓的效用,使人在血缘亲情的陶染与感化中,不由自主地恪守传统的孝悌一类道德。这样,原本在氏族社会之中,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礼乐系统就逐渐变得具有审美教育的色彩,从而与贵族的人格教育与道德教育相融合。郑玄注曰:兴者,以善物喻善事。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发端为言,答述曰语。《周礼注疏》引郑玄的注解将兴置于政教大义上去发挥,把它与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中之兴相类同,都视为政教概念。其实上文我们已引证朱自清先生的话指出过,郑玄的时代对《诗经》的解说是重义的时代,而周代的六诗之教与乐语乐舞之教一样,都是通过音乐教育的方式去实施的,此中所言之兴,与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有所不同,是从音乐与歌辞相一体的乐语即唱歌之教去教育贵族子弟的。兴道,主要是唱歌过程中产生的感发志意,从无形的音乐美感出发,进而深入到歌辞的意义中去,故而离不开讽诵与言语两方面的阅读和吟诵的升华。兴与道即导都有引发感染的意义在内,由美感的刺激开始,进而引譬连类,举一反三,这同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的美感功用有相通之处。近年来有学者对《周礼》中的六诗说法从美育学的角度去解说,认为六诗是周代诗学的教育纲领,它反映了周代声、义并重的诗歌教学由低级向高级延伸的过程。风赋为第一阶段,是基本功的训练,要求国子即贵族子弟能够熟练地歌唱诗,朗诵诗。前者是以声为用的教育,后者是以义为用的教育。比兴为教育的第二阶段,是诗歌的义理训练。雅颂是第三阶段,是正声诗乐的训练,要求国子能够严格地照周礼以诗为用。这种说法引起过另一些论者的不同看法。其中何者为确,这里不予评论,但这一观点至少可以启发我们从贵族教育课目的角度去考察六诗说,而不必囿于前人之说。参阅《周礼春官》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周代以《诗》为教是很普遍的事,当时人论兴也多从乐教的角度去说,明代李东阳对古代的乐教十分重视,主张从声教的方向去溯源诗教本义,是有相当道理的。
这种贵族教育中重视《诗》教的传统到了春秋时代获得了延续。《国语周语》中记楚大臣申叔时答楚庄王问如何教育太子时指出:
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广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且夫诵诗以辅相之,威仪以先后之,体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节义而动行之,恭敬以临监之,勤勉以劝之,孝顺以纳之,忠信以发之,德音以扬之,教备而弗从者,非人也。
申叔向楚庄王介绍如何教育子弟时,仍然将《诗》与《乐》、《礼》、《春秋》作为教育子弟的基本科目,《诗》可以濡涵人的道德,培养人格,使贵族子弟具备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品德与才华。这种教育观念,与孔子的六艺之教已经十分相近了。它与周代的贵族教育相比,更加讲究道德与实际能力的培养,以及政治识见的增长,而去掉了周代教育中的许多繁文缛礼、宗教神学的东西。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晋国大臣赵衰向晋文公推荐郤縠为三军统帅时,就称赞郤縠有着深厚的文化教养: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赵衰明确地将《诗》与记载夏商周历史文献的《书》相提并论,将它与人格的熏陶融合起来。孔子论兴正是在这种诗学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