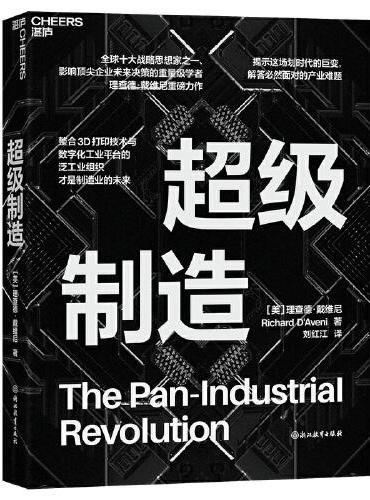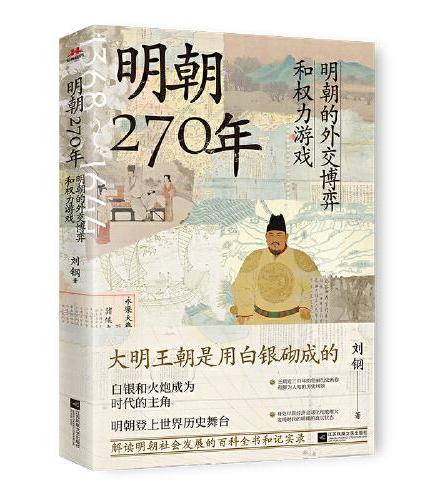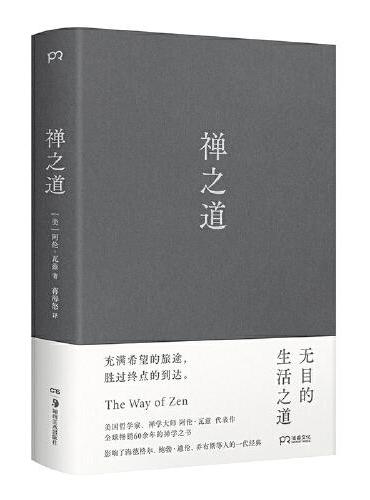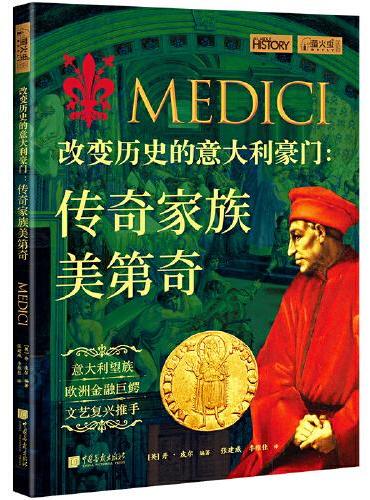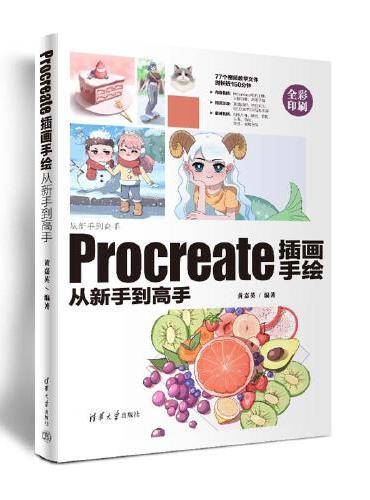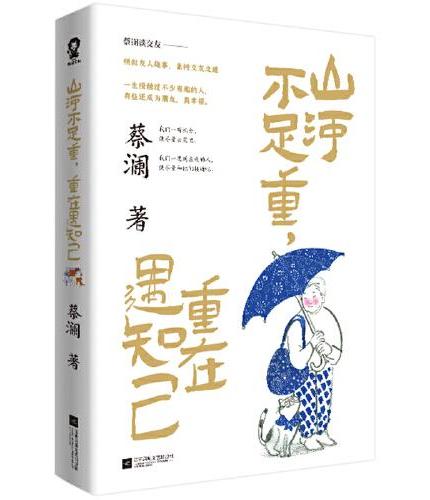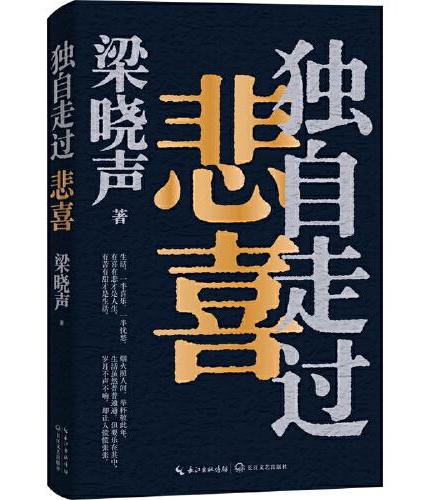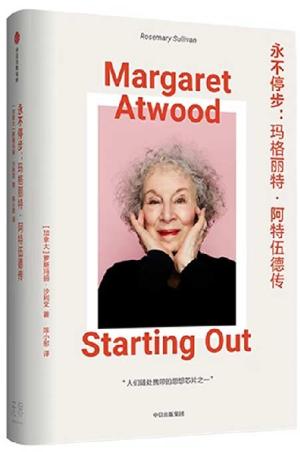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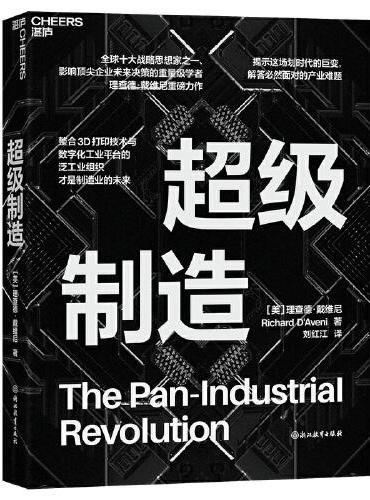
《
超级制造
》
售價:NT$
6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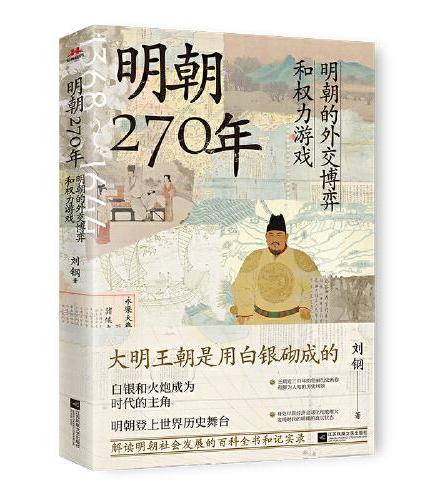
《
明朝270年:明朝的外交博弈和权力游戏
》
售價:NT$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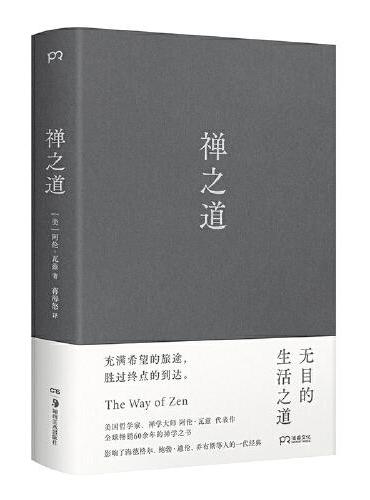
《
禅之道(畅销全球60余年的一代经典,揭示禅对现代人的解脱意义)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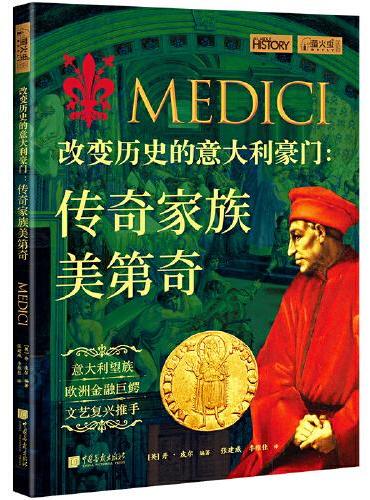
《
改变历史的意大利豪门 : 传奇家族美第奇
》
售價:NT$
4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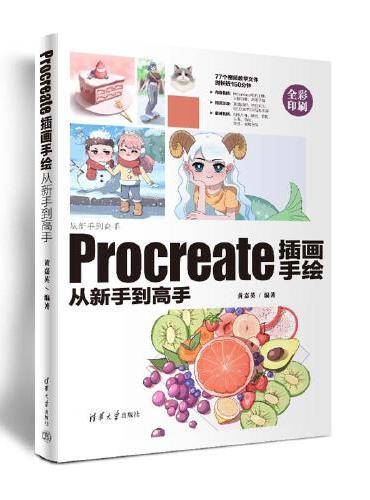
《
Procreate插画手绘从新手到高手
》
售價:NT$
4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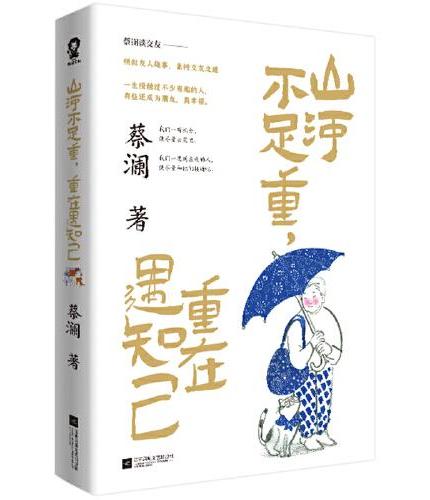
《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
》
售價:NT$
2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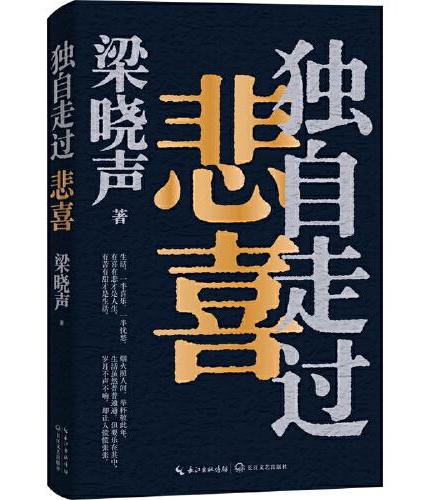
《
独自走过悲喜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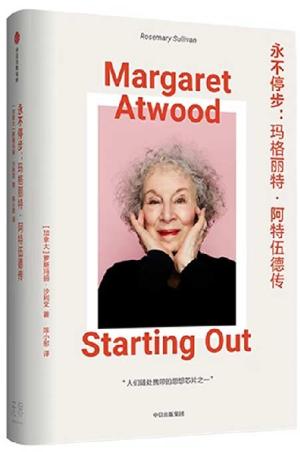
《
永不停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
》
售價:NT$
442.0
|
| 內容簡介: |
1945年前后的旧上海,古灵精怪的杂技女孩兰胡儿,犹太流浪者收养的一个中国孩子加里,他们在光怪陆离的上海大世界相遇。魔幻的西洋魔术与惊险的中国杂技,兰胡儿和加里珠联璧合般的表演,在上海滩风行一时。杂技和魔术艺人的卖艺生活是艰辛的。四年时间,两个少年人在重重磨难中渐渐长大,渐生情愫。他们一次次地死里逃生,一次比一次明白,此生不能分离。两人到底是不是双胞胎兄妹?真相重要吗?唯一的真相,是他们彼此相爱。
|
| 關於作者: |
虹影,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等。其长篇小说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国出版。《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1997《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好儿女花》,获《亚洲周刊》2009年十大小说。虹影曾获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意大利罗马文学奖,2009年被重庆市民选为重庆城市形象推广大使。
|
| 內容試閱:
|
当年写这部小说时,我个人生活正处于一个极其困难的时期,如同行走在钢丝之上,不管如何走,都免不了掉下悬崖。
于是我关起门来,饭菜都是从餐馆叫来,埋头写。做一个作家的好,就是你差什么,想象力就尤其发达。我设计了一对少年人在1945年前后的故事:加里王子和乱世女孩兰胡儿。一改往日小说凄楚与悲剧的结局,我创造了他们的世界,就像当年上海最美一天的霞光,光彩炫目。
他俩到底是不是兄妹呢?这点重要吗?想知道真相吗?
若是非要有真相的话,那么你只需要知道他们爱着对方,如兰胡儿所说,你活我活,三生三世,你死我死,此地此刻。
那是魔术,爱的魔术。记得最后完稿时,我个人的生活也出现了魔术。因此修订这小说时,我不得不在这里说,由于写这本魔术的小说,我没从钢丝上掉了下来,而是安全地降落到地面。
大世界中的小世界
虹影
一
他对我说,到上海去,上海会让你着迷。
他还说,她会喜欢你。她住在富民路的弄堂房子里,她果然待我如自家闺女,边夹菜给我边说大世界那些哈哈镜,那些坤角旦角,陈年谷子一粒粒道来。说是第一次进那儿就迷了路,人一生迷一次路值得。
她打开衣柜,抖了抖那裁剪合身的花布旗袍,上面的樟脑香让人感觉到韶华飞逝。我得顺着那旧电车铃声,在那会迷路的地方下来,推开那扇厚重的大铁门。
他们全在,等着我,一看就已等了许久:杂技女孩兰胡儿边上是燕飞飞,张天师站在石阶上,大厅另一端是魔术王子加里和所罗门王。
所罗门王说,他做了个噩梦,好久没有请人圆梦,要开口跟人说,却忘了梦。这会儿他正在想那个梦,就是发生在1945年,1945年已到了,就在眼门子上。
兰胡儿得和加里分离,他们背着困惑之极的身世之谜,在乱世一次次地从死亡中逃脱,一次比一次明白,此生不能分离。
是呀,戏就要开场,故事就如此开端。
二
面对大世界的那些楼梯,我是个胆小鬼,一个人走着时心惊肉跳。很多的声音,包括鬼声,飘入耳朵。当我跑到大世界外来远看,黄昏落日,站在天桥上吃着臭豆腐,那千妖百媚的上海呀,吸一口气,香气就钻进我身体里。
最后一次去,是在非典后,锁上了门,而且从那以后就没有再开门,干脆不营业。
他被拉了壮丁,辗转大小城市,最后停留在重庆,一生没有回来,他是我最爱的人。众所周知他是我养父。
她是他惟一的妹妹。她生得秀气,与小说中的苏姨一样不爱说话,可一说话就句句到点子上。她和他不太像,因为她是他家在饥荒时救下的孤女。
乱世之中,两人天各一方,彼此思念。她与我说得最多的是不在人世的哥哥。
梦里梦外,他俩用一颗普通人的心领我朝南走,棚户区,这儿是真正的上海百姓。我成长的贫民区山城也是如此,再穷得叮当响,入睡后还是有色彩缤飞的梦。兰胡儿和加里有这样的梦,他们和任何政治无关,虽然政治找着他们不放过他们。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只求生存下去。
三
写作这小说的一年半,开始是防盗门锁坏,叫人来修,结果弄不好,最好换掉。然后是打印机坏了,修时发现是磁头坏了,换掉。用了好多年的音响坏了,只能放磁带。只得换掉。冰箱突然一点也不发鲜,放进去的青叶子蔬菜发黄,也只能换掉。之间经历的修理与买东西的种种欺骗不能回想,坏掉的未必不是天意。写这小说,前后经过了北京重庆成都伦敦,北京、香港、德国和意大利诸多城市,突如其来的命运变故几乎毁灭了我,是精灵女孩兰胡儿救了我。
爱你就是要不顾一切。爱你到现在才知失去你可以,不能失去自己。
说句狠话真是生不如死,死不如写这两个魔术师。穿过时光之镜看见了内心冰山另一角。一个已过世法国女作家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又一艘客轮起航了。每次起航总是一个模样。每次总是载着头一次出海远航的旅客,他们总是在同样的痛苦和绝望之中和大地分离。
天已暗下来,乌云堆积。我脱了鞋,像兰胡儿一样,由着天性,抛开身后一切,升起帆,但愿雨下得别这么无情,闪电因为我远行稍稍有点儿礼貌,但愿向我挥手再见的养父和姨,泪水都咽在心里头。
九点零十分,冰雹也来了,是我离开的时候了。
曾跟兰胡儿和加里王子朝夕相处,现在他们年轻的气息还环绕在左右,他们的声音依然在梦里出现,就是昨夜,我走了很远的路,走得气喘吁吁,看见了心爱的猎犬珂赛特,跟着一个粗壮的猎人,奔忙在深山里,被追击的狼在嗅叫。冰雪如镜,映出我苍白的脸,魔术之棒上下移动,随她也随我,我们会在另外一个世界相遇。
这本书是纪念我有过的小世界。上天给的东西不能奢求太多,有一丁点就该满足,若是连这一丁点也没有,还是应该感激。现在我感激你不管你是一个人或是珂赛特追捕的猎物。
所罗门看见大岗在收拾一个架子和绳子,他很惊奇地问:怎么,你们想要玩高空飞人?
大岗说:兰胡儿差点,差点死了!他嘴笨,但说到了要害。
加里一听脸都白了,他一把去抓兰胡儿,只抓到她的长发,你没事吧。
没看见我活蹦乱跳像个蚱蜢?她甩掉他的手。
所罗门走到台下,张天师跟他大致讲了一下,讲得飞快,所罗门摇摇头,没有听懂。台上的加里给所罗门翻译了一下,说了一通。
所罗门摇摇头对张天师说:太危险,老朋友,不要弄有性命的危险游戏。我会想出办法来的。
这一天的戏还是旧节目:铜钱搭桥,加里和兰胡儿上台,接着是加里的悬空飞牌,大岗头顶瓷缸,仙女撒花兰胡儿一人演,她拿伞走绳一次,再拿司的克走一次,比以前一绿一红两少女同起同落,精彩程度差多了。
张天师和所罗门的节目在最后。两人一边照顾着后台,一边看着场子,不管大岗与小山如何起劲地敲锣打鼓,不管兰胡儿表演何种柔功,留声机放什么煽情的流行歌曲,场子里的看客比以前少得多,新客大多是第一次来大世界的小孩子们,拖着父母的手不愿意走。老客很少,他们都看过了,路过,晃一眼就走,有瘾头的老客真是比不上弹词戏文,新客又不如电影。
看来不下狠心,唐老板真会拿他们开刀,赶出大世界,弄个新班子来招客。
所罗门哪怕想着心事,也不像张天师那样露在脸上堆上眉头,他总是高深莫测地摸着他的半白胡子。这两天所罗门对兰胡儿还是不冷不热,不过对加里却没摆父王的谱。她在高高的单木凳上做柔功衔花顶碗,下面张天师的大袍戏法红花金鱼得细工慢活准备,她有意多花些功夫。木凳窄小,她转动身体,一只腿抬起,放下,另一只腿斜出,又放下。唱片放第二道,听得人心眼儿烦。
兰胡儿接过小山递上一叠碗,接碗到左脚,又接碗到右脚。平时练时用的是瓦片,上台用亮眼青花瓷碗。三叠青花瓷碗,每叠四个,正顶在她颤巍巍的头顶和双脚上。小山做了个手势,她的双脚伸开,只靠嘴咬住花,翻倒在半空中。小山和大岗从左右两侧过来。取过脚上的碗,她再用双脚捧取下头顶的碗。
这是最后一个动作:踢碗,翻身,落地,再伸手接住踢出之碗,本是最难做。她对自己说,好生稳住,等最后关头亮彩。她口衔住花里的钢架,躬起身子,随着音乐左扭右摆,等小山给信号也就是张天师准备好给小山信号,她才可以做最后的动作。
张天师那边越急越做不好,大岗今天也不知为何手脚格外迟钝,把带水的金鱼玻璃缸给张天师时,打翻了里面的机关,金鱼活蹦乱跳在地上,红花本就是绢花,只是要拾起鱼来重新放妥水。
加里在帮所罗门准备汽油之类,还有灭火器和水桶必须放在一边,这些东西缺一不可,若是万一做戏法有点漏洞,着了火,那可来不及了。
兰胡儿用牙齿咬住那么一点钢东西,整个身体悬在上面,再多一秒钟就坚持不住了,这时张天师朝小山做了一个手势,小山又朝兰胡儿做了信号。她盘在头顶的双脚,把四个青花瓷碗往高处一踢,喊一声嗨,倒翻到台上站定亮相收势,收势中右手一伸,把落下的一叠碗手里接住。这是最赢人喝彩的一招。
可这一次她觉得有点不对劲,盘弄柔功蜷翻身体时间太长了,双脚踢碗时,腿里少一把准劲,抛出的线就有点偏。
她一个后翻站定,伸出手才发觉事情非常不妙,碗斜飞出去,眼看要落到一边。
急着想落出一个漂亮的收势,若跳出一步去接那叠碗,收势就破了,如果那叠碗掉在地上,就会响亮地砸碎,满地瓷片。看客必然喝倒彩。
两难之境何弃何从?她倒翻到空中正要落地,偏偏天师班正在节骨眼上,任何失手,会有人那个监场子的人坐在下面会去报告给那个僵尸臭虫混账唐老板,哪一种砸场都会被赶出大世界。这一瞬间,她乱了方寸,如有千万颗尖针扎入般痛。
刹那间的事不容她决定,她落地做了一个漂亮的收势,展露笑容,心里备好了听到一叠瓷碗落地的满场倒彩。
就在这时,一个黑西装白衬衫白手套少年,从台侧大跳一步到台上,伸手接过正从空中落下来的一叠四个瓷碗,顺势举起,好像是早就安排好的收尾巧法。
这突如其来的结局,全场欢声雷动,连在一边还没有看出名堂的张天师和所罗门都加入座中人一片喊好之声。张天师在心里标了个尺寸,如果自己年轻十岁,恐怕这奔过去的速度,还可挽救局面,但是也抵不上加里那小子的手脚和临场变化的机智。
加里一手抱着一叠碗,一手递给兰胡儿,两人手拉手面朝看客鞠躬,在掌声中下场。兰胡儿走到后台,小山赶快把碗从加里手里接过去。张天师已在一片锣鼓声中穿着大袍精神抖擞地上场。
兰胡儿一直没有放开加里的手,正要问:你怎知我接不住那刁钻碗儿?话没说出口,她看到他一脸灿烂的笑容,突然止不住眼泪,一把抱住他哭了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哭,她没有感到什么委屈,躲过砸场的羞辱,避开了与大世界马上告别。她好像有许多哭的理由,没有一条能道清她为何这时候要哭。
加里让她的头靠在肩膀上,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就好,就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但是这样一哭一说,她忽然就觉得心里轻松了许多,刚才接碗不过是平常小事,月穿窗,云飞树,没啥可惊奇的。但是她心里回旋着一种说不出口的快乐,像是生生接了一整把天上掉下的最美妙的乾坤珠宝。
13
台子上张天师手中红花变出红金鱼来,有大岗的鼓声配合。后台里兰胡儿抬起头来,抹了一把眼泪,你总会来救我的,对不对?
加里正好也在说,你总是会来搭我一把,对吧?
他们俩都没有说完,惊喜地看着对方,忽然咯咯地笑起来,赶紧捂上嘴,那鼓声盖住了,不然全场都能听到这笑声。他们捂着嘴,弯下腰,笑着,指着对方的脸,眼睛闪闪发亮。
兰胡儿迟迟疑疑地说:难道只要我们在一起
加里接下去说:就不会有闪失。他想了想,我自己也不知道刚才怎么会跳出去的。的确,他没有练过如何处理空中接碗,甚至不清楚兰胡儿这个收势应当怎么做。他本能地朝空中一看,就明白了应当如何挽救。
而且,他想起兰胡儿做助手后,他的戏法越来越神妙,手法越做越花哨。
难道我和她加里出神地想。
兰胡儿想说什么,却没法说出口。
多少次在梦中,她听见他说:让我们一起来看美画片的人间。他和她穿过黑黑的通道,她跑不动了,他拉起她,路上不时有腊梅芬香桃花艳丽。他消失在大世界,不错,就是大世界。她焦急地找,找啊找,找到一面古铜镜子,他居然在里面,朝她伸出手臂。她踮起脚尖,羞得闭上双眼,一颗心狂跳不已。
加里低下头来,叫了一声:兰胡儿。
兰胡儿说:你的手,手心里有心。
这时他们听见所罗门在后台轻声叫加里,声音里有点不耐烦。的确,下面的四分艳尸还没有准备好道具箱子。她脸上的妆已被泪水弄糊,眼圈黑成一团,口红也淡掉,她得赶快去化妆,这具艳尸必须漂亮。
晚上收场后,兰胡儿看了一下加里,加里也在看她,两人一句话也没有说。都懂了应当留下。
等到其他人都走了,加里才说:我从来没弄过杂耍,从小还没有荡过秋千,我不知道怎么玩。
兰胡儿看着他瞧着后台那高架上垂下的绳子,他真是明白她的心思,省了她向他说这想法的功夫。她系上秋千,加里说:你先做一次,让我看。我再上来,我们一起试试。他把外套脱了。
兰胡儿点点头。
他们在里面折腾了很久,外面张天师和所罗门在场子大门缝里张望,看到两人在练飞紧张得气都不敢透。
他们互相看一眼,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还是所罗门觉得离开的好,他用手肘碰碰张天师。他们走到走廊另一头。
你是先知,无所不知,你说说这是哪门子事?张天师问。
所罗门听他话中有责备的口气,似乎是他一起隐瞒着什么秘密:我尊敬的天师,张神仙,我还等着你,告诉我是什么一个究竟!
这下僵持住了,谁也没把问题想清楚,只得往楼梯下走,所罗门走得很快,也不管张天师跟上没有,他说:只有一个可能:他们俩是
张天师急了,与他并排而行:说下去,是什么?
所罗门说,我只是猜想。
为何不说出来?张天师急了。
猜想的不算,所以,不说了!
张天师几步先下到楼梯底端,双手摊开,挡住路,非让所罗门说不可。
所罗门索性说个痛快:是你从沪西曹家渡那个人贩子买的?十多年前?他耸了一下肩,我真他妈老了,记不清他姓马或是李。
张天师急忙争辩起来:不对,我是从一个客栈主人那里买下兰胡儿的。在曹家滨,说是孤女,你知道,我们不买有家室牵连的,哪怕有卖身契,出事都不好说,我们这一行孩子活不长。他叹了一口气。
那么他们是一家子,到底是不?所罗门问。
我倒要问你从哪里买来的?张天师一步不让。
两人坐在梯子上,仔细搜刮记忆。
张天师买女孩的时间是傍晚,天未黑尽,所罗门买男孩时是漆黑天,他吃过晚饭去的。
你先买的,你看到两个小东西在一起?所罗门问。
哪会呢?人贩子不傻,他不会像卖小狗那样让我挑。我记得只说要女的四岁,五岁太大了,不好练骨架子,太小的婴儿,我一个男人家,怕养不活。张天师停了停,他一个个领出来让我看的。
糟糕,我先说好要男的。所罗门看着张天师,愁容满面地说:我们这一行收男徒,你知道的。不过我对那人说,我要六七岁当然,哪能相信人贩子。他牵来的加里,看来只有四岁样。孩子怪机灵,抓着我的腿不放,我本来不想要,可心一软,就没计较太小。
张天师沉思良久:那么你知道加里的生日吗?你总问过?
所罗门笑起来,人贩子会记下小孩生日?作罪证?我把买的那天算作加里的生日三月三十一日。
我也记得兰胡儿的生日买日,二月十日。
不是一天。所罗门松了一口气。
张天师一拍脑袋,说:糟了,怕是同一天,我记阴历!
什么阴历阳历,这样扯下去,扯不清楚。
我被你弄糊涂了。
我问你,我们这么互相盘查有什么好处?
所罗门说:真是的,好像我们犯了什么不过他没有说下去,却往回路上走,回到杂耍场子门口。在门缝时一看,招手叫跟在后面的张天师快到门缝里看。
兰胡儿与加里的秋千正恰荡成最大幅度,两人蝙蝠似的腿倒勾住秋千架,上身倒挂下来,却倒着身子拥抱在一起,想接吻,但是仅脸擦着脸一瞬间就分开,从一头猛飞到另一头。
张天师揉揉眼睛,再看。又拉下所罗门一起看。所罗门问他:怎么办?
张天师毅然举起手来轻轻敲门,他说:男女之事挡不住,五服之忌必须遵守,兄妹之伦更不能乱。
所罗门按住他的手,严厉地说:怎么就拆散?他们是不是兄妹,还没有能肯定!
先肯定不是兄妹了,才能谈别的。不然,生出儿子是天生残废。
所罗门直摇头:肯定是兄妹了,才能拆散。中国人怎么这个样?两个少年人,刚拥抱,准备接一个吻,吻还没有成,就想到生儿子了?!
他们从门缝里看到里面的两人分开了,攀回秋千架上。兰胡儿毕竟训练有素,很机灵地跳了下来。加里很兴奋,掏出一根绿方巾,手转了一圈,成了一朵玫瑰递给兰胡儿,她不好意思,把自己扎头发的红发带取下来,他把花插在她头发上。兰胡儿居然把发带交给加里,侧过身。天哪,他们在交换定情物!张天师叫道,把门敲得咚咚响。兰胡儿带着羞涩的红晕奔过来开门,看到是他们俩,高兴地喊道:
加里能演,我们能演明后天就可打大海报:加里王子与兰胡儿公主合演空中飞人!
张天师与所罗门面面相觑,一时没有话。加里过来说:父王,你就同意了吧!
兰胡儿说:其他节目我做加里助手,这个节目加里是我助手,两厢扯平,银子如何嗒嗒转父王师父商量。
所罗门断然说:我们玩戏法不玩杂耍,玩假不玩真。
父王,答应了吧!加里说。
所罗门知道天师班那个可怜的姑娘需要钱治腿,想起他和张天师在唐老板办公室受到的侮辱,他看了加里一眼,不耐烦地说:好了,收拾吧,我们早该回去了。
兰胡儿说:师父,我们这下可往那个姓唐的麻麻脸上打几颗钢钉!可是张天师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她不知这话错在哪里,她总是讨不了师父的好。
四个人在大世界门外分手,各自往自家方向走,兰胡儿和张天师过了马路,走进小街,张天师就把兰胡儿头发上的玫瑰摘了下来。
兰胡儿看着张天师,张天师手一动,花就不成样了,扔在地上。
张天师看到她眼里含着委屈的泪花,就只是说:真是没有出息,尽出我的丑!
14
燕飞飞度日如年地盼着拆右腿石膏时间。可能是伤口痊愈痒,她几乎常常到凌晨鸡叫第一遍时把兰胡儿踢下床。兰胡儿若不是有本领睡地板,肯定早被她折腾坏了。
燕飞飞说:好样的,快去师父那儿告状。
兰胡儿揉眼睛,不说话。燕飞飞伸过那只好腿,去碰兰胡儿的肩,大家都靠你挣钱,连我也要看你脸色吗?我上不了台,你才这么重要。
可是兰胡儿在地板上翻过身,闭上眼继续睡觉。眼前出现了加里拥抱她的情景,她浑身热乎乎,他想吻她,可是胆颤心惊闪开了。心里有个人的感觉竟然这般甜蜜,闭眼睁眼都会看见他。
她在师父房里见过一张发黄的照片。女子在前面,眉是眉,眼是眼,鲜花一样受看,身后站着两个豪气的青年汉子。传说若真,那女子就是苏姨,轻重瞧不出那人尖尖模样,也看不出师父曾经是那般戏里英雄。晃一个道错过一条河,人生就事事不方圆了。
大岗出来解小手,听到过一次燕飞飞半夜牢骚,他站在房门外看着阁楼。燕飞飞声音并不大,每个字都故意刺人。
大岗一直喜欢燕飞飞,但以前是一个做哥哥的喜欢。燕飞飞被唐老板整惨了之后,整个人变了样。自从她从医院回来后,那种认命的绝望,使一张本来姣美胜过月份牌美女子的脸,变得又黄又瘦。她见着他脾气更大,可是燕飞飞越是狠,大岗就越对她好。
燕飞飞自然知道大岗对自己好,可是她认为自己不配,叫那个坏男人糟蹋过了,她不能跟他好,她对他说,腿一好,她就要到江里洗掉身上那男人的臭味,再也不让任何男人碰身子。他不知怎么办?
苏姨看不下去了,说:大岗,你如果有心思,应该说出来,总不能让女孩子来求你说吧?
大岗是个憨厚人,他说他没法说出口。苏姨要他下个决心,他才说:我这人没什么本事,配不上燕飞飞,她跟了我,就得受苦。我怕说了,得罪燕飞飞。
我看你们俩是前世姻缘,贫贱夫妻,这事就让我来说吧。苏姨劝道,不过她是个苦命人,你就当对她更好一些。
从那以后,大岗就开始拼命攒钱。天师班能得一点空,他就去拉板车当苦力。上海本来就是住得人挤人,他知道这房子已挤不下。厨房是他和小山搭铺用,师父苏姨进出自己的房间都得侧着身子。怎么也挤不出一张床给他们成亲,只有他自己想办法弄钱去租个地方,哪怕是最简陋的棚屋。兰胡儿看到大岗如此辛苦,就说她愿意把房间让出来给他们,她到厨房和小山各搭一个铺将就睡就行了。
大岗坚决不同意,说兰胡儿睡不好的话,第二天演出会出事。不行,绝对不行。兰胡儿现在是天师班的挑梁角。
小山皱着眉头,突然拍了一下手,说他有主意,兰胡儿得睡好,楼下厨房给大岗和燕飞飞,他就在过道里打个地铺。
不知怎的燕飞飞听见了,远远地甩过话来:谁就能肯定我就站不起来,拆石膏后我苦练功,还能上台。话里意思一清二楚:谁就能定我的终身?大岗低垂下眼睛,苏姨脸色很难看。
兰胡儿打岔,这话字字在理。飞飞姐姐能上台。我和加里排练秋千,拿到钱就付医院正骨费。
那就先谢你兰胡儿了。燕飞飞碍着大家,从不会与兰胡儿撕破脸。
这天夜里张天师睡不着觉,苏姨却睡得很沉,翻了几转,弄醒了苏姨。要救眼下之急,就只有出秋千新招,让唐老板掏出钱来,张天师说。恐怕也只有这一个办法。
两人勾搭过了头怎么办?
这只是嫌疑。没准数的事。张天师觉得这话不通。不能让兰胡儿和加里好,好了就是害了他们。我就是看不得这两人在一块,更不得他们说话。这想法占了先。可是他耳尖,碰碰苏姨,让她听兰胡儿发出轻轻的鼾声。
睡得像小猪。苏姨说。
张天师笑了,说他可能是过虑了,小妮子生相思病,从来不会是这个样子,她给加里那红发带,小孩子办家家酒而已。
不过得仔细看他们训练,人命关天的事,不可含糊。他决定第二天让大岗和小山站在两边作保护,万一失手,还有个挡一把劲的机会。
三天后,大世界海报做了出来:
地中海加里王子
西域妖姬兰胡儿
珠联璧合大演出
特等惊险空飞人
这等夸口词,连唐老板似乎都挺满意,放在大世界大门当街口,还说:演好了,给你们画大广告牌。
张天师看完这个海报,心想他们怎么卖力气,都是为这个唐老板卖命。唐老板拿九成五,分半成给他们就算是大恩大惠了。不过如果客满,至少他就可以马上去借钱,给燕飞飞治腿要紧。
舞台地方太逼仄,张天师出个主意:把前排椅子拆掉,就在座池前面演,这样更安全一些,不容易撞到墙或其他道具,而且加上了舞台本来就有的两尺高度,做起来更宽裕。看到唐老板心情不错,张天师就向他提出这个要求。
唐老板说:好啊,有意思,新鲜!台上演到台下!他说派人来做。
没隔几分钟两个舞台工来了,帮助他们在顶棚上安装秋千绳钩扣,也将灯光调整到最佳位置。没隔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工人,帮助拆座位。
秋千飞人安排到最后一场。等一切弄妥当,秋千就长了好多,飞起来真是虎虎生风。观众从近距离看时,也亲身感到惊险万分。
兰胡儿突然发现自己第一次在这场子表演时,她和燕飞飞在门框上做的身高记号,她在光滑的门缝刻了一杠,她比燕飞飞矮一指宽,现在她高出那记号,虎口撑开也有一手掌。豆子油灯见影大小,她第一次觉得生命危如累卵:我兰胡儿其实也是怕这恶魔秋千!
危险重头戏,张天师说,必须再排练几次。排练时,所罗门也来看了,连连摇头,说这不是加里应当做的事,王子是一国之尊,不能拿宝贵身体去玩这种艺人勾当。但是一排练完,所罗门就要加里和兰胡儿跟他上一趟街。
他们排练任何节目时,都不穿上台服装,全是旧衣服,弄坏了,脱下来用针线补上。这次在绳上来回扯磨,好几个地方都撕烂了,他们像叫花子一样满身补丁。
可是叫花子不必拼命,他们在拼命,所罗门满腔感慨走在他们后面两步。
外白渡桥上这一阵子空得出奇,仿佛就他们三人。他们在他前面,年轻真好,即便在叫花子中间一站,加里也是王子相,兰胡儿,也是东方公主,而且这两个小东西在一起看上去好匹配。他们是兄妹?胡扯!那个不讲道理的天师大概请教了魔鬼。所罗门心里矛盾,他讨厌又喜欢兰胡儿,恨不得天天把加里锁在亭子间里。
过了桥到对面马路上,拐进小街就走进一家店铺。上海各种戏子艺人穷极就到那里,当出戏服。好多人拿了几个小钱,千恩万谢走了,做了回乡盘缠,很少人有机会咸鱼翻身弄了钱去赎回来。
一排排旧衣服中依次看,这种店铺霉味樟脑味,很难闻。兰胡儿在挑,加里跟着她挑。走了一圈,什么也没有看中。突然所罗门看到掌柜坐着的地方墙上,挂着两套一式鲜红的装束,看来是戏班子留下的,同样大小,可能也是给少年舞蹈演员的。扎腕扎踝甚至领口都有一道金边,缎子料,闪闪亮亮,煞是好看。他让两人去试衣:穿上紧身,显出身段。见他们试衣,掌柜的就抬价,要十元。
兰胡儿听见,气得把衣服一脱就要走,说另外一家当铺有同样货色,一元两套。
加里也说不是非要这样式,他把衣服也脱了。
掌柜不屑地说:没钱不要来啰嗦!来当铺还讲价?
所罗门还是舍不得,加里拉着他朝外走,可是那掌柜奔出门来,招手请回:好好,两元成交。
第一场演出,果然爆满。所罗门坚持把兰胡儿和加里都化妆成深鼻子高目的胡人,他亲自把两人眉毛挑高,兰胡儿嘴唇涂得鲜红,倒真是一个西域妖姬模样。场子整理一番重新开门时,观众都拥了进去,刚坐定,就看到锣鼓声中从舞台两边跑出一个红衣少年和一个红衣少女。
两人面带笑容朝观众颔首致敬后,就从两边登上梯子,同时跳上秋千。小山和大岗把梯子移走。秋千上的少年少女就开始面对面,腿交叉地站在底杠上,一伸一屈,秋千迅速荡了起来,越荡越高,古怪的西方古典音乐响起来。秋千往左升到几乎触及天花板,猛地回荡,又往右甩到不能再高的地方,再回荡,灯光照射着。看客脸往右往右,仰高,跟下,已经忙得眼睛顾不过来,这两个红衣人在空中像一道彩虹划过去划过来。
看客的心被紧张地提了起来,悬在空中。
秋千正到左边最高点,突然兰胡儿和加里一起喊了一声嗨,两人同时放开手,翻过身,跳起来又一起落在荡着的秋千上。他们依然面对面,却是用双腿倒勾在木杠上,呼啦啦快速冲过观众头顶。
这个场面把许多人吓得哇地叫起来,不是电影,是活生生的人在表演,胆子小的埋下脸,还是忍不住想看下去。
他们又听见了一声喊,兰胡儿竟然放开腿掉下来,只是沿着加里的身子滑落,靠他的双手抓住她的双手,两人成了倒挂的一串儿,从左一直俯冲下来,几乎从看客的眼前飞过,又高速冲上右边天花板。
看客中有些人,大多是女人把眼睛闭上,这样狂飞的少女,只靠两人手抓住,万一没抓紧飞出去,肯定摔成血饼,可怜如此年纪做短命鬼。
正在这时,兰胡儿嗨地一声,加里松开她的手,她再次在空中翻转过来,他马上抓住她翻递过来的脚。
可是,加里的手没有抓得牢兰胡儿的左脚,只有右腿在他手里,她歪斜过来,马上就要飞出去。看客大声惊叫,有的人似乎要夺门而去。那些胆大好奇的仍要看下去:在悬吊在快松开的一只手上,兰胡儿来回飞了两个来回之后,竟突然恢复了平衡,她的脚递了回去,加里伸出手一把抓住。全场透出一口气,响起激动的掌声。
那些害怕得大叫的人热泪盈眶,全场都在说:真是想不到,太险了!太好看了!吓死我了!他们拍得手都痛了,还在使劲地拍。
当他俩终于重新站在木杠上时,秋千渐渐荡平,大岗和小山走出来,把梯子架起,把两个人接下来。看客里不少人走上台去,摸摸这两人究竟是不是真人,他们回过头来,对台下说:哎呀,他们不是铁皮做的假人。这话又引起一阵兴奋的笑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