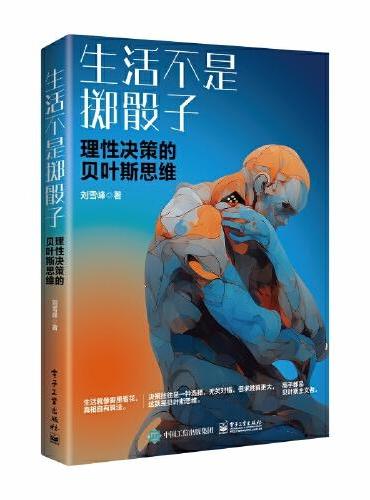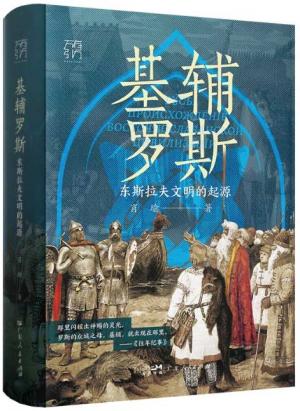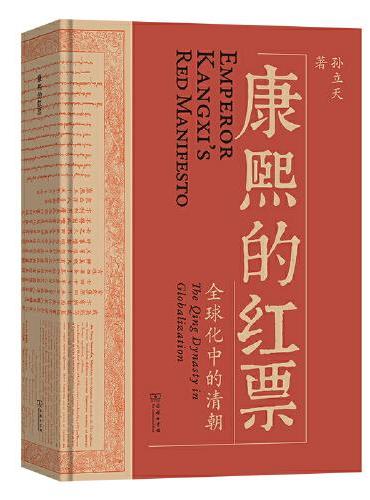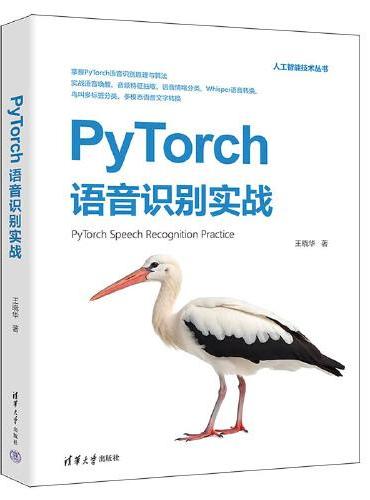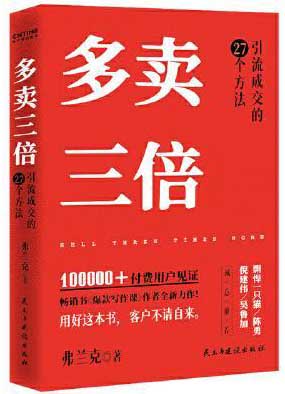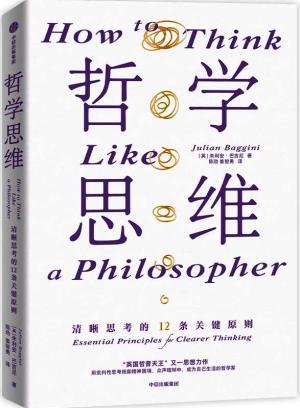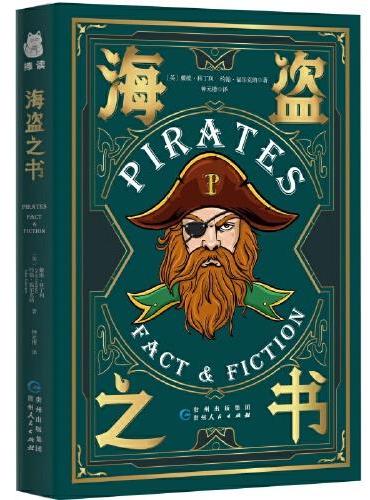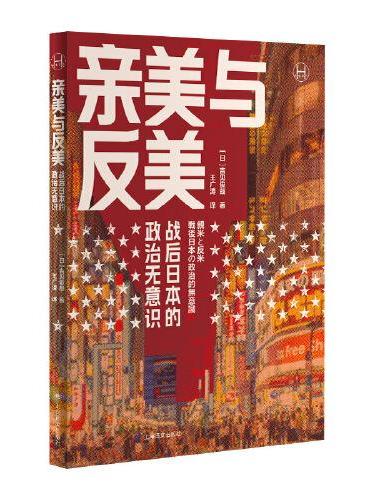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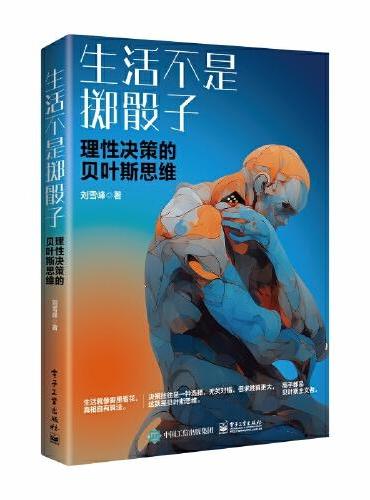
《
生活不是掷骰子:理性决策的贝叶斯思维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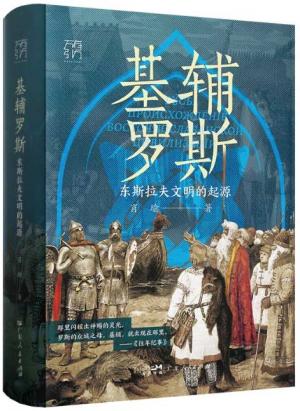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
》
售價:NT$
6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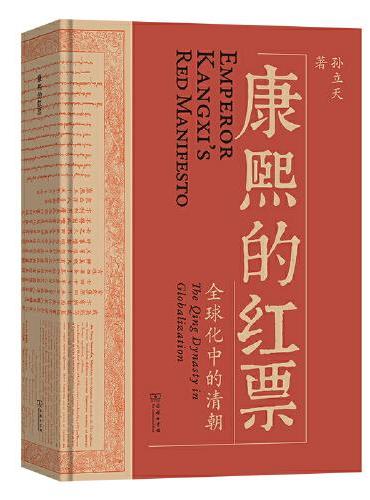
《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售價:NT$
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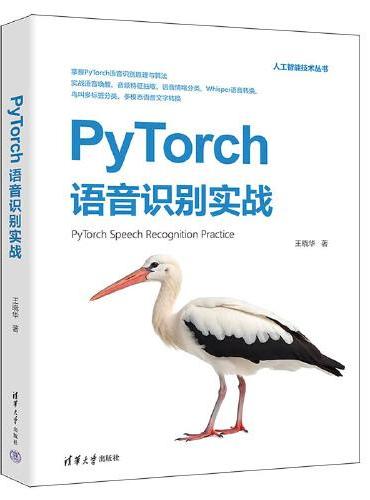
《
PyTorch语音识别实战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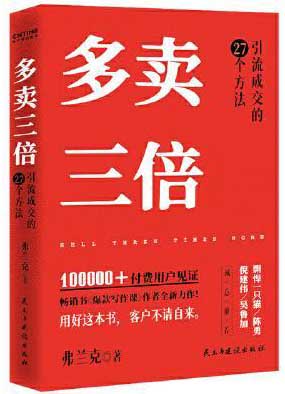
《
多卖三倍
》
售價:NT$
2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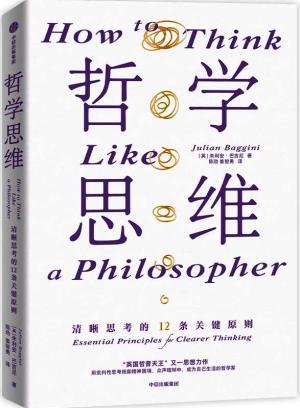
《
哲学思维:清晰思考的12条关键原则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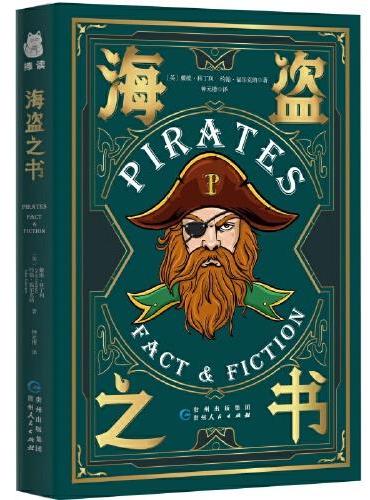
《
海盗之书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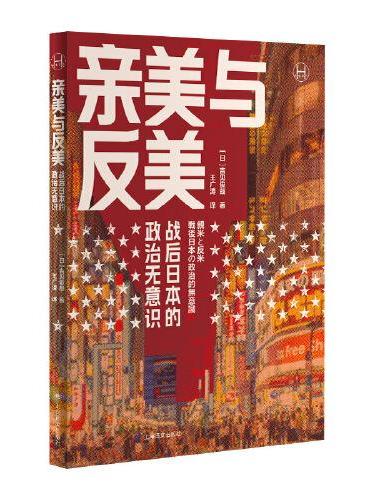
《
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
》
售價:NT$
325.0
|
| 編輯推薦: |
|
本书引人入胜地描写了泽尔达菲茨杰拉德及其所在的传奇圈子。作者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泽尔达而不是她更为出名的丈夫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更加公正地描绘了泽尔达的生活,而这也正是泽尔达穷其一生想要听到的声音。
|
| 內容簡介: |
|
泽尔达被菲茨杰拉德彻底摧毁的女人。 泽尔达留着短发,大胆而新潮,纵情于这个狂野的世界。 她和菲茨杰拉德去过的每个地方都变得人潮拥挤:纽约、长岛、好莱坞和法国里维埃拉。 他们无休止地参加迷人派对,包括注定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斯坦恩、萨拉、毕加索、庞德 派对无法永远持续下去。除了是知名作家菲茨杰拉德的妻子以外,泽尔达还是天才的作家、画家、芭蕾舞演员。但是,傲慢自私的丈夫毁了她,将她灵光四溢的日记抄袭进自己的小说,导致她的才华被否认,身心被摧残,直到去了精神病院 这,就是令人无法抗拒的泽尔达的故事。
|
| 關於作者: |
|
特雷泽安妮福勒,美国作家,拥有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学士学位及基础写作硕士学位。她的作品曾获得福克纳学会奖和托马斯沃尔夫小说奖。在离开学术界进行全职写作前,她曾做过助理编辑并教授过大学小说创作课程。作者是土生土长的伊利诺伊州人,作者现居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 刘昭远,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英语专业,专职翻译、写作,有翻译代表作《别对我撒谎》(广西科技出版社)、《特别的他》(四川文艺出版社)等。
|
| 目錄:
|
|
前言 001第一部 067第二部 211第三部 275第四部 327第五部 376 编后记 379 作者按
|
| 內容試閱:
|
|
第一部 如果不让水浸没你的头顶,你又怎会知道自己有多高? T.S.艾略特 1 想象一下,1918年六月底的一个清晨,那时的蒙哥马利城穿着她最美丽的春装,喷上了最好的香水与我那天夜里的打扮如出一辙。幸福大道上坐落着一幢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那是我们的屋子。覆盖在屋上的是绽放出白色花骨朵儿的络石藤和牵牛花。那是一个周六,时间还很早,屋外乌云重重。鸟儿们聚集在巨大的玉兰树上,它们扯着嗓子高唱着,像是要一争高下,在周日合唱团中夺取独唱者的位置。 我从后楼梯的窗户望去,见到一匹马儿步履缓慢地拉着一架摇摇摆摆的马车。马车之后跟着两个黑人女子,她们将自己所贩卖的蔬菜的名称高唱出来。甜菜!香豌豆!甜菜!她们的歌声比鸟儿还要响亮。 嘿,凯蒂。我朝厨房喊了一声。贝斯和克拉拉在外面呢,你听见她们的声音了吗?大木桌上摆着一只被洗碗巾盖上的盘子。这是什么?我满怀希望地问道,伸手想要从洗碗巾下掏出一块饼干。 是奶酪。好了,别摆出那副表情。凯蒂说着拉开了门,朝她的朋友们挥手喊道,今天什么也不买!随后她转身对我说:生活不可能每一天都一帆风顺,甜如蜜饯的。 茱莉亚老阿姨说过蜜饯是唯一一件能帮我抵御魔鬼的东西。我将饼干塞进嘴里,满嘴鼓囊囊的。先生和太太还在睡觉吗? 他们都在客厅呢。我看见您用了后楼梯,以为您早就知道了呢。我将饼干放到一旁,把我蓝色裙子的腰带又绕了一圈,让我光秃秃的脚踝多露出一寸。这样就好了。 也许我真应该给您准备一份蜜饯。凯蒂摇着头对我说,您至少应该把鞋穿上。 天气太热了再说如果下雨的话,我的鞋子会被浸湿,脚趾会皱起来,脚上的皮肤也会脱落,那样的话我就没有脚指头了,所以我才不要穿鞋呢,我今天晚上还要表演芭蕾舞独舞呀。 我要是以这副样子出现在公共场合,我妈妈可会用鞭子抽我。凯蒂像母鸡一样咯咯叫唤着。 她才不会呢。你都已经三十岁了。 您认为她会在意这些吗? 我知道我的父母至今仍会给我的三个姐姐和我的哥哥建议和加以管教,而他们中最小的比我都要年长七岁。他们均已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除了罗萨琳德,我们都管她叫亲爱的。和蒂尔德姐姐的丈夫约翰一样,她的丈夫纽曼正在法国战场上服役。要想为人父母,亲爱的他们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我又想起我的祖母穆西朵拉,想到她和我们同住时,凡是涉及爸爸,事无巨细皆要插手:从他的发型到他的治家之法。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离开你的父母,躲得远远的。 不管怎样,无所谓了。我一边说一边走向后门,确信自己逃脱在即,只要没人看见我 宝贝!妈妈的声音自我们身后的走廊飘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她惊呼道,你的鞋袜去了哪里? 凯蒂突然惊呼:我的乖乖,我刚想起来我们的萝卜不够用了。说完她赶紧出了门。 我只是 赶紧回房间穿戴整齐,你别指望可以这样到镇子里去! 我又不去镇里。我撒谎道,只是去一趟果园,我要为今晚的表演练习。我展开双臂做了个优雅的屈膝。 哦,亲爱的,那是当然。可你已经没时间练习了,不是说红十字会的会议九点钟开始吗? 什么时候?我转身看着钟表,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我赶紧从妈妈身边奔开,直奔上楼,嘴里喊着。我还是穿上鞋离开这儿好了! 别和我说你没穿紧身衣!妈妈喊道。 亲爱的出现在楼上的走廊里,身上还穿着睡衣,头发也未梳理过,眼中满是困意。怎么了? 纽曼今年秋天将要结束在法国的战争,随着潘兴将军的部队归国。亲爱的搬回了家,等着纽曼归国。如果他回得来的话。她阴郁的抱怨惹来了爸爸严肃的目光我们都管爸爸叫法官,他是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你要骄傲一些。他对亲爱的训斥道,无论结局如何。纽曼是为了南方的荣誉而战斗。而姐姐的回答是:爸爸,看在老天的分上,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了。 我对亲爱的回答。按照女皇大人的意思,我大概少穿了些衣物。 是真的,宝贝。你若是没穿紧身衣,男人们会认为你 淫荡? 没错。 也许我不在乎呢。我说,当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战争委员会说不用再穿束身衣他们说的是别再去买束身衣,不过这倒是个不错的借口。她随我进了我的卧室,就算你不在乎大众习俗,你也该替自己想一想。万一法官知道你半裸着出了门,他定会叫你藏起来的。 我也想着为自己着想,我说着脱下衬衫。可你们所有人都要介入我的生活。我下楼时妈妈仍在厨房里。比刚才好一些了。现在把裙子整理好。 她指向我的腰间。 不,妈妈。这会在我跑步时阻碍我。 赶紧整理好吧。我可不能毁掉法官的好名声,就为了让你跑快一些。 今天早晨所有人都在帮忙维护他的名声。再说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挑剔了? 这可事关颜面。你已经十七岁了 再过二十六天就十八了。 没错,这更是证明了我要说的话。她说,你已经不能再做个假小子了。 你可以叫我时尚样板。女孩儿们的裙边将会越来越高,这是我在《麦考尔》上读到的。 妈妈指着我的裙子说:可没有这么高。 我亲吻了她日渐松弛的下巴。再多的面霜和化妆粉都掩盖不了时间在妈妈脸上留下的印记。她已过四十四岁,岁月尽显在她皱纹丛生的脸上、她朝上梳的发型中、她对在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制衣厂生涯的忠诚里以及她的拖地长裙上。她拒绝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打仗呢。 她总会这样说,好像这话能够解释一切。当她好不容易在新年放弃裙撑时,我和亲爱的简直再骄傲不过了。 我说:够了,妈妈别等我吃午饭了,我要和姑娘们一同到外面吃饭。 我刚脱离妈妈的视线就坐到草地上脱掉鞋袜,还脚趾以自由。真糟糕。我暗自感叹着,我本人的自由为何就没那么容易获得! 当我前往德克斯特大道时,远处的天空电闪雷鸣。宽阔的大道一直延伸到半球形的州议会大厦,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壮观的建筑。我哼唱着等会儿将要表演的时光之舞,在草叶、湿苔藓和即将腐烂的梓木花的香味中蹦蹦跳跳。 芭蕾舞在那时是我的一项真爱。我初涉芭蕾是九岁那年。妈妈把我送去了温尼斯特教授的舞蹈学校她还以为这样就能将我从屋顶和树上拽下来。芭蕾的音乐和舞步是那样欢快、激情、浪漫,富有戏剧性,囊括了我对人生全部的渴望。我记得芭蕾中的装束、故事、表演桥段以及能让我不仅仅是小姑娘赛尔的可能性尤其是最后一条。我永远都在等待自己长到足够的年龄,我永远都盼着我能长大。 我经过米尔德里德街,就在它和赛尔街的交叉口没错,这条街道是以我家命名的。一滴雨滴在我的脸颊上,又有一滴落在我的前额,之后上帝打开了水龙头。我奔向最近的一棵树,躲在树枝下,不过这对我几乎没什么帮助。狂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树叶。暴雨如注,我瞬间就被淋湿了。当我全身已经湿到不能再湿的时候,我选择继续前行,将树木想象成剧团中摇摆的舞者,把自己想象成历经千辛万苦才从魔法师手中逃出来的孤儿。我也许会在森林中迷路,然而作为最优秀的芭蕾舞者,我的前方一定有一位王子在等待。 法院路与德克斯特大道的交会处有一座圆形喷泉,我倚靠在栏杆上,摇头将脑袋上的水甩干。几辆湿透的汽车顺着林荫大道驶离,有轨电车在轨道上咔嚓咔嚓地摇摆着,从我身边驶过。我真想把湿透的鞋袜扔进喷泉里,这总好过将它们湿漉漉地穿在脚上吧。可我转念一想十八岁,还有二十六天就到了,于是又将那该死的玩意儿穿了回去。 无论是否严格,我还是保持了得体的穿着礼仪。我在街道上走着,朝坐落在德克斯特大道林立商铺中的红十字会新办公室走去。虽说先前如注的暴雨现已停歇,人行道上却仍是行人寥寥,没多少人能见到我这狼狈的模样。这倒是能让妈妈开心。她总会担心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在心中抱怨,和所有女人一样。女孩们总有太多的规矩要遵守,还有太多关于仪容仪表的约束。腰背要笔挺精神,双手要戴好手套,嘴唇不可涂上颜色(亦不能被人亲吻),紧身裙万不可少,言谈举止要文雅端庄,双目要时刻规矩地低垂,思想则必须纯洁无瑕。而在我看来,都是些鬼话。男孩们之所以喜欢我就因为我可以和他们互射口水弹,因为我可以开没头没脑的玩笑;如果他们身上是我喜欢的好闻的味道,我也可以让他们吻我。我的判断标准均以好感为基准,而非旅鼠们的逻辑。抱歉了,妈妈,你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了。 二十位志愿者聚集在红十字会,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见到我时,几乎没有人因为我的状态露出半点惊讶。只有我的姐姐玛乔莉,她原本正捧着小册子和点心四处奔走,一见到我就开始大惊小怪。 宝贝,你的样子真可怕!你怎么没戴帽子?她想要理顺我的头发,尝试过后又宣告放弃。真是没法子。给你。她将一块毛巾递给我。赶紧擦干净。这里其实没那么需要志愿者,让我把你送回家吧。 别担心了。我用毛巾在脑袋上胡乱擦着。我知道她仍会继续担心下去的。我出生的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她在结婚前几乎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位母亲。她婚后搬去了一幢离父母家仅有两个街区的房子,然而她婚前形成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我将毛巾绕在她的脖子上,打算给自己找个座位。 我那时最好的朋友埃莉诺布劳德正坐在一张长桌前,省了我的一番寻找。我的左侧坐着莎拉 梅菲尔德我们管他叫莎拉二号。莎拉一号是我们的莎拉哈尔特,她这时候去了巴尔的摩的一所大学念书。莎拉二号和利维哈特是搭档,哈特光滑的、桃木色的头发和我的朋友塔卢拉班克何德 a的头发几乎一样好。十五岁那年,塔卢拉的那头乌发为她赢得了一场选美比赛,而现在她想要通过这场胜利为自己在纽约谋得一份职位。她和她的那头秀发四处旅行,虽说我热爱着蒙哥马利,可我仍是好生羡慕。肯定没人会管塔卢拉的裙子该有多长。等待会议开始的时间内,女孩们在密不透风的室内不停地给自己扇 风。我们的四周竖立着杏黄色的高墙,墙上都张贴有红十字会的海报。一张海报上印着一只装有纱线和编织针的柳条篮,这是在劝告读者我们的儿郎们需要短袜。请多织些袜子。另一张海报上是一幅鲜明的红十字标志,标志的一旁则印着一位护士,她穿着长裙和大袍子,而这衣服似乎没那么便于工作。护士拖着一副直角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受伤的战士,一块黑色的毯子盖住了战士与担架。从画面的角度来看,海报中的女战士简直像个巨人而那战士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从担架上滑下来,如果那护士不将自己的目光从远方转移回手头的事,他的脚就要滑下来了。图片的下方印着一行宣传语: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我用手肘捅了捅莎拉,又指向那张海报。你是怎么看的?她是不是个处女妈妈? 她没来得及回答。湿地板上传来一阵拐杖的敲击声,我们都转身望向矮胖的、身着铁灰色束腰套装的贝克太太。这是一位让人敬畏的太太,她专程从波士顿来到这儿,就为了指导志愿者们。如果有人将她送上去法国的船,这位女士似乎能凭着一己之力赢得战斗。 大家早上好啊。她用慢吞吞的,带着鼻音的语调说,我看你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我们的新办公地。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事实上,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扩大规模提高效率。 几个女孩发出欢呼声,她们是刚加入不久的新人。贝克太太点点头,这使得她的下巴短时间内缩进了脖子里。之后她继续说道:你们中已有些人学会了手指和手臂的包扎,腿部与身体的包扎与其原理相同。然而我们在处理伤口和照料病人的过程中仍要注意其他的不同之处。对于那些未接受过训练的志愿者来说,我将会从最基础的说起。我们首先从原色绷带开始说起。 贝克太太说起了绷带的长度、宽度和张力,并开始做示范,我则趁机挤干裙边的雨水。她将一根松松垮垮的布条递给离她最近的一个女孩,站起来,亲爱的。我要让你们分成两组,一组为包扎者,另一组为被包扎者。而包扎者的大拇指一定要放在绷带的上端,像这样,将食指抵在下面。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的手指始终要紧贴着绷带卷,大拇指要拉到最紧。大伙儿开始吧。 我从身后的一排篮子中取出一卷松松散散的绷带。它此刻还是纯白的,当然了,可它有可能很快便被鲜血浸透,沾上尘土,并将无可避免地惹来苍蝇。我见过这样一张照片,南北战争时期的军人们就遭受了这样的劫难,书本上描绘出了爸爸口中的美利坚联邦对我们施下的暴行。 我哥哥托尼比我年长七岁,如今正在法国服役。爸爸本打算用书本知识和人与人之间的探讨教育他。不过爸爸也从未将我赶出过客厅。我可能正在弹奏着简单的曲子,而他会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腿上。赛尔家在蒙哥马利有一段让人骄傲的历史。他翻动着书页说,你瞧。这是我伯伯威廉的老宅,他和他弟弟丹尼尔,也就是你爷爷都在这幢房子里长大。它后来变成了第一座南方联盟的白宫。 赛尔街就是以我们命名的对吗?爸爸?时年七八岁的我满心好奇地问。 那是为了纪念威廉和我父亲。是这两个男人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今天的样子,我的孩子。 托尼似乎将赛尔家的家族史当作理所当然,可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已然故去的先人,不停问着他们在何时做过些什么。我想要的是故事。 从爸爸那儿,我得知了他父亲,丹尼尔赛尔的故事。他创立了《塔斯基吉 报》,之后又回到蒙哥马利,参与编辑了《蒙哥马利邮报》,使其成了在本地政治方面颇有影响力的一种声音。爸爸还对我说了他母亲的兄弟:伟大的约翰泰勒摩根将军,他一有机会就会袭击北方军队,后来还成为了杰出的美国参议员。我还从妈妈那儿了解到了她的父亲,威利斯梅钦。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他和摩根参议员的友情也促成了我父母1883年新年夜里在摩根议员家舞会上的见面。 在红十字会的我不禁思量着,我们的家族历史对于托尼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负担,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压迫。也许这也是他之所以会娶来自佃农家庭的伊迪丝,婚后又离开蒙哥马利,四处漂泊的原因。作为家族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他并非爸妈的长子,不是以爷爷的名字命名的,肩上担负着蒙哥马利命运的儿子,他不是那个十八个月大就死于脑膜炎的儿子好吧,这可是个沉重的笑话。 我拆开白布包,将思绪转移回来,将绷带的末端递向埃莉诺。我昨天收到一封亚瑟布伦南写来的信。我说,还记得他吗?我们上次去亚特兰大认识的? 埃莉诺皱着眉,注意力都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她正想着要如何开始。是大拇指在下,还是食指在下? 食指。亚瑟家自大革命时期起就是做棉花生意的。他们家还留着一些不愿意离开的老黑奴呢。我爸爸说这证明了林肯总统毫无缘由地毁掉了南方。 埃莉诺成功地将绷带转了几个圈,然后抬起头。那个开着绿色多特车的亚瑟?我们一起坐进过那部闪亮的宝贝? 就是他。多棒啊。亚瑟说多特要比福特贵上两倍要贵一千块,也许更多。要是见到别人将那么多钱花在一部车上,法官一定会气得在法院门口裸着身子跳舞的。 这一想法将我自己逗乐。我继续向埃莉诺输送着绷带。我想象着爸爸身着条纹西装,手中拿着收拢的雨伞和皮包,从有轨电车中下来。他见到法院石阶门口停着一辆绿色多特,引擎盖光滑闪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连汽车的油门都闪着光彩。一位男士戴着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他就是恶魔的代表。他会将爸爸召唤到车边,他们之间将会有一段对话。爸爸将会摇着脑袋皱眉头,还会在空中挥动他的雨伞。他会举起一根手指,武断地向人家宣扬所谓的相对价值,又将铺张浪费的危害细数一番。那个戴礼帽的男人将会坚定地摇头,驱车而去,逼得爸爸别无选择,只能当即脱掉衣服开始跳舞。 在我想象的版本中,我不再让父亲的尊严占上风。而现实生活中,我从未见过哪个男人不穿衣服可我见过少年们的身体。我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品中见到的我想那些应该足够有代表性了。 说到裸露。埃莉诺将身子探过来,从我手中拿走最后一段绷带。 昨天夜里在电影院里,有个飞行员温德尔哈斯金斯,向我求证了一个流言的真伪。他问我你是不是真的穿着肉色的游泳衣大摇大摆地进了泳池。他明明是和梅 斯坦纳一起来看电影的,却问起了你的情况,这多有意思啊。梅当时正在贩卖部,也就没听见他这样问,不过他能这样做倒还是有几分绅士气的。 莎拉在一旁说着:我真希望我那天也在泳池边,真想看看那些老女人的表情。 去年冬天,泽尔达将一束槲寄生 a别在裙子上的时候,你在那舞会上吗?利维哈特问。 周三那天你们真应该加入我们。埃莉诺对大家说, 泽尔达趁着司机在角落里抽烟的时候抢占了他的汽车。我们将他气得吹胡子瞪眼,在裴瑞街上打滚! 我敢发誓,泽尔达。你什么有趣的事都经历过了!莎拉感叹道,却从未惹上过任何麻烦! 埃莉诺在一旁补充道:所有人都害怕她爸爸,所以他们只是对她挥挥手指,让她赶紧离开。 我点点头。即便是我的姐姐们都害怕他。 可你不害怕。利维哈特说。 他吠叫的时候远多过咬人的时候。所以埃莉诺,你是怎样和哈斯金斯击掌说的? 我说:别告诉任何人,机长,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泳衣。利维冷哼了一声。我说。你瞧,埃莉诺,这就是我之所以喜欢你的原因了。继续保持,用不了多久那些中年女人也会管你叫小恶魔了。 埃莉诺伸手从桌上的碗里拿出一根别针,将绷带底部固定好。他还问我你有没有哪个相好的情郎,你有哪些相熟的朋友,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也许他只是在找借口和你聊天呢,埃莉诺。莎拉突然这样想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至少也能想到一至两个关于我的问题吧。埃莉诺对莎拉温柔地笑道。不,他所关注的只有幸福大道六号楼的泽尔达赛尔小姐,爱慕她的芭蕾舞鞋和天使之翼。 还有魔鬼的笑容。利维补充道。 还有纯净的心。莎拉说。听了这话我赶紧做出呕吐的表情。 他说他不是真心待梅的,埃莉诺继续说,还有,他想要给你打电话。 他已经打过电话来了。 可你并没有答应他呀。 可是到今年秋天为止,我的日程都已经订满了。有那么多躲过了服役的大学男生,还有成群的来蒙哥马利军事中心受训的军官。有太多男人对我感兴趣,我已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莎拉握起我的手。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就不要再等下去了。你明白的,他们可能随时都会离开蒙哥马利。 没错。埃莉诺附和道,要么是现在就去相会,要么是永别。 我把手从莎拉手中抽出来,又从身后的篮子里拿来一卷绷带。再告诉你一遍,以防你没听过这个消息。我们在打仗呢!人们的感情随时都有可能告终,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话是这样说,但这从前也没能阻止你和那些军人们见面啊。要知 道这个男人可是英俊得没边儿 我知道他英俊。待他下次打来电话,也许我会 等会儿再聊天,姑娘们。贝克太太漫步到我们身旁。她将双手背在身后,胸部直挺着,像是军舰的舰首。你们的事也许很重要,但我们勇敢的小伙子们会感激你们为他们付出的速度与细心的。 待贝克太太走后,我歪着脑袋,假装自己是玛丽碧克馥,用前臂挡住眼睛哀叹着,哦!真是羞耻! 第一部 如果不让水浸没你的头顶,你又怎会知道自己有多高? T.S.艾略特 1 想象一下,1918年六月底的一个清晨,那时的蒙哥马利城穿着她最美丽的春装,喷上了最好的香水与我那天夜里的打扮如出一辙。幸福大道上坐落着一幢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那是我们的屋子。覆盖在屋上的是绽放出白色花骨朵儿的络石藤和牵牛花。那是一个周六,时间还很早,屋外乌云重重。鸟儿们聚集在巨大的玉兰树上,它们扯着嗓子高唱着,像是要一争高下,在周日合唱团中夺取独唱者的位置。 我从后楼梯的窗户望去,见到一匹马儿步履缓慢地拉着一架摇摇摆摆的马车。马车之后跟着两个黑人女子,她们将自己所贩卖的蔬菜的名称高唱出来。甜菜!香豌豆!甜菜!她们的歌声比鸟儿还要响亮。 嘿,凯蒂。我朝厨房喊了一声。贝斯和克拉拉在外面呢,你听见她们的声音了吗?大木桌上摆着一只被洗碗巾盖上的盘子。这是什么?我满怀希望地问道,伸手想要从洗碗巾下掏出一块饼干。 是奶酪。好了,别摆出那副表情。凯蒂说着拉开了门,朝她的朋友们挥手喊道,今天什么也不买!随后她转身对我说:生活不可能每一天都一帆风顺,甜如蜜饯的。 茱莉亚老阿姨说过蜜饯是唯一一件能帮我抵御魔鬼的东西。我将饼干塞进嘴里,满嘴鼓囊囊的。先生和太太还在睡觉吗? 他们都在客厅呢。我看见您用了后楼梯,以为您早就知道了呢。我将饼干放到一旁,把我蓝色裙子的腰带又绕了一圈,让我光秃秃的脚踝多露出一寸。这样就好了。 也许我真应该给您准备一份蜜饯。凯蒂摇着头对我说,您至少应该把鞋穿上。 天气太热了再说如果下雨的话,我的鞋子会被浸湿,脚趾会皱起来,脚上的皮肤也会脱落,那样的话我就没有脚指头了,所以我才不要穿鞋呢,我今天晚上还要表演芭蕾舞独舞呀。 我要是以这副样子出现在公共场合,我妈妈可会用鞭子抽我。凯蒂像母鸡一样咯咯叫唤着。 她才不会呢。你都已经三十岁了。 您认为她会在意这些吗? 我知道我的父母至今仍会给我的三个姐姐和我的哥哥建议和加以管教,而他们中最小的比我都要年长七岁。他们均已成人,都有了自己的孩子除了罗萨琳德,我们都管她叫亲爱的。和蒂尔德姐姐的丈夫约翰一样,她的丈夫纽曼正在法国战场上服役。要想为人父母,亲爱的他们还得等上一段时间。我又想起我的祖母穆西朵拉,想到她和我们同住时,凡是涉及爸爸,事无巨细皆要插手:从他的发型到他的治家之法。唯一的解决之道只有离开你的父母,躲得远远的。 不管怎样,无所谓了。我一边说一边走向后门,确信自己逃脱在即,只要没人看见我 宝贝!妈妈的声音自我们身后的走廊飘来。看在老天的分上,她惊呼道,你的鞋袜去了哪里? 凯蒂突然惊呼:我的乖乖,我刚想起来我们的萝卜不够用了。说完她赶紧出了门。 我只是 赶紧回房间穿戴整齐,你别指望可以这样到镇子里去! 我又不去镇里。我撒谎道,只是去一趟果园,我要为今晚的表演练习。我展开双臂做了个优雅的屈膝。 哦,亲爱的,那是当然。可你已经没时间练习了,不是说红十字会的会议九点钟开始吗? 什么时候?我转身看着钟表,只剩下二十分钟了。我赶紧从妈妈身边奔开,直奔上楼,嘴里喊着。我还是穿上鞋离开这儿好了! 别和我说你没穿紧身衣!妈妈喊道。 亲爱的出现在楼上的走廊里,身上还穿着睡衣,头发也未梳理过,眼中满是困意。怎么了? 纽曼今年秋天将要结束在法国的战争,随着潘兴将军的部队归国。亲爱的搬回了家,等着纽曼归国。如果他回得来的话。她阴郁的抱怨惹来了爸爸严肃的目光我们都管爸爸叫法官,他是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你要骄傲一些。他对亲爱的训斥道,无论结局如何。纽曼是为了南方的荣誉而战斗。而姐姐的回答是:爸爸,看在老天的分上,现在已经是二十世纪了。 我对亲爱的回答。按照女皇大人的意思,我大概少穿了些衣物。 是真的,宝贝。你若是没穿紧身衣,男人们会认为你 淫荡? 没错。 也许我不在乎呢。我说,当今的一切都不一样了。战争委员会说不用再穿束身衣他们说的是别再去买束身衣,不过这倒是个不错的借口。她随我进了我的卧室,就算你不在乎大众习俗,你也该替自己想一想。万一法官知道你半裸着出了门,他定会叫你藏起来的。 我也想着为自己着想,我说着脱下衬衫。可你们所有人都要介入我的生活。我下楼时妈妈仍在厨房里。比刚才好一些了。现在把裙子整理好。 她指向我的腰间。 不,妈妈。这会在我跑步时阻碍我。 赶紧整理好吧。我可不能毁掉法官的好名声,就为了让你跑快一些。 今天早晨所有人都在帮忙维护他的名声。再说了,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挑剔了? 这可事关颜面。你已经十七岁了 再过二十六天就十八了。 没错,这更是证明了我要说的话。她说,你已经不能再做个假小子了。 你可以叫我时尚样板。女孩儿们的裙边将会越来越高,这是我在《麦考尔》上读到的。 妈妈指着我的裙子说:可没有这么高。 我亲吻了她日渐松弛的下巴。再多的面霜和化妆粉都掩盖不了时间在妈妈脸上留下的印记。她已过四十四岁,岁月尽显在她皱纹丛生的脸上、她朝上梳的发型中、她对在爱德华七世时期的制衣厂生涯的忠诚里以及她的拖地长裙上。她拒绝尝试任何新鲜事物。我们在打仗呢。 她总会这样说,好像这话能够解释一切。当她好不容易在新年放弃裙撑时,我和亲爱的简直再骄傲不过了。 我说:够了,妈妈别等我吃午饭了,我要和姑娘们一同到外面吃饭。 我刚脱离妈妈的视线就坐到草地上脱掉鞋袜,还脚趾以自由。真糟糕。我暗自感叹着,我本人的自由为何就没那么容易获得! 当我前往德克斯特大道时,远处的天空电闪雷鸣。宽阔的大道一直延伸到半球形的州议会大厦,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壮观的建筑。我哼唱着等会儿将要表演的时光之舞,在草叶、湿苔藓和即将腐烂的梓木花的香味中蹦蹦跳跳。 芭蕾舞在那时是我的一项真爱。我初涉芭蕾是九岁那年。妈妈把我送去了温尼斯特教授的舞蹈学校她还以为这样就能将我从屋顶和树上拽下来。芭蕾的音乐和舞步是那样欢快、激情、浪漫,富有戏剧性,囊括了我对人生全部的渴望。我记得芭蕾中的装束、故事、表演桥段以及能让我不仅仅是小姑娘赛尔的可能性尤其是最后一条。我永远都在等待自己长到足够的年龄,我永远都盼着我能长大。 我经过米尔德里德街,就在它和赛尔街的交叉口没错,这条街道是以我家命名的。一滴雨滴在我的脸颊上,又有一滴落在我的前额,之后上帝打开了水龙头。我奔向最近的一棵树,躲在树枝下,不过这对我几乎没什么帮助。狂风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树叶。暴雨如注,我瞬间就被淋湿了。当我全身已经湿到不能再湿的时候,我选择继续前行,将树木想象成剧团中摇摆的舞者,把自己想象成历经千辛万苦才从魔法师手中逃出来的孤儿。我也许会在森林中迷路,然而作为最优秀的芭蕾舞者,我的前方一定有一位王子在等待。 法院路与德克斯特大道的交会处有一座圆形喷泉,我倚靠在栏杆上,摇头将脑袋上的水甩干。几辆湿透的汽车顺着林荫大道驶离,有轨电车在轨道上咔嚓咔嚓地摇摆着,从我身边驶过。我真想把湿透的鞋袜扔进喷泉里,这总好过将它们湿漉漉地穿在脚上吧。可我转念一想十八岁,还有二十六天就到了,于是又将那该死的玩意儿穿了回去。 无论是否严格,我还是保持了得体的穿着礼仪。我在街道上走着,朝坐落在德克斯特大道林立商铺中的红十字会新办公室走去。虽说先前如注的暴雨现已停歇,人行道上却仍是行人寥寥,没多少人能见到我这狼狈的模样。这倒是能让妈妈开心。她总会担心一些奇怪的事情,我在心中抱怨,和所有女人一样。女孩们总有太多的规矩要遵守,还有太多关于仪容仪表的约束。腰背要笔挺精神,双手要戴好手套,嘴唇不可涂上颜色(亦不能被人亲吻),紧身裙万不可少,言谈举止要文雅端庄,双目要时刻规矩地低垂,思想则必须纯洁无瑕。而在我看来,都是些鬼话。男孩们之所以喜欢我就因为我可以和他们互射口水弹,因为我可以开没头没脑的玩笑;如果他们身上是我喜欢的好闻的味道,我也可以让他们吻我。我的判断标准均以好感为基准,而非旅鼠们的逻辑。抱歉了,妈妈,你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了。 二十位志愿者聚集在红十字会,他们大部分都是我的朋友。他们见到我时,几乎没有人因为我的状态露出半点惊讶。只有我的姐姐玛乔莉,她原本正捧着小册子和点心四处奔走,一见到我就开始大惊小怪。 宝贝,你的样子真可怕!你怎么没戴帽子?她想要理顺我的头发,尝试过后又宣告放弃。真是没法子。给你。她将一块毛巾递给我。赶紧擦干净。这里其实没那么需要志愿者,让我把你送回家吧。 别担心了。我用毛巾在脑袋上胡乱擦着。我知道她仍会继续担心下去的。我出生的那年她已经十四岁了,她在结婚前几乎算得上是我的第二位母亲。她婚后搬去了一幢离父母家仅有两个街区的房子,然而她婚前形成的习惯早已根深蒂固。我将毛巾绕在她的脖子上,打算给自己找个座位。 我那时最好的朋友埃莉诺布劳德正坐在一张长桌前,省了我的一番寻找。我的左侧坐着莎拉 梅菲尔德我们管他叫莎拉二号。莎拉一号是我们的莎拉哈尔特,她这时候去了巴尔的摩的一所大学念书。莎拉二号和利维哈特是搭档,哈特光滑的、桃木色的头发和我的朋友塔卢拉班克何德 a的头发几乎一样好。十五岁那年,塔卢拉的那头乌发为她赢得了一场选美比赛,而现在她想要通过这场胜利为自己在纽约谋得一份职位。她和她的那头秀发四处旅行,虽说我热爱着蒙哥马利,可我仍是好生羡慕。肯定没人会管塔卢拉的裙子该有多长。等待会议开始的时间内,女孩们在密不透风的室内不停地给自己扇 风。我们的四周竖立着杏黄色的高墙,墙上都张贴有红十字会的海报。一张海报上印着一只装有纱线和编织针的柳条篮,这是在劝告读者我们的儿郎们需要短袜。请多织些袜子。另一张海报上是一幅鲜明的红十字标志,标志的一旁则印着一位护士,她穿着长裙和大袍子,而这衣服似乎没那么便于工作。护士拖着一副直角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受伤的战士,一块黑色的毯子盖住了战士与担架。从画面的角度来看,海报中的女战士简直像个巨人而那战士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从担架上滑下来,如果那护士不将自己的目光从远方转移回手头的事,他的脚就要滑下来了。图片的下方印着一行宣传语: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我用手肘捅了捅莎拉,又指向那张海报。你是怎么看的?她是不是个处女妈妈? 她没来得及回答。湿地板上传来一阵拐杖的敲击声,我们都转身望向矮胖的、身着铁灰色束腰套装的贝克太太。这是一位让人敬畏的太太,她专程从波士顿来到这儿,就为了指导志愿者们。如果有人将她送上去法国的船,这位女士似乎能凭着一己之力赢得战斗。 大家早上好啊。她用慢吞吞的,带着鼻音的语调说,我看你们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我们的新办公地。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我们必须继续事实上,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扩大规模提高效率。 几个女孩发出欢呼声,她们是刚加入不久的新人。贝克太太点点头,这使得她的下巴短时间内缩进了脖子里。之后她继续说道:你们中已有些人学会了手指和手臂的包扎,腿部与身体的包扎与其原理相同。然而我们在处理伤口和照料病人的过程中仍要注意其他的不同之处。对于那些未接受过训练的志愿者来说,我将会从最基础的说起。我们首先从原色绷带开始说起。 贝克太太说起了绷带的长度、宽度和张力,并开始做示范,我则趁机挤干裙边的雨水。她将一根松松垮垮的布条递给离她最近的一个女孩,站起来,亲爱的。我要让你们分成两组,一组为包扎者,另一组为被包扎者。而包扎者的大拇指一定要放在绷带的上端,像这样,将食指抵在下面。在进行的过程中,我们的手指始终要紧贴着绷带卷,大拇指要拉到最紧。大伙儿开始吧。 我从身后的一排篮子中取出一卷松松散散的绷带。它此刻还是纯白的,当然了,可它有可能很快便被鲜血浸透,沾上尘土,并将无可避免地惹来苍蝇。我见过这样一张照片,南北战争时期的军人们就遭受了这样的劫难,书本上描绘出了爸爸口中的美利坚联邦对我们施下的暴行。 我哥哥托尼比我年长七岁,如今正在法国服役。爸爸本打算用书本知识和人与人之间的探讨教育他。不过爸爸也从未将我赶出过客厅。我可能正在弹奏着简单的曲子,而他会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腿上。赛尔家在蒙哥马利有一段让人骄傲的历史。他翻动着书页说,你瞧。这是我伯伯威廉的老宅,他和他弟弟丹尼尔,也就是你爷爷都在这幢房子里长大。它后来变成了第一座南方联盟的白宫。 赛尔街就是以我们命名的对吗?爸爸?时年七八岁的我满心好奇地问。 那是为了纪念威廉和我父亲。是这两个男人使得这座城市成为今天的样子,我的孩子。 托尼似乎将赛尔家的家族史当作理所当然,可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已然故去的先人,不停问着他们在何时做过些什么。我想要的是故事。 从爸爸那儿,我得知了他父亲,丹尼尔赛尔的故事。他创立了《塔斯基吉 报》,之后又回到蒙哥马利,参与编辑了《蒙哥马利邮报》,使其成了在本地政治方面颇有影响力的一种声音。爸爸还对我说了他母亲的兄弟:伟大的约翰泰勒摩根将军,他一有机会就会袭击北方军队,后来还成为了杰出的美国参议员。我还从妈妈那儿了解到了她的父亲,威利斯梅钦。他是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他和摩根参议员的友情也促成了我父母1883年新年夜里在摩根议员家舞会上的见面。 在红十字会的我不禁思量着,我们的家族历史对于托尼而言会不会是一种负担,甚至是难以忍受的压迫。也许这也是他之所以会娶来自佃农家庭的伊迪丝,婚后又离开蒙哥马利,四处漂泊的原因。作为家族中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他并非爸妈的长子,不是以爷爷的名字命名的,肩上担负着蒙哥马利命运的儿子,他不是那个十八个月大就死于脑膜炎的儿子好吧,这可是个沉重的笑话。 我拆开白布包,将思绪转移回来,将绷带的末端递向埃莉诺。我昨天收到一封亚瑟布伦南写来的信。我说,还记得他吗?我们上次去亚特兰大认识的? 埃莉诺皱着眉,注意力都集中在手头的工作上,她正想着要如何开始。是大拇指在下,还是食指在下? 食指。亚瑟家自大革命时期起就是做棉花生意的。他们家还留着一些不愿意离开的老黑奴呢。我爸爸说这证明了林肯总统毫无缘由地毁掉了南方。 埃莉诺成功地将绷带转了几个圈,然后抬起头。那个开着绿色多特车的亚瑟?我们一起坐进过那部闪亮的宝贝? 就是他。多棒啊。亚瑟说多特要比福特贵上两倍要贵一千块,也许更多。要是见到别人将那么多钱花在一部车上,法官一定会气得在法院门口裸着身子跳舞的。 这一想法将我自己逗乐。我继续向埃莉诺输送着绷带。我想象着爸爸身着条纹西装,手中拿着收拢的雨伞和皮包,从有轨电车中下来。他见到法院石阶门口停着一辆绿色多特,引擎盖光滑闪亮,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连汽车的油门都闪着光彩。一位男士戴着大礼帽,身着燕尾服,他就是恶魔的代表。他会将爸爸召唤到车边,他们之间将会有一段对话。爸爸将会摇着脑袋皱眉头,还会在空中挥动他的雨伞。他会举起一根手指,武断地向人家宣扬所谓的相对价值,又将铺张浪费的危害细数一番。那个戴礼帽的男人将会坚定地摇头,驱车而去,逼得爸爸别无选择,只能当即脱掉衣服开始跳舞。 在我想象的版本中,我不再让父亲的尊严占上风。而现实生活中,我从未见过哪个男人不穿衣服可我见过少年们的身体。我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品中见到的我想那些应该足够有代表性了。 说到裸露。埃莉诺将身子探过来,从我手中拿走最后一段绷带。 昨天夜里在电影院里,有个飞行员温德尔哈斯金斯,向我求证了一个流言的真伪。他问我你是不是真的穿着肉色的游泳衣大摇大摆地进了泳池。他明明是和梅 斯坦纳一起来看电影的,却问起了你的情况,这多有意思啊。梅当时正在贩卖部,也就没听见他这样问,不过他能这样做倒还是有几分绅士气的。 莎拉在一旁说着:我真希望我那天也在泳池边,真想看看那些老女人的表情。 去年冬天,泽尔达将一束槲寄生 a别在裙子上的时候,你在那舞会上吗?利维哈特问。 周三那天你们真应该加入我们。埃莉诺对大家说, 泽尔达趁着司机在角落里抽烟的时候抢占了他的汽车。我们将他气得吹胡子瞪眼,在裴瑞街上打滚! 我敢发誓,泽尔达。你什么有趣的事都经历过了!莎拉感叹道,却从未惹上过任何麻烦! 埃莉诺在一旁补充道:所有人都害怕她爸爸,所以他们只是对她挥挥手指,让她赶紧离开。 我点点头。即便是我的姐姐们都害怕他。 可你不害怕。利维哈特说。 他吠叫的时候远多过咬人的时候。所以埃莉诺,你是怎样和哈斯金斯击掌说的? 我说:别告诉任何人,机长,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泳衣。利维冷哼了一声。我说。你瞧,埃莉诺,这就是我之所以喜欢你的原因了。继续保持,用不了多久那些中年女人也会管你叫小恶魔了。 埃莉诺伸手从桌上的碗里拿出一根别针,将绷带底部固定好。他还问我你有没有哪个相好的情郎,你有哪些相熟的朋友,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也许他只是在找借口和你聊天呢,埃莉诺。莎拉突然这样想到。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至少也能想到一至两个关于我的问题吧。埃莉诺对莎拉温柔地笑道。不,他所关注的只有幸福大道六号楼的泽尔达赛尔小姐,爱慕她的芭蕾舞鞋和天使之翼。 还有魔鬼的笑容。利维补充道。 还有纯净的心。莎拉说。听了这话我赶紧做出呕吐的表情。 他说他不是真心待梅的,埃莉诺继续说,还有,他想要给你打电话。 他已经打过电话来了。 可你并没有答应他呀。 可是到今年秋天为止,我的日程都已经订满了。有那么多躲过了服役的大学男生,还有成群的来蒙哥马利军事中心受训的军官。有太多男人对我感兴趣,我已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 莎拉握起我的手。如果你喜欢他的话,就不要再等下去了。你明白的,他们可能随时都会离开蒙哥马利。 没错。埃莉诺附和道,要么是现在就去相会,要么是永别。 我把手从莎拉手中抽出来,又从身后的篮子里拿来一卷绷带。再告诉你一遍,以防你没听过这个消息。我们在打仗呢!人们的感情随时都有可能告终,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话是这样说,但这从前也没能阻止你和那些军人们见面啊。要知 道这个男人可是英俊得没边儿 我知道他英俊。待他下次打来电话,也许我会 等会儿再聊天,姑娘们。贝克太太漫步到我们身旁。她将双手背在身后,胸部直挺着,像是军舰的舰首。你们的事也许很重要,但我们勇敢的小伙子们会感激你们为他们付出的速度与细心的。 待贝克太太走后,我歪着脑袋,假装自己是玛丽碧克馥,用前臂挡住眼睛哀叹着,哦!真是羞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