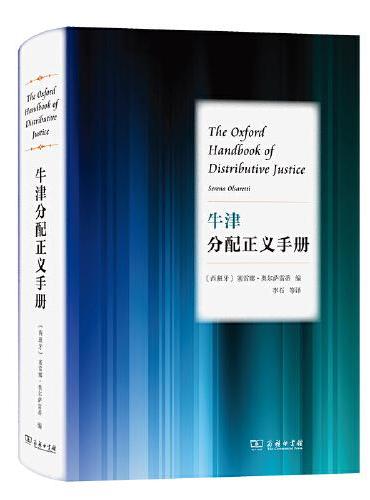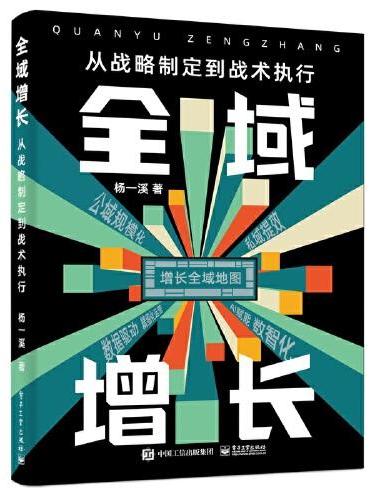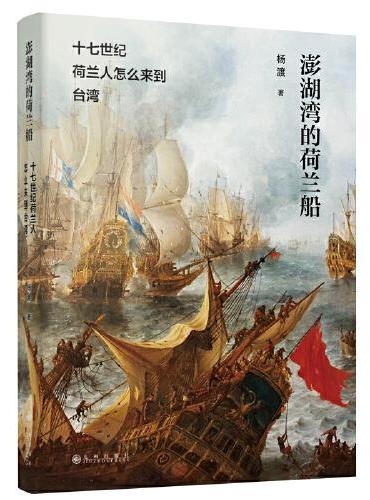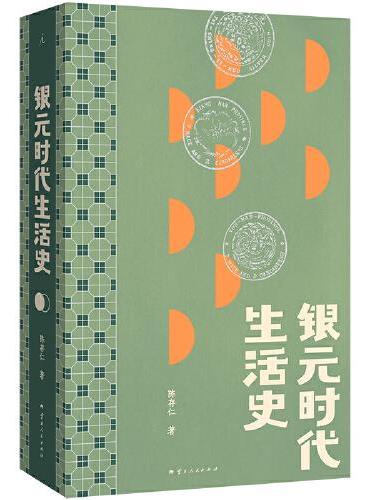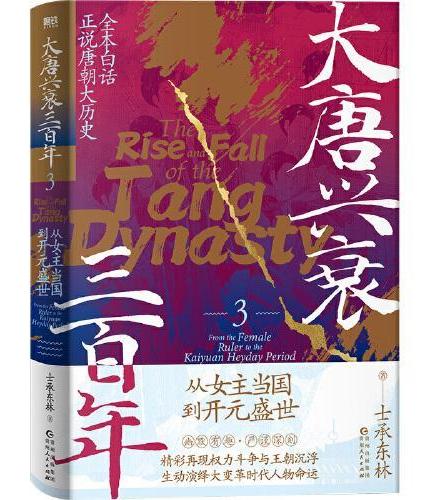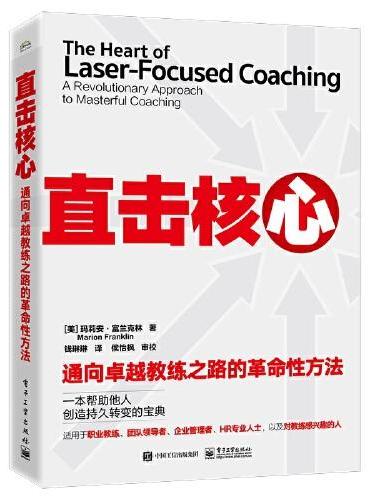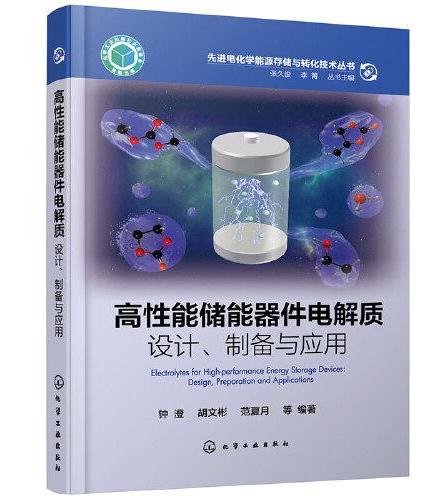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听闻远方有你2
》
售價:NT$
24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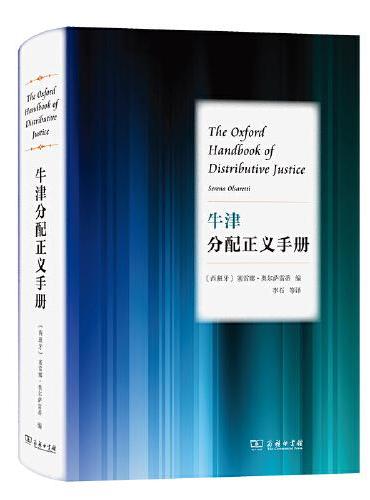
《
牛津分配正义手册
》
售價:NT$
20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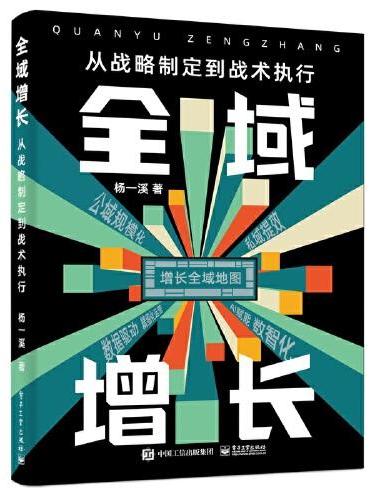
《
全域增长:从战略制定到战术执行
》
售價:NT$
6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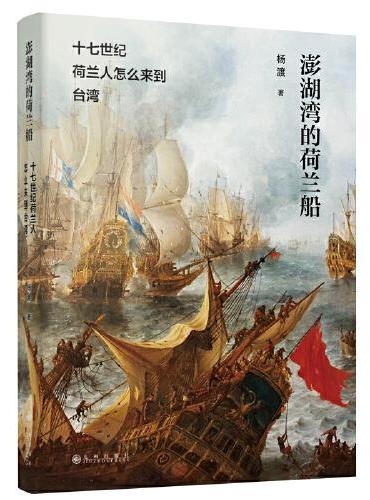
《
澎湖湾的荷兰船:十七世纪荷兰人怎么来到台湾
》
售價:NT$
3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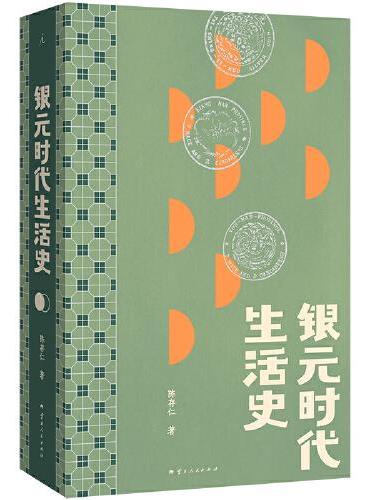
《
银元时代生活史
》
售價:NT$
4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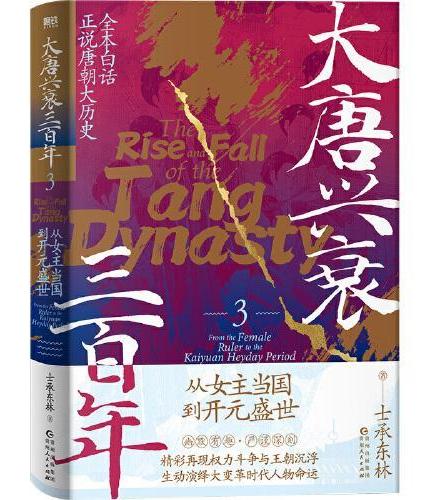
《
大唐兴衰三百年3:从女主当国到开元盛世
》
售價:NT$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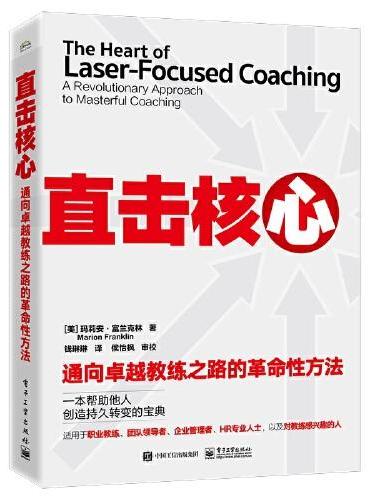
《
直击核心:通向卓越教练之路的革命性方法
》
售價:NT$
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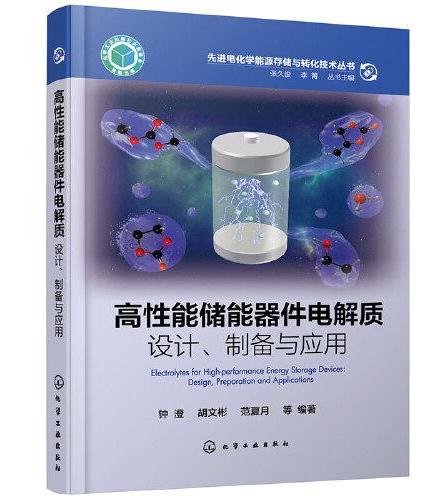
《
高性能储能器件电解质:设计、制备与应用
》
售價:NT$
493.0
|
| 編輯推薦: |
|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作者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经过精心细致地翻译,再现了这套经典外国名著的语言和内涵魅力。虽然小主人公阿廖沙在童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是痛苦、黑暗的路途,却也在苦楚的行进中找到了生命的希望和生机,给人们以精神世界的鼓励,以及与苦难抗争、寻求光明道路的振奋力。
|
| 內容簡介: |
|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苏联作家高尔基的三部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生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前一位进步青年的成长历程。主人公阿廖沙在小市民习气浓厚的外祖父家度过了童年时代。随着外祖父家的衰败、社会腐朽的加深,阿廖沙被迫走向社会,以苦力维持生计。在这个阶段,阿廖沙接触到了启迪他灵魂的宝物——书籍。当满怀理想的阿廖沙前往喀山求学时,俄国革命和进步人士的熏陶又对他产生了思想的震动……
|
| 關於作者: |
|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苏联著名作家、诗人、政论家,出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木工家庭。高尔基是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在1892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时用到的笔名,有“最大的痛苦”的意思。高尔基父亲早逝,他随母亲寄居外祖父家,十一岁时在“人间”开始独立谋生,1892年投身于文学创作事业。
|
| 內容試閱:
|
《童年》
一
昏
暗狭窄的房子里,我的父亲在窗下的地板上躺着。他穿着一身白衣,身子伸得老长,光着脚的脚趾张开着,有些奇怪,手指无力地打着弯儿,安静地放在胸脯上。他紧紧地闭住了那双快乐的眼睛,像极了两枚黑色的铜钱,他的脸色发黑,而且他还龇牙咧嘴的,好像在吓唬我。
母亲跪在他旁边,用一把黑色小梳子为父亲梳理着头发,那把梳子是我常常拿来锯西瓜皮的。母亲上身没穿衣服,下身围着红色的裙子,把父亲那长长的、软软的头发从前额梳到后脑勺;母亲自言自语着,声音既沙哑又沉重,大滴大滴的泪珠不停地从她那双肿大了的眼睛里流出来。
外祖母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她有着圆润的身材,大大的脑袋,大大的眼睛,还有她那挺可笑的松软的鼻子。她身着一身黑装,仿佛整个人都变柔软了,在我看来,这好玩极了。她也在哭,浑身颤抖,弄得我的手也抖起来,而且,她仿佛是非常熟练地伴随着母亲在哭。她要把我推到父亲身边去,我心里害怕,而且觉得别扭,所以,我躲在她的背后,怎么也不愿意去。
我还从来都没见过这种阵势呢,我夹杂着莫名其妙的不安与紧张的心情,更加不明白外祖母反复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快,跟爸爸告别吧,孩子,你再也不会看到他了,亲爱的,他还不到年纪,可是他死了……”
我向来都相信外祖母说的话。尽管现在的她,穿了一身黑衣服,显得脑袋和眼睛都出奇地大,既奇怪又好玩,那我也是相信她的。
在我小的时候,我得过一场大病,是父亲一直看护我,而且他是很开心地在看护我。可是后来却奇怪地换成了我的外祖母来照顾我①。
“你是从哪里来的呀?”我问她。
她是这样回答的:“我是从尼日尼①来的,得坐船来,不能走着来,水面上是不可以走的,小鬼!”
在水上不能走?还要坐船?这真是太有趣了!我觉得这个可笑,是因为在我家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波斯人,他们还染了头发,在地下室还住着一个贩羊皮的老头儿,他是卡尔梅克人②,脸色黄黄的,他们沿着楼梯能骑着栏杆滑下去,如果摔倒了,就会翻着跟头向下滚。这一切我都十分清楚,但是这些和水又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这一切不是很乱套吗?真是糊涂得让人好笑。
“可是为什么说我是小鬼呢?”
“因为你多嘴多舌!”她也笑着对我说。
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天起,我就爱上这个讲话又和气又亲切又快乐的老人了。现在,我希望她领着我快点儿离开这间屋子,因为我在这里真的是太难受了。
母亲那止不住的泪水和悲痛的哭号令我心神不定,我感到十分压抑,特别不安。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这么柔弱的样子,她向来都是态度严厉的。我的母亲个子高大得像一匹马,筋骨坚硬,手劲儿特别大,她总是打扮得很利索,是个很少说话的人。可是现在呢,不知道是为什么,她全身都弄得乱七八糟,全身似乎都膨胀起来了,衣服破烂凌乱,这让人看起来特别不舒服。以前,她的头发会梳得很整齐地贴在头上,像一顶又光又亮的大帽子一样,可是现在,她的头发都在赤裸的肩上披散着,垂落到脸上了,还有她那编着辫子的半头头发,在睡着了的父亲的脸旁边来回摆动着。即使我已经在屋里站了很久,她也并没有看我一眼,而是一直在为父亲梳着头发,并且一直在号啕痛哭,眼泪哗啦啦不停地流着。
门外嘁嘁喳喳地站着些人,有穿黑衣服的乡下人,也有警察,他们透过门缝伸着头往屋里看,还有警察不耐烦地吼叫着说:“快点儿收拾!”
窗户用黑披肩遮着,一有风,披肩就被吹起来,像帆船似的。这让我想起了以前有一次父亲带我去划船的事。我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天上一声雷响,我被这雷声吓了一跳。父亲却哈哈大笑起来,用膝盖紧紧地把我夹住,大声对我说:“没事的,‘大葱头’①,不要怕!”
想到这里,我看见母亲突然费力地从地板上站了起来,可是没站稳,仰面倒了下去,头发全都散在了地板上。她紧紧地闭着双眼,原本苍白的脸现在变得铁青。她也像父亲似的咧着嘴,声音特别可怕地说道:“阿列克赛!滚出去!关上门。”
外祖母把我一把推开,跑到门口冲着门外喊:“你们别怕,亲爱的人们,为了基督,请不要管她了,离开这里吧,这只是生孩子,不是霍乱,好人们,请原谅!”
我跑到了黑暗的角落里,又躲到了一只箱子的后面,在那里看着母亲在地上一边打滚一边呻吟,牙齿被她咬得咯吱咯吱地响,外祖母跟着她在地上爬,既高兴又亲切地说道:“噢,圣母保佑!以圣父圣子的名义,瓦留莎,要挺住啊!”
我被这个场景吓坏了。她们在父亲的身边爬着,又来回碰他,又叹气又喊叫,可是父亲却一动也不动,仿佛还在笑呢。她们在地板上折腾了好久,有好几次母亲站起来又倒下了,而外祖母,她像一个奇怪的大皮球,又黑又软,在屋子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后来,我突然在黑暗中听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哭声。
“噢,感谢我的上帝!”我的外祖母说道,“是个男孩!”
说罢,她便点燃了蜡烛。
可能是我在墙角慢慢睡着了的缘故吧,后来的事情就记不清了。
在我记忆中的第二个印象,是在坟场上荒凉的一角,那是个雨天,我站在小土丘上,小丘面被雨水冲得溜滑。我看着他们把我父亲的棺材放到一个墓坑里,坑底下全是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有两只青蛙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站在墓坑旁边的人,除了我,还有我的外祖母,浑身被雨水淋湿的警察和两个手里拿着铁锹、脸色阴沉的乡下人。雨点是温暖的,像细碎的玻璃珠子一样不停地打在大家的身上。
.................
《我的大学》
于是,我到了喀山大学①,去那里学习,表面上看起来如此。
让我有上大学这个想法的,是尼古拉·叶夫列伊诺夫,一个中学生。这是个漂亮的青年,很讨人喜欢,一对柔和的眼睛,让女人都嫉妒。我们合住在一栋房子里,他住在阁楼上,我们相识是因为他注意到我手里常常拿着书。相识不久,叶夫列伊诺夫竟然说我有“从事科学研究的天赋”。
“您为科学而生!”他边说边潇洒地甩着飘逸的长发,像马鬃在飞舞。
当时我还不了解,就算一只普通的家兔也可以为科学做贡献。叶夫列伊诺夫还是很热情地向我解释:我这样的年轻人正是各个大学所需要的。自然而然地和我聊罗蒙诺索夫②的故事。叶夫列伊诺夫还告诉我,我到了喀山,可以在他的家里寄居,用秋冬两季的时间,学习中学课程,“随随便便”地去应付几场考试(他说的是“随随便便”)我就可以申请到大学的助学金了,在大学再学习五年,我就是个“学问人”啦。听他说的好像很容易,毕竟叶夫列伊诺夫只是个十九岁的青年,没有丰富的阅历,又心地善良。
他结束了中学的考试,离开了这,回家去了,过了两周,我也出发了。
临行前,我年老的外祖母劝告我:“你不要再对别人发脾气了,越发脾气越凶狠,为人又冷傲!跟你外祖父一模一样,你不知道他的下场吗?不幸的老头儿,活着活着,就活成了傻子,你要谨记,上帝不计较人的对错,魔鬼才会斤斤计较这样的事!再见啦!唉……”
满是褶皱的脸上蓄着的泪水被她抹去,接着对我说:“以后咱俩再也不能相见了!你这孩子又心野了要天南海北地乱跑,我老啦,活不久了。”
这几年,我常常离开我善良又年老的外祖母,她几乎见不着我。但是一想到要和血脉相连、体贴入微的外祖母恐成永别,我不禁悲从中来。
我站在轮船的尾端凝视着外祖母,她站在码头的边缘,一只手画着十字,一只手用破旧的披肩角儿擦抹着自己的脸和那双对世人饱含慈祥关爱的眼睛。
于是,我到了这座城市,一座半鞑靼式的城市,在一座平房的一间小屋里住了下来。这座平房坐落在一条偏僻街道尽头的土岗上,显得孤零零的。平房的山墙对面发生过火灾,灾难过后地上长满了荒草;在杂草丛和灌木林里,倒塌的房屋楼阁隆成一堆废墟,废墟的下面是一个大地窖。那些流浪的野狗在这里出生,也在这里死亡。这个地窖令我刻骨铭心,这是我的第一所大学。
在叶夫列伊诺夫家,他的妈妈靠微薄的抚恤金支撑整个家庭,抚养着两个儿子。刚到他们家的那几天,我经常看到这个面色苍白的矮小寡妇从市场回来,她看着放在橱桌上的买来的东西,眉头紧锁地思量着眼前的难题:即使不算上自己,如何能够用一块小小的肉,做出一顿丰盛的美餐,满足三个健壮的大孩子?
她是一个沉静的女人,虽然无可奈何,灰色的眼睛依然有着温和和坚毅的精神,就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知道自己再也没有能力把车拉上坡,依然不余遗力地拼命往上拉。
在来到她家的第四天早上,那时她的孩子都还没有睡醒,我在厨房帮着她洗菜。她小心翼翼地低声问我:“你来这想做什么?”
“读书,上大学。”
她在错愕中用菜刀划破了她的手指头,她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嘴唇还正吮吸着伤口的血,紧接着又惊叫着跳了起来:“哎哟,真是见鬼了。”
她用手绢包扎好伤口,又夸赞我:“你削土豆削得挺好!”
哈!这有什么难的!我趁机向她讲述我过去在轮船上做帮厨的经历。她又问我:“你认为,就凭这点能力你就能上大学吗?”
当时我还不了解什么叫作挖苦。我对她的话信以为真了,就原原本本地向她介绍了我那些规划好的目标,还告诉她,经过这些努力,我就可以步入科学的殿堂。
她叹了口气,喊道:“哎!尼古拉!尼古拉……”
恰巧这时,尼古拉到厨房洗漱。他睡眼蒙眬,头发散乱,但还是和平时一样精神。
“妈妈!把肉包成饺子吃多好啊!”
“嗯,好吧。”妈妈依从了他,回答道。
这正是我炫耀烹饪知识的时机,我接过话头:“那点瘦肉拿来包饺子,可真是太少了。”
这把瓦尔瓦拉·伊凡诺夫娜惹怒了。她狠狠地讽刺了几句话,羞愧得我脸颊发红,耳根发热。她转身走了,手里的几根胡萝卜也被她扔在桌子上。尼古拉向我递着眼色解释道:“生气啦……”
他坐在板凳上,对我继续说道:“女人就是比男人容易动怒。这是女人与生俱来的,这种说法,记得某个瑞士的大学者做过无可辩驳的论证,英国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①也探讨过这个问题。”
尼古拉很喜欢和我交流,每当这个时候,他就会教我一些生活必不可少的常识。他所说的话,我都是倾耳细听。后来,听来听去,我竟然把傅科、拉罗什富科和拉罗什雅克兰②弄混了。我也记混了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③砍了迪穆里埃④的头,还是迪穆里埃砍了拉瓦锡的头?这个青年人一心一意想“把我教育成人”,他也确信他能做到。可是,他的时间不多,也没有好的条件来细心教我。他是个轻佻浮躁和自私的年轻人,他无视了妈妈可怜:整日操心、举步维艰地维持家庭。他那死板笨拙的中学生弟弟更难体会到这一点。我倒是很快就看透了这个妈妈那套复杂的厨房手法。我清晰地明白她的技巧多么精巧:每天费尽心机地填饱两个孩子的肚子,还有我这个长相一般、行为粗俗的流浪青年。不言而喻,分给我的每一片轻薄的面包,也像压在我心头的一块沉重的石头。我想我应该去做点工作。每天早上我早早地出去,不想在她家里吃白食,如果不幸遇上有风雨的坏天气,我就在废墟下的大地窖里躲避,坐在那里听洞外的倾盆大雨和狂风呼啸,周围弥漫着死猫死狗的腐烂气味,我才意识到:上大学—纯粹是白日做梦啊,如果当初我去了波斯,也许会比来这里好。于是我开始幻想,自己成为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法师,把谷子变得像苹果那么大,把土豆变到一普特①那么重,总而言之,我为这个大地,为这个站满穷途末路的人的大地,幻想出不少造福百姓的事情。
我已经学会了幻想,幻想那些不同寻常的冒险和高尚的英雄事迹。这些幻想帮助我度过了举步维艰的苦难日子。可是苦难的日子太多了!我都幻想成瘾了。我并不盼望他人的救济和从天而降的好运,我的意志反而被锤炼得更加刚毅;苦难的生活,使我越来越坚强,越来越聪明。我很早就知道,人会在艰苦环境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为了不挨饿,我常常去伏尔加河的码头。我在那里容易找到工作,挣到十五到二十戈比的工钱;在那儿,我和那些装卸工、流浪汉、无赖混在一起,我感觉自己像一块生铁被扔进了通红的炉火里,每天都有深刻的印象烙印在我心上。我的周围环绕的尽是些痴狂大胆、粗俗鲁莽的人。我喜欢他们愤恨现实生活的态度,欣赏他们敢爱敢恨的乐观心态。因为我有和他们相似的经历,我和他们的接触更加容易,我也更愿意融入这个率真刺激的圈子里去。加上我过去阅读过勃莱特·哈特②的作品和许多“低俗”的小说,这就更激发了我对他们的同情心。
有一个叫巴什金的职业小偷,曾经在师范学校学习过,现在是一个受尽折磨的肺病患者,他机智地劝我说:“你怎么胆怯得像个女孩儿?难道是担心别人责怪你不老实?对女孩儿来说老实是应该的。但是,对你而言—只是一条枷锁而已。公牛老实,是因为甘草喂饱了它的肚子!”
披着棕黄色头发的巴什金,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和演员一样,身体矮小而灵敏,像轻快的猫。他总以教育者和保护者的态度对待我,看得出来,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能够有所成就并得到幸福。他人很聪明,读书又多,最喜欢的是《基度山伯爵》①。
“这本书有主题,有感情。”他这样说。
他喜欢女人,一聊起女人的话题就兴致勃勃,眉开眼笑,病态的痉挛自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这让我感到恶心。但是我还是会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话,我觉得他的声音婉转动听。
“女人,女人!”他精神亢奋地喊道,泛黄的脸颊上浮现出红晕,黑亮的双眼闪烁着欣赏的光芒,“为了女人,我可以不择手段,付出一切。女人就是妖魔,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罪孽!没什么比跟女人恋爱还美妙的啦!”
他很有讲故事的天赋,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妓女们编一些小调,那是一些关于不幸爱情的哀怨动听的小调。在伏尔加河的两岸,人们传唱着由他编写的小调,下面这首盛行的小调就是他的作品:
我家境贫寒,相貌丑陋我的衣服破破烂烂姑娘!就凭这些啊没有人会和你拜堂……
特鲁索夫是一个行踪隐秘难测的人,他对待我也很不错,这个人仪表堂堂,着装奢华,手指像音乐演奏家的手指一样纤细灵巧。在城郊造船厂附近,他开着一间挂着“钟表匠”招牌的小店铺,实际业务是倒卖盗窃来的赃货。
“彼什科夫,你可不要有当小偷的想法!”他一边对我说,一边正派地摩挲花白的胡子,眯着狡黠而高傲的双眼,“我想,你会另谋出路的,你是个注重精神追求的人。”
“什么是注重精神追求?”
“嗯,就是不嫉妒、不羡慕,有的只是好奇……”
这样的评价我是担当不起的,因为我羡慕过很多人和事,比如巴什金用诗歌交流的语言能力,不拘一格的比喻和高超的表达能力,就让我羡慕。我记得他在讲爱情故事时,常用到这样的开头:“在乌黑的夜里,像蜷缩在树洞里的猫头鹰一样的我,无聊地坐在偏僻简陋的斯维亚日克斯镇的一家店里,那时正是秋末的十月,阴雨绵绵,秋风萧瑟,像受了委屈的鞑靼人在哀歌,歌声哀怨又悠长,没完没了:噢—噢—呜—呜—呜……
……恰巧,她回来了,那么轻飘、靓丽,如同太阳初升时的云霞,眼神虽然清纯无邪,却是伪装的,她真诚地说道:‘亲爱的,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明知道这是谎言,但还是信以为真!理智上我清楚明白,情感上又总是不愿相信她在说谎!”
他在说话时,有节奏地摇摆着身体,眯着眼睛,时不时地还会抚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也清澈动人,有点像夜莺在唱歌。
我还羡慕过特鲁索夫,他可以绘声绘色地讲述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的故事,刻薄地嘲讽大主教的生活。有一次他还偷偷地告诉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这个皇帝万事亲力亲为!”
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小说里的一种“坏人”,这种“坏人”总是在小说结尾的时候,出人意料地变成了胸怀坦荡的英雄人物。
一旦夜里天气闷热,人们会到喀山河的对岸,坐在岸边的草地上或者矮树林里,一边吃喝,一边吐露各自的心事。人们通常是谈论生活的困苦,人际关系中的纠葛,尤其喜欢探讨女人的问题。一旦他们谈论起女人来,总是充满怨恨、忧伤或动人的情绪,并且怀有窥探黑暗的心思,在这种黑暗里充满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在星光黯淡的夜里,我曾经在那长满河柳树的闷热洼地里和他们度过了两三个夜晚。由于靠近伏尔加河,这里空气更加潮湿,像金蜘蛛一样的船桅灯在黑夜里四处爬行,富庶的乌斯隆村里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的窗户里,发出的光亮,在漆黑的岩石河岸上,像一团团火球和火网。轮船的蹼轮拍打着河水,发出隆隆的声音。
...........
《在人间》
一
我
来到人间,在城里街道旁一家“时式鞋店”里当学徒。①
我的老板个头很矮,体形肥胖,他那黑得发红的脸很粗糙,牙齿呈青绿色,眼角塞满了眼屎。我觉得他是个瞎子,为了证实我的猜测,我开始扮各种鬼脸。
“不要扮鬼脸。”他声音不大但却很严厉地说。
这双浑浊的眼睛看得我很不自在;但我还是不相信他能看见我,我觉得他只是凭直觉猜出我在扮鬼脸吧。
“我说了,不要扮鬼脸。”声音更低了,但说这话时他那厚厚的嘴唇几乎都没有动。
“别挠手。”又传来了他那低沉、干巴巴的声音,“记住,你现在在城里大街上的一等店铺里做学徒,就应该像一座雕像一样纹丝不动地站在店门口……”
我不知道什么是雕像,从手到臂肘,疥癣虫咬得我的两只胳膊全是红斑和脓疮,难受得我不得不挠手。
“你在家里做什么活儿?”老板盯着我的手问道。
我刚说完,他就摇了摇他那长满白发的脑袋,不屑地说:“捡破烂儿啊,还不如要饭的呢,也比不上那偷东西的。”
听他这么说我立马得意地说:“我以前也偷过东西呢。”
听到我说这话,他突然像猫伸出爪子似的,将两只手往账桌上一撑,吃惊地眨了眨那双瞎子般空洞的眼睛,瞪着我说:“什么?你还偷过东西?”
于是我将偷东西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噢,这倒是小事,我们不会计较的。但你要敢在我这儿偷鞋、偷钱,我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送到监狱里,一直关到你长大……”
他说这话时表现得很和气,却着实把我吓坏了,我也因此更加讨厌他了。
店铺里除了老板,还有雅科夫的儿子—我的表哥萨沙,另外还有一个稍大点的红脸伙计,这个人伶牙俐齿,很会招揽生意。而萨沙身着一件红褐色礼服,戴着衬胸,扎着领结,散着裤腿。他态度傲慢,从不把我放在眼里。
外祖父带我去见老板时,曾嘱托萨沙凡事要多照应我。萨沙皱着眉头,趾高气扬地说:“那他得听我的话。”
外祖父伸出一只手将我的头按下:“论年龄,萨沙比你大,论职位,萨沙也比你高,你得听他的话啊……”
萨沙顺势瞪着我说:“你可别忘了外祖父的话!”
于是从第一天起,他就仗着他有点资格,开始颐指气使地对我摆起谱儿来。
“卡希林,别老瞪眼!”老板说。
“老板,我没有。”萨沙低下了头;然而老板仍继续说道:“别老是板着一张脸,顾客会当你是一头公山羊的……”
那位稍大点的伙计向顾客赔着笑脸,老板也难为情地咧了咧嘴,而萨沙红着脸,灰溜溜地躲到柜台后面去了。
我不喜欢这些对话,好多我都听不懂,有时甚至觉得他们在讲外国话。
每当有女顾客上门时,老板便从衣袋里抽出一只手捋捋他的鬓发,然后堆起满脸甜甜的微笑。这时他的脸上便布满了皱纹,但那双瞎子般浑浊的眼睛却没有一丁点儿变化。那位稍大点的伙计挺直身子,两只胳膊紧贴腰部,然后毕恭毕敬地摊开双手。而萨沙却紧张得不断眨眼,他极力想掩盖那暴出的眼珠。我则站在店门口,一边偷偷地挠手,一边留心观察他们做买卖的规矩。
那位稍大点的伙计走到女顾客面前跪下来,然后张开手小心翼翼地为女顾客量鞋的尺寸,生怕把女人的脚碰坏了。其实这位女顾客的脚很肥,像一个倒放的歪脖子酒瓶。
有一次,在为一位太太量脚时,这位太太的脚不停地动,她缩起身子说:“哎呀,你弄得我好痒啊……”
“这个,是出于礼貌,太太!”大伙计连忙解释道。
看着他对女顾客做出的肉麻动作,实在搞笑,为了避免笑出声来,我急忙扭过脸去对着玻璃门,可我又忍不住想要观察他们做生意的样子,而同时我也怀疑自己能否学会那样毕恭毕敬地张开手,动作灵巧地为顾客穿鞋。
平时老板常和萨沙待在柜台后面的账房里,只留下大伙计一人招待女顾客。有一次,来了一位棕红色头发的女顾客,他摸了摸那女人的脚,然后将拇指、食指和中指捏成一撮送到自己的嘴边吻了吻。
“哎—哟—,你这个调皮鬼!”那位女顾客嗔叫道。
大伙计就鼓起腮帮子,使劲发出亲吻的声音:“啧……啧啧!”
看到这儿,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站都站不稳了,于是赶紧扶住门把手,门被猛地推开了,我一头撞在了玻璃上,玻璃碎了。那位大伙计冲着我直跺脚,老板用他那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敲我的脑袋,萨沙也要动手拧我的耳朵。傍晚同路回家时,萨沙严肃地训斥我:“这有什么好笑的?你再这样胡闹,人家会把你赶走的!”
他向我解释,大伙计讨太太们的欢心,是为了店里的生意能兴隆起来。
“太太们有时就算不需要买鞋,也会跑到店里来看一眼这个讨人喜欢的伙计,捎带再买双鞋。你怎么这么不懂事,真叫人操心……”
这话让我很生气,我没让任何人替我操过心,更别说他了。
每天早晨,病恹恹、爱发脾气的厨娘总是先叫醒我,过一小时后才叫醒萨沙。我起来后要为老板一家人、大伙计以及萨沙擦好皮鞋,洗好衣服,烧好茶水,为所有炉子准备好柴火,还要把午饭用的饭盒洗刷干净。到了店铺,我还要扫地,掸灰尘,准备茶水,给顾客送货,然后再到老板家取午饭。每每这段时间,萨沙便不得不代替我在店铺门口站岗。他觉得站在店铺门口很没面子,就责骂我:“懒家伙,让别人替你干活儿……”
在这里,我嗅到了乏味、沉闷的气息。我已经习惯了从早到晚待在库纳维诺区①用沙土铺成的道路上、在浑浊的奥卡河边、在旷野和树林中的生活。这里没有外祖母,没有小伙伴,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聊天的人。在这里,生活向我袒露出它那丑恶虚伪的本质,这令我愤怒。
经常有女顾客什么也没买就走了,每次碰到这种情况,他们三个就很气愤。老板会立刻收起他那甜甜的笑容,然后命令萨沙:“卡希林,把货收起来!”
随后便骂道:“呸!这头蠢猪跑到我这儿来啦!这个臭婆娘肯定是自己在家闲得发闷,就跑到人家铺子里瞎逛。她要是我婆娘,我可要给她点厉害尝尝……”
他的老婆有一双黑色的眼睛,鼻子很大,身材又干又瘦,经常像对待下人一样,对他又跺脚又责骂的。
他们经常一见到熟悉的女顾客便卑躬屈膝,献殷勤,说各种奉承讨好的话,可一送走她们,便用各种脏话骂这些女顾客。每次听到这些脏话,我都恨不得跑出去追回那个女顾客,把他们说的脏话全告诉她。
当然,我也知道背后说别人坏话这样的事很常见,可这三个家伙议论他人的话真的非常可恶。好像觉得他们自己是最了不起的,甚至可以担任全世界的法官。他们嫉妒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也从不夸赞别人,对每个人的缺点都略知一二。
有一次,一个女郎来到店里,她脸色红润,双瞳明亮,身披天鹅绒大衣,上面镶着黑皮毛领,在黑皮毛领的映衬下,她的脸如鲜花一般漂亮。她将大衣脱下来交给了萨沙,如此显得更加漂亮了。她那苗条的身材紧裹在蓝灰色的绸衣里,耳朵上的钻石很耀眼。她使我想起了美丽无比的瓦西莉萨①,我断定她是省长夫人。老板和店员们对她点头哈腰,说尽了讨好的话,他们大气不敢出,像捧着一盆火似的。这三人像着了魔似的,在店里来回跑,货架上的玻璃掠过他们的影子,好像周围的东西着了火,正在渐渐熔化,马上就要变成另一种形状,另一种样子啦。
这位女郎很快就选中了一双价格昂贵的皮鞋,然后离开了。
她一离开,老板就吧嗒了一下嘴,吹了一声口哨,骂道:“这只母狗……”
大伙计也轻蔑地随声附和:“她不过是个女戏子!”
于是他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这个女郎的一些情人以及她那奢华糜烂的生活。
吃过午饭,老板便到店铺后面的小屋里午睡了,我趁机打开他的金怀表,往里面滴了几滴醋。他醒后惊慌地跑出来,手里拿着那块怀表问:“这是怎么回事?怀表冒汗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难道要出什么乱子吗?”
而我在一旁窃喜。
尽管每天奔忙于店铺和家里的各种杂事琐事中,我仍感到很无聊,很烦闷。我常常自己盘算着:干一件什么事才能让他们把我从铺子里撵走呢?
一些行走在大街上的路人,身上落满了雪花,他们行色匆匆地从店铺走过,像是落了队的送葬人,急着追赶前面的棺材。马蹒跚地拖着车子,吃力地轧过雪堆。店铺后面教堂的钟楼上,每天传来凄凉的钟声,告诉人们大斋期到了。那一下一下的钟声就像枕头敲打在脑袋上,不痛不痒,却使人麻木,耳朵发鸣。
一天,我正在店铺门前的院子里清理刚送到的货箱,这时在教堂里看门的歪脖老头儿走到我跟前。他身体很脆弱,软得像布人似的,身上的衣服像被狗撕咬过一般破烂不堪。
他对我说:“上帝啊,可不可以给我偷一双套靴啊?”
我没有回应他。于是他在一个空箱子上坐下,打了个哈欠,然后在嘴上画了个十字①,又说:“你给我偷一双吧,好吗?”
“不能偷东西!”我回答他。
“可是有人偷啊,你应该尊重老人!”
我很喜欢他,他和我周围的其他人不一样。我感觉他判定我会为他偷东西,于是我答应他从通风窗里递给他一双套靴。
“那好,你不是在骗我吧?嗯,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会骗我的……”他很平静地说。
他的靴子踩在脏兮兮的泥雪上,他用土烧烟斗抽着烟,静静地在这儿坐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吓唬我说:“要是我骗你呢?我一拿到靴子就去找你的老板,说这双靴子是花半卢布从你那儿买来的,而事实上这双靴子价值两卢布多,那你怎么办?啊?你只卖了半卢布,那剩下的钱去哪儿了?你买糖吃了?”
似乎他已经照他刚才所说的那样做了,我呆住了,盯着他。他一边嘴吐青烟,一边瞧着自己的长靴,继续轻声地嘟囔道:“如果是你的老板指使我来试探试探你:看那小子是不是个贼坯子,你怎么办啊?”
“那我不给你套靴了!”我生气地说。
“你已经答应我了,不能说话不算数。”
他一把抓起我的手,将我拽到他跟前,用他那冰凉的手指敲了敲我的脑门儿,懒洋洋地说:“你怎么轻易就说:‘给,拿去吧?!’”
“是你要求我这样做的。”
“我的要求多着呢!那我要你去抢劫教堂你也去吗?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相信陌生人呢?唉,你这个小傻瓜……”
说完,他把我推到一边,站起身来:“我穿不着偷来的套靴,我又不是阔老爷。我就是和你开个玩笑……看你这么老实,你可以在复活节那天到钟楼上敲敲钟,看看这座城的风景……”
“我很熟悉这座城。”
“可从钟楼上望下去,它很漂亮啊!”
他慢悠悠地用靴尖踩着雪,朝教堂的拐角走去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很不安:这老头儿就只是开个玩笑?还是真的受老板之托来试探我的?我甚至都不敢进店铺了。
突然萨沙闯进院来,朝我大吼道:“你在搞什么鬼?”
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火,抡起钳子就朝他甩了一下。
萨沙和那个大伙计经常偷老板的东西,他们把一双皮鞋或便鞋藏在火炉的烟囱里,走之前悄悄地往外套的衣袖里一塞,就离开了店铺。我很厌恶这种事,也有些恐惧,我仍记得老板对我的恐吓。
我问萨沙:“你偷东西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