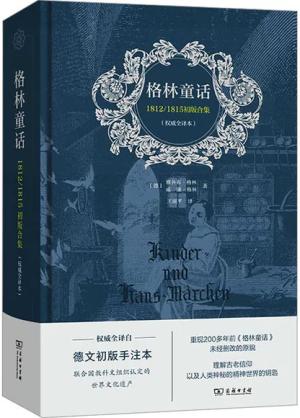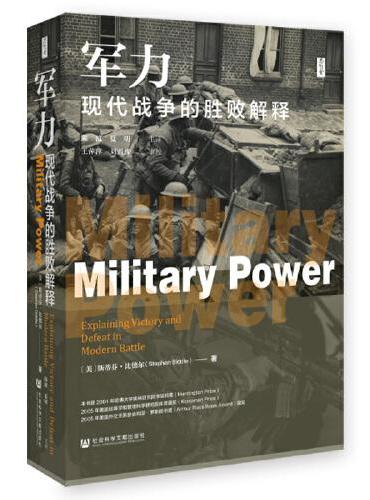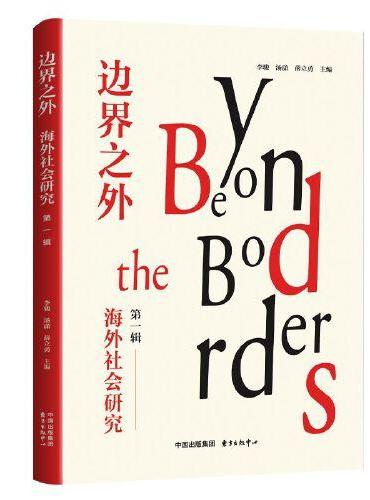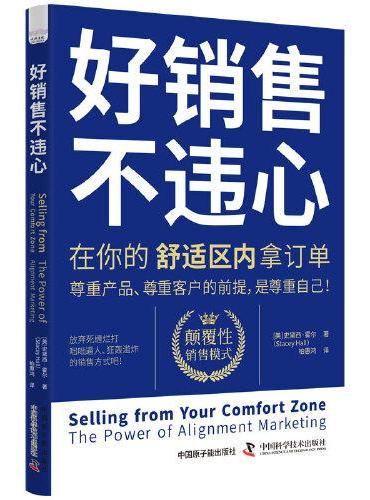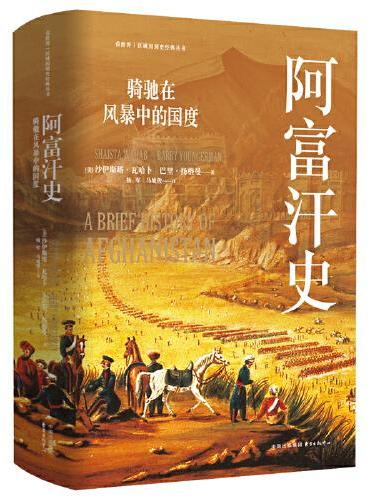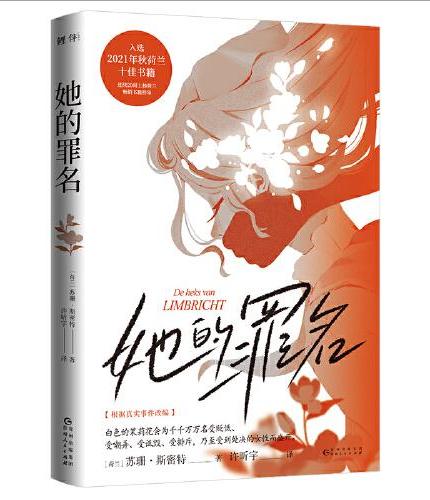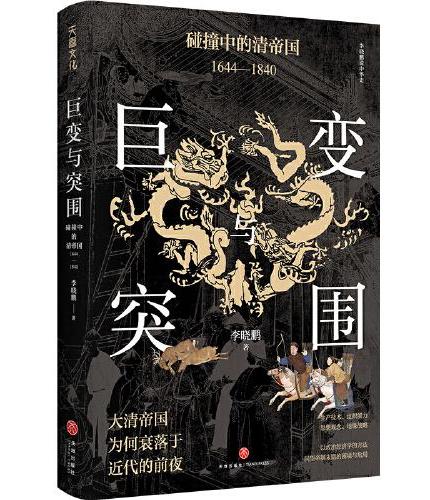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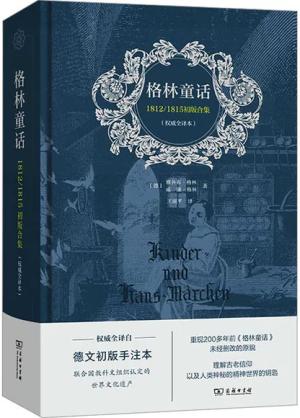
《
格林童话:1812/1815初版合集(权威全译本)
》
售價:NT$
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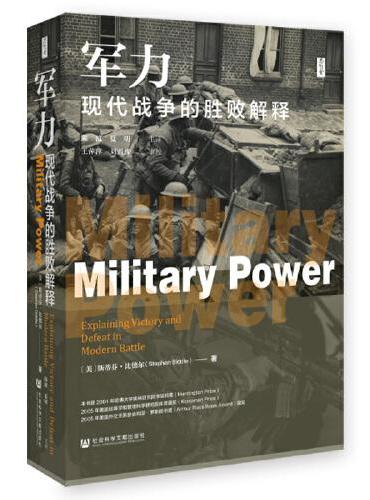
《
思想会·军力:现代战争的胜败解释
》
售價:NT$
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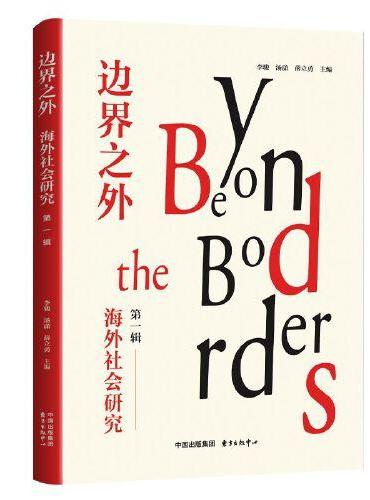
《
边界之外:海外社会研究(第一辑)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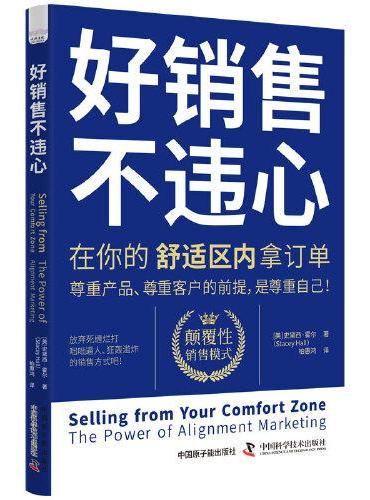
《
好销售,不违心:在你的舒适区内拿订单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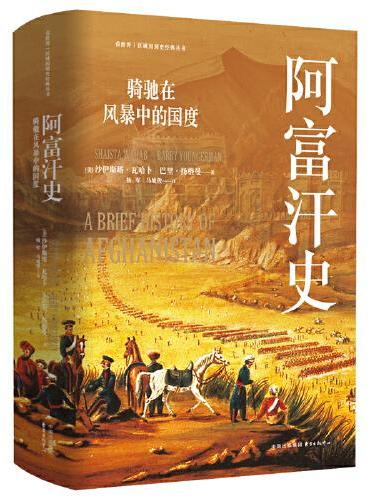
《
阿富汗史:骑驰在风暴中的国度
》
售價:NT$
549.0

《
背影2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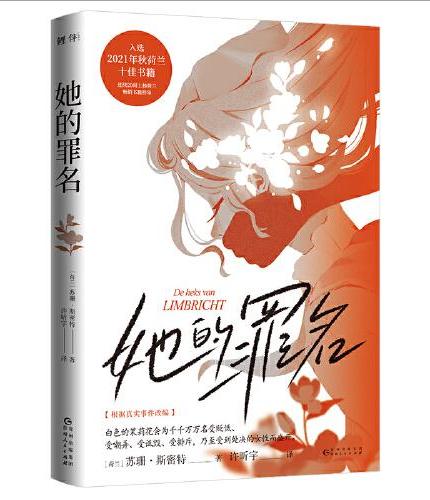
《
她的罪名
》
售價:NT$
27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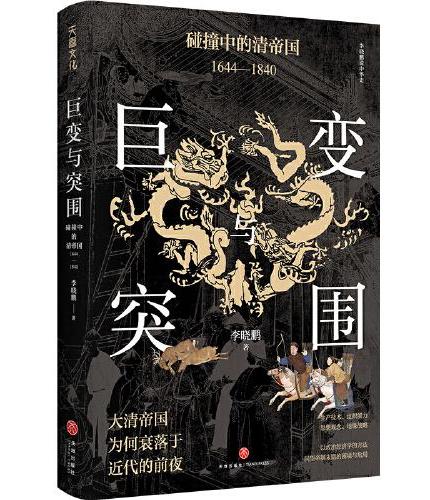
《
巨变与突围:碰撞中的清帝国:1644—1840
》
售價:NT$
437.0
|
| 編輯推薦: |
1.在福克纳的文学成就中,短篇小说占据半壁江山,与长篇小说共同成就了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的诺贝尔文学奖殊荣。
2.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是他长篇创作的源头和基石,在艺术上一脉相承,在可读性上,短篇小说优于长篇。
3.福克纳研究和译介专家李文俊、陶洁领衔翻译,囊括黄梅、朱炯强、姚乃强等知名翻译家译作。
4.除收入福克纳经典短篇《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烧马棚》《夕阳》《调换位置》等外,还收入鲜见版本的《希望之树》《黄铜怪物》等,此外还新增了《遍地黄金》《艺术之家》《宾夕法尼亚车站》等数篇初次翻译出版的福克纳短篇代表作。
|
| 內容簡介: |
|
福克纳是长篇小说巨匠,也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此文集收录的篇目均为福克纳短篇小说中的杰出之作,代表了福克纳短篇小说的文学风格和主要成就。无论在题材内容或手法技巧方面,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他大部分的短篇小说还是以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描述的还是那个王国的沧海桑田和世态人情,探讨其中的家族、妇女、种族、阶级等问题,表现“人类的内心冲突”。
|
| 關於作者: |
|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新奥尔巴尼,20世纪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他以小说见长,同时也是诗人和编剧家。他一生共写了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约克纳帕塔法县,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主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一九四九年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
| 目錄:
|
目录
序言
烧马棚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黄铜怪物
死里逃生
艾莉
那黄昏时分的太阳
伊万吉林
公道
胜利
调换位置
宾夕法尼亚车站
艺术之家
遍地黄金
希望之树
|
| 內容試閱:
|
烧马棚
治安官借了杂货店在坐堂问案,杂货店里有一股乳酪味。捧着帽子、蜷着身子坐在人头济济的店堂后边的孩子,觉得不但闻到一股乳酪味,还闻到了别的味儿。他坐在那里,看得见那一排排货架上密密麻麻地摆满了罐头,看上去都是矮墩墩、结结实实、神定气足的样子,他暗暗认过罐头上贴的招牌纸,可不是认招牌纸上的字,他半个大字也不识,他认的是那上面画的鲜红的辣子烤肉和银白色的弯弯的鱼。他不但闻到了乳酪味,而且肚子里觉得似乎还嗅到了罐头肉的味儿,这两股气味不时一阵阵送来,却总如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于是便只剩下另一股老是萦回不散的味儿,不但有那么一股味儿,而且还有那么一种感觉,叫人感到有一点恐惧不安,而更多的则是伤心绝望,心口又跟从前一样,觉得一腔热血在往上直冲。他看不见治安官当作公案的那张桌子,爸爸和爸爸的仇人就在那桌跟前站着呢。他就是在那种绝望的心情下暗暗地想:那可是我们的仇人,是我们的!不光是他的,也是我的!他是我的爸爸啊!虽然看不见他们,却听得见他们说话,其实也只能说听得见他们两个人在说话,因为爸爸还没有开过口。
“哈里斯先生,那你有什么证据呢?”
“我已经说过了。他的猪来吃我的玉米。第一次叫我逮住,我送还给了他。可他那个栅栏根本圈不住猪。我就对他说了,叫他防着点儿。第二次我把猪关在我的猪圈里。他来领回去的时候,我还送给他好大一捆铁丝,让他回去把猪圈好好修一修。第三次我只好把猪留了下来,代他喂养。我赶到他家里一看,我给他的铁丝根本原封不动卷在筒子上,扔在院子里。我对他说,他只要付一块钱饲养费,就可以把猪领回去。那天黄昏就有个黑鬼拿了一块钱,来把猪领走了。那个黑鬼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说:‘他要我关照你,说是木头干草,一点就着。’我说:‘你说什么?’那黑鬼说:‘他要我关照你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木头干草,一点就着。’当天夜里我的马棚果然起了火。牲口是救了出来,可马棚都烧光了。”
“那黑鬼在哪儿?你找到了他没有?”
“那黑鬼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没错儿。我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
“这可不能算是证据。不能算证据,明白吗?”
“把那孩子叫来问问好了。他知道的。”孩子起初也只当这是指他的哥哥,可是哈里斯马上又接着说,“不是他。是小的一个。是那个孩子。”蜷缩在后边的孩子,看见他和那桌子之间的人堆里立刻裂开一条道儿来,两边两排铁板的脸,道儿尽头就是鬓发半白、戴着眼镜的治安官,没戴硬领,一副寒酸相,正在那里招手叫他。孩子矮小得跟他的年纪很不相称,可也跟他父亲一样矮小而结实,打了补丁的褪色的工装裤穿在他身上都还嫌小,一头发根直竖的棕发蓬松稀乱,灰色的眼睛怒气冲冲,好像雷雨前的狂风。他看见招手叫他,顿时觉得光秃秃的脚板下像是没有了地板;他一步步走去时,那两排一齐扭过头来冲着他看的铁板的脸分明似千斤重担压在他身上。他爸爸穿着体面的黑外套不是为了出庭听审,是为了搬家,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对他一眼也不瞅。那种要命的伤心绝望的感觉又梗在心头了,他心想:他是要我撒谎呢,这个谎我不能不撒了。
治安官问了:“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低声答道:“‘上校沙多里斯’·斯诺普斯。”
“啊?”治安官说,“大声点说。‘上校沙多里斯’?在我们本地用沙多里斯上校的名字做名字的人,我想总不能不说实话吧?”孩子没有吭声,心里一个劲儿地想:仇人!仇人!眼睛里一时竟什么都看不见了,所以他没有瞧见那治安官的神色其实倒很和蔼,也没有听出治安官是以不高兴的口气问这个叫哈里斯的人的:“你要我问这个孩子?”不过这句话他倒是听见了,随后的几秒钟过得好慢,这挤满了人的小店堂里除了紧张的悄声呼吸以外,再没有一丝声息,他觉得就像抓住了一根葡萄藤的梢头,像打秋千一样往外一荡,飞到了万丈深涧的上空,就在荡到这最高点时,地心似乎霎时失去了吸力,于是他就一直凌空挂在那里,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算了算了!”哈里斯暴跳如雷,气势汹汹地说道,“活见鬼!你打发他走吧。”于是孩子立刻觉得那流体般的时间又在他脚下飞快流去,那乳酪味和罐头肉味,那恐惧和绝望,那由来已久的热血上涌的苦恼,又都纷至沓来,在一片纷纭之中还传来了人声:
“这个案子就这样了结了。我虽然不能判你的罪,斯诺普斯,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个劝告。你还是离开本地,以后不要再来了。”
爸爸第一次开了口,声音冰冷而刺耳,平平板板,没有一点轻重:“我是要搬走了。老实说有的地方我也真不想住下去,尽碰到些……”接下去的话真下流得无法落笔,不过这话却不是冲着哪一个说的。
“这就好。”治安官说,“天黑以前就赶着你的大车走吧。现在宣布,本案不予受理。”
爸爸转过身来,于是孩子就跟着那硬邦邦的黑外套走去。爸爸虽然是个精悍个子,走路却不太灵便,那是因为三十年前偷了匹马逃跑时,脚后跟上吃过南军纠察队的一颗枪弹。一转眼他的面前突然变成了两个背影,原来他哥哥不知从哪儿的人堆里钻了出来,哥哥也只有爸爸那么高,可体格要粗壮些,成天嚼那嚼不完的烟叶。他们走过了那两排面孔铁板的人,出了店堂,穿过破落的前廊,跨下凹陷的台阶,迎面只见一些小狗和不大的孩子踩在那五月的松软的尘土里。正当他走过时,听见有个声音在悄悄地骂:
“烧马棚的贼!”
他猛地转过身去,可眼睛又看不清东西了;只觉得一团红雾里有一张脸儿,好似月亮,却比满月还大,那脸儿的主人则比自己还要矮上一半,他就对准那张脸儿往红雾里扑去,虽然脑袋撞了个嘴啃泥,却觉得并没有挨打,也并不害怕,就爬起来再纵身扑去,这次还是一拳也没挨,也没有尝到血的滋味,等到再一骨碌爬起来,只见那个孩子已经没命地逃跑了,他拔起腿来追了上去,可是爸爸的手却一把把他拉了回来,那刺耳的冰冷的声音在他头顶上说:“去,到大车上去。”
大车停在大路对面一片刺槐和桑树丛中。他那两个腰圆身粗的姐姐都是一副假日打扮,妈妈和姨妈则身着花布衣,头戴遮阳帽,她们早已都上了大车,坐在家具杂物堆中。连孩子都记得,他们先后已经搬过十多次家了,搬来搬去就只剩下这些可怜巴巴的东西——旧炉子、破床破椅、嵌贝壳的时钟,那钟还是妈妈当年的嫁妆呢,也记不得从哪年哪月哪日起,就停在两点十四分左右,再也不走了。妈妈这会儿正在淌眼泪,一瞧见孩子,赶紧用袖子抹了下脸,就要爬下车去。爸爸却叫住了她:“上去!”
“他弄破啦。我得去打点水,给他洗一洗……”
爸爸却还是说:“回车上去!”孩子爬过后挡板,也上了车。爸爸爬到赶车的座儿上,在哥哥身边坐了下来,拿起去皮的柳条,朝瘦骡身上猛抽了两下,不过这倒不是他心里有火,甚至也不是存心要折磨折磨牲畜。这脾气,正仿佛多少年以后他的后代在开动汽车之前总要先让引擎拼命打上一阵空转一样,他总是一手挥鞭,一手勒住牲口。大车往前赶去,那个杂货店,还有那一大堆人板着面孔默默看着,都给丢在后头了,一会儿路拐了个弯,这些就全瞧不见了。孩子心想:永远看不见了。他这该满意了吧,他可不是已经……想到这里他马上打住了,下面的话他对自己都不敢说出口。妈妈的手按在他肩头上了。
“痛吗?”妈妈问。
“不,”他说,“不痛。甭管我。”
“看血都结块了,你干吗不早点擦一擦呢?”
“等今儿晚上好好洗一洗吧,”他说,“甭管我了,放心好啦。”
大车只顾往前赶。他不知道他们要上哪儿去。他们从来没人知道,谁也从来不问,因为大车走上一两天、两三天,总会来到个什么地方,总有一所这样那样的房子等着他们。大概爸爸事先已经安排好了,要换个农庄种一茬庄稼,所以这才……想到这里他又不得不打住了。爸爸总来这一套。不过,只要事情有一半以上的把握,爸爸干起事来就泼辣而有主见,甚至还颇有些魄力。这是很能使陌生人动心的,仿佛他们见了潜藏在他胸中的这股凶悍的猛劲,倒不觉得很可靠,而是觉得,这个人死死认定自己干的事绝错不了,谁只要跟他利益一致,准也可以得到些好处似的。
当夜他们露宿在一个小林子里,那是一片栎树和山毛榉,旁边有一道清泉。夜里还是很冷,他们就生了堆火挡挡寒气,正好附近有一道栅栏,就偷了一根横条,劈成几段当柴烧——火堆不大,堆得很利落,简直有点小家子气,总之,那手法相当精明;爸爸的一贯作风就是只烧这样的小火堆,哪怕在滴水成冰的天气里也是这样。到年纪大些以后,孩子也许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会想不透:火堆为什么不能烧得大一些?爸爸这个人,不仅亲眼见过打仗的破坏靡费,而且血液里天生有一种爱慷他人之慨的挥霍无度的本性,为什么眼前有东西可烧却不烧个痛快呢?他也许还会进而想到有这么一个理由:在那四年工夫里美国南北战争自一八六一年四月爆发至一八六五年四月结束,历时整整四年。北军是蓝色制服,南军是灰色制服,下文所说“穿蓝的”和“穿灰的”,即指此而言。,爸爸老是牵了一群群马爸爸称之为缴获的马藏在树林里,见人就躲不管是穿蓝的还是穿灰的,那小家子气的火堆就是他赖以度过漫漫长夜的活命果子。到年纪再大些以后,孩子也许就看出真正的原因来了:原来爸爸心底深处有那么个动力的源泉,最爱的是火的力量,正像有人爱刀枪火药的力量一样,爸爸认为只有靠火的力量才能保持自身的完整,不然强撑着这口气也是白白地活着,因此对火应当尊重,用火也应当谨慎。
不过现在他还想不到这一层,他只觉得他从小到现在,看到的总是这么小家子气的一堆火。他只管坐在火堆旁吃他的晚饭,爸爸来叫他时,他捧着个铁盘子,已经迷迷糊糊快要睡着了,于是只好又跟着那直挺挺的背影,随着那生硬而严峻的颠颠跛跛的步子,上了高坡,来到了洒满星光的大路上,一扭头,只见爸爸背对着星空,看不见脸儿,也辨不出厚薄——就是那么一个一抹黑的剪影,身穿铁甲似的大礼服分明不是他自己定做的,像白铁皮剪成的人形儿一样扁扁的、死板板的,连声音也像白铁皮一样刺耳,像白铁皮一样没有一点热情:
“你打算当堂说了。你差一点就都对他说了。”孩子没应声。爸爸在他脑袋边上打了一巴掌,打得很重,不过并没有生气的意思,正如在杂货店门口他把那两头骡子抽了两鞭一样,也正如他为了要打死一只马蝇,会随手抄起一根棍子来往骡子身上打去一样。爸爸接下去说的话,还是一点不激动,也一点没冒火:“你快要长成个大人了。你得学着点儿。你得学会爱惜自己的血,要不你就会落得滴血不剩,无血可流。今儿早上那两个人,还有堂上的那一帮人,你看有哪一个会爱惜你?你难道不知道,他们就巴不得找个机会来干我一下子,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搞不过我。懂吗?”孩子在二十年以后倒是思量过这件事:“我那时要是说他们不过想搞清真相,主持公道,那准又得挨他的打。”不过当时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哭。他就默默地站在那里。爸爸说了:“问你,懂吗?”
“懂了。”他小声说。爸爸于是就转过脸去。
“回去睡吧。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了。”
第二天果然就到了。过午不久,大车就停在一所没有上过漆的双开间小屋前,孩子今年十岁,十年来大车在这种模样的小屋前就先后停过了十多回,这回也还跟以前的那十多次一样,是妈妈和姨妈下了车,把东西搬下车来,两个姐姐、爸爸和哥哥都一动不动。
“这屋子只怕连猪也住不得呢。”一个姐姐说。
“怎么住不得呢,你住着就喜欢了,包你不想再走了。”爸爸说,“别尽在椅子里坐着啦,快帮你妈搬东西去。”
两个姐姐都是胖大个儿,奇笨如牛,爬下车来时,满身的廉价丝带飘拂成一片;一个从乱糟糟的车肚子里掏出一盏破提灯来,另一个则抽出了一把旧扫帚。爸爸把缰绳交给大儿子,不大灵便地从车头上爬了下来。“等他们卸完了,你就把牲口牵到马棚里去喂一喂。”说完他喊了一声,孩子起初以为那还是冲着哥哥说的呢,“跟我来。”
“叫我吗?”孩子说。
“对,叫你!”爸爸说。
“阿伯纳!”妈妈这是喊爸爸。爸爸停了脚步,回过头去——那火性十足的日渐花白的浓眉下,笔直地射出两道严厉的目光。
“从明天起人家就要做我八个月的主子了,我想我总得先去找他说句话。”
他们又返身顺着大路走去。要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应该说要是就在昨晚以前——孩子一定会问带他上哪儿去,可是现在他就不问了。在昨晚以前爸爸不是没有打过他,可是以前从来没有打了他还要说明道理的;那一巴掌,那一巴掌以后的沉静而蛮横的话声,仿佛至今还在耳边回响,给他的唯一启示就是人小不济事。他这点年纪实在无足轻重,索性再轻一些倒也可以遵命飞离人世,可偏偏飞又飞不起,说重又不重,不能在人世牢牢地站定脚跟,更谈不上起而反抗,去扭转人世间事情的发展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