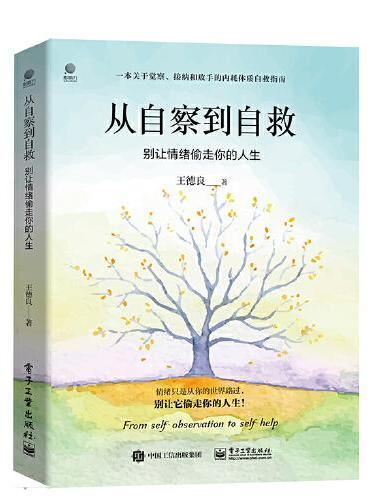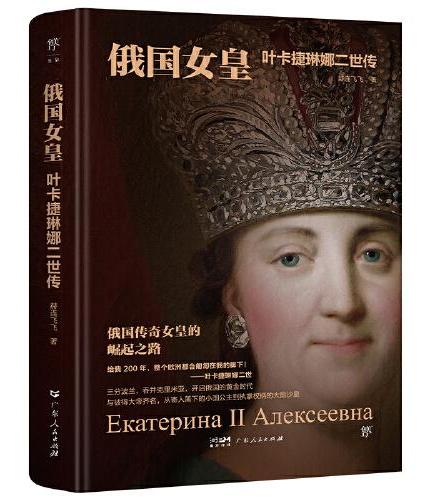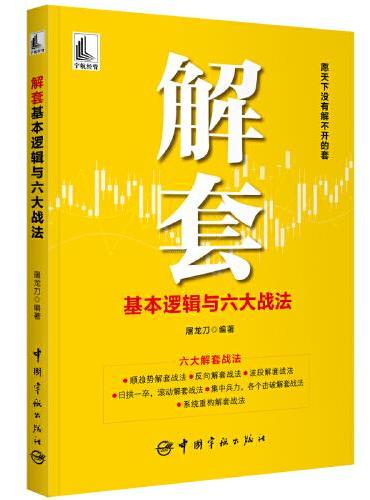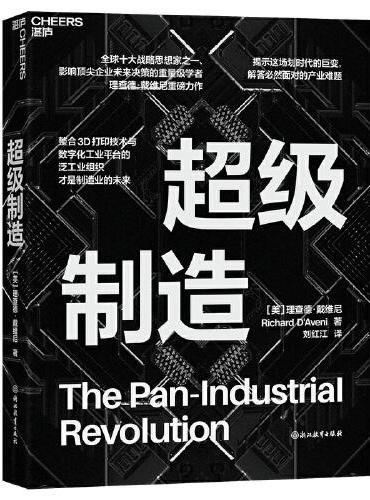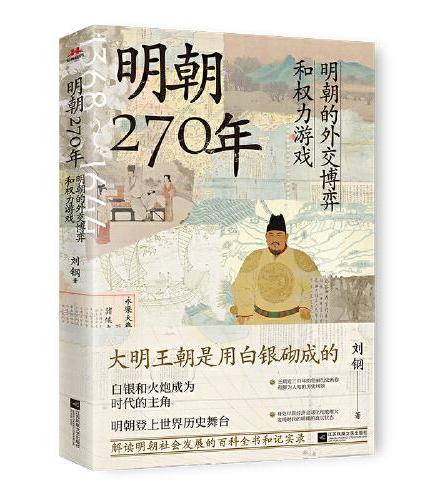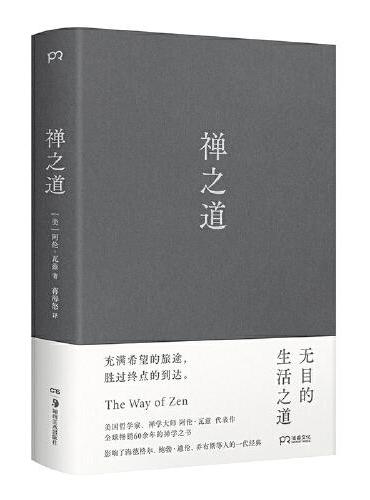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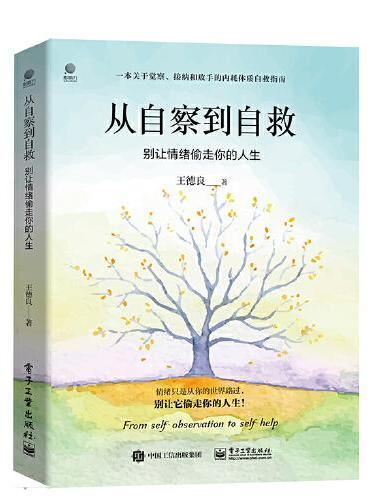
《
从自察到自救:别让情绪偷走你的人生
》
售價:NT$
420.0

《
晚明的崩溃:人心亡了,一切就都亡了!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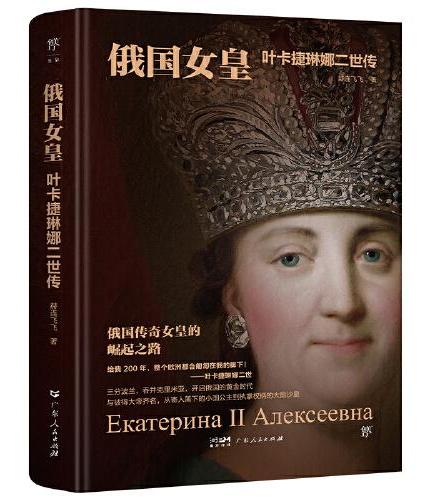
《
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传(精装插图版)
》
售價:NT$
381.0

《
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
》
售價:NT$
2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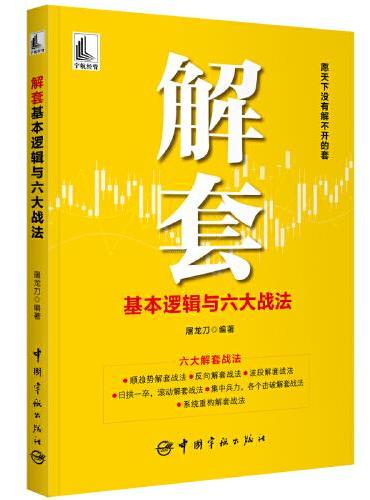
《
解套基本逻辑与六大战法
》
售價:NT$
2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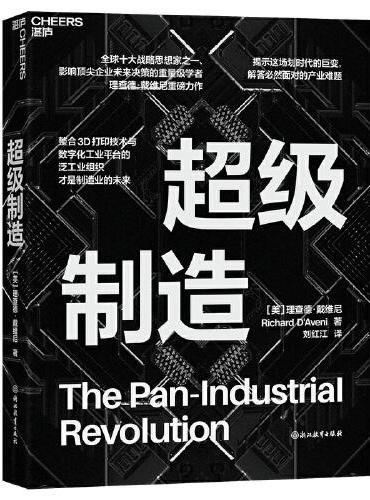
《
超级制造
》
售價:NT$
6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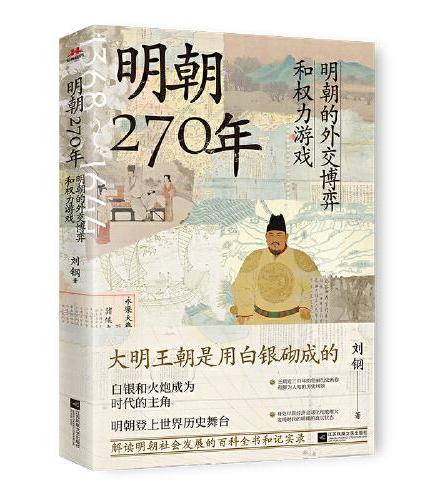
《
明朝270年:明朝的外交博弈和权力游戏
》
售價:NT$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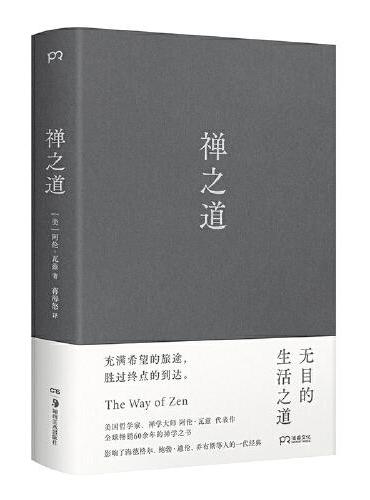
《
禅之道(畅销全球60余年的一代经典,揭示禅对现代人的解脱意义)
》
售價:NT$
386.0
|
| 編輯推薦: |
这一个关于原谅与信仰的故事,作者以罕见的阿米什社会为背景,描述身体缺陷的男孩伊莱,在经历一场重大的变故之后,如何化解对肇事者的责怪以及对自己的自责,从而原谅别人和自己,获得温暖与平静心灵的过程。
故事温暖动人,以“宽恕”为主旨,从一个孩子成长的视角,观看人性。在美国一经出版就引起广泛关注,成为畅销叔。得到《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的推荐,并多次荣获图书界大奖。
|
| 內容簡介: |
阿米什人认为,用相机拍下照片,会偷走人的灵魂。伊莱,一个双手长着蹼的男孩,在一个夏天偷走了一台相机。
车祸夺走了五个姐姐的生命,伊莱不顾一直以来的信仰禁忌,拍下了姐姐们的照片,同时也带走了他们的“灵魂”。
然而,他无法原谅肇事司机,也无法原谅自己。伴随着他的成长,一段关于“宽恕”的旅程从此开启。
在旅程的终点,他的心终于获得了自由。
|
| 關於作者: |
|
荷莉佩恩:毕业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小说家、剧作家、写作辅导师。凭借处女作《处女情结》一书,提名维吉尼亚联邦大学 “小说新人奖”,并获邦诺连锁书店 “优秀新作家”奖,声名大噪。
|
| 內容試閱:
|
一
我家农场的路边生长着一棵胡桃树,在它厚厚的树皮上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它像是一道被雷电击中形成的伤疤,但一般人却不容易看见。那些怀有宗教信仰的人坚信是上帝之手造就了这道伤痕,然而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体会到这道印记的神圣之处。
他们说事故是因为意外才发生的。认识我姐姐们的人都会这样说,“这纯属意外”。但我想告诉人们的是这世界上并没有意外,有的只是机缘。
是的,在一个完美的世界中,我想这样对人们说。经过我家农场的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这里好似天堂,如果我不在此讲述我的故事,我的寓意就会让人产生误解,我正在逐字逐句地重建我的天堂。
和这棵老胡桃树一样,我也被击中过。不过不是被雷电,不是被马匹,也不是被任何人造的东西。就在一年前,我被命运击中。对阿米什男人来说,这是一件比在进入到徘徊期[1],决定是否受洗还要庄严的事情。
[1].徘徊期是指来自宗教规定的阿米什青年的一个对自由的实验期,当他们能够独立地生活时,就可以开车、喝酒,体验其他主流美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徘徊期过后再决定是否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徘徊期一词是高地德语“四处走走”的直译。
去侍奉教会,而你知道这有可能会改变一生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阿米什人[1]感到恐慌了。因为我们不能为此做准备。没有需要学习的课程,也没有需要参加的考试。甚至当一个人被选中时,阿米什人会传统地表示慰问而不是祝贺,这并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对所有人而言。
据我所知,没有男孩儿会梦想长大后成为一名牧师,他梦想的是这种命运永远不要发生在他身上。因为这不仅仅是短短几年的任命,而是要终其一生的责任。
我就是那个为此担惊受怕的男孩,即使是在四十五岁这个年纪,低着头,闻着有些破损的皮革制作的赞美诗集的味道,也依然心有余悸。它们在我们十个人之间分发,我们这十个人就是被家人、朋友、邻居所提名的授圣职的人选。我们的衬衫都被汗水湿透了。大家都坐在桌边,不停地流着汗,紧张地盯着这些赞美诗集。我发誓我们的恐惧若聚在一起就能生出火来。诗集中有一张纸条上有两句诗文,一句来自箴言篇,一句来自使徒行传。所说的基本上就是任何人若在诗集中发现这张纸条就是上帝做出的选择。每个人的手都在哆嗦,腿在桌面下颤抖,一旦有机会,有人就会像发疯一样乱跑,以此来逃避被选中用其一生来作为献身者的责任。我不确定我们之中有人认为自己具有成为一名合格牧师所需具备的品质,如提摩太反复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警惕、冷静、行为良好、热情好客、善于教导”的人。我们之中有人具有这样的资格吗?我们之中有谁做好了用余下的一生来献身的准备?
我知道我没有。我有妻子、孩子和工作,我继承了家族的拍卖生意,还有五英亩的乐园需要保护。一夜繁忙的拍卖就已经让我喉咙发干,更别提周日上午的布道了,在和我一起坐在桌边的人中,我是最不可能的人选。
他们不知道吗?我不是献身者,我曾是一个小偷。在多年的隐瞒和羞愧之后,我想告诉他们我在九岁的时候偷过一台相机。阿米什人不喜[1].阿米什人(Amish)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又称亚米胥派、阿曼派),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欢别人为他们拍照,虽然我曾看见过少数阿米什人高兴地从软帽的黑色帽檐的阴影中抬起他们的眉眼,面对相机微笑,分享他们简单生活的快乐。但我们信仰伪神,我们相信一张简单的相片就能偷走我们的灵魂,尽管相片没有揭示出微笑背后的秘密、一切我们眼中所隐瞒的东西,以及一切我们选择无视的东西。我从不想要相机,但也不完全是这样,我想要的是它所留下的东西。
二
虽然差不多四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事故发生的那一天。1976年7月6日,周二,赶集日。一个来旅游的家庭忘记带走他们的相机,随之留下的还有一些零钱。我把这些硬币丢在爷爷糖果摊后面的雪茄盒里,这些小摊一个挨一个立在集市的帐篷里。我的姐姐们把我留在柜台,偷偷溜出去看本地的青少年们在停车场放烟火。我虽不能透过高大的帐篷看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我知道大姐姐汉娜用爷爷的糖果来换取多彩烟雾弹。女孩儿们会在谷仓后面把它点燃,在那儿她们能跳舞而不会被父亲看见。每年的7月4日之后,集市上就会开始卖烟火,她就会用软糖来跟本地的男孩儿们换取烟火。供应本县的易爆品有一半儿都是这些男孩儿们从卡罗莱纳州弄来的。她很大胆,虽然她不能看见这些有色烟雾的危害,但是她却知道照片所能造成的伤害。
她返回想拿更多的软糖,但却停住了,她看见一个游客家庭的男孩儿也带着相机过来了,想要给我拍张照片,汉娜叫他不要拍。她那时十九岁,但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时毫不畏惧。起初她的声调很温和友好,但这男孩儿还是继续给我拍照。
我让他拍了。
以前没有人想为我拍照片。而这并不重要。人们不允许我们为游客拍照而摆出造型。父母曾无数次地教育我们这一点,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我的大姐姐却执行得最好。有一天她带我们放学回家,在路上遇见一辆旅游巴士停下来看我们,汉娜把我和莎拉拉到一边。“如果他们坚持要拍照,你们就闭上眼睛。”她说,“眼睛是灵魂的大门。无论你做什么,都要锁好它,要低着头,或者看旁边。”然而我想知道如果被拍了照片后灵魂又会怎样。汉娜还说只要我们不直视相机,上帝就知道我们还不打算放弃灵魂。
游客们喜欢汉娜和我的姐姐们。他们毫无疑虑地开着租来的车挤在我们的农场边上,看着我们用双手双脚在土地上劳作。我们习惯了这些相机,就如同在成长过程中习惯了我们农场上的小世界,从蜘蛛咬伤到有毒的藤蔓。相机跟汽车一样,我们都尽可能地避开。然而我并不认为游客是故意想伤害我们。我的姐姐们有着脱俗的美丽,因此看见她们的人都很喜欢她们。她们有着和母亲一样的蓝色眼睛和白皙的瑞士人般的皮肤,脸颊衬着胡桃色的头发,和着教堂里的那种红棕色及金色,盘成圆形发髻,用发夹别在后颈。而我只拥有同样颜色的头发。我是个男孩儿,没有什么能够配得上她们的美丽和优雅。
九岁的我只有她们一半儿高,且较瘦弱,勉强能够到柜台。我常常躲在姐姐们的后面,从箱子里舀糖果。但是这个带着相机的男孩儿有着某种让我想被他看见的东西。我拿着常用来铲糖果的小铲子,从柜台后走出来,让他能更好地看见我,我拉起草帽的帽檐,露出眼睛,咬住嘴唇,强忍着微笑。相机的咔嗒声,在他通过镜头看见令他兴奋的东西时舌头所发出的啧啧声,这些声音让我感觉很舒服。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而我喜欢这种被关注的感觉。这个男孩儿靠得更近了些,红色的肚皮抵着柜台。他的皮肤被晒红了,流着汗水,在玻璃上留下看起来像光亮的甜甜圈一样的印记。
我突然咧嘴而笑,露出缺掉的牙齿,我认为他想要看看我齿间的空隙。我喜欢这种在说话时像在吹口哨的感觉。“甜玉米。”我说道并指着缺掉的牙齿。
“你得到钱了吗?”
“得什么钱?”
“你的牙啊。”
“没有,你掉了牙齿得到钱了吗?”
“保持你手的姿势不动。”他说。
这个男孩儿拍了更多的照片,我看见他的手指按下快门,力求精确并符合意图,他就像在狩猎一样。突然,一副剪刀和戴着一枚大金戒指的有很多汗毛的手盖住了我的脸。
“请不要给他拍照。”
我听出了这声音。一阵低沉而洪亮的声音,在北费城的童年生活经历让这声音听起来更加严厉。这绝对是勒罗伊.费舍尔,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在需要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雇他当司机。我们在大篷货车里与他相处了很长时间。他把这当成是副业,是为他想买的位于斯特拉斯堡的理发店储备资金。在天气恶劣的时候,如果他为了我父亲的拍卖而在深夜出行,我的家人会送给他烟斗丝。他照顾了我们,我们也报以关心。他是我父母唯一邀请来到我们家的外人。我们从未将他称为“英国人”[1]。他就是勒罗伊。我们爱他。他还是我们所认识的唯一的黑人。
他的手在我的面前挥舞,手指闻起来有滑石粉和生熏香肠的气味,他把熏香肠用干酪薄片裹起来当“午饭”吃,我还看见他指甲里也嵌了一点。他拿着一把剪刀,刀片上还粘着一根阿米什男人四分之一寸的银色鼻毛,他是理发师。他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把凳子、一块罩单、一把手持镜子和斜对角。对本地人和游客来说,勒罗伊.费舍尔一直固守在爷爷的糖果摊旁边,他模仿阿米什人很在行,他用减弱的且抑扬顿挫的话语能精确地模仿高地德语的口音,那是我闭着眼在糖果摊后面听到的,我那时认为勒罗伊绝对是阿米什人。
“听着,”他说,“逗你笑是我的职责,你最清楚这点。保罗和玛丽很喜欢花生酱和果冻?没开玩笑,是真的!”我好奇的是他是怎么学会这种口音的,“上帝在我的梦中对我轻语。”他说。这让我有时认为勒罗伊或许就是上帝。我曾问过主教上帝是不是黑人,他告诉我说:“上帝没有面容。”我意识到他的肤色并不重要。在宗教改革时期的瑞士没有黑人,勒
[1].阿米什人把非阿米什社区的人称之为“英国人”。罗伊的先人生活于北费城一带。
尽管这一切的证据显示勒罗伊可能是上帝或至少非凡人,但他却没有宗教信仰。他很少像其他很多美国人那样谈论耶稣。他家里的墙上和摊位上都没有木制的十字架,他也不会随身戴着会悄悄走进集市去买黏糊糊的小圆面包和肉条三明治的修女们挂在脖子周围的红色串珠。他在夏天的每个周二就会出来为大家提供服务,我带着敬佩和嫉妒观看他用黑色的手指摆弄剪刀很多年了。但在那一天我却不希望他出现。
“走开,勒罗伊。”我说。
“随你便。”
“勒罗伊不会走开,我也不会,除非这个男孩不在这里。”
汉娜走上前来站在我们中间,勒罗伊收回他的手。我的耳朵发烫,皱起鼻尖,我的目光转移到她掉在地上的紫色烟火弹,接着又盯着她握紧的拳头。她的声音颤抖着。
“走开,伊莱。”
“我还没拍完哪。”那男孩说。
“伊莱.伊曼纽尔.约德。”
“他还没拍完。”我说。
我的脚后跟用力踩进地面,拒绝离开,我感到了混凝土地面的冰凉。这个男孩拍了更多的照片。尽管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还是很喜欢。我对受相机关注的喜爱超过了对失去灵魂的恐惧。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有从外面来的人想看我。
“如果你不停下来,我就拿走你的相机。”汉娜说。我的姐姐们一个接一个慢慢走过来,她们闻起来有烟火和鞭炮的味道,还有一些破损的纸条卡在她们的祈祷帽上。她们在贝勒的面包摊前停下,站在我们对面,汉娜威胁的语气吸引了她们。她们对着摊主和他的女儿艾玛私语,艾玛用沾满面粉的手捂着她们的嘴。从刚学走路那会儿我和艾玛就成了好朋友。她的父亲是我们教区的主教,她就像我的另一个姐姐。她盯着我们,看上去惊呆了,还不停地摇着头。
这男孩举起相机,缓慢地向我走来,靠近了甘草车轮糖。
“跟我击掌吧。”他说,并敲敲我的手,将他的手掌摆出击掌的姿势,尽管那时我几乎不会说英语,但我还是明白他的意思,甚至连我们的狗都知道“跟我击掌吧”是什么含义。我曾看见过年长的男孩儿们在“徘徊期”时彼此击掌,大摇大摆地带着晶体管收音机在他们的四轮马车边行走,费力做出耍酷的样子。
我举起我的双手,期待着他跟我击掌,但他却拍了一张照片。他大笑起来发出哼哼的嘲笑声。
“哇哦,这真是又大又丑的手啊。”他说。
“你说什么?”勒罗伊问道。
“又大又丑。”他冲我眨眨眼,慢慢地说。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过来。在家里我们都说高地德语,这是一种瑞士德语的方言,我们在阅读时几乎全部使用德语,包括阅读圣经。从六岁之后我才开始说英语,听力比口语要稍好一些。“又大又丑”,这简单的词语仿佛在我的胃里翻搅,我想说什么又好像都哽在喉咙里。我抬起头看见了这个男孩儿的父母,他们回来是争论我姐姐找给他们的用五十美元买两美元二十三美分糖果的零钱。我期待他们会对儿子说点什么,说任何话都行。
“请不要惹我们生气。”汉娜说。
这个男孩儿又笑了起来并向母亲求助。
“母亲,阿米什人不会生气的,是不是?”
“他们不会的。”她边说边咔的一声合上钱包。
汉娜突然伸出手,去拍打相机,还把手心紧紧按在镜头上。男孩儿抬起头,显然受到了惊吓。汉娜凝视着他,耐着性子等这男孩儿离开。她的脸颊变得通红,脖子上也起了红斑点。我从未见过她如此不安,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时勒罗伊转身走开了,他知道在那天他只能帮我到那儿。
这男孩儿举起手把汉娜的手掌从镜头上挪开,并对着我拍了最后一张照片。
“笑笑啊,手又大又丑的人。”
但我没有笑。我收回我的双手,在背后握着拳头,像汉娜那样捏着手指。现在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上泛着红光,脖子上也开始发烫。我噘着嘴,不再微笑。我盯着地面,看见来往的鞋子都停下了,露脚趾的凉鞋紧张地改变方向,一位护士用白皙的脚后跟挠着脚踝。没有人走动,但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我感觉到后背的灼热感一直烧到了我的腰部,又进入了我的肺。我曾带着敬畏之心看见过一位越南兽医在市场的停车场里弹奏手风琴。那时我感觉我的肺就像是那架手风琴,被挤压而感到窒息,受到现实无情的打击。之前从未有人告诉过我的手很丑陋,我只知道它们有些不一样。医生为我得出的诊断结果是并指,是一种阿米什人中常见的遗传病。医生还说这没什么。“那就当一名优秀的游泳健将,”他开玩笑说,“就像一只金毛猎犬!”
指尖的“蹼”从第一处指关节到第三处指关节,皮肤是半透明的且较柔软。我把指尖的“蹼”卷进拳头里,把我的脸埋在里面,突然间,让人无法摆脱的,我意识到了关于我自己。这个男孩是对的,我的双手的确是又大又丑。这就像是上帝点燃了一盏油灯并说道:“伊莱,这就是你。”我再也不想受到任何人的关注。
我站在那里,眼睛盯着甘草车轮糖,不能移开,这时一阵类似炸弹爆炸的声音让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像发狂一样散开了。本地的一个少年点燃了一枚M-80焰火,它穿过帐篷飞过市场。那个男孩儿在跑出去的时候把相机留在了柜台上,它静静地立在那儿,等待着。
我要拿走它,我对自己说,并且丝毫没有感到歉意。
我知道这不对,但我不在乎。
我扫描着空荡荡的市场,在爷爷糖果摊旁边的货摊上找到一排没有脸的阿米什人玩偶。共有六个,五个女孩儿和一个男孩儿,就像我和姐姐们一样,但是没有眼睛。我弯下腰来对着玩偶低声说话,请它们允许我拿走这台相机。我在甘草车轮糖的箱子上挖了一个洞,把它藏了起来,我闭上眼睛祈祷这个有红色肚皮的男孩儿永远不要再回来。当我抬起头,视线越过玩偶们,我看见了勒罗伊.费舍尔站在他的镜子面前看着镜子里的我。
记得那晚我不想上床睡觉,因为我不想去思考我是怎样度过那一天的。在晚餐时,我想象主教问我:“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即便我们的厨房很暖和,但当想到答案时我还是打了一阵寒战。我怎么能告诉主教或者我家里的任何人说我偷了一台相机?从此我变得沉默。每当我要吃东西时,就会看见勒罗伊脸上疑惑的表情,我丢下叉子,看着盘子里自己的倒影。在伊萨克叔叔和我的侄子们以及贝勒主教来访时,家里的餐桌就会变得拥挤。这顿饭是用来庆祝的。就在这周之前,十八岁的双胞胎姐妹凯蒂和艾拉,她们宣布了受洗的决定并在秋天加入教会。因为我的父母设想并期望他们的大女儿汉娜也会受洗,他们就觉得应邀请主教参加晚宴,并提供我家的马棚作为举行仪式的地点。但是那天没有人谈到洗礼,而是都看着我,并表示担心。
只有伊萨克叔叔问了我是否安好:“艾玛告诉我你在集市那天遇到了些事情。”他说。
我吞咽了一下但没有说话,而是盯着一块块的食物——用卤水泡过的胡萝卜、花椰菜、黄绿色的蜡豆。我的母亲在我的背后停下,手里拿着盛着面包卷的篮子,她用手腕的背面按着我的额头。她只是边叹气边看着我的姐姐们,想知道关于我古怪行为更多的信息,为什么我不吃东西?为什么我的手垫在屁股下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