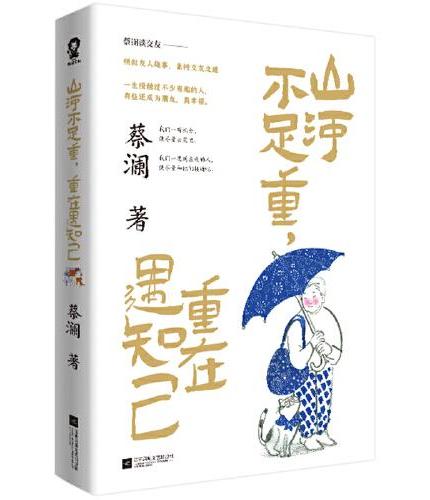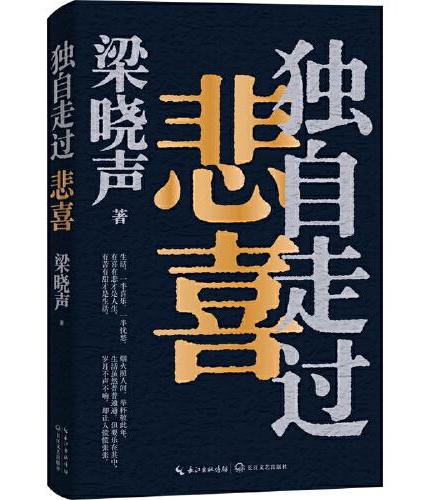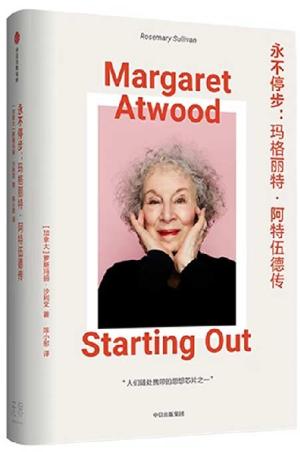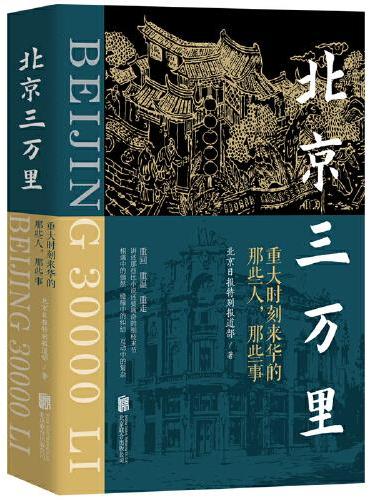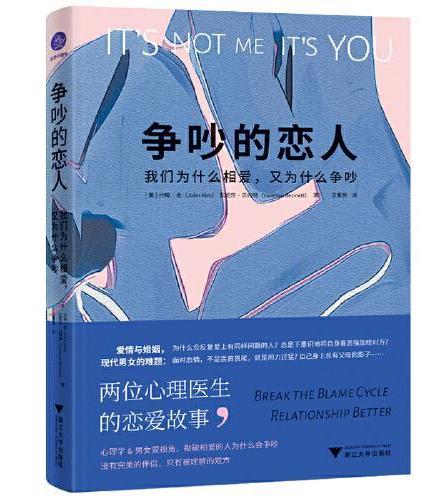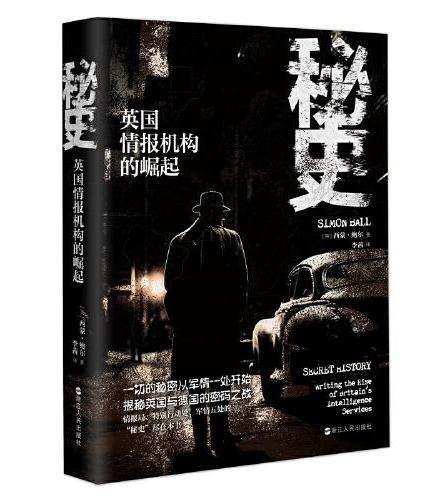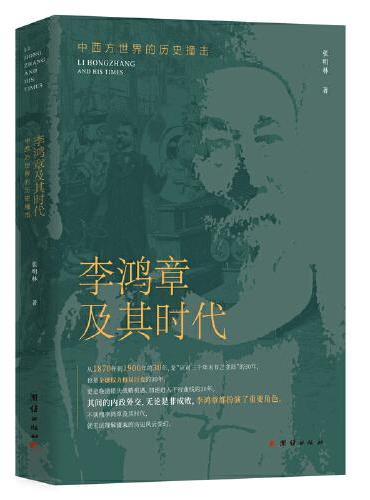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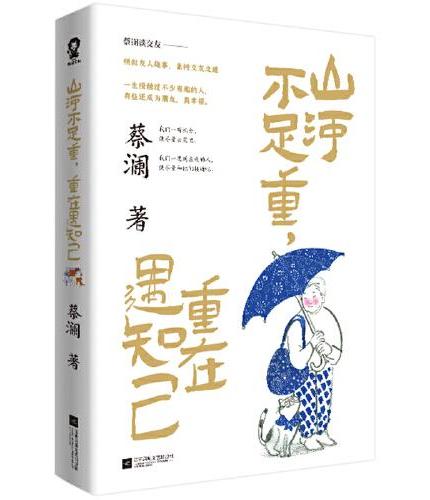
《
山河不足重 重在遇知己
》
售價:NT$
2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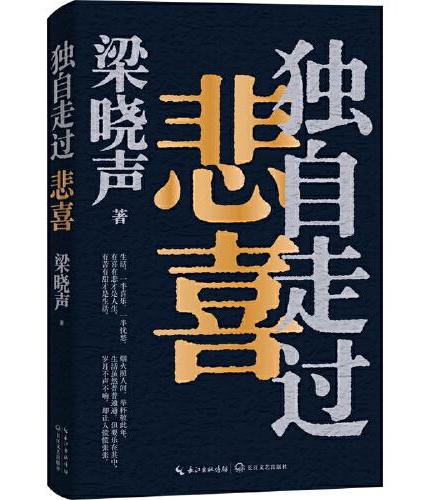
《
独自走过悲喜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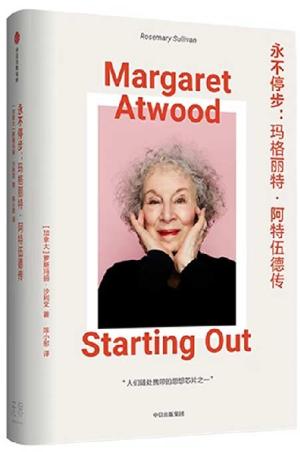
《
永不停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传
》
售價:NT$
442.0

《
假努力:方向不对,一切白费
》
售價:NT$
3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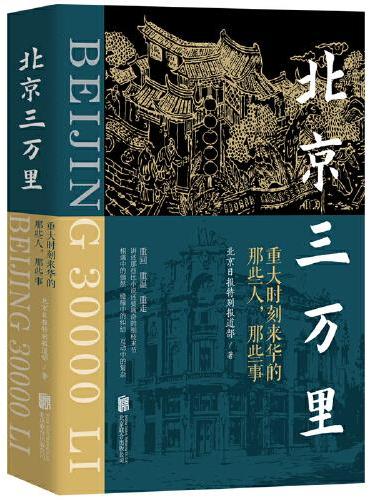
《
北京三万里(重回、重温、重走、重述破冰者眼中的“北京印象”,讲述那些比小说还要离奇的细枝末节)
》
售價:NT$
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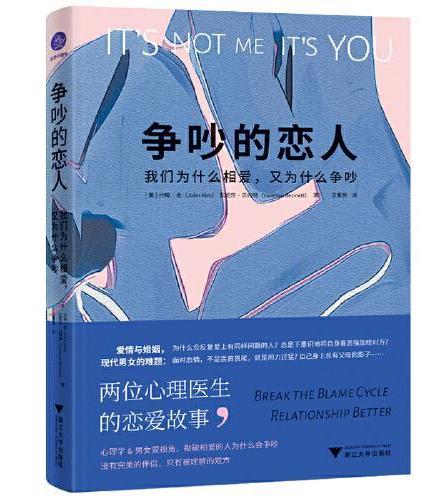
《
争吵的恋人:我们为什么相爱,又为什么争吵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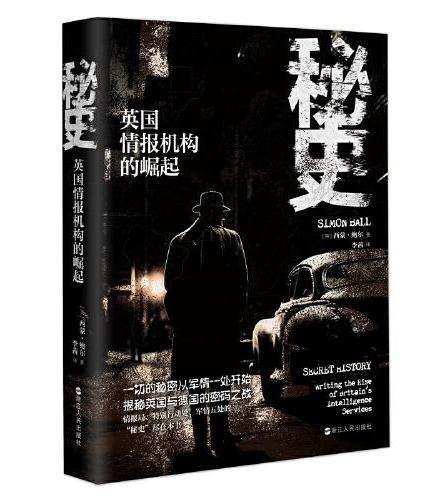
《
秘史:英国情报机构的崛起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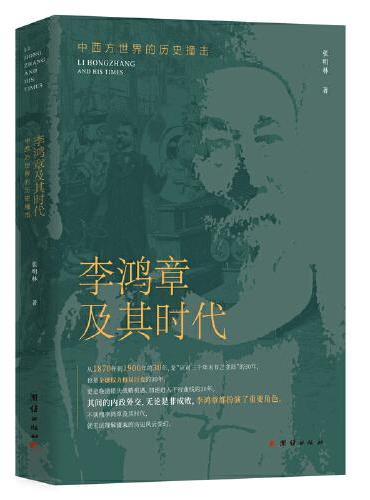
《
李鸿章及其时代:中西方世界的历史撞击
》
售價:NT$
330.0
|
| 編輯推薦: |
1.诺曼·马内阿是当代最具天赋、最具独创性的东欧作家,以深刻、纯粹的写作捍卫良心的自由。其作品获得多项欧美文学大奖,如:法国美第奇奖、德国奈莉·萨克斯文学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美国犹太图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意大利那不勒斯文学奖等;
同时获得菲利普·罗斯、索尔·贝娄、君特·格拉斯、奥尔罕·帕慕克、伊姆雷·凯尔泰兹、辛西娅·奥兹克、齐奥兰、保罗·贝利、奥克塔维奥·帕斯等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赞誉。
2. 《流氓的归来》是诺曼·马内阿获得评论界普遍喝彩的文学回忆录,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3.著名作家李静睿(网名:阿花的伊萨卡岛)为本书写序倾力推荐。
|
| 內容簡介: |
|
《流氓的归来》是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的回忆录,书中他对自己的经历,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描写——包括对人生最隐私的部分:性恋、恋母情结、婚姻、家族秘密、犹太身份的认同、流亡者的归属、自我的认可等方面的叙述,坦诚深刻得到令人惊叹的地步。马内阿的创作由此超越通俗意义上的是非褒贬,最终超越自我,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人性,并折射了那个灰色的时代。
|
| 關於作者: |
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 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纳粹集中营幸存者。1986年离开罗马尼亚。先到西柏林,后定居美国纽约。著作有《黑信封》《流氓的归来》《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必须幸福》《十月,八点钟》等。
马内阿是当今世界被翻译得最多的罗马尼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与赫塔·米勒并称为罗马尼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作品曾获意大利诺尼诺文学奖、意大利那不勒斯文学奖、美国犹太图书奖、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法国美第奇外国作品奖、德国奈莉·萨克斯文学奖、西班牙《前卫报》最佳外文著作奖等多项欧美文学大奖。
马内阿的作品流传广泛,佳评如云,不仅是近半个世纪东南欧文学的骄傲,也是当代世界文学罕有的精品。他也因此被认为是比昆德拉更深刻、更纯粹的东欧作家,甚至被比作卡夫卡的继承者。
|
| 目錄:
|
诺曼·马内阿:每个阵营的局外人李静睿
初篇
巴内绿草
乔尔马尼亚
花脸小丑奥古斯都的马戏场
往昔的痕迹(Ⅰ)
新日历
爪子(Ⅰ)
第一次回归(小说过去时)
开始前的开始
流氓年
布克维纳
切尔诺贝利,1986年
在一片含苞欲放的花丛中
流浪的语言
陌生人
布卢姆日
逃避
往昔的痕迹(Ⅱ)
玛丽亚
国王万岁
乌托邦
佩日普拉瓦,1958年
职员
离开
夜班
蜗牛壳
爪子(Ⅱ)
维也纳躺椅
对前世生活的回忆
第二次回归(后世)
在路上
第一天:1997年4月21日,星期一
第二天:1997年4月22日,星期二
夜的语言
第三天:1997年4月23日,星期三
第四天:1997年4月24日,星期四
午夜对话者
第五天:1997年4月25日,星期五
存在之家
第六天:1997年4月26日,星期六
第七天:1997年4月27日,星期日
夜行火车
第八天:1997年4月28日,星期一
第九天:1997年4月29日,星期二
最长的一天:1997年4月30日,星期三
倒数第二天:1997年5月1日,星期四
最后一天:1997年5月2日,星期五
|
| 內容試閱:
|
新日历
1988年1月20日,星期三,这是D日(D-Day),决定性的日子(Decision Day)。我已经在这个过渡性的城市逗留了整整一年。经过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之后,目前已经到了无法再拖延的时刻。“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克尔凯郭尔这么念叨。犹豫不决似乎没有什么新奇。犹豫不决了一生的荒唐,又被持续了一年多。
说穿了,这一切,不过是归属感着落不明所致,以及这种感觉的可笑性,如此而已。我们的主人公面色苍白,他被自己的滑稽剧选为主角,并被这滑稽剧弄得不知所措。在星球上众多的、被每一时刻的麻烦缠身的人当中,他显然是其中之一。难道,他还没有从禁锢了一生的皮囊中解脱出来吗?难道,尽管他记不住一小时前见过的脸孔,却还没有忘却往昔吗?
“轮到您了。您得与委员会小组面谈。”
穿着蓝制服的女士向他示意。他抓起公文包,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那长凳上另外还挤了五个人。
她说:“您先与法国领事谈。完后,再回到我这边来。”
她向他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左边的那扇门。
仅三步,就到里面了。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一位瘦骨嶙峋的先生,请他在自己对面坐下。他坐下,把包放在两臂中间。
“您想用德语?要不,还是用法语?”那位法国人用德语问。
“法语就行。”他,签证申请者,用德语回答。
“那我很高兴,我很高兴,”这位官员微笑着用法语接着说,“罗马尼亚人几乎都会说法语,不是吗?我在巴黎的罗马尼亚朋友对法国社会适应起来一点儿困难也没有。”
“对,对罗马尼亚人来说,法语很容易。”这个罗马尼亚人,用法语确认。
他更仔细地端详这个坐在面前的先生。这个罗马尼亚人,用罗马尼亚语想:如今的时代,所有的考察官都比被考察的要年轻。
这位官员有一张长形脸,鼻子突出,鼻梁细瘦,双眼很黑,显出智慧,头发浓密,他的笑容年轻而悦人。他的领带结是松的,天蓝色衬衫领子的口子也开着,没有系扣子的深蓝色西装,潇洒地从他消瘦的肩头垂落下来。他的声音和蔼亲切,是的,既和蔼又亲切。
“昨天我跟一位罗马尼亚女士提起您。因为知道今天我们要谈话,我就问她是否认识您。”
申请人没有反应。他只是用法语(这语言刚说出了让他吃惊的话)保持沉默。
他面前的法国官员点起了一支香烟,然后,把双手掌心朝下放在写字台的边上。他在皮转椅里舒适地放松了两肩。他在这转椅里显得更自在了。
“您不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昨天,我看您填的表格,这些书名……这个巧合让我吃惊。”
他在说“这些书”的时候,从书桌上拿起了申请人填的表格。他在空中举起这份表格,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接着是一段冗长而无法解释的沉默。只是过了片刻后,这法国人才重新抑扬顿挫地说:“我看过您的小说《俘虏》(Captives)。”
静谧的房间里,这个节奏完美的句子,令人想到击剑角斗。剑锋所指:中!不,房间里的静谧未被刺破。
那法国人接着说:“我想,大概是在70年代中期,我在巴黎上大学,我选了一门罗马尼亚文。”
申请人摘下眼镜擦拭。
“那时大家都在谈论审查。审查和隐语。独裁制度下的隐语评论?!囚犯们的……隐语。”
申请人抓紧了提包的手柄。他想用自己会说的所有语言这么吼叫:骗子!此刻,他肯定,面前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外交官。难道西方与东方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暗示,一样的语言,一样的陷阱?……这个非党人士,曾经拒绝了与本国的魔鬼达成协议,难道,此刻,他得被迫跟他们的国际同谋成交?难道,在还没有获得无国籍证书之前,他已经变成一个毫无防卫的囚徒了?已经成为一个无名的贱民,一上来就任人宰割?
终于,他用法语结结巴巴地说:“这对我来说非常意外。我不知道,从来没人向我提起这个……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竟然出现在巴黎。”
“这对我也非常意外。您想,当我在这表格上看到您的名字……”
他重新把书桌上那张申请人的表格拿起来,再重新把它放下。
“我看到这个名字,那些书名……您应当在法国定居,而不是在德国。”
应当在法国定居……这是建议?一种许诺?一个不用明示的契约?但都不像。他对签证申请人非常有礼,把他当作一个著名人士对待,充满了敬意。如果这些都是些陷阱,那也不是用来对待凡夫俗子的。
“对一个罗马尼亚人来说,最合适的流亡地是法国,这您知道。您很快会有朋友。跟其他许多著名的同胞一样,您会用法文写作……”
没错,这位考察官不仅知道小说《俘虏》的书名和主题,而且了解伊奥奈斯库—齐奥朗—伊利亚德
的三重奏,他甚至提到碧贝斯克公主(Princess Bibesco),还有诺亚蕾丝公主(Princess de Noailles)和娃卡瑞斯克公主(Princess Vacaresco)
,他爱坚持区分一个是大公主另一个是小公主。他甚至听说过本杰明·冯达
。他显然是备了课的。
对话以同样的形式,一直进行到最后。结果,考察官从书桌的另一边,挪到了被考察者身旁。表明他友好的最终证据:名片——他的名片上有柏林的地址和巴黎的地址;邀请晚宴;答应帮忙,任何性质的帮忙——要是有必要,就在那儿,柏林,或者,更理所当然,在巴黎。总之,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每种情况下,任何时刻,他这么念叨,带着微笑。他与他友好地握手,并穿过对方的眼镜片,送去了这个意思:要是能在这个命运让我们意外认识的地方,共同度过一个晚上,那真是太好了。
这位成了朋友的官员,不仅把他送到门口,而且把他送到那个穿天蓝制服接待员所在的前厅里。他宣布:他的这位朋友,某某先生,已经结束了与法国当局的面谈,现在可以接着与掌管西柏林的其他强权盟国代表交涉了。面对拉丁人的结盟,德国秘书毫不怯弱,她镇静地等着这两个说法语的人分手。
左边的门关上了。这位签证申请者被撂在那儿,继续等待。他看了看表,中午12点差10分。这时,德国秘书终于抬起眼睛,用她短促生硬的德语说:“完了。今天你没事了。明早8点你再来。先到前门登记你的名字,然后9点钟到135室去。”
那天很冷,但有太阳。他先乘公共汽车,然后是有轨电车。下午2时左右,他终于到家了。
他到达这个过渡城市已经有一年多。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自由岛上,感到十分自在。色彩缤纷的广告,繁多的商店,人们自管自的忙碌,这一切,对这个外国人来说,逐渐地,都成了习以为常的生活景色。而仅在这不久以前,他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这里的自由让他惊喜而又害怕。他已经不再能回去了,但似乎对新生却没有准备。太多的不肯定,太多的心理障碍。在原来那个火柴盒的生存中,在习以为常的挫折和幻想的并存中,不知怎么,他觉得自己绝无仅有,觉得自己是重要的。难道他将丢失那个在岁月长河中成形的、刻入社会暗号的语言吗?这等于自杀,这与回到惯于谋杀的祖国没有什么两样。起码,他这么想。
与法国专员面谈的前一夜,是无数个犹豫不决的漫长之夜中最艰难的一夜。自从他,也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扎入这个自由岛以来,那些不眠之夜,一直折磨着他。无论这另一个世界带给他多少欢乐和新生,他仍然害怕,在有了一定年纪的这时,自己会变成一个不断得学说话的孩童,并将在这个第二次儿童时代,磕磕巴巴地,连着手势,用含糊不清的发音,来表达各种感恩之情。
过渡城冲破夜晚的白雾,显露出它豪华的高楼和大道。远处,传来了节日的音乐。这个充满了艺术家和间谍的城市,有着极其丰富的夜生活。他好像看到了那道城墙:它围护自由,使其不受墙外囚徒世界的骚扰;它围护墙那边的监狱,使其不受自由病毒的侵入。
一夜,一日,再过一天,再走上几步,这个50岁之人,便会在这另一个世界,得到新生。从1988年1月21日起的生活,被叫作:来世。
他躺在沙发上,瞧着日历上画着红圈的地方。他起身,用红笔,仔细地在红圈上写上:MARIANE(玛丽安娜)
!对着这名字,静想了片刻:不,不够好!他抹去了这个名字,然后,还是用红笔,在这页日历的底边,写了:FRANCE(法国)!接着,他微笑了,像是一个对阿姨耍了把戏而兴高采烈的孩童。他又在那个字旁边加了:ANATOLE,ANATOLE FRANCE(阿纳托尔·法朗士)
。他这才又回到沙发里。在里面坐了很长时间,他的右手,一直握着那个法国官员的名片。
与这位巴黎代表共进晚宴,共进许多晚宴?这能洗去自己从令人怀疑的乔尔马尼亚来的嫌疑吗?这需要时间,需要进一步的许多见面。而且连一场关于文学的讨论他都没来得及与这位自己的仰慕者展开呢。不知此人是以何种语言读了自己的书?他慢慢地,将法国官员的名片撕成碎片,一再证明:对于自由世界能够提供的优惠,他显然不懂如何加以利用。
次日,1988年1月21日,这个外国人又来到市中心,沿着库夫斯坦大道,来到了郊区神圣的三国委员会。他按照要求,准8点即到大门,9点,出现在135室门前。他手携提包,在135室门外的长凳上,耐心等着。11点15分,接待女士,不说一句话,向他指着右边的美国门。
跨三步,他进入了门里。办公桌后面一位年轻秃顶的先生,请他在办公桌前坐下。他坐下了,双手捧着提包。
“说英语吗?”这美国人用美国口音的英语问。
“说一点儿。”申请人用含糊其词的国际语回答。
“好吧,不过我们也可以用德文,怎么样?”这美国人继续用带美国口音的德文说。
申请人点了点头。他细心观察面前的这位先生,此考察官甚至比前一天的那位更年轻。他结实的身材,固紧在大翻领的咖啡色制服里。里面的白衬衫的领口非常紧,他的脖子却很粗,很白。双眼很黑,带有审视的目光,双手很小。左手一指戴着很粗的金戒指,与外衣袖口露出的白衬衫袖口上的金扣链相配套。
“护照。”军人的口气,军人的风格。
申请人朝着双臂间捧着的大包低下头去。他从里面拿出一个夹着许多纸张的绿色夹子,从夹子里拿出绿色的护照。考察人一页一页仔细地翻阅。
“您不是头一次到西方旅行。”
对这个评论,申请人没有评论。那位强权代表盯着他看了很长时间,然后,语气坚定地把笼罩室内的沉默打破了:
“您在这之前两次到西欧,一次到以色列。”
沉默开始沉重起来。
“您旅行的经济来源?”沉默被打破了,“您的东欧钱币在西方是不能兑换的。除非政府提供西方货币。而政府只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才这么做。”
“我从来没有用政府的钱旅行过。”他赶紧对持怀疑人提出抗议,“我在国外的亲戚给我寄的钱。”
“亲戚?好慷慨……他们在哪里?在哪个国家?”
旅行者不能让可疑的沉默变得更加可疑,于是赶快将自己四散的家族成员们所在的国家一一列出来。
“在美国也有吗?”这位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兴奋起来。“在哪儿?是些什么样的亲戚?”
“我妻子的妹妹。她与一位美国人结婚十多年了。她是两个美国孩子的母亲:一个10岁的女孩,一个4岁的男孩。”
“那么柏林呢?您是怎么来柏林的?您的亲戚总不见得为您选了这么一个地方吧?我想您的亲戚不会热爱柏林的。”
沉默又延长了。这次,这美国人好像对自己很满意。
“我来这儿是因为德国政府提供的奖金,我在申请表的个人履历部分中清楚地解释了。”
“是的,您清楚地解释了。”这位官员承认,并从办公桌上举起了一个卷宗,在空中举了一会儿,然后把它放下,并把它推到一边,它似乎对他再也不重要了。
“你得到了失败者向胜利者提供的奖金,我们可以这么说吗?”
他好像并不急于结束关于德国的话题。战胜敌人完全不是容易的……他好像在提示:这才是把他,一个美国年轻人,和面前的这位上了年纪的东欧人,结合起来的真正原因。
德国是因罪孽感而设立奖金?是的,这位奖金获得者,曾经多次这么认为。这是战败者们向他们无法灭绝的幸存者们提供的奖金?这是战败后的德国,在复兴后,向永远处于失败地位,且注定贫困和移民的东欧提供的奖金?战后的德国,尽管处于被压缩到最大限度的德国边境内,却仍然以同样的旗帜,同样的国歌,保持了勤奋和效率。即使巴伐利亚,也没有像一些人所预见的:歌德和俾斯麦的国家将由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掌管。新预言家们肯定:犹太人将要求德国人用三代人的时间来证明他们不再反对而是维护犹太人,然后,犹太人才会重新认领他们在灾难中失去的德国国籍。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这个幸存者,自言自语,重复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对事实做了相反结论的玩笑,把事情给看反了,从右向左,犹如希伯来文的《圣经》。而事实是,人们要求,从死亡集中营出来的幸存犹太人,必须向那个想要灭绝他们的国家,用血缘来证明他们的所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被允许得到那个令人羡慕的战后德国国籍,这个国家对不再指望享有胜利果实的穷人和失落者们慷慨施舍奖金。
签证申请人自然没有时间来诉说这一切。那个年轻的考察官截断了对话,他开始书写起来,他在填写卷宗里的问答。要不然,他也许会乐于听到这些用来取悦于强权的讥讽联想的。
当申请人从公文包上抬起眼时,他看到,这位美国官员已经站起身来,微笑着向他伸出手来。“先生,祝您好运,祝您好运气!”他向他祝贺,用美国的方式,此刻,他放弃了他们共同敌人的语言。
这个关键日的下一步,是会见英国雄狮,其实它已经不再是狮子了。那位女接待员,此刻,正津津乐道地在讲电话,她没有发现,美国的面试已经完毕。甚至在她放下话筒时,仍然没有注意到她前面的影子。
“接着是跟英国人见面吗?”这个外国人腼腆地问。
“先生,什么也不接着,”她脱口而出,“您的事情结束了。杰克逊先生也替英国人签了字。”
申请人捏紧了提包柄,然后,朝着出口走去。
“先生,请别忘了,明天上午9点30分。”
反正,是完了,却又没完。他转过身来,对着接待女士,不知所措。
“明天您将与德国当局做最后的会谈。在一楼,202室,9点30分。”
这是沉闷阴湿的一天。他向着汽车站,慢得不能再慢地走去。
爬楼梯,用慢得不能再慢的步子,走向三楼,七号单元。他从大衣口袋里拿出钥匙,打开门,在门口待了片刻。房内很暖,静得很。他没有脱下大衣,从桌上拿起那只粗大的红笔,走向日历。他用手指把日历翻到1月20日那页,然后翻到1月21日那一页。他在1988年1月22日星期五那页上,画了个圈:两个粗大的圈,红颜色的。然后,他在上面写着:“假如我活到明天,”接着,又加上括弧,在里面写上:“托尔斯泰公爵,亚斯纳亚·泊利阿纳
。”
这位幸存者,又一次得以存活过来。他想起了那位波兰诗人的《天堂的报告》,便大声朗读起来:
天堂里的劳动时间是每星期三十小时
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
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很容易猜想出诗人在此指的是何处。要是他将诗句写成散文,那么,那个法国官员和英国与美国的官员们,都将明白这个编成暗语的报告:在天堂里,人们每星期只劳动三十小时,他们的工资却更高而物价则持续下降,体力活并不累人(因为重力比较小),砍木头并不比打字更艰苦。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然后,他试图加以简化:社会制度稳定,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对了,这用来当每日的祈祷文很好。
他又把波兰诗人的文字过了好几遍,他在每个诗行里挑选出一些文字,好让明天那个他要会见的德国官员读起来容易些。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接着,他又概括了下一段诗:只有极少数人见到上帝。他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其余的人只能聆听关于奇迹和洪灾的报告。
那晚无梦,一觉睡到闹钟响。
出门之前,他又退回来,从桌上拿起祈祷文的草稿: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他叠起纸张,放进口袋里。他觉得受到一些保护,他又熬过了一个晚上,他也会熬过这将临的一天。
他在指定的时间,来到了指定的房间。一个矮小短矬的德国官员,没有穿制服打领带,穿一条灯芯绒裤子,一件很厚的羊毛外套,绿色的,里面的羊毛衫,也是绿色的。他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头路分在中间。双手很大,上面有大块浅色的斑,他的前额和头颈上也有类似的斑。
一个半小时的面试后,这外国人晕晕乎乎地出来,记不住被问了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这个办事员对他重复了两次的警告:您选择的道路将是漫长的,没把握的,第一步仅是第一步。
对,对……布克维纳,他的出生地,那是第一步,然而,正如他所了解的,德国身份是由血缘认可的,而非取决于出生地点。我们不是法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不,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即使我们是在盟国大委员会的楼里面……这个官员这么解释了,一边站起身,大惊小怪似的,朝天举起了双手、抬起双眼。
“出生在德国并不等于就是德国人!哪怕出生在德国内陆!更别说别的地方……”他重新低下头,念表格上的内容,继续核对上面的外国名字。“啊,对了,布克维纳……以前是奥地利的省份,我们承认。但这只延续了百来年,我们承认。奥地利和德国是两码事,完全两码事。作为从东欧来的,先生您肯定了解这一点。那个疯子毁了德国,正因为他,现在这个盟国大委员会设在柏林……”这个纯德国血统的德国官员,朝着无耻玩弄了德国命运的万能上帝,重新举起了双手、抬起眼睛。“不是吗?那个疯子,就是因为他,德国没完没了地在赔偿,再赔偿,并一再欠下新的债,吞下新的诅咒,并得承受由这个盟国大委员会送来的乞丐和穷人潮水般的入侵。而那个疯子甚至根本不是个德国人,他是奥地利人,众所周知。从那个林兹,从奥地利,来了个疯子阿道夫!……他本人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个事实。而且,即使你是德国人,但你离开德国八百年了,那你还算什么德国人?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您的一位女同胞,她自称:既然她是被驱逐的德国人,她认为,她现在要重归德国。八百年过去了!八百年,您听见了吗?八——百——年,自从德国殖民者远征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那个百纳沱(Banat)。”
这个异国名字“百纳沱”,是罗马尼亚西南部的一个省,古老殖民者的后代们至今仍然生活在那里。但他面前的卷宗里并没有这个名字,它也不在布克维纳的旁边,他只是在自己的记忆里找出了它。他显得对自己非常满意。
“对了,对了,bestimmt,百纳沱!八百年之后……人们可以立刻看出区别来,从口音,从用词,从举止,请相信我,请您相信我。”
总之,昨天的面试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前天的也不是这么回事,而今天就不同了:实际上,这位好意的德国代表是想告诫他。
他来到汽车站,然后坐有轨电车,心里想着那位德国官员的话,忘了下车,到了城市的另一头——
一个有着低层房屋的郊外住宅区。他叫了一辆出租,让司机开往市中心的纪念大教堂(Ged·chtnis Kirche)的废墟附近。
教堂四周的人行道上满是生气勃勃的行人。市中心,到处是人,尤其是年轻人。他,心不在焉,踏上了一条边缘小路,走进了见到的头一家饭馆,弥补这徒劳的一天,犒劳自己受到的令人迷惑的挫折。
晚上,当他打开单元的房门时,黑暗中,他听到室友惯常的问候。“做决定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时刻。”与每天晚上一样,克尔凯郭尔先生满怀心计地这么念叨。是的,然而,犹豫不决所带来的精神错乱,也是不能忽略的。于是,这般夜间的争执便毫无疑义。
上床前,他念了晚祷:在天堂里人们真的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人们无法准确地将灵魂和肉体区分开来,于是他便带着一滴脂肪和一线肌肉来了。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社会制度稳定而执政者讲理。上帝只对少数纯净无瑕的人显露。在天堂里人们生活得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好。
一个月之后,他到了巴黎。在那里,他无数次地后悔没把那个盟国委员会的法国仰慕者的名片保存下来。又过了一个月,他又跨出更远的一步,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来世。这是跨越汪洋的一大步,在1988年3月,这一大步,把他带到了新世界。
在众多外国人中做一个外国人的欢乐,自由女神像和自由的限制及其面具,新街区和新语法,这些不仅包围着他,同时也活在他的身心里,弃国而去的创痛,心灵和头脑的新毛病,身处异地的眩晕,活在自己来世新生活里的机遇。一点儿,一点儿,他开始接受这新日历,接受天堂的飞跃数目:自由流亡生活的每一年,都相当于前世生活的四年。
到美国一年半后,也就是说,按新日历算,便是第六年,柏林墙轰然倒塌。在社会主义乔尔马尼亚,喀尔巴阡山的白脸小丑和他的妻子墨尔杜同志受到了审判。他现在是希望重归往昔,重归故国,重过旧日吗?从另一个王国传来的信息打消了他这些念头。他重新审视了以往经历的困惑,重念了波兰诗人关于天堂报告的诗(他已经把它当作祈祷文),又复习了关于天堂的现实警句: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
奥维德(Ovid),这个被罗马帝国驱逐的古代诗人,生活在遥远的东方,黑海边的托米省(Tomi)的锡西厄沙漠(Scythian),他是否超越了悲哀?此刻,话得反过来说:在托米省与他自己之间,距离日复一日地变得遥远。纽约那多礁石的哈德孙河畔,是他沉船的地方,在他的新家,眼前的罗马,悲伤是用抗抑郁药剂和练身房来治疗的:抑郁是体内化学平衡的失调,而非个性的缺陷。每一种东西都有其疗法。请拨1—800—求助热线。
1997年,新日历的第九年,即柏林D日——1988年冬天的柏林——后的第三十六年,向他提供了回到往昔的空间和时间的机会。
按新日历算来,这时的他,已经有94岁了。老了,太老了,已经不适合再做这般远行了。但是,与此同时,如果按他抛弃前世日常生活那日算起的话,他仅为11岁。对于一个如此年轻而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类朝圣似乎又显得过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