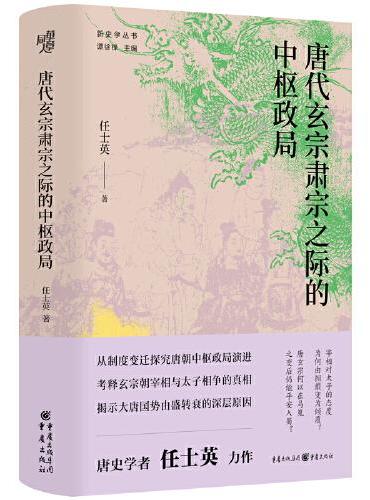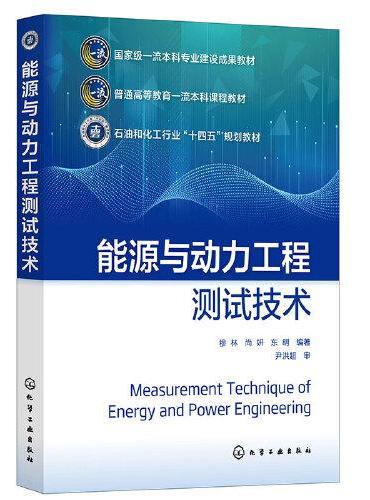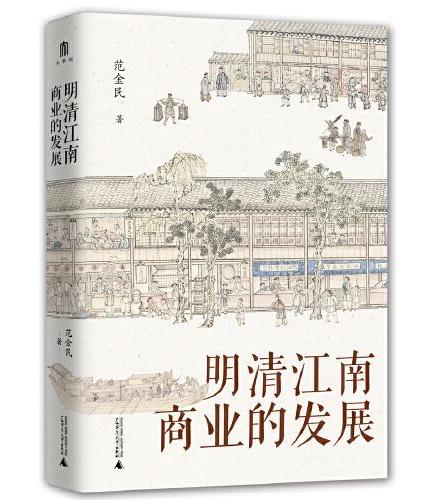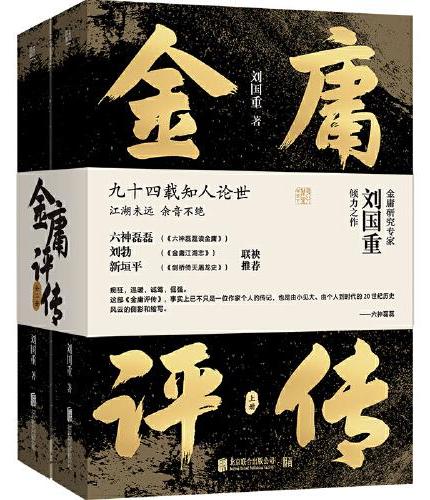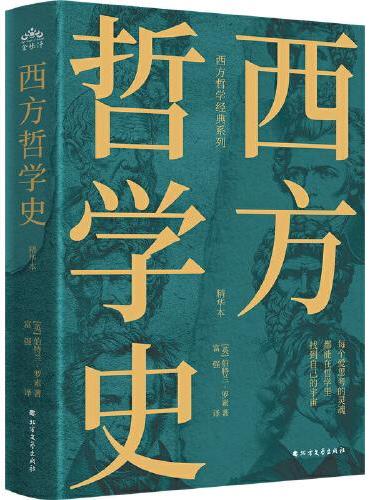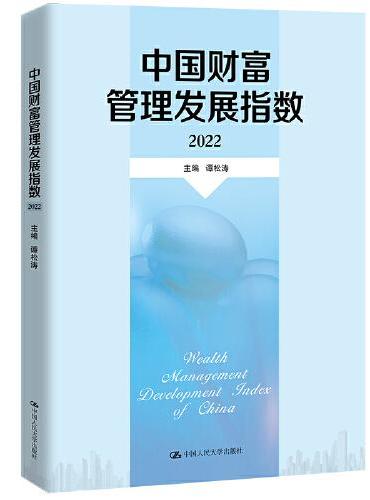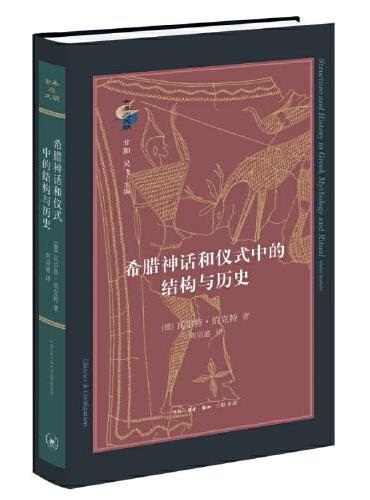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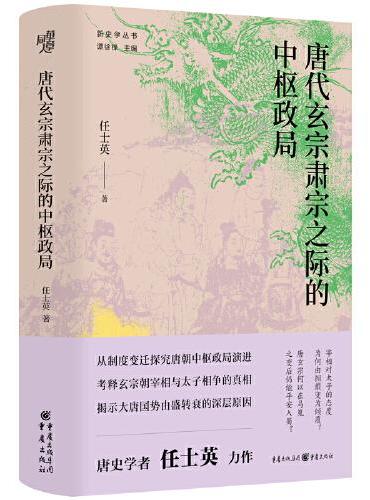
《
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
》
售價:NT$
4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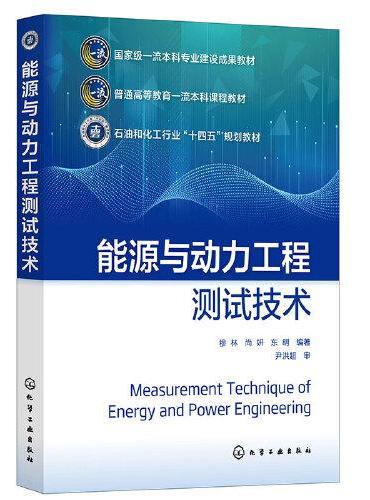
《
能源与动力工程测试技术(穆林)
》
售價:NT$
4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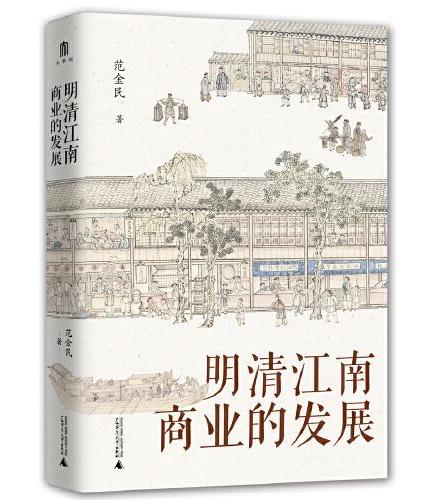
《
大学问·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
》
售價:NT$
4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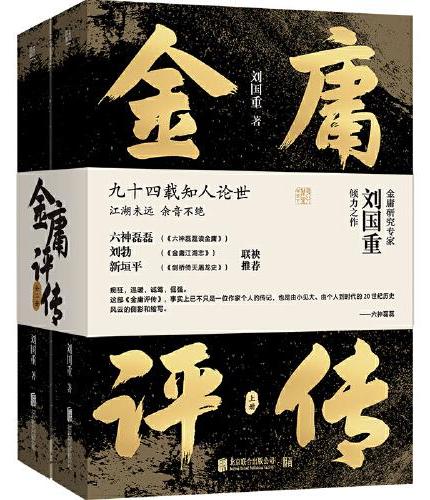
《
金庸评传
》
售價:NT$
9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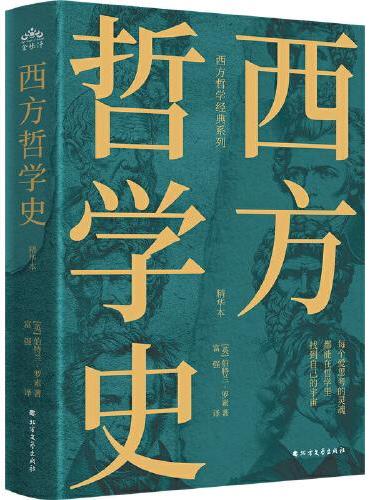
《
西方哲学史
》
售價:NT$
4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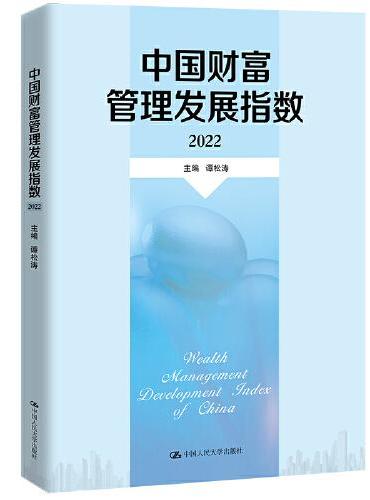
《
中国财富管理发展指数(2022)
》
售價:NT$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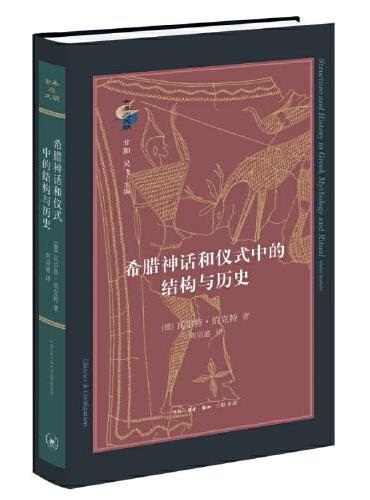
《
希腊神话和仪式中的结构与历史
》
售價:NT$
437.0

《
世界花纹与图案大典
》
售價:NT$
1669.0
|
| 編輯推薦: |
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研究视域从来没有离开过对中国社会的人文关注。
如今,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
新时期呼唤新人文,也不断催生着新人文。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作者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些看法。论述了先秦、魏晋、宋明、晚清四个历史阶段中,中国哲人以经典诠释、义理体认的方式,建构“中国哲学”的历史过程,并探讨了当代“中国哲学”如何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参入全球化文化交流等问题。
|
| 關於作者: |
|
朱汉民,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教授,历史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国书院学会会长、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重大学术工程、国家重点图书、教育部社科重点项目和其他部省科研项目二十多项。出版《宋明理学通论》《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等个人学术专著二十多种,主编文库、丛书、丛刊等十多种,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委、省政府平定的“首届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获得湖南省政府颁发的“徐特立教育奖”等荣誉。
|
| 目錄:
|
目录
自序 001
第一辑 中国哲学建构的反思 001
当代中国哲学建构的双重理据 003
义理之学
——中国哲学原型简析 013
易学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019
中国知识传统的审思 030
中国传统“内圣外王之道” 041
谁误读了“格物致知”? 066
第二辑 先秦理性 073
“五经”思想的信仰与理性 075
原始儒学的经典诠释与义理建构 083
先秦的性命学说 091
先秦儒家“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 101
儒家主体性伦理和安身立命 109
儒、道的和谐思想 123
第三辑 魏晋玄理 127
王弼的经典诠释方法:本末之辨 129
玄学的《论语》诠释与儒道会通 136
王弼的义理易学 151
玄学的身心之学 169
玄学与性理之学 185
第四辑 宋明近思 201
周敦颐易学的宋学精神 203
胡安国《春秋传》的“圣人以天自处”论 212
朱熹《大学》“明明德”诠释的理学意蕴 225
朱熹经典诠释的两重进路 239
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语言—文献 246
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实践—体验 258
朱子“自得”思想的义理内涵 265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280
朱熹“四书”学与儒家工夫论 288
朱熹对“天理”的时空追溯 296
王阳明的工夫与本体 302
王船山的道统、治统与学统 311
第五辑 晚清转型 325
魏源:学、治、道的转型 327
曾国藩的礼学与礼治 342
郭嵩焘:开放的道统 350
湘学的传统形态与近代转型
——以谭嗣同及其浏阳之学为视角 361
谭嗣同的新仁学 379
后记 387
|
| 內容試閱:
|
自序
我在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哲学”是一门既具有人类哲学普遍性,又有中国文化特殊性的学科。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通常认为只有百年历史,在当代还受到身份“合法性”的怀疑。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个基本前题,即哲学是人类出于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而建立的理论体系,它本是人类各民族的一种普遍性精神现象,表达出人类的普遍性精神需求。那么,作为五千年文明组成部分的“中国哲学”,其历史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们也得特别注意,我们的先贤是用一套自己的学术术语或科目,来表达中华民族对宇宙、社会、人生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应的理论体系。他们曾经以“道学”、“玄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身心之学”、“理学”等等学术科目,命名今天所谓的“中国哲学”。所以说,“中国哲学”既存在于中国学术文化的脉络中,又表达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性哲学精神。
第二,“中国哲学”是以中国文化独特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它的形态是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
“中国哲学”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学术形态(如诸子学、玄学、理学),而是一个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华文明在两千多年前的“哲学突破”时,就开始形成独立的哲学思考。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国哲学”的独特形态就一直处在具有内在理路的历史建构过程中,产生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等。只是到了近百年,原本具有内在理路而独立发展的诸子学、经学、玄学、理学,因为与西方的哲学相遇,故而有了一个让中国传统的道学、经学、玄学、理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的机会。我们急切希望自己的道学、经学、玄学、理学获得一种人类普遍哲学的身份,如是开始了参照和类比西方哲学模式的“中国哲学”的重建。其实,西方哲学并不具人类普遍哲学的身份,所以,对西方哲学的简单类比并不能完全让中国的玄学、理学轻易地获得一种人类普遍哲学的意义,当代学界并不满意近代以西方哲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这种研究模式使“中国哲学”学科缺少中国文化的特色。但也不是要回归传统的玄学、道学、理学、义理之学、性理之学,这些传统学术的形式、内容和方法更是早已经存在,无须我们“重建”。我们相信,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应该是一种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参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和对话的哲学建构活动。
那么,这种“中国哲学”具有哪些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呢?它又是如何在历史中建构起来的呢?
首先,是经典诠释。经典诠释既能够体现“中国哲学”的文化特殊性,又是“中国哲学”能够实现历史建构的根本途径。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创造并不体现为独立撰写自己的哲学著作,而是从事经典诠释的工作。先秦诸子既是“六经”的诠释者,又是中国哲学经典的创造者,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思潮中均产生了中国思想史上最具思想创新的哲学家,但是,他们的思想创新并不体现于独立撰写自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从事经典的注释。譬如,孔子对“五经”的整理和诠释,王弼对《周易》、《论语》、《老子》的诠释,朱熹对《周易》、《诗经》、“四书”的诠释。奠定他们作为哲学家地位的正是这些对古代经典的重新注释。他们通过诠释经典,最终建构出义理之学、玄学、理学的哲学体系。
其次,是义理体认。古代中国人建构哲学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不是那个独立于人的宇宙存在,关注点也不是世界的普遍本质与规律,他们的思想出发点是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其哲学关注点是人参赞宇宙进程的实践活动。古代中国的哲学传统更为关注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活实践与操作程序,而并不特别在意应如何认识宇宙世界的存在和本质,中国哲学传统的着重点不是世界是什么,而是人应该怎样。故而,中国古代哲学家通过诠释经典而建构义理,总是与他的自我体认联系在一起的。譬如,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哲学形上学,并不是建立在“我思故我在”的逻辑思辨的基础之上,而是他在“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的实践工夫中体认出来的。王阳明在生活实践中体悟到并倡导“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工夫论,故而才有“心即理”的本体诠释。
上述看法,只是我个人对“中国哲学”学科的一点浅见。多年来,我写下一些关于中国哲学的文字,主要是关于中国哲人的经典诠释、义理体认,并通过这种方式从事“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我认为,中国哲人通过经典诠释、义理体认而建立的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思考,使得“中国哲学”成为一门既有人类哲学普遍性,又有中国文化特殊性的知识体系。
所以,我将这些论著汇集出版时,命名为《经典诠释与义理体认——中国哲学建构历程片论》。这本论文集的第一辑主要涉及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后面四辑论文,则是对中国哲学历史建构的探讨,涉及的时段主要有先秦、魏晋、宋明、晚清四个阶段。全书的主题就是通过对中国古代经典诠释、义理体认的研究,以探讨“中国哲学”的历史建构过程,并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建构应该如何既坚持中国文化主体性,又积极参入全球化文化交流等问题。
谁误读了“格物致知”?
我们都承认,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学科建构过程,就是一个以西方哲学为范本,从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寻求能与之相对应的历史资料,并不断按此范本作出新的理解、解释、发挥的过程。以这种方式建构起来的中国哲学史,固然为建立合乎现代知识规范的中国哲学学科体系以及中西文化沟通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但是也因此出现种种“误读”,而失去对中国思想历史原貌、本来意义的真实把握。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宋明理学因重视天人的形上思考而被现代学人视为一种哲学化的儒学,故而也是为西方哲学范本解读、发挥最多的学说。在理学集大成者朱熹那里,“格物致知”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最方便与西方哲学思想作比附、诠释的部分。在关于朱熹的现代解释中,一个比较一致的倾向,就是以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来解读、分析、评论朱熹的“格物致知”。尽管有可能对其作出肯定的(如冯友兰)或否定的(如牟宗三)评价,但他们均认同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比较一致,诸如:肯定主体的“心”与客体的“物”及“理”是一个主客对立的关系,主体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感知、认识而获得具体的经验知识(格物),主体将具体的经验知识提升、扩充为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致知)。
但是,这种关于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解读,却不能解释朱熹思想体系中的许多基本观念,譬如,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认识论观念强调主体之心与客体之物(或理)是分离的,必须通过主体认识客观事物以后才获得对物理的认知,但朱熹却总是坚持主体在“格物致知”以前万理具足于心之中,即“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① 。“心与理一”的前提消除了认识论的那种主客对立。又如,西方哲学认识论关注知识的来源及知识的客观真实性与普遍性等,但是朱熹的“格物致知论”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学者应如何以心中之理去对应万物之理,即如何在生活实践中推广、实现心中本有之理,内以修己,外以治世。当许多学者不能解释这些现象时,就认为朱熹的哲学思维混乱。其实,造成这种“不通”或“混乱”的不是朱熹,而是现代学人用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逻辑体系“误读”了朱熹。
应该说,在朱熹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并不能等同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或知识论,而是关于如何实现和完成修己治人的工夫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将“格物致知”纳入朱熹思想中那个完整的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行程中去,才可能对“格物致知”作出合乎历史实际、文化精神的解读。
什么叫作“工夫论”?和西方哲学重知识论不同,儒学重视的是修己治人的工夫。一方面,儒家的工夫论是包括了如何体认天地万物、建构天地之理的知识在内。朱熹说:“圣门日用工夫,甚觉浅近。然推之理,无有不包,无有不贯,及其充广,可与天地同其广大。故为圣,为贤,位天地,育万物,只此一理而已。”② 日用工夫所推行的理也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天理作为一个贯穿日用伦常并记载于儒家经典的普遍法则,必然会体现在天地万物之中,对天地万物之理的自觉体认也就是“工夫”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夫”又是实践性的,它又必然会体现为人的身心一体的客观性活动,而不仅仅是对儒家经典的传注训诂或对外在事物的认知,也就是说工夫不等于那种“语言—概念”的知识形态。朱熹反复对学生说:“讲学固不可无,须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说,不过一两日都说尽了。只是工夫难。”③ “小立课程,大作工夫。”④ “自早至暮,无非是做工夫时节。”① 可见,朱熹所说的“工夫”是一种身心一体的实践性活动,他一直强调这种日用实践工夫为儒者“第一义”的学问。由于儒家工夫论是认知活动与日用实践的统一,故而决定了这种工夫论是一种知行结合的构架。所以,在朱熹的学术视域中,儒家学说就是知行合一的工夫论记载。譬如《大学》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论语》的操存、涵养,《孟子》的尽心、存性、体验、扩充,《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以及尊德性、道问学、极高明、道中庸等等,这些修身工夫原就是先圣先贤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的个人体悟、经验总结,但是它们均可以纳入那个知行统一的工夫论构架中去。
我们如果要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作出合乎历史原貌、文本意义的解释,必须将其还原到朱熹关于“格物致知论”的历史语境中去,特别是将其置之于完整的工夫论体系中去,这样才会真正理解“格物致知论”的本义,而不至于将其从工夫论中剥离出来,片面地将其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作比附。
1. 从朱熹关于修己治人工夫论的完整“规模”、“行程”来考察“格物致知”的本来意义。
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并非西方哲学的认知论,只要将其纳入儒学的工夫论体系之中,就能确切地把握其本有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文化内涵。而所谓的工夫论体系,既包括“大学”的工夫论“规模”,也要注意朱熹关于“小学”工夫的补充,因为后者更进一步确定了“格物致知”的工夫论意义。
朱熹认为,《大学》一书包含着儒家工夫论的“规模”、“纲领”,即《大学》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工夫论“行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工夫论“行程”是以“格物致知”为工夫论行程之首,尽管朱熹对“格物致知”作了类似认识论的阐发,但是并没有违背宋代新儒学大师强调儒学以修身工夫为根本的为学宗旨。朱熹始终是一个以成德之教、修身工夫为根本宗旨的儒者,他一直坚持以“格物致知”为标志的“知”的工夫应该归之于“第一义”的“行”的工夫。这一点,在朱熹建构的《大学》工夫体系将《小学》工夫纳入这一点上,就表现得十分鲜明。
朱熹以毕生精力建构《大学》工夫论体系,但是他同时强调,《大学》的工夫必须有“小学”工夫的基础。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以“小学”工夫作为“大学”之“行程”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一个有志于儒家圣学的学者,在做“格物致知”等“知”的工夫之前,就必须经过“小学”的“行”的工夫的冶炼。他提出:“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① 朱熹强调“小学”关于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等“行”的工夫是格物穷理等“知”的工夫的基础,只有在经过“小学”工夫的成功培养之后,方可进入“大学”阶段的格物穷理工夫。所以,他在淳熙十四年(1187)序定成《小学》一书,进一步将“小学”纳入“大学”的工夫论体系中。一旦朱熹将“小学”的工夫纳入“大学”工夫的“规模”、“行程”中去,他所重视的“格物致知论”体系就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儒家工夫论的特色,也就体现出朱熹为何总是强调实践工夫是“第一义”工夫的真正原因,正如下图所示:
洒扫、应对、进退 → 格物致知 → 修齐治平
(行的工夫) (知的工夫) (行的工夫)
在这个完整的儒家工夫论的体系中,我们发现,“格物致知”的知识论方法鲜明体现出“行”是“第一义”的工夫这一重要思想。“格物致知”所获的得各种知识道理,原来均是来自于“行”的工夫之中,“大学”所完成的穷理致知工夫,实来源于“小学”的事亲从兄的日用实践,“小学”的实践工夫是“大学”穷理工夫的基础和本原。朱熹反复强调“小学”与“大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① “大学”阶段通过“格物”、“致知”工夫所发明的知识道理,原来均与“小学”阶段的实践工夫中所做的“事”有关,是从“事”中“发明”出来的。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朱熹总是反复强调实践工夫是“第一义”。
2. 从朱熹的格物致知论的具体内涵,进一步分析考察其工夫论本义。
现在,我们进一步将“格物致知”纳入儒家“修己治人的规模”中,将“格物致知”的知识理性与正心诚意的道德涵养以及修齐治平的经世实践结合起来考察。朱熹继承了早期儒家将知识追求纳入道德修身、政治实践的思想传统,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不过是他的修己治人的工夫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故而在本质上说并不是一种认识论,而是一种成德工夫论。既是一种成德工夫,那么,所谓“格物致知”的思想,无论从其目的、内容、过程来看,均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不同,表现出一种修身工夫论的鲜明特征。
其一,“格物致知”的目的是“明明德”的伦理政治,它只是“修己治人的规模”中的具体“行程”,其目标则是道德修身与政治实践。具体来说,“格物”、“致知”的环节,只是为了过渡到“正心”、“诚意”的下一个环节。这一点,朱熹在《大学章句》中有明确的解释:“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知既尽,则意可得而实矣,意既实,则心可得而正矣。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② 在这里,“格物致知”的知识追求,只是为了道德意志的笃实与道德观念的明确,也就是为了“明明德”。朱熹强调“格物致知”是进德工夫的基础,他解释“诚意”说:“经曰:欲诚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诚。盖心体之明有所未尽,则其所发必有不能实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谨乎此,则其所明又非已有,而无以为进德之基。”③ 也就是说,“格物致知”是为了实现“心体之明”,从而为下一步“正心”、“诚意”的进德工夫奠定基础。由此可见,道德修身的行程体系决定、制约了“格物致知”只是修身工夫的一个“行程”,它和那种获得客观知识的认识论目标是不同的。
其二,从“格物致知”的内容来看。,由于格物致知是为了实现修己治人的成德工夫,故而决定了这种认知活动的主体内容是人伦日用。所以,朱熹在诠释“格物”之“物”和“致知”之“知”时,十分强调这种知识对象是伦理道德之“理”。他说:“格物穷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穷得到后,遇事触物皆撞着这个道理:事君便遇忠,事亲便遇孝,居处便恭,执事便敬,与人便忠,以至参前倚衡,无往而不见这个道理。”① 尽管朱熹在诠释“格物致知”的对象时,也将它们扩展到天地阴阳、昆虫草木之理,但是,由于“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正心诚意、明明德,这就使得朱熹在诠释“格物致知”时,始终不愿偏离仁、义、忠、孝、恭、敬等伦理规范之类的“理”,并竭力将“格物致知”的内容限制、集中在人伦之理之上。
其三,从“格物致知”的过程来看,“格物致知”的过程并不体现为主体认识客观世界,建构知识体系,而是一种追求如何合乎“天道”、“天理”的主客合一的实践活动。因此,所谓“格物致知”并不是那种因主客之分而必须通过感知、理性而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的活动,那是西方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则强调“格物致知”是“天理具足”的人在处事应物的种种生活实践中感悟、发明实行各种各样“当如此”、“当如彼”的道理,他所理解的“格物致知”总是离不开行的,所以他经常说:“格物,是穷得这事当如此,那事当如彼,如为君便当止于仁,为人臣便当止于敬。”② 这些“当如此”、“当如彼”的道理不是逻辑化的知识体系,而是体现为人应如何做的行为规范、活动程式。“格物致知”的结果不是形成关于客体世界“是什么”的静态知识,而是关于主体应该“如何做”的动态实践。所以朱熹以为:“‘格物’二字最好。物,谓事物也,须穷极事物之理到尽处,便有一个是,一个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① 这样,“格物致知”就成了在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活动中获得“是”、“非”标准的重要步骤。那么,“格物致知”的过程是主体心中之理与客体事物之理相互印证、融通、实现的实践过程,这个过程的最终结果正如朱熹所说:“大凡道理,皆是我自有之物,非从外得。所谓知者,便是知得我底道理,非是以我之知去知彼道理也。道理本固有,用知方发得出来。若无知,道理何从而见。”② 因此,所谓的“格物致知”,一方面就是知得“我自有之物”的道理,另一方面则是要将自有之理去应事事物物之理。由于“我底道理”与“万物之理”其实就是同一个理,那么,“格物致知”最终就是实现“合内外之理”。《朱子语类》载:问:“格物须合内外始得?”曰:“他内外未尝不合。自家知得物之理在此,则因其理之自然而应之,便见合内外之理。”③ 这个“合内外之理”不是一个对象化的“语言—逻辑”的抽象知识系统形成过程,而是一种主客合一的“参天地,赞化育”的实践活动过程。
在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构过程中,学者们在不懈地寻找那些能够和西方哲学体系对应的部分,并作出合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基本概念构架的“现代”误读。所以,如何以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历史文本、思想体系为基点而建构出合乎中国历史实际、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的”哲学,应是二十一世纪中国学人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
(原载2012年3月26日《光明日报》)
曾国藩的礼学与礼治
一、从礼学到礼治
将学术与治术统一起来,这既是儒家士大夫的学术理念,又是传统中国的政治理想,尽管在现实中这种学术理念、政治理想总会出现严重分裂的局面。曾国藩作为一位兼学术大家与军政名臣于一身的人,他最想实现的就是学术与治术的贯通,即研究治术化的学术、实践学术化的治术。所以,他在学术上的宗旨是“以礼为归”,故而在政治实践上则是以礼治为本。
曾国藩穷毕生之力从事礼学研究,无论是礼经、礼仪的历史考证,还是礼义的理论验证,或者是求仁于己的身心体悟,其最后的指向均是经世治国,即希望使学术最终落实于治术。所以,曾国藩一谈及治术,总是归结到礼治:
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乎归?亦曰礼而已矣。①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②
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表明他大量阅读同代及前人的礼学著作,这对他的礼治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努力通过礼制考订以寻求治世之方的政治理念之中。曾国藩继承了先秦以来儒家重视礼制的传统,他认为礼学的地位之所以特别重要,就在于礼制在建立政治等级秩序、确定日常行为方式、维护和谐社会生活方面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
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胾有定位,纟委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未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①
在曾国藩看来,礼学在学术上的重要性,起因于礼治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那么,从事礼经研究、礼仪考订,就有着十分明确的经世治国的目的。譬如他认为礼经本来就是经世之书,他认为:“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橐,妖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② 他不仅肯定礼学就是经世之术,同时强调礼学在经世治国实践中的特别价值。他充分肯定清代兴起的礼学思潮与经世致用的密切联系,他说:“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③ 曾国藩继承了清代礼学诸家如顾亭林、江慎修、秦树澧等通过礼学研究、礼仪考订以寻求经世之术的学术特点,但是和清初至清中叶的礼学家不一样的是,他本人将礼学中的天文、地理、官制、军政等各个方面的学术探索直接运用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活动之中,并且创造了巨大的政治事功,被列为“中兴第一名臣”,这正是曾国藩礼治实践的结果。
二、统领湘军时的礼治实践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曾国藩的政治实践方面,考察作为湘军统帅、“中兴名臣”的曾国藩是如何运用以礼为本的经世之术的。曾国藩将礼学付诸政治实践,其影响最大、事功最著者,当属他在创建湘军时所形成的一套军制军礼,这是他的礼治实践的成功之处,也是他能够修齐治平、成事建功的基本条件。本文以此作为考察的重点。
曾国藩对清廷的国家军队——绿营的各种弊端,诸如军风败坏、习气散漫、建制不合理等均有深刻的认识。他希望通过一系列合乎礼的精神的军制改革,建立起一支“别树一帜”的有战斗力的军队。《清史稿》载:
(曾国藩)又慨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如戚敬元所纪者。论者谓国藩所订营制、营规,其于军礼庶几近之。①
其实其他古礼亦早已残阙,但是,曾国藩却努力通过“博稽古法,辨等明威”的学术探索而制订出湘军的各种营制营规。这一制订军礼的活动一方面保持继承了古代军礼的一些传统,尤其是明代戚继光所记的《记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军礼专篇,另一方面又进行军制方面的改革,使湘军的营制营规成为清代军礼的重要体现。② 而曾国藩在军礼方面的卓有成效的探索,正是创建巨大政治事功的根本条件。
曾国藩以礼治军、制订军制军礼的特色与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勇由将招”的招募制取代八旗绿营的世兵制,使湘军成为一支包括古代社会中家族、姻亲、邻里乃至师生关系在内而具有宗法特色的军事组织,从而更有效地发挥礼治在建军作战中的作用,强化军队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绿营的弊端是“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而湘军实行“呼朋引类”的招募方式,使得一营之内包括家族、宗亲、邻里等各种宗法关系,湘军的将领之间更是包含兄弟、宗亲、姻亲、师友等宗法社会关系,故而使得“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弁勇视营哨,营哨视统领,统领视大帅,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① 。本来礼治的核心是从宗法血缘关系来建立政治秩序,曾国藩也正是用这种宗法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组建、管理军队。一方面,湘军的营制,坚持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另一方面,湘军的统领、营官们在招募乡勇、组建湘军时,总是将同乡、亲友招进来,正如湘军将领刘长佑向朝廷所说:“臣由书生以团练杀贼,谬膺重寄,所与立功,非臣亲党,即臣邻里。”② 这样做就强化了湘军内部的凝聚力,此正如曾国藩本人所说:“既得其人??皆令其人自为,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庶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③
其二,与湘军浓厚的宗法色彩相应,曾国藩凸显了礼治所具有的仁与刑、恩与威并重的特色,强调了礼治具有的内(自治)与外(治人)结合的宗法型政治文化精神。在中国古代,“礼”本来是指外在的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与行为规范,但儒家学派在遵礼、爱礼的同时,强调了礼所包含的思想情操、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精神内涵,故而,儒家推崇的礼治就包括了外在礼节与内在修身、严刑峻法与仁心爱民的二重性,从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曾国藩在其经世实践中将礼治文化的二重性发展到极致。譬如,他在统领湘军、治军带勇的过程中就十分强调仁刑结合、恩威并用的礼治特色。他在总结自己的带兵之法时说:
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思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小大,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①
治军者通常都强调威猛之气,“礼”的秩序、规范是军队形成这种“威猛”战斗力的保证。但曾国藩还强调治军中仁恩的一面,将孔子关于忠恕之道的仁爱思想贯彻到带兵之中,并将“待弁勇如待子弟”的血缘情感渗透到军队以增强军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其实,礼治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威猛、严酷的一面,同时也体现在施恩、仁爱的一面,后者尤体现出孔孟儒学关于礼治的理想。曾国藩的礼治实践正是对二者的充分利用,他声称:“威恩并施,刚柔互用,或一张一弛,有相反而相成。”② 可见他深刻地把握了礼治的实质,并充分发挥了儒家政治文化的优势和特点。
其三,曾国藩以礼治军的特色,还体现在他对礼的教化精神的重视与实践上。儒家礼治的根本精神,就是强调维护礼不能依赖于暴力,而是要通过教化的方式使人们自觉地遵循礼的义务性规范,这就是孔子所要求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③ 。所以儒家一直将“修六礼”、“明七教”④ 的礼教作为礼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任务。湘军组建的一大特色,是儒生与山农的结合,正如当时人们所记:“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⑤ “迨曾国藩以儒臣治军长沙,罗泽南、王錱皆起诸生,讲学敦气谊。乃选士人领山农。”⑥ 这种儒生与山农的结合,使得曾国藩有条件对湘军实施以“训”为中心的儒家礼教的教化活动。由于他对礼教的特殊重视,故而将有关礼教的“训”置于比军事的“练”更加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在形式上,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儒将承担着训导兵勇的任务,即如他本人所说:“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① 另一方面,他们所“训”的内容,主要是合乎礼教的为人之道,具有浓厚的礼教色彩。如曾国藩所亲自撰写的“上而统领,下而哨弁”的《劝诫营官四条》,其内容无非是“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等,均是道德礼仪方面的教化。尤有特点的是,曾国藩的军事训练内容既包括营规,又包括家规,使得其以礼治军的礼制色彩更浓。曾国藩作出这样的“劝诫”与规定: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②
上述从形式到内容的礼教活动,是曾国藩治军的一大特色,也促使他能够组建起这样一支合乎儒家礼教精神的具有“忠义血性”的队伍。
三、礼治的学问基础
“学”与“治”的贯通向来是儒家的理想,而曾国藩像所有的儒家士大夫一样是这一理想的追求者。但是,和许许多多儒家士大夫不一样的是,曾国藩努力通过“礼”去实现“学”与“治”的贯通:他的礼学已经实践化为一种礼治的经世活动与制度建设,他的礼治又以深厚的礼学为思想基础与学术依托。这样,曾国藩的礼学有了不同于其他礼学家的学术特色,同样,他的礼治又有了不同于其他军政大臣的风貌。
曾国藩倡导以礼治国、以礼治家、以礼修身,而且均取得了重要的社会功效,为当时及后世的人们所称道。当然,他的礼治实践体现得最充分、最有特色且影响最大者,仍属他的以礼治军。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创建、领导的湘军在他一生的政治活动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经历的时间长,政治影响大,涉及的地域广;另一方面,由于他在组建并领导湘军时能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创造性,从而湘军的组建、治理表现出更多的礼治特色。本来,湘军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地方团练,但是,它在以后的发展中胜过并取代了清朝八旗、绿营的国家正规军队,做出了左右近代中国政局及发展轨迹的一系列重要史事,并且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晚清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发展,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应该与曾国藩的礼学理念及其礼治实践密不可分。
《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的政治事功时提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曾国藩本人在为湘军将领之一的罗泽南撰写碑铭时曾这样说:“无本者竭,有本者昌。”“大本内植,伟绩外充。”① 应该说,曾国藩及其湘军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巨大的政治事功,是由于他的礼治实践中,完全坚持了“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② 。而他的礼治实践又来自于他的儒家礼学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理念,他一直将“大本”归之于“闽洛之术”的儒家学说。可见曾国藩及其湘军的“本”植根于儒学学问与“礼”的理念之中,这是他取得政治功业的根本原因。
从曾国藩组建、领导湘军的全过程来看,他确是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推行他“礼治—礼学”统一的原则。从组建湘军的建军宗旨来看,曾国藩坚持以维护儒家礼教为己任,讨伐太平天国背弃民族礼教文明的种种思想与行为,提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① 。他赋予湘军以礼教文明维护者的神圣使命,奠定了湘军与儒家礼教文化的内在联系。这一维护礼义人伦的建军宗旨,使得湘军能够更加全面地渗透以儒学为根基的礼治精神。从湘军构成来看,这是一支由“儒生领农民”的队伍,儒生是礼教文化的实践者、维护者、传播者,而山农则是中国“宗法—礼治”社会的基础,儒生与农民的结合而建立的湘军,正好是中国礼治社会的浓缩,能够充分地实现曾国藩以礼治军的政治理想。再加之湘军实行“乡党信从”、“父兄子弟”的“呼朋引类”式的招募制,故而湘军内部的上下、左右关系类似于家族内部的礼制秩序,能够实现“皆如子弟之事其父兄焉”的既有政治等级统属,又有宗法家族亲情的关系,从而建立起以“政治—宗法”关系为基础的军营制度,形成一种比较典型的礼制秩序。同时,曾国藩所实施的“训作人之道”的教训内容,也主要来自于礼教观念,包括“父兄教子弟之家规”,或出于儒家礼教的经典如《孝经》、《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等等。可见,湘军的军事训练从内容到形式均体现出礼治的要求与礼学的渗透。
曾国藩在组建、统领湘军的政治实践中坚持了上述礼治的理念、制度、原则与方法,而这些理念、原则、制度、方法均来自于曾国藩一生追求的礼学学问。这些看起来有些古老、不切实用的儒家礼教学说又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湘军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使这样一支由农民组建的民间武装,发展成为一支具有文化理念、作战能力并能取代晚清政府的国家军队的“军事—政治”实体。这应是《清史稿》赞扬的“国藩事功,本于学问”的根本原因与重要理由。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1期,与吴国荣合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