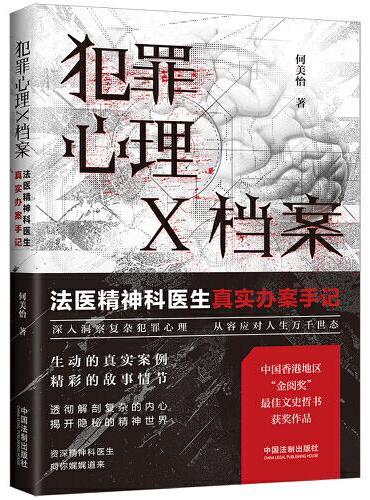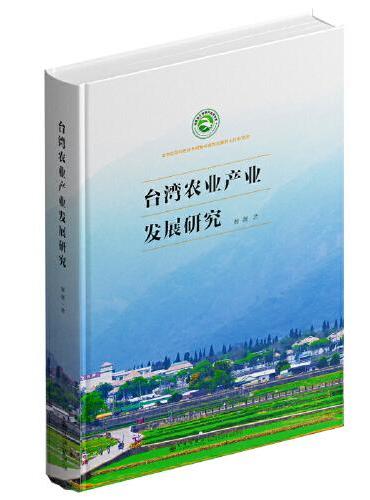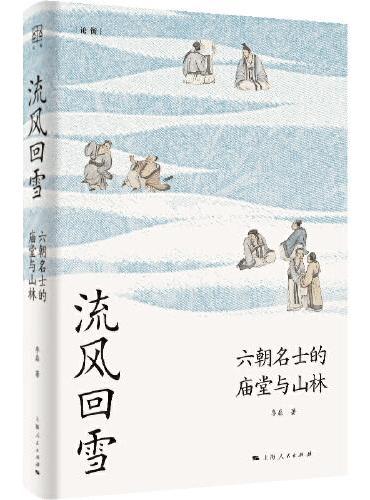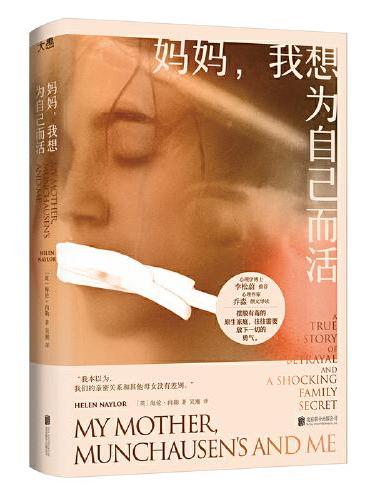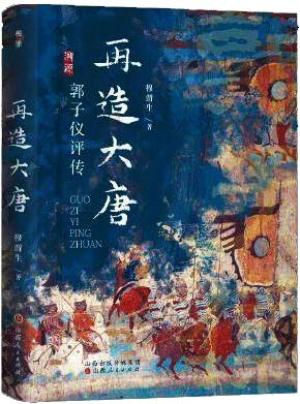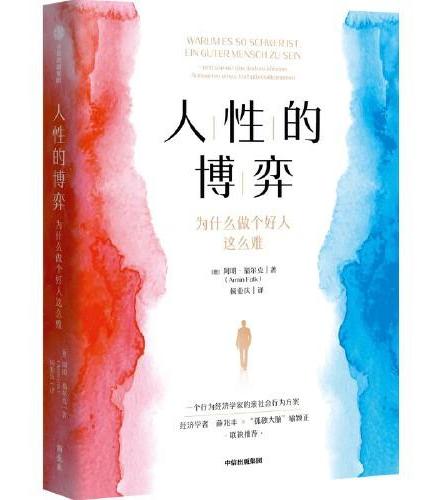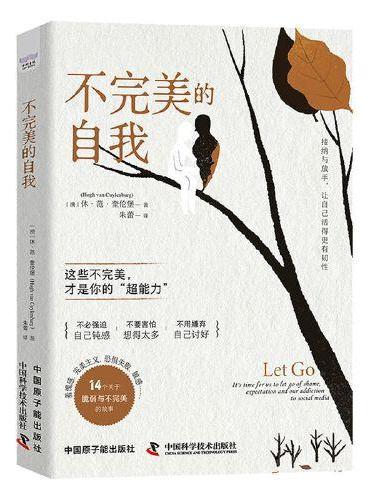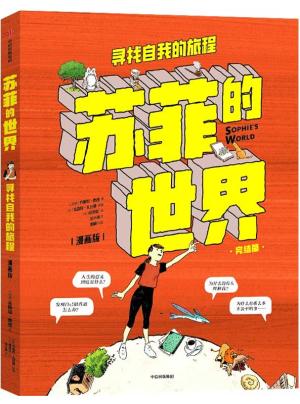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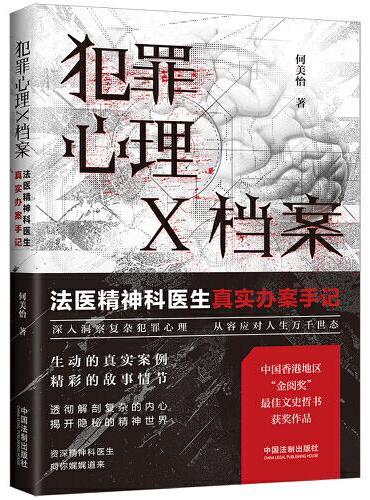
《
犯罪心理X档案:法医精神科医生真实办案手记(第一季)法医精神科医师心理解剖手记
》
售價:NT$
26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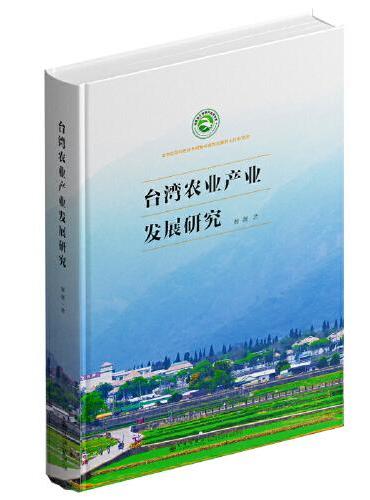
《
台湾农业产业发展研究
》
售價:NT$
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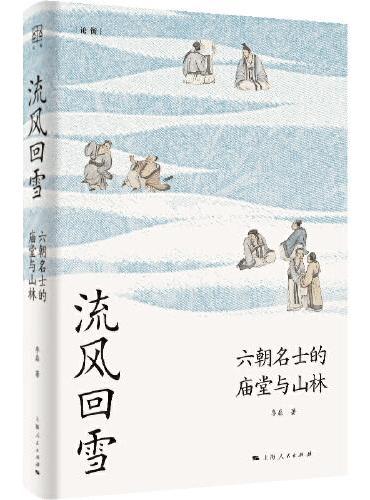
《
流风回雪:六朝名士的庙堂与山林(论衡系列)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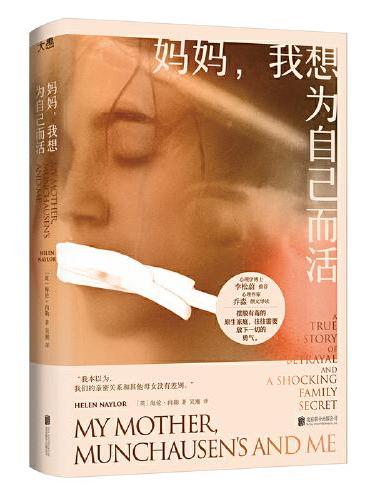
《
妈妈,我想为自己而活
》
售價:NT$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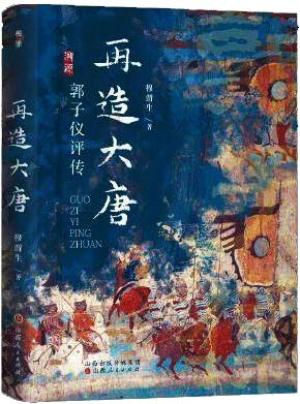
《
再造大唐:郭子仪评传
》
售價:NT$
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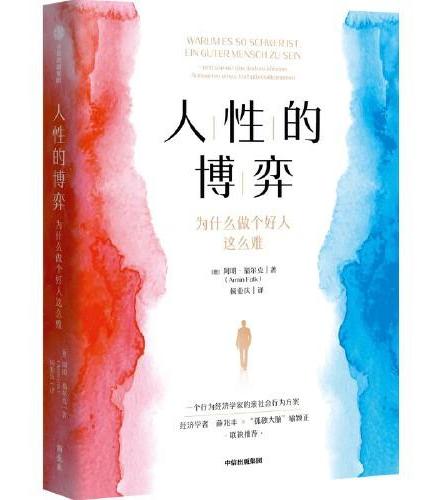
《
人性的博弈 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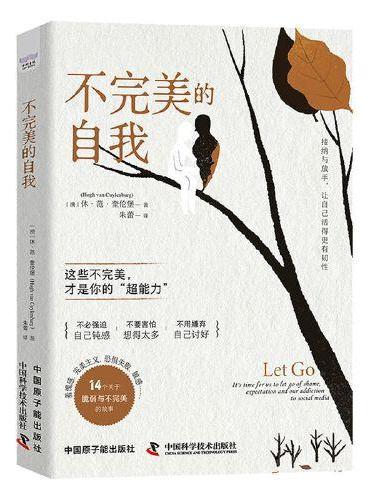
《
不完美的自我:接纳与放手,让自己活得更有韧性
》
售價:NT$
33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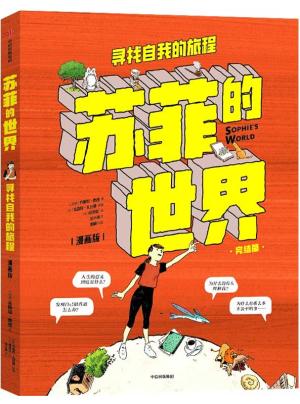
《
苏菲的世界(漫画版):寻找自我的旅程
》
售價:NT$
442.0
|
| 編輯推薦: |
|
《在迦南的那一边》是爱尔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塞巴斯蒂安巴里的新作,获得2012年沃尔特司各特文学奖,并获2011年布克奖提名。《在迦南的那一边》用塞巴斯蒂安巴里招牌式的精美绝伦的文字讲述了又一个伤心欲绝的故事。说是故事,里面却包含了历史太多残忍的真相,以及貌似诡异却又不可避免的结局。人类内心最深的隐痛往往就寄宿在转瞬即逝的一闪念中,巴里技艺的精湛便在于勾画这一闪念,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个表情,有时候是一个动作,所以对于战争的痛恨与对于命运的无奈便都寓意在其中了。
|
| 內容簡介: |
|
《在迦南的那一边》的主人公,八十九岁的莉莉布里决定用一种“安静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她用一生的时间来逃亡与躲避,命运却总能以最出其不意的方式扼住她的脖颈,夺走她的挚爱,摧毁他们的肉体,撕裂他们的灵魂,一个都没有留下。伤痕累累的几代爱尔兰人背负着痛苦的伦理悖论无声地向历史问责。
|
| 關於作者: |
|
塞巴斯蒂安巴里,爱尔兰当代最优秀的作家、诗人与剧作家之一,爱尔兰影星琼奥哈拉之子。其文学生涯始于诗歌,近年来,小说创作上的成就为其赢得了极高的文学地位,其作品多次获得布克奖提名,长篇小说《秘密手稿》获包括科斯塔年度图书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大奖。巴里的小说语言优美,富有诗意,善用深沉忧郁的历史视角探究爱尔兰与爱尔兰人充满悲欢离合的曲折命运。
|
| 目錄:
|
失去比尔的第一天
失去比尔的第二天
失去比尔的第三天
失去比尔的第四天
失去比尔的第五天
失去比尔的第六天
失去比尔的第七天
第二部分
失去比尔的第八天
失去比尔的第九天
失去比尔的第十天
失去比尔的第十一天
第三部分
失去比尔的第十二天
失去比尔的第十三天
失去比尔的第十四天
失去比尔的第十五天
失去比尔的第十六天
失去比尔的第十七天
|
| 內容試閱:
|
失去比尔的第一天
比尔永远去了。
一颗八十九岁的心蓦然碎裂的时候会发出怎样的声音?也许比寂静多不了几分,只是一丝轻细的微响罢了。
我四岁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瓷娃娃,是从一个性情古怪的人那里得来的。我母亲的妹妹住在维克罗郡,那个瓷娃娃是她从自己和姐姐的童年时代一直珍藏下来的,她把瓷娃娃送给了我,作为对我母亲的纪念。对于四岁的我来说,这样一个瓷娃娃显得无比珍贵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美丽。直到现在,我眼前依然能浮现出她那张彩绘的脸庞—沉静而富于东方韵味,还有穿在她身上的蓝色丝绸衣裙。让我大为困惑的是,这样一件礼物令父亲感到很不安。我无法理解这有什么可烦恼的。他说,一个小女孩承受不起这件礼物,虽然他自己非常宠爱这个小女孩,简直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
从我最初得到那个瓷娃娃大约过了一年光景,赶上一个星期日,我硬要带上她一起去教堂做礼拜,虽然父亲絮絮叨叨了很长时间表示反对,我仍然坚持要这么做。父亲总希望人有来世,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算是个虔诚的教徒。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执拗得很,他觉得瓷娃娃不管怎么说也不适合带进教堂去做礼拜。
倔强的我硬是抱着她走进了马尔伯勒大街上的代主教座堂,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是因为那里的气氛庄严凝重,给人一种威压之感,她竟然从我怀里掉了出来。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确定,或者说不能完全确定,当时的自己是不是鬼使神差,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之下松开了手。不过,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立刻就后悔了。教堂的地面是用石板铺成的,非常坚硬。她的漂亮衣裙也没能挽救她的命运。她那完美无瑕的脸庞撞在石头上,摔了个稀巴烂,比一颗破碎的鸡蛋还惨不忍睹。在那一瞬间,我的心都碎了,她发出的破裂声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演化成了自己的心碎裂开来的声响。虽然那是一种孩子气的胡思乱想,但我现在确实觉得,也许那就像是一颗八十九岁的心因悲伤而碎裂的声音—一个细小而轻微的声音。
但那声音给人的感觉仿佛是一片乡村风景,连同它所有的一切—炉台、牛栏、牲畜和人,全都被洪水吞噬,陷入一团漆黑,淹没在恐怖和惊惧之中。这情形就像是某个人,某个强大的机构,某个来自天国的中央情报局,对我这个小小的机械装置了如指掌,非常清楚我是怎么安装而成,正在按照一本小册子或者说明书,一个齿轮一个齿轮、一根电线一根电线地把我拆开来,压根儿没去想重新组装这码事儿,眼看着我身上所有的部件被丢得七零八落,落得残缺不全而无动于衷。悲痛让我感到无比恐惧,没有什么能给我一丝安慰。装在我颅骨里的仿佛不是我的头脑,而是一个炽热的火球,我在里面熊熊燃烧,伴着惊恐和痛苦。
上帝原谅我。上帝保佑我。我必须让自己平静下来。我必须平静下来。求求你,上帝,保佑我吧。你看见我了吗?我坐在这儿,坐在铺着红色塑料贴面的餐桌旁。厨房里有光亮在闪烁。我沏好了茶。虽然心绪不宁,我还是用开水烫洗了茶壶。我给自己加了一勺茶,也给茶壶加了一勺。我像往常一样,让茶泡上一阵子,像往常一样坐在一旁等着。黄色的阳光从面朝大海的窗户射进来,看上去给人一种结结实实的感觉,就像是一面古铜色的旧盾牌。此时,我身上穿着一件用厚实的亚麻布做成的灰色长裙,几年前我在主街上掏钱买下来的那一刻就后悔了,现在仍然后悔,虽然在这种寒冷难熬的天气里,这件裙子穿起来很暖和。我要喝点儿茶。我要喝点儿茶。
比尔永远离我而去了。
在人们的传说中,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父亲说,我呱呱落地那会儿,就像是一只聒噪的雉鸡从藏身的地方猛地飞出来。我父亲的父亲曾经是维克罗郡休姆伍德庄园的管家,所以他知道雉鸡从隐蔽处突然冲天而起是怎样一种情景。母亲是在天刚破晓,不再需要烛光照明的时候死去的。那是在离海不远的多基村。
许多年来,这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故事罢了。然而,当我自己即将成为人母,那一幕突然之间变得真真切切,仿佛触手可及。在克利夫兰那个小小的房间里,我拼命使着劲儿把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她。在那之前,我对母亲从没有过什么真正的念想,然而,就在那一时刻,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亲密的人类情感。当有人终于把婴儿放在我的乳房上,我像动物一样大口喘着气,一时间,一种无可比拟的幸福感涌遍我的全身,我为她纵情流泪,对我来说,这眼泪比一个王国都更值得珍重。
四岁时,在附属于都柏林城堡皇家小教堂的那家小小的幼儿园里,我开始接受问答形式的天主教教义启蒙。对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谁创造了世界?”授课老师奥图尔夫人给出的答案是“上帝”,我心里非常明白她说的根本不对。她站在我们面前,朗声读出那个问题,然后用和鹪鹩一般响亮的嗓门做出回答。当时,我也许有点儿倾向于相信她的话,因为她穿着和都柏林动物园里的海豹一样颜色的灰裙子,在四岁的我眼里颇有几分威仪。当我走进教室的时候,她的态度非常和蔼可亲,还给了我一个苹果。但我觉得世界是我的父亲—詹姆斯帕特里克邓恩创造的,他后来成了都柏林都市警察署的高级警官,虽然当时还不是。
据传言,我父亲曾经率领众人在萨克维尔大街上冲击拉金一伙。当时,贴着一脸假胡须的拉金走过奥康内尔桥,穿过帝国饭店的一道道大理石走廊,出现在一个阳台上,无视法律对此明令禁止的规定,开始对聚集在下面的成百上千名工人发表演说,我父亲和其他警官当即命令守在那里随时待命的巡警抽出警棍冲上前去。
儿时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事件发生的当晚,当时我不明就里,还以为父亲的行为有多么英勇无畏。我不免在自己的臆想中添枝加叶,在我的想象中,父亲身骑白驹,手持礼仪宝剑,威风凛凛。我仿佛看见他跃身向前,如同发起一次真正的骑兵突击。他的骑士风度和勇气让我大为惊叹。
时隔几年我才明白过来,当时他是自己走上前去的,那天有三名工人遇难。
这些陈年旧事,和我此时的悲痛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徒增我心头的重负。现在我要喘口气,再开始慢慢道来。
我参加完葬礼回到家,发现在我出门的时候,老朋友迪林杰来过门厅,留下一束鲜花,没等我回来就走了。那是一束非常昂贵的鲜花,他还在上面放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送给我亲爱的朋友布里太太,希望在她痛失亲人的时候给她一些安慰。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假如诺兰先生还活着,我觉得他一定也会不声不响地前来造访。但那不是我所希望的。如果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现在了解到的事情,如果诺兰先生不是在那个时候去世的,我可能会继续把他想象成自己这辈子最亲密的朋友。他的离世,和我的孙子比尔死去的时间相隔如此之近,给人一种怪异的感觉。一切事情的发生总是接二连三的,这毫无疑问是个事实。第三个死去的将会是我自己。我已经八十九岁了,很快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比尔我怎么能活下去呢?
我不能什么也不说就做出这样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我去说给谁听呢?迪林杰先生?沃洛翰夫人?还是我自己?我不能不把自己的绝望说出来就撒手而去。我通常很少陷入绝望,而且我希望自己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尽可能少地流露出这种情绪。这根本不是我的一贯风格,所以我不能长时间沉浸在绝望之中。我感到了深深的绝望,我担心它会让我的胰脏出毛病,诺兰先生就是因为这个古怪、忧郁的器官丧了命,但我可不想再承受多久。等我和往昔的影子,和未来的一片蓝色苍茫倾诉过之后,我的生命就到此为止了,我这样希望,也这样祈祷。然后我就会寻找一种安静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对于上帝赐予我的这个世界所呈现出的一切奇妙景象,我并不是漠然而无动于衷的—不管是小时候在都柏林去过的哪个角落,还是都柏林城堡里哪个不起眼的小庭院—在我眼里,那里仿佛是个灰尘弥漫的乐园,还有近些时候眼中所见的雾霭,那雾霭宛如四肢长长的人或动物,大队人马浩浩荡荡侵入汉普顿,是要发动进攻还是大败而归,是要出门远征还是返回故土,很难说个究竟。
我期望着,我祈祷着,让诺兰先生沿着一条漫漫长路向下进入地狱,田野开始在他周身燃起熊熊烈火,阳光呈现出令人张皇失措的炫目色彩,眼里的景象骤然一变,让他感到莫名惊诧—这并不是家乡那广阔无垠的烟草地和让人赏心悦目的苍翠群山啊—因为他虽然取了个爱尔兰名字,却是个土生土长的田纳西人,而且,就像任何一个将要死去的人一样,他也许曾经想象着,当死亡来临的时候自己会自然而然踏上回归故乡的路途。在他活着的时候,我原本是非常喜欢他的,而且好多好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是朋友,但是现在,让魔鬼牵着他的手,领着他走进烟熏火燎的野地真是再恰当,再合适不过了。
我开始猜想,魔鬼也许比其他人更具有正义感,虽然他正让我经受着巨大的痛苦。
“只有不诚实的人才能真正做到诚实,只有失败者才能真正获得成功。”—这是我的孙子比尔在参加沙漠战争之前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他时不时会这样灵光一闪。那时候,十九岁的他已经离过一次婚,已经认定自己的生活—或者用他的话来说,是生命—毫无意义。那场战争夺走了他的最后一丝灵光。他从战火纷飞的沙漠回到家,就像亲眼目睹了魔鬼创造的一次奇迹。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他和朋友一起出门闲逛,大概是去喝点儿酒吧,那是他的一大嗜好。第二天,一个清洁女工在他过去就读的那所中学的厕所里发现了他。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他怎么会一时心血来潮,偏偏翻墙而过爬进了那个地方。他是在星期六晚上自杀的,我觉得他这样做的原因是想让看门人在星期天发现他,而不是让星期一成群结队蜂拥而入的孩子们看见。他是用自己的领带在门闩上吊死的。
为什么他死了而我还活着?为什么死亡要把他带走?
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什么能让我动笔写点儿东西了。我讨厌写字。我讨厌钢笔、纸张,还有一切烦琐的玩意儿。我觉得,不动纸笔我也过得挺好。噢,我这是在对自己撒谎。一直以来,我都非常害怕书写,直到八岁才勉强会写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乔治北街的修女们对我可没有好脸色,不过,有时候书也会给我帮大忙,这话一点儿不假—对我来说,它们就像是乐善好施的撒玛利亚人。我学习厨艺的时候曾经看过的那些食谱—噢,那是在多年以前,可后来这些年头,我有时候还会回过头去翻看那本破破烂烂的《白宫食谱》,好让自己回想起那些记不太清的细枝末节,这是很自然的事儿。好厨师无一例外,哪怕是在他们最喜欢的烹调书里也曾经挑出过毛病,然后在页边空白处标注出来,看上去跟一本古书差不多,比方说被焚毁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一本古书。星期日我有时候会读读报纸,在一种特定的心境下,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那架势就像是一团愈燃愈烈的火焰在一整份报纸上蔓延。我还非常喜欢读《圣经》,这种时候更少。《圣经》犹如一首特别的乐曲,你并不能随时抓住它的旋律。我的孙子比尔也喜欢《圣经》,他专门从中拆出了《启示录》的章节。他说,那部分文字就像是沙漠,科威特的沙漠,燃烧啊燃烧,跟火湖一样。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将被扔进火湖里。
我喜欢听人家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过去,在爱尔兰,我们把这叫作神聊,娓娓道来的故事,即兴脱口而出,博人一笑,而不是那些让人心情沉重的历史传说。
我这辈子,自己经历的故事就已经够多的了,更不要说我的雇主沃洛翰夫人。
“沃洛翰”(Wolohan)当然是个爱尔兰姓氏,不过在爱尔兰语里没有“w”,我只能猜测这个字母是多年前她的上一辈人到了美国给加上的。因为我发现,在美国,词语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它们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像美国人一样。似乎只有美国的鸟儿始终没有变化。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鸟儿的习性和颜色曾经勾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心,而且让我糊里糊涂分不清楚。近来,这一带的海滨雀、长嘴秧鸡、美洲黑羽椋鸟、笛鸻,还有十三种刺嘴莺,成了海滩上一道美丽的风景。掐指算来,我走过不少地方。我碰上的第一个城市是纽黑文,可能有人会说,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当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我的丈夫塔格。噢,那算得上是个疯狂的故事。不过,我还是等到明天再试着写出来吧。现在我身上发冷,虽然初夏的天气已经有足够的热力。我感到冷是因为我感觉不到自己的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