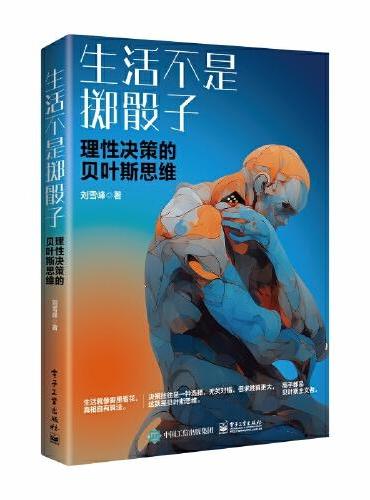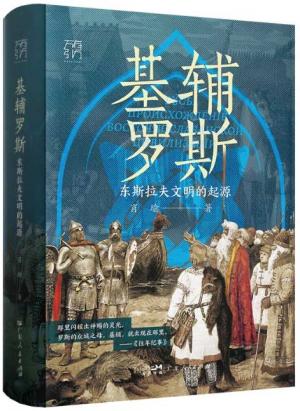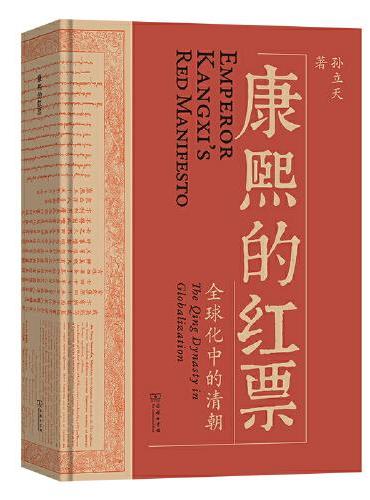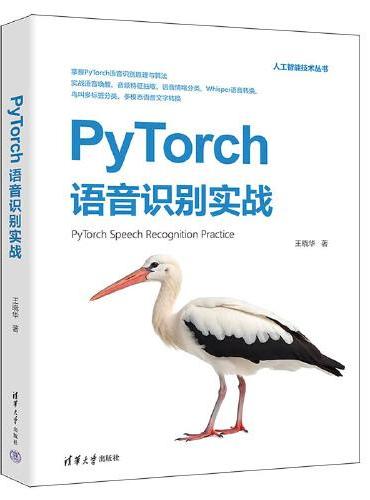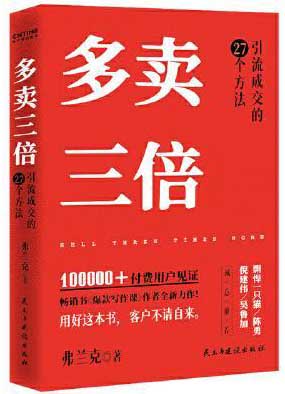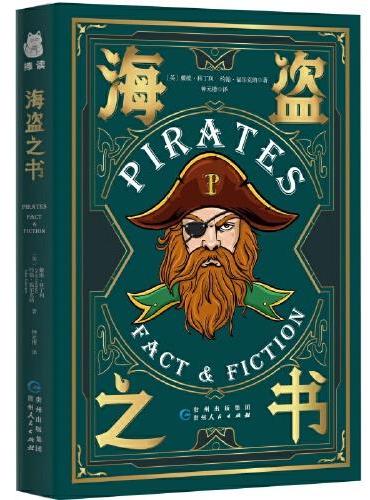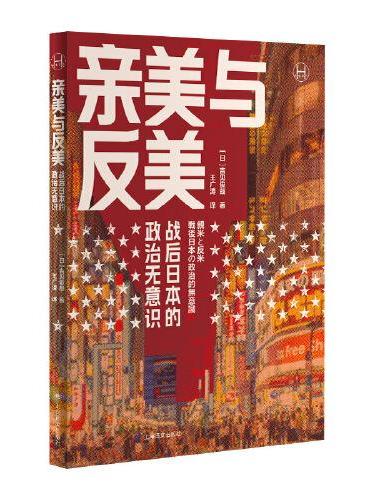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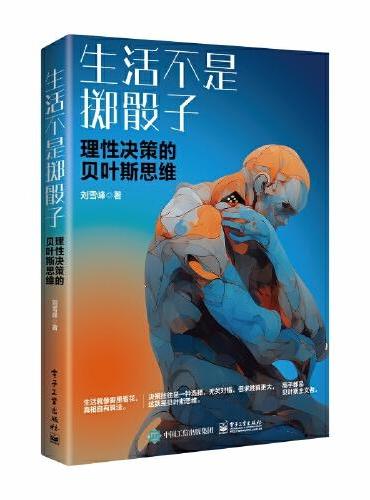
《
生活不是掷骰子:理性决策的贝叶斯思维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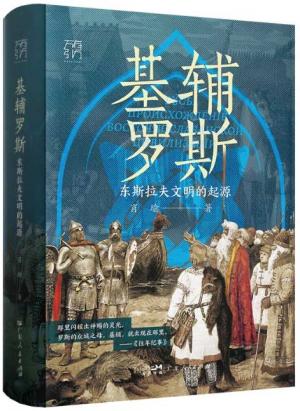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基辅罗斯:东斯拉夫文明的起源
》
售價:NT$
6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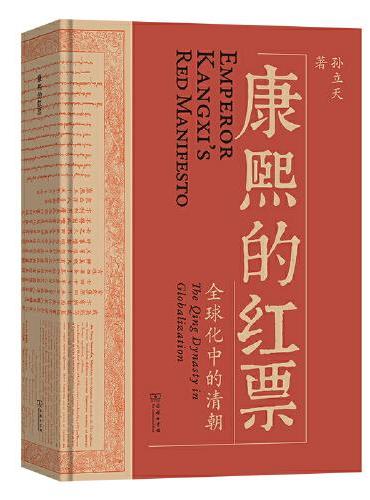
《
康熙的红票:全球化中的清朝
》
售價:NT$
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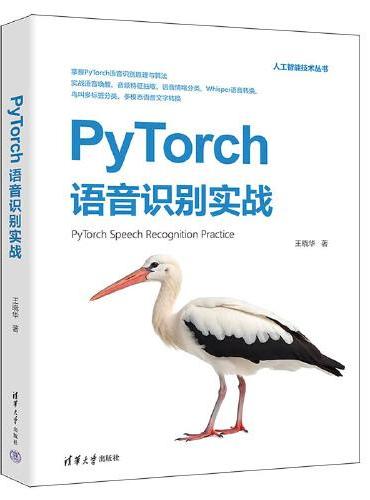
《
PyTorch语音识别实战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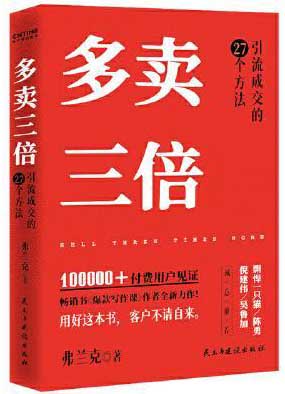
《
多卖三倍
》
售價:NT$
25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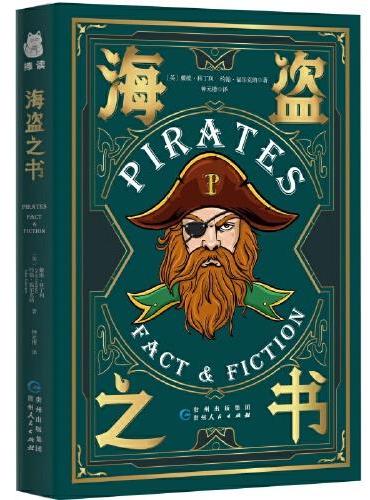
《
海盗之书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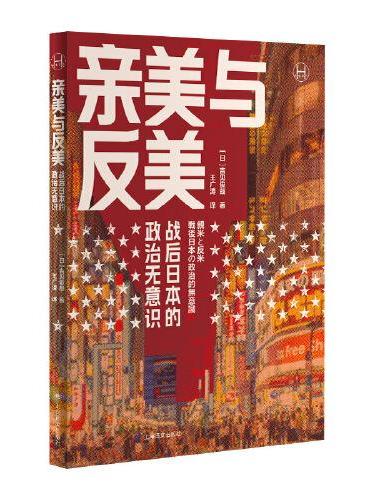
《
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
》
售價:NT$
325.0

《
亲爱的安吉维拉:或一份包含15条建议的女性主义宣言
》
售價:NT$
274.0
|
| 編輯推薦: |
|
《锯齿形的孩子》是以色列文学大师大卫格罗斯曼写给孩子的成长之书、冒险之书。十二岁的诺诺跟随一个国际大盗,闯祸,历险,揭开秘密,展开了一段他做梦都想不到的成长之旅。大卫格罗斯曼是《少年Pi的奇幻漂流》作者扬马特尔奉为大师的作家,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获26届欧洲电影奖。
|
| 內容簡介: |
|
男孩诺诺被送上火车,据说车上有爸爸策划的生日礼物。他终于找到那个等他的老人——一个国际大盗,他们劫持了火车,开始了做梦都想不到的冒险。当一老一少都成了忘年交时,诺诺在报纸上看到自己被绑架的消息……
|
| 關於作者: |
大卫格罗斯曼,1954年生于耶路撒冷,当代最负盛名的以色列作家之一。著有《羔羊的微笑》《证之于:爱》《私密语法手册》《直到大地尽头》等。他拿遍以色列各种文学奖项,并在欧美广受肯定,赢得保罗奥斯特、扬马特尔、科尔姆托宾等作家的称赞。
他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多年来与阿摩司奥兹等人协力促进巴以和平。他的一个儿子在巴以冲突中死去,但他依然坚守和平立场。
|
| 目錄:
|
1
2
3 大象亦有柔情
4 我戴着单片眼镜初次登场
5 等等,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6 有个东西抓着我
7 试驾火车,真难停下来!
8 玩具部门的恶作剧
9 我们逃脱了法律制裁
10 这一章我不打算加标题,尤其是不幽默的标题
11 以法之名:快停下!
12 我揭露了他的身份:金麦穗和紫围巾
13 感情是否可以触摸?
14 通缉:达西妮亚
15 斗牛
16 黑暗与黑暗之间的一线光明
17 她与他的身体之间无限的距离
18 像一只夜行动物
19 沙滩骑手
20 真的有灵魂转世吗?还有,我上了报纸头条
21 回归枪口,说起爱情
22 鸟儿与冬天
23 的确就像一部电影
24 侦探的儿子
25 佐哈拉起身穿越月亮,而丘比特换上了重型武器
26 世界上从来没有两个人如此格格不入!
27 空旷的家
28 这就过分了
29 世界上还会有奇迹发生吗?拭目以待
|
| 內容試閱:
|
1
火车轰鸣,就要驶出车站了。孩子站在一节车厢的窗边,看着站台上与他挥别的那对男女。男人一只手摇晃着,动作轻微而羞涩。女人挥舞着双臂,甩着红色的大围巾。那个男人是孩子的父亲,而女人是加布瑞拉,也叫加比。男人穿着警察制服,因为他是个警察。女人穿了条黑裙子,因为黑色显瘦。竖条纹的衣服同样也显瘦。最显瘦的是,加比曾开玩笑说,站在某个比她还胖的人身边,只是到现在她还没找着这么个人。
孩子倚在车窗边,火车渐行渐远。他看着他俩,犹如一幅再也无法重见的图画——那个孩子就是我。我想,他们现在要孤独地过上两天了。一切都不能挽回了。
这个想法抓住我的头发,一把一把地将我拉出窗外。爸爸瘪了瘪嘴,按加比的说法是“审判前最后的警告”。算了吧。要是他真的在乎我,就不会把我送去海法两天,而且是送到那个人那里。
一个穿着列车工作服的男人,站在站台上,朝我用力吹了吹哨子,用大幅动作示意我把脑袋收进去。真是要疯了,这满满一车的人,怎么穿着制服、吹着哨子的人偏偏向我挥手。我偏不把头收进去。这样爸爸和加比就能看着我直到最后一刻,就能记住这个孩子。
火车还未驶出站。它缓慢地穿过混合着柴油味的闷热气浪。我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感觉。旅行的气味。自由。我在旅行!是我一个人!我把一边脸颊伸到热风里,接着又换另一边脸颊,试图风干爸爸的吻。他从来没有像这样当众亲吻过我。这算什么,亲亲我,然后把我送走。
现在已经有三个列车员在站台里朝我吹哨子了。就像是我给自己组了个管弦乐队。因为这会儿已经看不见爸爸,也看不见加比了,我懒洋洋地把身子慢慢收了回来,显得我压根不在乎那哨子声。
我坐了下来。要是车厢里有人做伴就好了。现在怎么办?从这儿到海法要四个小时,而他将在路途的终点等着我。他比我更抑郁,更愤慨,更绝望,他是撒母耳史勒哈夫博士。他是教师、教育家,写了七本教育学和公民权益的教科书,他正好也是我的伯父,爸爸的长兄。
我站起来。检查了两遍如何打开窗户,如何关上它。我打开又关上垃圾桶的盖子。车厢里也没别的什么可以开开关关了。所有东西一切正常。火车里真是井井有条。
我爬到座位上,整个身子钻进上边的行李层,然后又头朝下地翻回到车厢地板上。我要检查看看有没有人碰巧掉了钱在椅子底下。可惜没人掉钱,都是些细心人。
爸爸和加比真该死,他们怎能就这样把我送到撒母尔伯伯那儿去呢,再过一个星期就是我的成人礼了。好吧,爸爸对他的哥哥怀着敬仰,特别崇拜他那套教育学理论。那加比呢?加比可是在背后叫他“猫头鹰”。难道这就是她答应送我的特别礼物?
我座椅的皮套上有个小洞。我把手指塞进去,将它弄成个大洞。有时在这种地方可以捡到钱。但我只摸着了海绵和弹簧。
我能用手指钻上四个小时,至少挖通三节车厢,挖出一条通向自由的隧道,从此消失,不用到撒母耳史勒哈夫(原姓费尔伯格)那儿去, 也许他们还会再送我过去一次。
没等钻通三节车厢,我的手指已经疼得不行了。我伸开腿躺在座位上。我是个囚犯。是个转移中的犯人。正被移送法办。我兜里的钱掉了出来,硬币滚得满车厢都是。有些我找着了,有些却没有。
家里的每个年轻人一生当中都得在史勒哈夫伯伯那儿经历一次这样的摧残,加比管这种痛苦的仪式叫“史勒哈夫化”。
但对我来说这是第二次。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孩子经历两次这样的事还能保持精神正常的。
我跳到座位上,开始在车厢壁上敲敲打打。不一会儿我又改成敲有节奏的鼓点。
说不定隔壁车厢坐着个像我一样倒霉的囚犯,想要与他同病相怜的兄弟通个信?可能这火车里坐满了要送去我伯伯那儿的少年犯?我又敲了敲,这次是用脚。检票员进来了,叫我安静坐好。我坐了下来。
上一回我被“史勒哈夫化”以后,我的整个人生都终止了。那是在我惹了潘西娅马乌特耐尔那头母牛之后。那一次,伯伯把我关在一间又小又闷的屋子里,毫不留情地教训了我整整两个小时。他一开始还轻声细语地,甚至还记得我的名字。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就像以往那样完全忘记他在哪儿了,也忘了跟谁在一起。他感觉就像是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在城市广场上,面对着人群,里边有他的学生,有慕名而来的仰慕者。
而现在,又来了。而且毫无意义。我又没犯事儿。“成人礼之前,你得好好听听撒母耳伯伯的话。”加比说。突然间他又成了“撒母耳伯伯”。我可从来不知道。
为了离开我的父亲,加比需要我不在她身边。
我站起身来,四下踱步,又坐下来。过去他们不允许我去旅行。我了解他们。要是没有我在他们中间,他们就吵个不停,说出一些相互威胁的话,没法弥补。这就是我的命运,现在已经确定了。
“干嘛不等工作的时候再谈?”父亲朝加比问道,“我都已经迟到了。”
“因为工作的时候办公室里总是有人走来走去,中途也会有电话打进来,没法谈啊。来吧,先进咖啡馆再说。”
“咖啡馆?”父亲吓一跳,“大白天的?要不要这么严肃啊?”
“你别把什么事都不当真。”她恼了起来,眼泪还没掉下,鼻头已经泛红。
“如果还是那件事的话——”父亲厉声道,“你趁早忘了得了。自从次咱们谈过后我的情况仍旧是老样子。我还是办不到。”
“这次你得听我讲,”加比说,“让我一气儿讲完。听我说话你起码做得到吧!”
于是他们上了警车,父亲发动了引擎。他面色凝重,肩上的警衔闪闪发光。加比则缩在一旁。甚至都没人开口讲话——他们之间已经在闹矛盾了。加比从她包里找出一个圆形的小镜子,瞅了会儿映在镜子里的脸,想要紧一紧她那蜷曲不堪、纠结成一堆的发髻。“一脸猴儿样。”她心里说。
“不对!”我跳了起来。此时我正在一趟开动的列车上。
我从来不会让她去自取其辱。“你偏偏长着张有意思的脸。”这会儿我发觉这么说还不能完全说服她。我得补充说:“关键是你还很有内在美。”
“我们听到了。”她尖酸地回答道,“奇怪的是从来没举办过一届‘内在美’选美大赛。”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正站在那个小手柄旁,是个红色的手柄,固定在车窗边。就我的状态来讲,这可不是个好位置。一旦拉动手柄,可以让整列火车停下来。我读着列车管理警告:仅在紧急情况下允许拉动拉杆。无故拉动拉杆导致全车制动者,将面临高额罚款及刑拘处罚。我的手开始发痒。指尖痒,指间也痒。我又高声朗读了一遍具体的条款。没用。掌心也开始出汗了,我便把手插到兜里,可没一会儿又抽出来了。没见识过我这双手的人就会说——不过是手脚好动,捂不住。我全身都开始流汗了。于是我摸向脖子上的项链,那上面挂着一颗子弹,沉重而冰凉,能使人镇静。这是你父亲身上的,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是从他肩膀里取出的,
它守护你不被无端伤害。然而我整个身体开始感到刺痛。
我知道这种感觉,并且知道最后会怎么样。我心中开始了这样的对话:“也许火车司机压根不会知道是在哪个车厢拉动的这个手柄?但是如果在驾驶室里有一个设备能显示拉动手柄的位置呢?好吧,我可以在这里拉了,然后逃到其他车厢去。但如果他们在手柄上找到我的指纹怎么办?要不用布把手指包上再拉?”
我绝不能参与这样的讨论。当我开始这样争论时,我总是输。我后背的肌肉鼓了起来,我像父亲那样站起身,结实、强壮得像头熊,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但都于事无补。我双眼之间有个地方时常感觉灼热,在这种时刻它变得更热了,这会儿它来了,它在控制我,到最后一刻我完全屈服了。我把手脚绑在一块,蜷缩着躺在座位上。加比管我的这种举动叫“防御性抵触”。每个东西她都能作出具体的定义。
“我已经不是个小女孩了,”她这会儿在咖啡馆里对爸爸说,“我和你还有诺诺已经生活了十二年了。”这会儿她仍然控制着自己的声音,安静而理性地说着话。“十二年来,我带大他,照顾你们俩,打理你们家。我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了解你,无论如何我是那么想和你一起生活。不仅仅是想要当你工作上的秘书、家里的厨子和保洁。我想和你住在一起,当诺诺的母亲,无论白天黑夜。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告诉我?”
“我还是没办法,”父亲说,并用他的手掌紧紧握着咖啡杯,加比等了一会儿,深呼吸一下,然后说:“我已经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你看啊,加比,”父亲说,眼神闪烁不安,透着不耐烦,“像我们这样有什么不好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这对我们仨都挺好的,包括孩子。为什么突然间要改变?”
“因为我已经四十岁了,雅各,我想过完整的日子,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家庭。”现在她的声音都嘶哑了,“我想要跟你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你和我的。我想知道我俩的结合可以造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得再等一年,也许我就老到不能生育了。我还认为诺诺应该有一个真正的母亲,而不是个半吊子的妈妈!”
她这会儿跟爸爸说的这番话,我都能背下来了。她这段演讲已经对着我操练够了。还是我给她贡献了那条感人的句子“当诺诺的母亲,无论白天黑夜”。我还给了她一条很实用的建议:别哭。千万千万不要在他面前哭!因为只要她一开始哭,就全完了。爸爸受不了她掉眼泪。什么人掉眼泪他都受不了。
“加比,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叹了口气,偷偷瞄了一眼手表,“再给我一点时间。这么大的事我不能仓促地下决定。”
“我都等待十二年了,再也不能等了。”
沉默。他没有回答。她的双眼已热泪盈眶。拜托,请控制自己,控制一下,加比,你听见了吗?
“雅各,你现在就当着我的面直接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沉默。她的双下巴都在颤抖。她的嘴唇抽搐着。如果她开始哭,就注定要完了。还有我也完了。
“因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会起身就走。就这一次了,到此为止。再也不会像从前一样没完没了。到此为止!”她激动地拍着桌子,眼泪已经顺着她圆圆的脸庞流了下来,眼妆全花了,淌下来,流过她的雀斑,糊在她的嘴周围的两道凹纹里。爸爸把脸扭向窗口的方向,因为他无法忍受看到她哭,也许他纯粹就是不愿意看她这个样子,泪眼婆娑,又红又肿,脸颊本就胖嘟嘟的,还不停颤抖着。
这一刻她真不好看。这其实挺不公平的,因为如果她再漂亮一丁点,比方说长一张可爱的樱桃小口,或是翘翘的鼻子,爸爸都有可能因为她那唯一一点美丽之处而突然爱上她。有时候哪怕是最微小的美都足以赢得一个男人的心,即使这个女人并非“外在美”选美冠军。但是,当加比哭着的时候,恕我直言,她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
“好吧,我明白了。”她捂着那条红围巾哽咽道,那围巾之前倒是派上了更为体面的用场。“我真是个傻瓜,我一直认为你可以改变的。”
“嘘……”他乞求她,扫了一眼周围。我当然希望在咖啡厅的人此刻都盯着他。所有的厨师、服务员和咖啡师都从厨房出来,站在他边上,穿着围裙,抱起双臂,狠盯着他。如果有一件事能使他害怕,那就是这个人人围观的场景。“你看,嗯,加比,”他试图安慰她。这回他似乎温柔了一些,也许因为身边还有别人,要么就是因为他感觉到,这次她是来真的了。
“再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好吗?”
“想什么?想我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你还让我给你更多的时间?你是要到那时才告诉我,咱俩没戏了?到时谁还肯看我一眼?我想成为一个母亲,雅各!”人们都盯着他,他恨不得钻进地缝里,然而加比还继续说着:“我能给孩子很多的爱,也能给你!你看我做诺诺的母亲做得多好,你怎么就不能试着去理解我呢?”
即使在我们事先排练的时候,加比也一度特别入戏。她哭泣,恳求,就好像我是我爸爸一样。但一会儿,她又能突然打住,红着脸说抱歉,有些事情不适合告诉我这个年龄的小孩子。唉,其实无所谓,反正我什么都知道了。
我不是什么都知道,但这会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加比卷起那堆湿透的纸巾,塞进烟灰缸。她从红肿的眼睛上擦去花掉的化妆品痕迹。
“今天是星期天,”她说,努力保持着声音坚定,“成人礼在下周六。我就给你时间,直到下周日上午,你有整整一个星期来做决定。”
“你这是给我下最后通牒?这事儿不是你靠威胁就能解决的,加比!我还以为你有多聪明。”他说话不紧不慢,但双眉之间已蹙起来,怒不可遏。
“我已经没有等待的气力了,雅各。我都聪明了十二年了,还不是孤单一人。说不定蠢一点倒更好。”
爸爸什么也没说。他的红脸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红了。
“好了,我们开车回去工作吧。”她嗓音嘶哑地说,“对了,要是你的答案跟我猜的是一样的,你最好现在就开始找一个新秘书。我要与你断绝一切 接触。嗯。”
“你看,嗯,加比……”爸爸又来了。他想不出什么别的话来,也就是“你看,嗯,加比”。
“就到下周日。”加比打断他,站起来,走出了咖啡厅。
她要离开我们。
她要离开我。
在火车上,我的胳膊和腿恨不得马上去抓那个制动拉杆。紧急情况,紧急情况,用大红色写在小拉杆边上的这两个词像是在对我尖叫。我坐在这列越驶越远的火车上,我的生活即将被摧毁。我捂住耳朵,对自己大声喊“阿姆农费尔伯格!阿姆农费尔伯格!”,就好像有人在外面试图告诫我不要碰那个拉杆,要从我自己手上救下我自己。这个人就像父亲,或是老师,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甚至是感化院的负责人,“阿姆农费尔伯格!阿姆农费尔伯格!”。但是,什么都帮不了我。我独自一人。我是被遗弃的。我就不应该离开家。我现在必须回去。马上。我踉踉跄跄地走向那个拉杆,向它伸出手,我的手指已经抓着它了,因为现在真的遇上了紧急情况。但就在这时,就在我要使出全力拉起这个拉杆的时候,身后的车厢门打开了。有两个人正要朝里走,一名警察和一名囚犯。他们都在那儿站住了,充满疑惑地盯着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