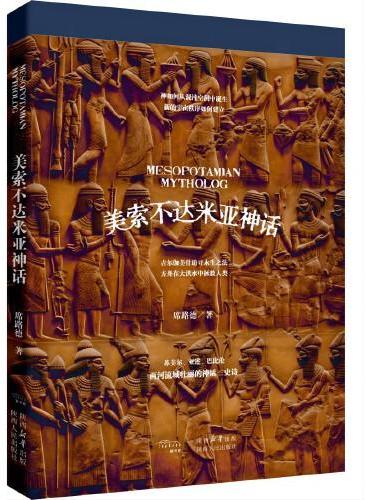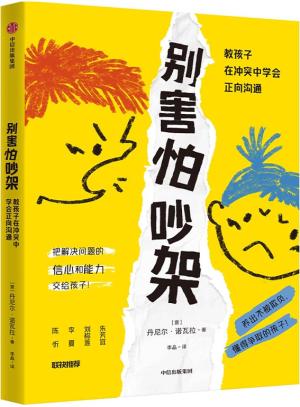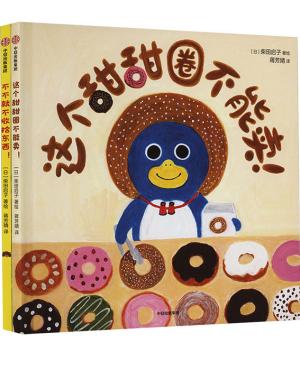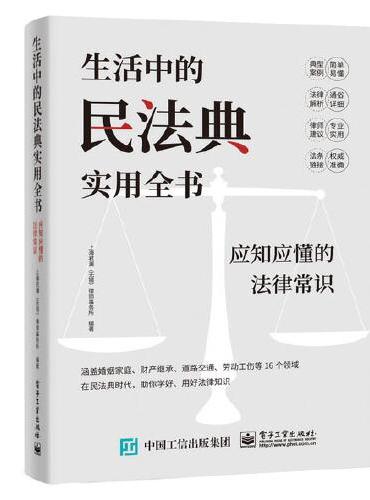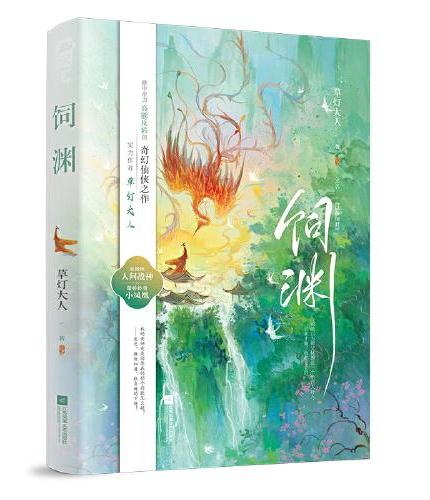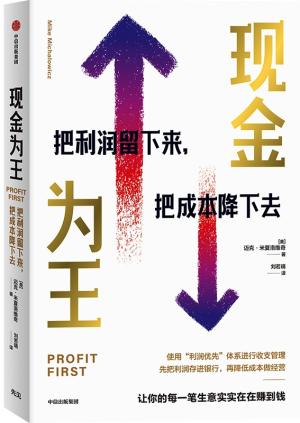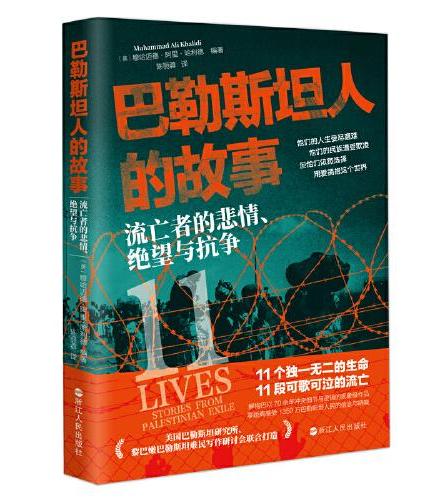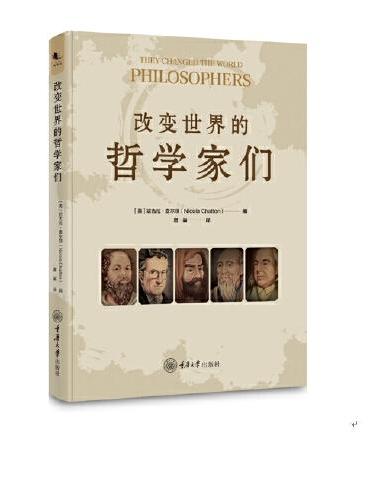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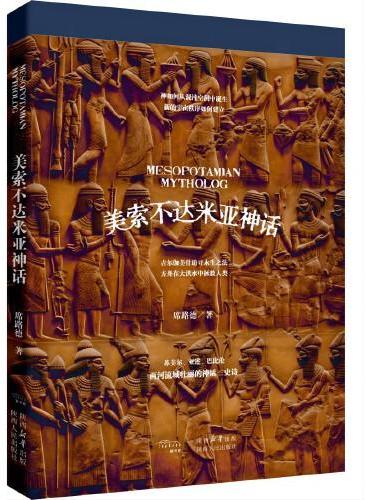
《
美索不达米亚神话
》
售價:NT$
39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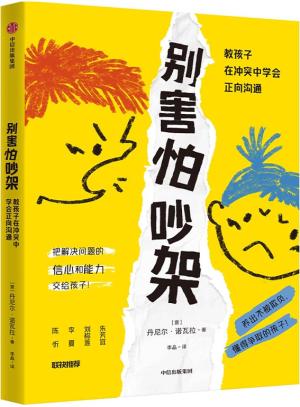
《
别害怕吵架:教孩子在冲突中学会正向沟通
》
售價:NT$
27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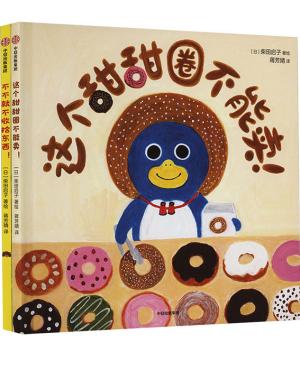
《
这个甜甜圈不能卖:奇思妙想爆笑绘本(全2册)
》
售價:NT$
4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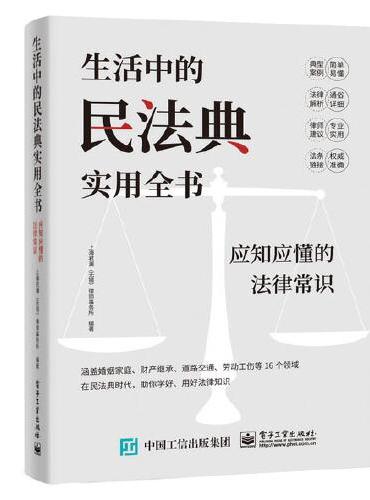
《
生活中的民法典实用全书:应知应懂的法律常识
》
售價:NT$
49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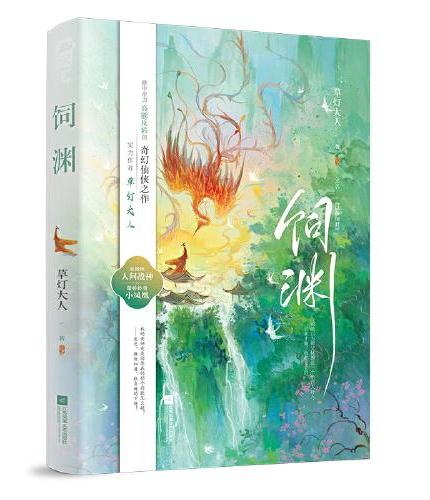
《
饲渊
》
售價:NT$
22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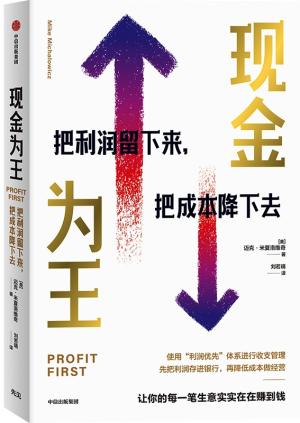
《
现金为王:把利润留下来,把成本降下去
》
售價:NT$
3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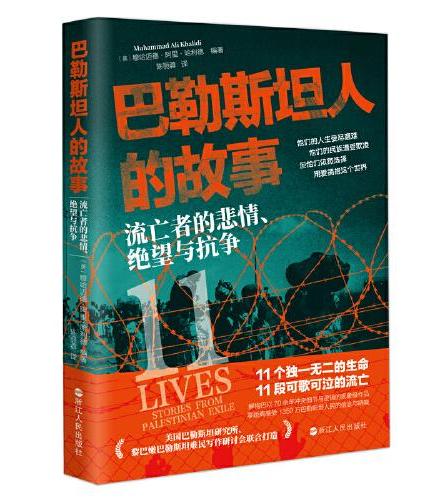
《
经纬度丛书·巴勒斯坦人的故事:流亡者的悲情、绝望与抗争
》
售價:NT$
49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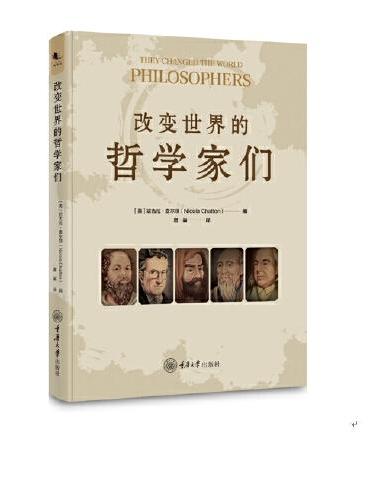
《
改变世界的哲学家们
》
售價:NT$
493.0
|
| 內容簡介: |
六十年前,因兵痞拦棺抢劫引发一场惨案,参与者皆丧命灾厄,主犯马三炮更是死得离奇,临死时留下了一枚神秘的袁大头。
六十年后,为了治疗身上与生俱来的痼疾,我跟着舅爷来到乡下学习异术,目睹了舅爷用民间流传的异术救人消灾的惊心动魄,更亲历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怪异事件。当水落石出,一切的源头竟然是那枚佩戴在我身上的袁大头。而后神秘的人物纷沓而来,离奇怪事更加频繁地爆发,我和舅爷将如何面对随之而来的漫天风雨。
|
| 關於作者: |
|
飞行电熨斗,原名王兆阳,知名文学团体雁北堂成员,天涯莲蓬鬼话写手,著有多部惊悚悬疑小说,其网络原名《一枚袁大头》的作品一经发表随即引发巨大轰动,成为网络志怪小说的领军人。
|
| 目錄:
|
第一章 老兵诡事 1
第二章 老家灵异事件 33
第三章 舅爷收徒 48
第四章 听舅奶讲怪事 62
第五章 志豪命悬一线 78
第六章 追寻救命伴生树 93
第七章 造纸厂替人消灾 102
第八章 爷爷的袁大头 118
第九章 续阳接命 134
第十章 滔天大祸 142
第十一章 古城轶闻 162
第十二章 灵物黄皮子事件 188
第十三章 临终表白 206
第十四章 极阴之地 220
第十五章 百脉血 汴梁石 234
第十六章 回天乏力 250
|
| 內容試閱:
|
这是一个灵异故事。
爷爷参军入伍不久,因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很被他的领导看重,没两年就从一个大头兵升到了文书少尉这个位置,专门负责所在部队的文书往来和一些文职后勤工作。按理说这是个好差事,因为那时候的国民党兵,正规部队还可以,像他们这些后来收编的当地军阀武装,战斗力不行,装备更别说了,那就是炮灰的命。
文职,就等于不用去送死,打仗的时候待在后面,等打完了,再冲上去统计一下阵亡名单和缴获、损失的装备就可以了。
规定虽然是这个样子,但不一定总能执行。有一次,由于将官人手不够,部队为了押送一批军用物资到豫鲁交界处,就临时抽调我爷爷和另一名文官负责这次押运任务。当然也有一个理由就是,东西送去,还要办交接手续,清点货物,这些事情武官是干不来的。不过,光有当官的自然不行,跟着他们一起的,还有三十多名扛枪的大兵,相当于一个排的兵力。
那年头儿火车慢,按我爷爷的话说,你只要耐力好,会长跑,就算按时开车,晚点个五分十分钟到都能撵得上。
和我爷爷一起执行这项任务的同僚姓黄,虽然他们俩平时不带兵,也没有武官的火爆脾气,但毕竟军衔在这儿摆着,那些当兵的一路上倒也和他们相安无事。
但当时的火车实在太慢,从上午十点左右出发,跑了一天,快到午夜了,才走了一半路程。夜里子时刚过的时候,火车又在一个小车站停下了,司机说是要例行检修,大概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士兵们闲来无事,纷纷下车在附近活动一下,反正就算是突然开了,他们也追得上。我爷爷则和姓黄的同僚坐在闷罐车大门边上,一边抽烟一边探讨这个小车站的地名——“土地陈”。
“一般情况下,小地方取这种名字,最大的原因是迷信,比如说土地公公曾在这里显过灵,而村中又以陈姓居多,或许是百姓自发改的,或许是某些官员改的。”
“当然,不排除是皇帝钦赐的可能性,因为皇帝老儿随便一句话,下面就当圣旨了,改个地名还不是小事一桩?更何况以前如果住的地方名字是皇帝钦赐的,该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儿。”
他们俩正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隐约就听见远处随风传来一阵呜里哇啦的声音。这声音像是人吹奏出来的,听起来虽然单调,却有一定的曲调。只不过我爷爷怎么回忆,也没想出这是用什么乐器奏出来的。西洋乐器在那时候的农村基本上不会出现,唢呐的声音要更嘹亮一些,没有这么低沉,而笛子和箫又没有那么厚重。
倒是他身旁那位年纪稍大的文官听到这个声音后,脸色一变,赶忙站起来朝着外面的大兵喊道:“集合啦——都快点上车!”
喊了几遍,那些大头兵压根连听也不听他的,依然是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抽着烟、聊着天。这个文官的表情逐渐尴尬起来。
那声音越来越近,士兵们也察觉到了,纷纷扭头朝车站的一边瞧去。我爷爷看出他这个同僚可能知道些什么,问道:“这声音是怎么回事儿?刚停了一小会儿,离开车还早呢,你叫他们回来干吗?”
“……”同僚欲言又止,我爷爷那时候也年轻,好奇心强,又追问了两遍,他才说道,“这是出殡的队伍。吹得那个东西叫殇篪,是夜间出殡时吹奏的。我老家有时候也这样做。”
“夜间出殡?”我爷爷惊奇不已,他活了二十来年,头一次听说夜里出殡,而且还是午夜时分。
“对!”那个文官狠狠抽完最后一口烟,说道,“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规矩,在我们老家,只要是横死的人,一般都选在午夜前后出殡。当然,我说的这个横死,是专指被别人故意杀害的。夜间阴气大,才比较容易把他们的魂给送走,防止以后害人。”
“那你让他们回来又是什么意思?”爷爷依然有诸多不解,指着车站上的士兵问道。
“夜间出殡,来的都是亲朋好友,冤死之人就在后面跟着。有外人在,不吉利,非但不吉利,而且还有可能被冤魂上身,是需要回避的。”那名文官解释道。
“哦……”爷爷答应着,却没有当回事儿。虽然他的老家有许多事情更邪乎,但他并不信这些东西,只是敷衍了一下,表示知道了。
眼看士兵们都不听招呼,那名文官也放弃了叫他们回来的打算。可能他也觉得都是军人,人多势众阳气大,对这些邪乎的东西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况且那个年头,当兵本就是件不吉利的事儿,也不在乎多那么一点儿。
很快,出殡的队伍就出现在了车站一侧。借着站台上昏暗的灯光,爷爷看到队伍还不算长,也就十几个人,光是抬棺材的就占了一半。然后有两个打招魂幡的,两个撒纸钱的,两个吹奏殇篪的。
那殇篪说来奇怪,有二尺来长,手腕粗细,通体灰白,吹奏的人需要用两只手同时握着,不像笛子那样,还需要腾出几根手指去按压音孔,看来音调的变化全凭吹奏人的嘴来完成。而这一队人,竟然没有一个披麻戴孝的,只是象征性地都穿着件麻布背心,统一了着装。
队伍的最前面,有一个老道士,发髻盘得挺高,一身灰色道袍脏兮兮的,不知道多久没洗,胡子和头发也都蓬乱地披散着。只见他左手捏了个指诀,一边念念有词,一边带着队伍缓慢前进,还时不时地从肩上的褡裢里抓出一把纸钱,撒向空中。
他撒的纸钱和身后那两个撒的显然不一样,一黄一白,而且道士的黄纸上似乎还画有红色图案。送葬队伍来到了站台,看样子他们是要从这里跨过铁道,去往对面的山坡。因为其他地方都是农田,路并不好走。终于到了近前,老道士显然没想到会停着一列火车,而且还有这么多当兵的,一挥手,队伍停了下来,殇篪那令人压抑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咳……夜送喜神,望无关人等回避——!”老道士清了清嗓子,又从褡裢中掏出一个三角铁和小铁锤,朗声说完后敲了一下,“叮”一声,颇为清脆。
这些当兵的虽然打仗不一定行,但尸体见多了,谁还在乎这个?于是乎在老道士敲了一声后,过了老半天,只是站在中间的几个人象征性地把路让开,但他们并没有回到车上去的意思。这些家伙显然也想看看这午夜送殡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老道士见没人听招呼,扭脸一瞧,看到了坐在车厢边上的我爷爷他们,投来一束求助的目光。
由于是军官级别的,爷爷他们俩穿得比较讲究,衣服板正、料子好,而且那年头士兵和军官的最大区别就是——军官穿皮鞋。
所以老道士一眼就看出他们两人才是头儿。
同僚见一时僵在这里,赶忙站起来再次喊道:“叫你们回避!没听见吗?都赶紧给我上车!”
总算有人拖着步子慢慢朝列车上走来,但不知道是谁咳嗽了一声,那几个刚迈了两步的又退了回去。
我爷爷也渐渐瞧出来,这些当兵的其实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趁这个机会,让他们两个文官吃吃苦头。说白了,就是要和他俩对着干!
因为文官在部队里一向总被别人瞧不起,特别是最底层的士兵。作为文官,虽然也是官,但吃得穿得都比他们好,发的军饷也比他们多,更重要的是不用去前线打仗,就在后面写写字出出主意就能被长官赏识,是这些大头兵怎么也想不通的。
所以,日积月累,就从最开始的质疑,变成了敌对。现在又逮着这么个机会,这些兵痞摆明了是想难为他们俩。
有人会说,部队里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谁敢以下犯上啊?话是这么说,但是那个时候比较特殊,好多兵以前本来是做土匪的,只不过后来被收编,换了层皮而已,他们这群人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更何况面对的是两个文官,只要别做得太过分,就算任务完成回去告到他们长官那里也不怕!试问哪个当官的不护犊儿?我自己的兵,怎么打怎么骂都可以,但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
那个同僚也终于怒了,拔出腰间的手枪喝道:“我命令你们!马上上车!!!”这些兵一而再,再而三地落他的面子,刚才没人也就罢了,现在还当着外人的面,这已经到他容忍的极限了,他再也憋不住了。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要不要回避的问题了,而是在气势上谁能压得住谁。
见他掏枪,士兵们的气势顿时弱了几分。长官掏枪指着当兵的,可以;当兵的敢掏枪指着长官,那就是大忌,回去是要挨军棍的。他们再怎么胡闹,只要我爷爷他们俩掏了枪,这些人也没辙。
这时一个五大三粗的士兵从人群中走出来,我爷爷认得这个人叫马三炮,仗着身子骨壮实,手里又有枪,平时无恶不作。可是这家伙会打仗,死在他手里的日本鬼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要不是他这个人品行实在太差,恐怕早就当上排长了。
“呵呵,两位长官,”马三炮走过来,笑嘻嘻地对着我爷爷他们俩道,“咱们这次押送的是战备物资,可是关系到前线将士们的吃穿性命,马虎不得!听说最近这一片地方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这些人夜里出殡,搞不好就打算整什么幺蛾子,还是我带着几个兄弟先去查一查吧!”
爷爷本来就不知道是真是假,心想去查一查也好,但他还想听一听身旁同僚的意见,毕竟他能知道殇篪这种乐器,年纪也长,应该可以分辨出来实际情况。
不过这个马三炮虽然走过来说了一大通,看着像是在请示,却没有一点请示的意思,他自个儿把话说完,没等爷爷他俩回答,就立刻转过身,走到士兵中间说道:“来几个人,查一查他们!别是土匪!”
说完话,领着几个人就过去了。
当爷爷的同僚回过神来想要阻止,这些家伙已经端着枪走到出殡的队伍里。查了一会儿,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马三炮心有不甘,突然大声喊道:“再来几个人,把这棺材撬开来瞧瞧!”
“不行!”老道士本以为他们例行检查一下就算过了,谁知道还要开棺验尸,立刻回身护在棺材前,斩钉截铁地道,“任何人都不能打开这口棺材!”
“呦?”马三炮等的就是他这句话,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老道士问,“你该不会和他们是一家人吧?”
“自然不是!贫道受聘而来!”老道士答道。
“既然不是一家,他们家人还没吭声呢,你着个什么急啊?!”马三炮说着一把推开老道士,手就拍在了棺盖上。
他这一拍,似乎发现了什么,马上低头在棺材上细细查看。搞得连我爷爷都心痒难耐,想知道这家伙在搞什么名堂。
“金……这是金丝?!”马三炮看了半天,随手在棺材上一拽,似乎揪出一根头发丝一样的东西,拿起来借着灯光,边看边说,“金子?”这些当兵的一听到这俩字,顿时呼啦啦都围了上去,就连远处看热闹的也忍不住跑了过来。
顿时,出殡的队伍被当兵的挤散了,十几个亲属看着里面被围起的棺材,敢怒不敢言,谁让人家有枪呢!
“别动!!!”老道士见当兵的围上来就要扯那些金丝,大喝一声,抢了过去。我爷爷也是事后才知道,这口棺材外面横着走了七十二根、竖着三十六根全部由纯金打造的丝线。虽然细,但加在一起估计也有一两来重,怪不得这些当兵的要抢。
马三炮这时再次领头出来道:“你不让我们开棺检查,恐怕里面装的不是人吧?”
“我怕你们承受不了开棺的后果!”老道士盯着他,针锋相对。
“哼!不就是死人嘛!爷我见多了!不怕!来啊,把棺材打开!”老道士越是不让看,马三炮就越是来劲儿。
“啪!”一声枪响,爷爷的同僚这时候终于看不过去了,站起来朝天开了一枪。
他也瞧明白了,什么土匪,都是借口,这年头儿土匪都当兵了,哪里还来的土匪?这个马三炮原来就是个土匪。再者说,土匪敢来劫军队的物资?除非他们不想混了。
枪一响可不打紧,送葬的队伍被惊着了,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快跑呀!”十几个人瞬间跑得烟消云散,东西扔了一地,连最重要的棺材也不要了。
“马三炮!回来吧,别难为死人!”我爷爷适时地叮嘱他道,话里软中带硬。
“长官!”到这一步了,马三炮自然不会死心,回头喊道,“这个道士说什么也不让看,里面一定有猫腻!我估计不是药品就是军火!这要是让咱们碰上了,可是大功一件啊!如果里面真是死人,兄弟我带上几个人,恭恭敬敬地给人家送回去!”
“马三炮!记得你的任务,是押送货物!不是盘查老乡!”爷爷身旁的文官跳下车走过去,瞪着马三炮道,“你如果执意要违抗军令,别怪我就地正法了你!”
“怎么?您要崩我啊?”马三炮眉毛一扬,阴阳怪气地道,“没问题,我认!但是请今天的兄弟们做个证,我马三炮是为了确保物资安全,才检查的这一队可疑人员。回去照实告诉老总,就算我老马没白死!”说着,他就要去掀那个棺材盖。
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来,我爷爷他们俩也毫无办法。这不是在战场,可以就地枪决逃兵,况且他俩的理由的确不够充分。真杀了他,这些当兵的即使不暴动,回去了也一准儿要告黑状,到时候他们有嘴也说不清。无奈,两人只得眼睁睁地看着马三炮去掀那棺材盖子。
“啪!”老道士一巴掌按在了棺材盖上,发出一声闷响,不过他看马三炮的眼神此时发生了变化,不再是愤怒,而是毫无情绪,就像是在看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
“你是执意要看?”老道士一字一顿地问道。
“我还就是非看不可!”马三炮算是杠上了。他其实心里应该很清楚,这里面的八成是死人。但是这家伙还有个别的心眼儿,外面用金丝圈着的棺材,里面的陪葬品一定不会差!刚好爷爷同僚那一枪把那些送葬的人都吓跑了,这可正是个绝佳的机会,如果不打开顺上几件,他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
“好!好!好!”老道士盯着他看了好久,突然又扭头问走过去的那个文官道,“老总,您这个兵的品性怎么样?”
“品性?……”文官压根儿没想到他会这么问,愣了好久才说道,“原来就是土匪,现在当了兵也是个兵痞!”马三炮今天多次不给他面子,他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
不过这个姓马的却一点也不介意,还颇有些引以为傲。正是因为他原来的土匪身份,这家伙才能在军营里横行无忌。
“好!”老道士接着道,“那就是咎由自取!贫道没什么好说的,奉劝诸位一句,不想惹祸上身的,最好站在一旁别动这口棺材,告辞!”说完,他甩袖就要走。
“等等!”马三炮这时把流氓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喝住老道士说,“我可没说放你走,如果这里面的不是死人,你是要跟我们走的!去两个兄弟看住他!”说完,他双手一用力,就将棺材盖掀翻在地。
棺材只有在下葬前才会打上钉子钉死,现在自然是一推就开,棺材上的金丝早让其他几个士兵扯了个七七八八。马三炮的目的在里面,外面的这一小点儿金子他压根不会放在心上。
棺盖“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所有人都下意识地退了一步。马三炮也慎重起来,慢慢朝里面探头看去。
“哎呀!!!”待这家伙看清棺材里面后,突然大叫着往后跳去,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个不轻,他自己却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娘的,真是个死人,还睁着眼,故意吓老子啊!”
“睁着眼?”老道士听他这么说,身子一震,问道,“她……真的是睁着眼的?”
“你自己去看呗!”马三炮探头瞅着棺材里面,心不在焉地道。
“罢了罢了!”老道士的神情顿时萎靡起来,“想死的就去看吧!想要命,就离得远一些!”
说完,他又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回身拽着正要上前的马三炮道,“你刚才不是说如果真是死人,就把棺材送回去吗?现在就送!赶快送!你可能还会有活路!”
“嘿嘿,对不起,本人有任务在身,不能耽搁。”马三炮打掉了老道士的手,说道,“我那也是迫不得已,例行检查。顶多一会儿再帮忙把盖子合上,就麻烦您老回去把家属叫来继续吧!”
“你……你……无可救药!”老道士被耍,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又拉着那位文官走到我爷爷跟前,凝重地说道:“二位老总,看你们还算正直,老道士我就多说一句废话,你们千万不要靠近那口棺材!否则性命不保!至于你们那些手下,能不能活着,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告辞!”说完,两手一拱,挥袖而去。爷爷他们两人愣在当地,等回过身来想要找老道士问个清楚,早已没了他的踪影。
再看棺材那里,马三炮早已从里面“淘”了不少好东西,有各种纯金打造,镶着宝石的头饰,还有金戒指、玉镯子、金项链什么的。看样子里面的死者是个女性。
其他士兵见他真捞着了宝贝,连忙一哄而上,生怕落后了什么也抢不着。
但好东西都让马三炮占了先,此时这家伙正一脸坏笑地抱着东西朝我爷爷他俩走来。“我说两位长官,”马三炮得着了值钱货,心情大好,乐呵呵地道,“您二位也别和我这小人置气,这么多东西,你们喜欢哪个,只管拿!咱有钱大家分,我老马绝对不是抠门的人!”说完,他把一捧珠宝送到了我爷爷他们面前。
爷爷还没来得及说话,另一名文官就低吼道:“马三炮,你明抢人家的殉葬之物,这和盗墓有何区别?!你就不怕遭天谴吗?!”他们俩都是读过书的人,对不义之财自然不屑。
“二位爷,别说笑了!”马三炮见爷爷他们没有伸手来拿的意思,一边快速把手缩回去,一边继续懒洋洋地道,“都这年头了,兵荒马乱的,活人都快饿死了,您还管这个?再说是他们送葬的自己跑了,我们不要白不要啊!前两年,那个孙大麻子,不是把慈禧老佛爷的坟也扒了?咱们这算多大的事儿啊?!”
别看这家伙从小没念过一天书,一番话下来,倒是把两个读过书的文官给呛得说不出话来。
“马三炮,”我爷爷思量了好久,终于开口道,“你别忘了那个老道士最后的话,这个队伍,这口棺材,包括这个时间出殡,都是非常不吉利的。你有命拿,倒是有命花才行啊!”
“哈哈!”马三炮仰天打了个哈哈,接道,“长官,咱们是当兵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还怕这个啊?!实话跟您说了,我当兵前,干的就是这个买卖!我老马今天敢拿,就不怕那女人明天来要债!”
另一个文官还想说什么,我爷爷赶忙拉住他道:“行,该说的我们都说了,怎么做,看你们。我只要求一点,最后给人家收拾干净。三分钟后所有人上车集合!”
“得嘞!这事儿交给我您就放心吧!”马三跑一听上头终于松口了,把东西往怀里胡乱一塞,就又冲了回去,嘴里还喊着,“你们这帮兔孙!下手给我轻点,别惊了人家大姑娘的魂儿!”
本来,鉴于马三炮今晚所做的事情,我爷爷他们完全可以以违抗军令、扰民和盗墓数罪并罚,当场枪毙了他。但这家伙一早就打好了算盘,绝不吃独食,而且还发动其他士兵,就连那棺材里的值钱物件,他都故意留下来不少,为的就是让其他人也拿,好给自己打掩护,分担罪责。
如果真要枪毙他,不但其他士兵人心惶惶,搞不好还会兵变。这个重责,可是谁都承受不起的。最后他们俩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求这次押运任务顺利完成就好。
棺材里就那么大个地方,什么能拿,一眼就看见了,那些当兵的没半分钟就哄抢了个干干净净,除了尸首的衣服外,头饰耳环戒指,一个不剩都被他们扒了下来。
快五分钟的时候,所有人才慢悠悠地走回来,在火车旁列队站好,等待长官整顿。
“报数!”我爷爷见来的差不多了,站起来喊道。
“一!……二!……三……四!……三十四,缺一!”当最后一个人报完,爷爷这才发现还少了一个,他没怎么想,搭眼一看,就知道是马三炮不在。
“马三炮呢?!”同僚也一眼看了出来,紧跟着问道。
“嘿嘿呵呵……”士兵们一听两位长官问话,没人回答,反倒都猥琐地笑了起来。
“来啦来啦!”爷爷他俩还没搞清楚什么情况,就顺着马三炮的声音看见这家伙提着裤子,从棺材那边跑了过来。
“你干什么呢?!”我爷爷心里咯噔一下,厉声问他道。
“这家伙的那根东西又不听主子话了呗!”马三炮没张口,倒是离他最近的一名士兵抢着说道。说完,下面一片哄堂大笑。
马三炮不仅不觉得丢人,扎好腰带后,还自豪地挺了挺腰,照着那个“打小报告”的人脑袋上就是一巴掌,但谁都看得出来,纯粹是象征性地打着玩。
“就你个龟孙长舌头了不是?!”虽然骂骂咧咧,但这家伙一脸满足的笑意。
“马三炮!看上人家了,就扛回去当婆娘呗!多好啊!不吃你的不花你的,什么时候想了,脱裤子就行!”队伍另一头不知道是谁喊道,又是引来一片更大的笑声。
“行啊!”马三炮一听,正色道,“放几天,我就给你扛去吧?!”
笑声再次高了一个调。
“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另一个文官实在忍不住了,手按在枪匣子上就要冲过去,我爷爷赶忙拉住他,低声道:“别冲动,这些兵都得了他的好处,现在不是办他的时候,等任务完成,回去向营长汇报,张营长一向注重军纪,一定会严办他的!”
“哼!人在做,天在看!就让这个狗×的再多活两天!”另一个文官喘了几口粗气,总算放弃了把马三炮“就地正法”的念头。
又喧闹了好一会儿,列车终于再次启动。整辆车内都在谈论着今晚的“收获”和马三炮的“销魂时刻”,唯独我爷爷他们俩,坐在最中间的闷罐车里,默默无言。
对于他们这些读书人来说,挖坟掘墓的行径,那是天理不容的事情,简直就不应该是人做的。但又一想,孙殿英几年前就这么干了,到现在,人家是冀北保安司令。不但活着,而且越活越好。
反正这个年代,人都是被逼疯的,普通老百姓为了不饿死,甚至可以“易子而食”。这些当兵的为财,那更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爷爷反复想着那老道士的最后几句话,觉得马三炮一定会遭天谴,但也不排除老道士唬人的可能。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半夜,爷爷被一阵哗啦啦的声音吵醒,往外面一看,竟然下雨了,而且是瓢泼大雨。
此时已经是十一月中旬了,按理说雨季早已过去,下得这么大,也的确罕见。爷爷正奇怪间,却隐约听见睡在他对面的另一名文官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下车……往前走……活命……”
“你说什么?”爷爷没听清,一边问一边凑过去。
“要活命……下车……往前走……”晚上漆黑一片,货车车厢里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直到爷爷来到了同僚的面前,才发现他依然睡着,双眼紧闭,嘴唇倒是不停动着。
原来是在说梦话!
“嘿!醒醒!”半夜说这种话是有些瘆得慌,何况又有先前的事情,爷爷不想听,只管摇醒他那个同僚。
“啊?……怎么了?”摇了两下,那人就醒了,揉着眼睛问道。
“你做的什么梦?怎么说这种话?”反正是醒了,爷爷只管问道。
“我……没做什么梦啊!”同僚想了想,回道。
“下雨啦?哎?车怎么又停了?”同僚一醒,就看到了外面的情况,爷爷本来还想问,却被他这么一打岔,给遮了过去。
扭头一瞧,的确,刚才光顾着看下雨听梦话了,没发现火车又停了。而且仔细听去,附近还有哗啦啦的水声。
这个年代,而且又是这种天气,按理说火车非但不能停,还要加速前进,因为此时情况复杂,如果有人有心偷袭,正是最好的下手时机。
想到此处,他们俩瞬间背心都凉了,难道车头已经被“占领”了?
要想知道怎么回事,只有过去看看,列车一共六节车厢,士兵被平均分在了每节,况且这么大的雨,面对面说话也只能勉强听得见,叫人去看显然不现实。如果真出了事,爷爷早就想好了,宁可被俘虏,也不能空着手回去,那是要枪毙的。
同僚自然也是一样的心思,两个人没敢犹豫,在车厢一角找到两件简陋的蓑衣,披上后掏出手枪,就下车往车头的方向走去。
出来才发现,火车前半截停在了一座桥上,下面是一条不知名的河,倒也不宽,但因为大雨,河水上涨,眼看就快要淹没桥面了。
那年头的桥简陋得很,除了铁轨,根本就过不了人,前面的车厢又锁死了,爷爷他们没办法,只得爬上去,从车顶过桥。
他们俩穿的皮鞋,在车厢与车厢之间需要跳过去,雨天也湿滑,在桥中间,爷爷的同僚跳过去没站稳,脚下一滑,眼看就要跌入河中,多亏爷爷先过来了,眼疾手快,赶忙一把拽住,这才没要了他的命。
过了桥又跳下来,往前走了没几步,大雨中勉勉强强看到前方车头里微弱的光。顺着光又走了一段,这才瞅见车外面站着两个人。
爷爷心叫不好,赶忙贴着外面的山崖往前慢慢挪,直到很近了,才发现原来是火车司机和锅炉工,正大声交谈着。
“什么情况?”爷爷待看清后,放下心来,收起枪,走上前问道。
“哦,老总!”司机回过头来看到是“仅有”的两位长官,赶忙指着前面说道,“雨太大了,把山冲垮啦!过不去啦!”由于雨实在太大,司机在外面和他说话,都是用喊的。
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爷爷他们这才发现,前方几十米处,在车头灯光的照射下,铁轨直接被各种大石和泥土埋住了,显然是从旁边山上掉下来的。
“有紧急处理办法没有?”爷爷的同僚大声问道。
“那也得等雨停了啊老总!”司机愁眉苦脸道,“天亮了派人沿铁轨出去送信,叫人来帮忙清理才行啊!现在想走,不可能的!”
“咱们自己清理呢?”爷爷问道。
“您看那石头,”司机又抬起手指着前面道,“都是上千斤的,咱们这么些人也没工具啊!再说,雨再这么下,随时都有再冲垮的可能,太危险啦!”
“那你说怎么办?!”爷爷没想到第一次出来执行任务,就遇到这么个麻烦,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一时没了主意。
司机想了片刻,答道:“现在肯定是不能走了!非要等到雨停或者天明才行啊!我往后倒倒吧,停在桥上也不安全啊!”
“那……行吧!就按你说的,抓紧时间!”爷爷眼看没别的办法,也只能先这么着了。
司机得了命令,刚扒着扶手要上车,后面却突然传来一阵隆隆声,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见整辆火车向外侧慢慢歪去。
“不好!桥垮啦!快叫人下车!”爷爷立时反应过来,一定是桥被河冲垮了,桥上的两节车厢脱轨后在拉扯其余的车厢。如果不赶紧把人都叫出来,搞不好整辆列车都有被冲下去的可能。
但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瞬间,爷爷的话刚喊出来,车头就已经被拽倒了,刚好外面又是一段比较陡峭的山坡,整列火车滚下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车头里还有一名副司机,几个人忙手忙脚把他拽了出来,爷爷正准备去后面喊人,却被司机拽住了喊道:“老总,别过去!你听山上的声音,马上就要垮啦!咱们先顾自己吧!”说完,硬扯着爷爷他们俩跑到了之前那段滑坡的地方,找了块最大的石头往上爬。
这块石头,据爷爷说直径约有三米多,呈扁平型,他们几个人刚爬上去,只听见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从上面的山坡上传来。还没来得及害怕,车头那束强烈的灯光瞬间就被掩埋了。泥石流夹着整列火车,汹涌地朝山下冲去。要说真是他们几个命大,泥石流刚好就被这块巨石割开了。饶是如此,站在石头上的他们也感觉到不停地晃动,并且逐渐朝山坡的边缘滑动。
在这漆黑的雨夜,没人敢动。山坡虽不算深,也不陡,但他们脚下随时有再次塌方的可能,到时候就算摔不死,也要被这些巨石压死。
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连一分钟也没有,但爷爷他们却觉得有一辈子那么长。这种命悬一线、生死不由己的感觉,的确让人崩溃。渐渐地,轰隆声停了下来,雨似乎也越来越小。火车司机打开腰间的手电,几个人顿时惊呆了,只见面前到处都是泥土和石块,原来的铁轨、树木,全都没了踪影,包括那辆列车。
“报应啊……报应啊!”爷爷的同僚目瞪口呆地瞧着这一切,嘴里念念有词。
“这……这也太邪乎了……”想起刚才同僚在车上的梦话,连爷爷也怀疑,难道真是报应?一车当兵的,无一生还,除了他们俩没有动那些殉葬品,只剩身边这三个火车工,因为停车的时候他们在车头检修,自然也没空去理会那个。
好在没过多久雨就停了,天也蒙蒙发亮,放眼望去,原先几十米深的沟,被填的只剩下十几米,哪里还有火车的影子,到处都是淤泥和石块,还有被冲倒的树木。那些在车里睡觉的大头兵,自然也都没得活了。
爷爷他们沿着铁路线走了大半天,总算来到一个小站,联系到上峰,汇报完情况后,他们俩也就返回了部队。
虽然是天灾,但上面生气起来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可那个年头找口饭吃很不容易,特别是在部队里当文官,算得上是一件美差了。爷爷他们也不忍心放弃这么好的一份工作,只能硬着头皮回驻地报到。
好在上面并不是很责怪他们,但不仅无功还损失惨重,为以儆效尤,每人还是挨了二十军棍,抬回营房养伤。
随即,从上去抢修铁路线回来人口中得到的消息是,那天晚上,除了他们那个方圆六里的小山沟,整个豫北和山东,都滴雨未下。这让爷爷他们俩更认为是动了那口棺材才招惹来的灾祸。除了他们五人,所有拿了东西的大兵都丢了性命,那老道士临走时所说的话,竟然全部应验了!
同僚却始终觉得,这样反而便宜了那个马三炮,一死不足以赎回他的罪过。
只有那天晚上同僚的梦话,被爷爷深藏在了自己的肚子里。因为这毕竟太不可思议了,如果不是这句梦话,很可能连他们俩都要留在那个小山沟里。
本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但让所有人都不可思议的是,就在爷爷他们回来后第三天,挨过军棍的屁股刚好一点,能下地了,那个当时带头起哄,带头开棺,带头哄抢陪葬品,甚至侮辱死者的人——马三炮,居然奇迹般地也回来了!本以为老天有眼,谁知道竟把这个最该死的给放了回来。
马三炮不是空手回来的,他还背着一个大箱子,里面装的是那列火车上最贵的一箱药品——阿司匹林。
这下可有意思了,因为爷爷他俩以为所有人都死了,所以并没有汇报当晚扒棺哄抢的事情。如今,马三炮带着最值钱的货物回来,不但不用受罚,而且还被长官全营通报嘉奖,外加两个月的军饷。
看似这家伙命大,但又有些不同,回来后的马三炮变得少言寡语,始终面无表情。他这种人本应该在什么时候都是最活跃的,可就连发大洋的时候,脸上的那抹笑意看起来也勉强得很。
同僚自然不会理他,爷爷找了个机会,问马三炮究竟是怎么逃出来的。他却用那一双冷冰冰的眼看着爷爷,始终不开口。
不说就不说吧——维护军纪的被罚,带头起哄的反而被褒奖,纵然爷爷比他同僚脾气好,看到这种结局,也是一百二十个不愿意。
这次事情总该结束了吧?不,依然没有!俗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在爷爷他们回来后的第五天,也是马三炮回来后的第二天,军营里发生了件耸人听闻的事情。
由于马三炮他们排,除过他已经“全军覆没”,这家伙被分在了另外一个排里,而且升官了,当上了那个排的副排长。
可就在他回来后的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全营早上就被一声撕心裂肺的吼叫给惊醒了。
爷爷自然也被吓醒,起初他们以为是“营啸”。可听了半天,发现只是一个人在喊,也就放下心来。
要知道军队里最害怕的就是“营啸”。当兵的都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经年累月下来精神上的压抑可想而知。另外一方面传统军队中非常黑暗,军官肆意欺压士兵,老兵结伙欺压新兵,军人中拉帮结派明争暗斗,矛盾年复一年积压下来。尤其是大战之前,人人生死未卜,不知自己什么时候一命归西,这时候的精神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在这时候,往往可能只是一个士兵晚上做噩梦的尖叫,就会造成大家都被感染上这种歇斯底里的疯狂气氛,彻底摆脱军纪的束缚疯狂发泄一通。一些头脑清楚的家伙开始抄起家伙来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由于士兵中好多都是靠同乡关系拉帮结派,于是开始混战。这时候那些平时欺压士兵的军官都成了头号目标,混乱中每个人都在算自己的账,该还债的跑不了。中国古代军队就曾多次发生这样的夜惊,也就是“营啸”。
也有迷信的人说,这是由于军队常年征战,阴气渐渐大于阳气,才会招致阴魂寻仇,故而产生“营啸”。
不管怎么说,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后果是非常可怕的,军队的制度纪律会在瞬间毁于一旦,造成重大的人员和经济损失。人们被惊醒后,都想知道究竟是从哪里发出的,于是纷纷披上衣服走出营房。爷爷一出来就看到,声音应该是来自一排,也就是马三炮才分到的那个营房,因为此时他们排的人都光着膀子,站在外面朝屋里看,但却没人敢进去,显然是刚跑出来。
此时惨叫声已经止住,营长也披着衣服走了过来,还一边骂骂咧咧地:“狗×的!不好好睡觉,半夜吓老子,不想混了?!”
“一排长!怎么回事!你们屋谁他妈卵子痒了?”营长来到营房外,吼道。
“到!报……报告营长!”光着膀子的一排长打着哆嗦道,“是……是马三炮,我们……我们屋里有个死人!”
“狗×的!”营长象征性地踹了他一脚,骂道,“当兵的还怕死人?死了抬出来啊!马三炮死了?”
“不……不是,是马三炮叫的!”一排长说着扒开看热闹的人道,“别他×的看了!都滚回自己屋去!”这才让出一扇窗户,回头瞅着营长,意思是我也说不清楚,您自己看好了。
“狗×的!”营长愣了一下,这才迈开大方步,来到窗口,朝里面看去。由于门口人围得多,爷爷他们文官又在军营一角,并没有凑到最前面,自然也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营长看了半天,抬手挠了挠头,问身边的一排长道:“这是怎么个情况?马三炮招妓?把妓女都带了回来,你个狗×的干什么吃的?这都不管?!”
“不……不是的,营长!”一排长不知道从哪捞来一件外套,穿上道,“昨晚我们睡觉的时候好好的,这个女人什么时候进来的,我也不知道,而且她像是个死的!您看她穿的衣服,还有那脸色,脚也绑着,这分明是一身丧装啊!”
爷爷刚听到这里,就被他那个同僚拽着往前凑去,很快俩人就来到了另一个窗户口,往里面那么搭眼一看,顿时倒抽一口凉气。
只见并排能躺二十来人的大炕上,只剩下中间的马三炮,和一个浑身上下衣饰华丽的女人并排躺着。
此时的马三炮浑身哆嗦,满头大汗,双眼直视屋顶,一眼都不敢看别的地方。倒是他身旁的那个女人,睁着双眼,模样倒还不错,但却是一脸的死灰色。
她穿戴整齐,一身大红色的丝绸衣服,上面绣着各种花鸟鱼虫,艳丽至极,明显一个清朝大家闺秀的样子。
但现在已经是民国二十多年了,这个样子打扮的,多是大户人家入葬的时候才穿。
虽然并不认得这个女人,爷爷他俩却一猜就知道,一定是那晚棺材里躺着的人,因为此时马三炮的胸前,摆着那晚他从棺材里拾来的“宝贝”。
这些东西,两天前他回来时,爷爷并没有见过。
“愣什么愣?去几个人,给老子抬出来啊!”营长一句话,把爷爷他们俩从思考中拽了回来。
虽然当兵的都不怕死人,但这么平白无故地多出来一个,也都瘆得慌,营长一句话喊出来好半天,愣是没人敢进去。
营长本来正睡得香,让吓了一跳,这会儿又使唤不动人,自然怒了,掏出手枪,拉开枪栓,指着一排长道:“一排长!给老子进去抬人!我数十个数,里面那两个家伙弄不出来,就当场崩了你!”
“是!”一排长见这架势,知道逃不过去了,把披着的外套一扔,冲身边的手下喊道,“胆小的就在这儿待着,胆大的跟我去抬人!凡是进去的,以后都是我的亲兄弟!有我命,就有你命在!”
要说这一排长也是个人物,一句话,他们排立刻冲进去一大半,毕竟是顶头上司,肯说出来这样的话,就说明以后打仗会照顾自己,不至于派去当炮灰。比起以后铁定会死,和现在可能会死,大兵们还是算得过来账的。
半分钟不到,十几个人就七手八脚地将屋里一活一死两个人抬了出来,放在营房外的空地上。
全营的人顿时哗啦啦都围了上来。
“怎么回事儿?”营长见马三炮这时坐在地上喘着粗气,似乎好了那么一点,瞪着他问道。
“……”这家伙不知道是吓住了还是和爷爷问他的时候一样,双眼死死盯着营长,就是不说。
营长眼见从他那里问不出来什么,也没撤,毕竟昨儿个才嘉奖过,今天就处罚,有点自己扇自己脸的意思。转头看见了我爷爷他们俩,带着一脸疑问,明显是问——这家伙之前发生过什么事儿吗?
爷爷迈前一步,正打算汇报那晚的事情,不想后腰却被那个同僚掐了一把,愣是将到嘴边的话给咽了回去。
“有屁就放!”营长见爷爷明显有话要说,不耐烦地催道。
“报告!”爷爷先敬了个军礼,脑子一转说道,“这马三炮在前几天的任务中一切正常,他回来后我也曾经问过他怎么逃生的,这家伙就是不说,我也没办法!”
“说跟没说一个样!”营长把这句话过了一下脑子,就又冲一排长道,“先把这女的抬到后山坡上埋了!这马三炮,等他好点了再说!”说完,就转身回去接着睡觉了。
眼看没什么新鲜了,围着的士兵也都渐渐散开,各回各的营房去了,毕竟天刚亮,还能睡个把时辰。
没经历过那晚事情的人,自然不会觉得有多诡异,但我爷爷他们俩可不一样,于是两人找了个偏僻的地方,不等同僚说话,爷爷就开口问道:“我刚才要汇报,你怎么不让我说啊?”
“看到了吧?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同僚先是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接着道,“你也不先想想,那晚的事情说出来,谁会信?再者说,当时不汇报,现在汇报,让上峰怎么看你这个人?更何况,你也见了,那个女尸摆明了是要来寻马三炮的,你如果说出来坏了她的事,谁敢保证她不会把你也扯进去?要我说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马三炮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早就该死了。当初他侮辱那具女尸的时候,哪怕多一点点善心,也不会落得这么个下场!现世报啊!”
听同僚这么一说,爷爷顿时也是一背汗,没人信,上面怪罪,他都不怕,怕就怕真是坏了那女尸的“好事”,再来缠他,可就要了亲命了!
当下两人决定将这件事烂在肚子里,不再告诉任何人,反正现在这世上除了他们俩,只剩马三炮一个人知道,其他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那三个开火车的并不知晓这件事。
至于马三炮,干出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自己也绝对不会说。如果一旦说出,在别的地方也就罢了,在部队里,是要吃枪子儿的。但是,还有一点,两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这死人真的会诈尸?半夜跑来和马三炮睡在一起?
其实想要知道怎么回事儿并不难,看马三炮的样子,就知道前几天肯定也是这样,不然那家伙也不会天天像丢了魂儿似的。所以,只要今晚看着他,什么情况就一清二楚了。
虽然好奇,但毕竟有可能关系到性命,爷爷他俩也是心理斗争了好久,到底要不要一探究竟?
最后还是同僚给了个意见:这件事如果搞不清楚,会在心里憋一辈子,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准备充分点,今天白天准备点辟邪的东西,晚上呢,俩人就在自己的营房里,拿着望远镜看,反正不出去,不靠近,要求不高,只要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行。
主意已定,两人也不睡了,分头行动,同僚上街去买回来只黑狗,中午宰了两人把肉一吃,血留着晚上使,顺带再看看能不能寻摸几个法器、道符什么的,以备急用,而爷爷则负责去借两个望远镜来。
整个白天,两人都没再见到马三炮,据说他躲在营房里死活不出来,营长也有意不去管他,但听一排的人说,这家伙嘴里好像一直念叨着“甩不掉了,逃不掉了”之类的话。
想必是这家伙以为回到军营就不怕了,谁知道那女尸竟明目张胆地跟了过来。直到下午五点多,全营正吃晚饭的时候,一排那里突然又热闹起来,原来马三炮不知道从哪里摸来一把刺刀,趁别人吃饭的时候照着自己肚子上就是一下,好在身边的人眼疾手快,丢下饭碗将他按住,这才捡回一条命。
但那刺刀多锋利?不死也是重伤,得亏营里都配有军医,给他打了一针镇定的药,再把伤口缝合,简单消消毒就给抬回了一排。
营长知道事情后,反应也快,爷爷那个同僚刚好是负责发放军饷的,被叫去半天后回来说道:“马三炮这样子,营长说不能让他当兵了,给他结算结算,一等能下床,就打发他回老家去好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越发匪夷所思,本来两人准备好了夜里看热闹,竟然又跑出来这么一出,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的看,不过反正东西都准备齐了,有没有就只管瞧瞧呗。要是明天一早马三炮就死了,或者过几天伤好回家,这件事非得让他俩一辈子什么时候想起来就抓心挠肝的。
入夜后,爷爷他俩把黑狗血、道符什么的都在窗台上准备妥当,就熄了灯。当官的好就好在,两人一间,想干什么也没人知道,不像那些大头兵,一个长条炕上就能睡一二十人。
营地里夜间有人执勤,况且他们这里还有不少军用物资,探照灯什么的灯火通明,所以想要观察马三炮,倒也轻松。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爷爷他俩也不是干等,两人就着中午的狗肉,再加上之前藏了些白酒,一边等一边有吃有喝,倒也不枯燥。
可眼瞅着过了午夜,一排那里除了几个肾不好的老兵出来撒尿外,半个晚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更别说僵尸了。
时间越等越久,酒也越喝越多,又过了至少一个时辰,两个人酒意上涌,就快要挺不住了,爷爷正准备就此打住,倒头睡觉,拿着望远镜的同僚却突然压低声音喊道:“快看快看!你看是谁?!”……难道女鬼真来了?!
刚躺下的爷爷一翻身坐起来,抓到另一个望远镜,朝一排门口望去,果然吃了一个大惊!
女鬼没来,但却有一个人,悄悄推门从屋内走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肚子上还裹着纱布的马三炮!
“哎我说!真是见鬼了啊!”爷爷的同僚一边看着望远镜,一边低声道,“我饭后专门问了医生,他这个样子是下不了床的!”
“尿急呗!”爷爷也是目不转睛,瞧着外面的那个人。
“但他用了镇定的药啊!大夫说这家伙就算醒,最早也到明天中午了!”同僚说出了另一个理由。
“人和人的体质不一样!”爷爷知道虽然有些牵强,但的确没有更好的理由了。
“恐怕不是!”同僚撇着嘴道,“你看他手里拿的什么?”
爷爷循着人影看去,只见马三炮虽然走得慢,但手中却拿着一样东西,细长把,下面有个巴掌大的尖头形状,分明是一把铁锹。
他拿铁锹干什么?居然还是在重伤的情况下。
眼看这家伙就要走出视线,爷爷的同僚突然扔下望远镜,把窗台上的辟邪物往外套里一揽,就从炕上跳下来去穿鞋。
“你干什么?”爷爷虽然早就猜出了他的意图,但还是顺口问了一句。
“走呗!看看去,你不想知道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同僚一边穿鞋一边道,“我告诉你,马三炮以前干的是挖坟掘墓的勾当,他那些不义之财可比咱俩的辛苦钱多了去了!如果这家伙是去埋东西的地方,咱们改天有空趁他不备顺出来点儿,不过分吧?就算劫富济贫了!”
爷爷没再说什么,这点确实击中了他。反正那家伙的东西都是偷来的,如果真能顺来几件,自己就可以回家买上两亩地,娶个媳妇儿,不用再在这乱世里过什么有了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了。
虽然跟着同僚出来,但有一点爷爷想不通,马三炮如果这么有钱,为什么还要当兵?
之后过了许多年,他才渐渐明白,这家伙挖坟掘墓,该得罪的都得罪了,所以收手后故意来当上几年兵。一方面是在军队里,那些被他挖了祖坟的人不敢寻仇,更重要的是军队人多气旺,将身上的阴秽气给洗一洗。
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看来这次就算人再多,也救不了他!
爷爷他们俩就这么偷偷摸摸地出了营房,一路躲着岗哨,同时跟着马三炮来到了军营的紧后头。
这里就一幢大房子,住的是营长和参谋们。由于比较靠里,相对安全,所以只有楼前面的一个岗哨。
绕过岗哨,爷爷他们就看到马三炮攀着围墙,跳到了军营后的山坡上。
既然跟到这里,再说放弃的确有些可惜,两人也赶忙七手八脚地翻过墙。为了不被发现,两人不敢开手电,在黑暗的山坡上睁大眼看了好久,直到适应了黑暗,才隐约瞧见前方不远处有个人影在移动,于是再次跟上。
山坡并不高,走没多久,就看到黑影停了下来,随即响起了嚓嚓的掘土声。
“嘿嘿,真没想到这家伙把东西竟都藏在了这儿!”同僚眼瞅着快要宝贝到手,兴奋地低声说道。
爷爷可没有那么乐观,因为他清楚地记得,早上一排长他们就是把那个女人的尸体埋在了这一片,当时在山下的营地里看得很清楚。
但是,马三炮要真是夜里来掘尸,那他早上完全没有害怕的必要啊。
掘土的声音持续了没一会儿就停止了,但爷爷他俩已经离得很近,不敢再上前看个明白,只有等着。
约摸过了有十几分钟,期间偶尔能听见马三炮粗重的喘息声。直到再次有了动静,他们俩慌忙向后退了些,就只见黑影已经折回来,向山下走去。
但这次的人影有些不大一样,马三炮的肩上似乎还扛了一个什么东西。
等人影下了山,同僚赶忙冲到刚才挖掘的地方,双手在泥土里乱刨一气。
“妈的!什么都没有!这家伙都带走了!”在确定什么也没发现后,同僚丧气地蹲在一旁。
爷爷脑子里反复在想早上的情形,包括这深夜里马三炮重伤后的一系列古怪动作,他本就不相信这里埋了什么值钱货,再说了,部队是经常换防的,马三炮总不可能走到哪儿,就把自己的宝贝跟着埋在哪儿。他一定是会找一个安全的所在,等到一切风平浪静了,再说往外挖的事情。
而此时,马三炮上来的目的很可能只有一个——就是挖那具女尸!
爷爷在泥土里摸索了一圈,很快就发现有一小截布料落在里面,虽然看不清是什么纹样,但手感质地是丝绸无疑。
……军营里哪来的丝绸?答案是没有!只有那个女尸的身上才有这个料子。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是刚才马三炮掘尸的时候,铁锹不小心割掉的。所以……他真的是在挖那具女尸!想到此处,爷爷顿时不寒而栗,赶忙把推测告诉了同僚。
“不……不会吧!这也……太……太邪门了吧!”同僚听后,嘴巴都不利索了。
“邪不邪门,早上就清楚了。这个地方咱们还是少待为妙!”爷爷往更深了想,马三炮既然害怕,很有可能刚才的人并不是他,或者说并不是他的意识。更何况受了这么严重刺伤的人,还用了镇静剂,连大夫都说最早明天午后才醒,他居然晚上就能上山,还干这么重的活,完全不符合常理。
此时两人早就被冷汗塌湿了衣服,哪还敢再找什么“财宝”,连滚带爬地回了营房。
半夜无话,也没人敢睡。好不容易睁着眼熬到天亮,意料之中的“营啸”果然再次发生了。这次不是马三炮一个人在叫,而是真的几十人在嘶吼。
好在前日已经发生过一次,人们多少没有那么意外,反而都穿戴暖和了,方才走出营房去瞧瞧又是怎么回事儿?
爷爷他们俩是最后出去的,因为原因已经猜到了,肯定是那具女尸又一次“莫名其妙”地“钻”进了营房,睡到了马三炮的身边。
果不其然,没多久,一排长又带着人将一男一女抬了出来。女的就不表了,倒是马三炮,整个腹部的绷带全被鲜血染红,这显然是他夜里“重体力劳动”所带来的结果——缝合的伤口都绷开了。这家伙此时也醒了,但是双眼无神,气若游丝,估计是被同舍的人给吓醒的。
营长看着眼前的景象,挠头不已。
“杀……杀了我吧……我……我不想活了。”马三炮第一次开口说话,竟然是这么一句,顿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究竟怎么回事?!”营长皱眉不已。
“……”马三炮依然守口如瓶,就是不说。
“再不说老子崩了你!”营长终于憋不住了,掏出手枪,顶在马三炮的脑门上,威胁道。
可是这家伙非但不怕,反而露出了一抹解脱般的笑意,就那么温柔地盯着营长,等他开枪。
营长自然不会开枪,虽然这年头枪毙个大头兵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可他又没犯错,就这么随便杀了,人心何向?
两人僵持了一会儿,营长只得收起枪:“奶奶个熊的!你个龟孙王八蛋伤好了就给老子滚!此处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神!”说完,转身又对一排长道,“一排长,架火,把这女人烧了!”
“是!”
“长官且慢!”说话的是营长参谋。
“怎么?”营长转过脸,一脸疑惑地道。
参谋清了清嗓子,道:“现在显然是这女尸在作祟,下属以为,咱们还是小心处置为妙。”
“满嘴放炮!”爷爷的同僚听了,忍不住低声咒骂。因为到底是谁搞得,他俩清楚得很。
“怎么个小心?”这种事营长自然也是头一次碰上,只能听参谋的。
“……”只见参谋趴在营长的耳边低声说了半晌。完后营长又想了想,说道:“好吧,依你!这事儿交给你去办!尸体先不烧,摆在军营正中间的空地上!”
“是!”一排长应了后,又指着地上的马三炮问道,“营座……那这家伙……”
“军医那里有个单间,先让他住那,一等能下地,就让这家伙滚蛋!”营长也怕这时候将马三炮赶出去,镇上的民众看了影响不好,甚至以后会招不到兵。
一早上无事,女尸被摆在军营中间,也是妙招,本来那些大头兵挺怕的,可一上午走来走去,也没见它动过,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慌就慢慢消散了。
午饭过后,爷爷他们俩看天好,正在军舍外下象棋,却见营参谋领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