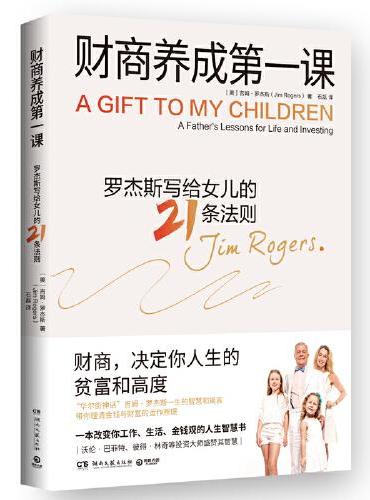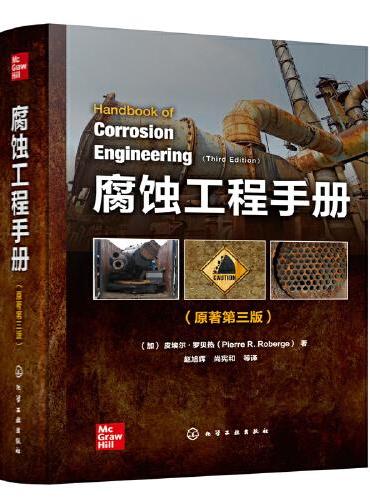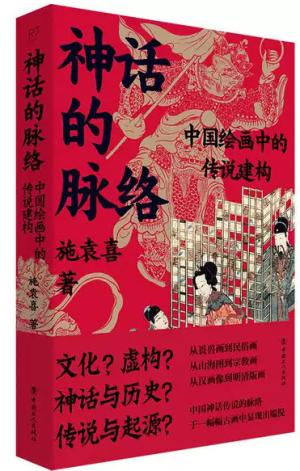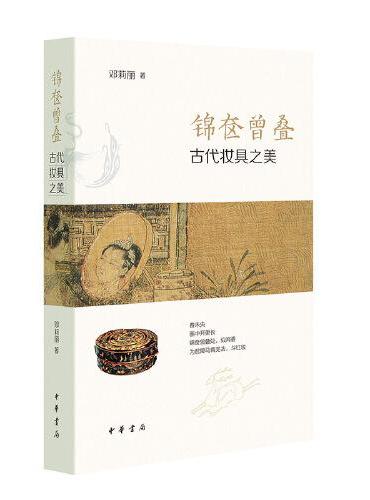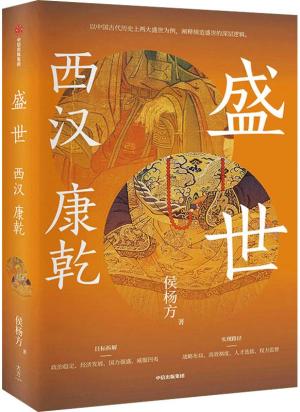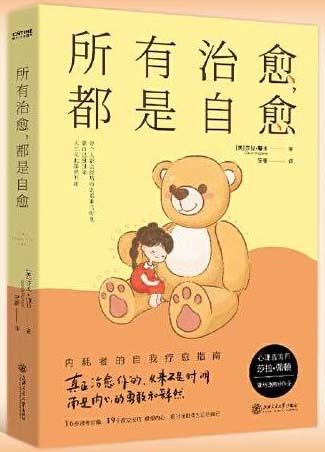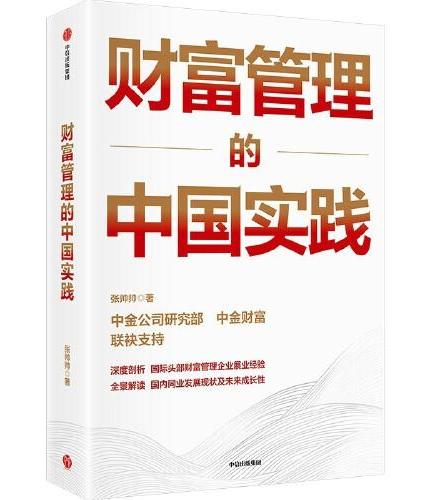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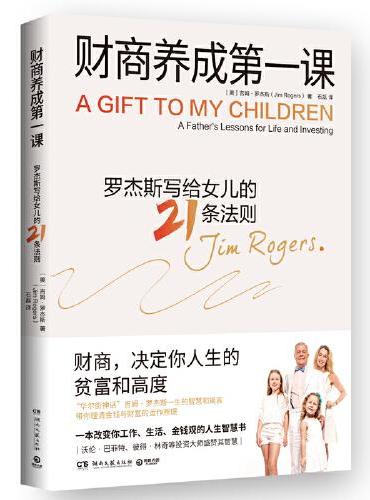
《
财商养成第一课
》
售價:NT$
3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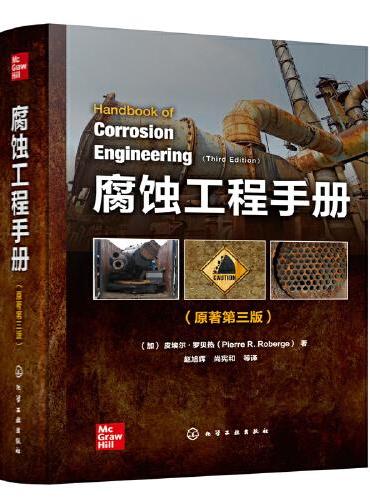
《
腐蚀工程手册(原著第三版)
》
售價:NT$
22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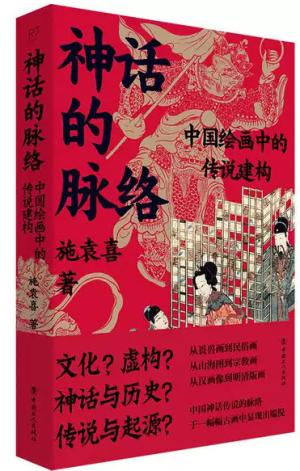
《
神话的脉络:中国绘画中的传说建构
》
售價:NT$
43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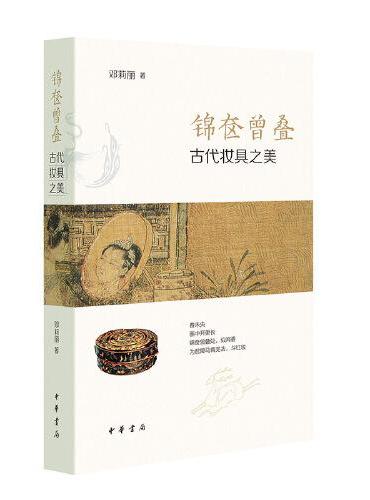
《
锦奁曾叠:古代妆具之美
》
售價:NT$
7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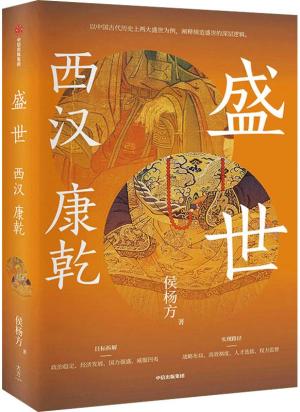
《
盛世:西汉 康乾
》
售價:NT$
54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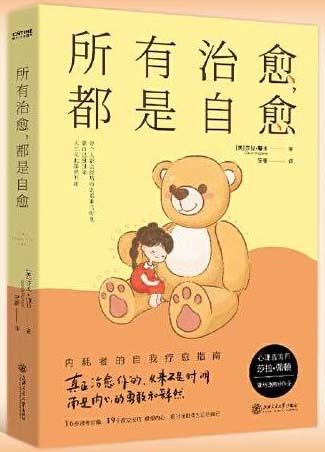
《
所有治愈,都是自愈
》
售價:NT$
38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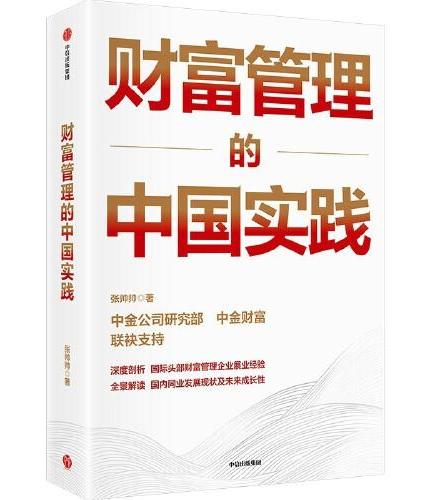
《
财富管理的中国实践
》
售價:NT$
717.0

《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附作者篇目索引)(全四册)精——中国古典文学总集
》
售價:NT$
2789.0
|
| 編輯推薦: |
《非人的诗学》分为两部分,用诗歌批评的方法,分别解构现代著名德国诗人保罗策兰(1920—1970)和著名法国诗人勒内夏尔(1907—1988)。
编辑推荐1.评论家认为,周理农的作品“那体味的切肤入里,思辨的伤筋动骨,低眉抽心而天地洞开”。
编辑推荐2.周理农的清醒和智慧,让他的文字显得深刻而隽永,读来非常精彩。
编辑推荐3.从荷尔德林以来的德国诗歌传统,最后在保罗策兰这里终结于一种罪责的不可命名性。在今天,尽管诗歌还在不断地写出,但在诗歌的内部,只是有着一个不再为任何东西所动的语言的废墟。在策兰的诗里,这个废墟仅仅作为一个艺术的证明而成为作品,或者说,一种言说的不可能性最后变成了身体的处境。一个无从引领的盲目的身体既是在最边缘的地方,但也是在诗歌的内部,终结了一个伟大的“诗人的时代”。
而在另一个诗歌传统中,法国诗人勒内夏尔通过迎接“一个朴素的早晨”的到来,抵御着一切主体必有的谵妄。在我们这个时代,主体并没有被取消,而是处在了一个谵妄的位置上。在这里,勒内夏尔的诗歌仍然是作为大地把我们的脚跟紧紧吸住的秘密、作为一团古老的火的谜题和格言,它表明我们人性真正得到修
|
| 內容簡介: |
《非人的诗学》分为两部分,用诗歌批评的方法,分别解构现代著名德国诗人保罗策兰(1920—1970)和著名法国诗人勒内夏尔(1907—1988)。
诗歌中主权话语的声音,从未受到世界的邀请,它也丝毫不欠人类,而这就是人类自我奠基的言论。缺少这样的言论,诗就只不过是一个还未打开的语言的皱折,或者说,它像一只未充气的气球,还处在一个不可观察的位置上。
诗歌终究表达出的是按照真实本身来生活的意愿,但我们只能让词语去过那种生活,是吧?诗歌作为一种被言说的生活,那就是词语的机会:“用一只从未露面的手,扑灭火灾,扶起/太阳,重建情人。无物宣告这一如此强悍的存在。”(《闪电的胜利》)
最终,这个世界到底能从诗人那里得到什么?——它要求诗人看到的世界因他的眼光而得救,这就是夏尔说诗人是一个“绝对的职业”的原因。如果在人类灾难之地旁边必有一个凯旋之地,那么在今天这个一切东西都遭到贬值的世界里,上帝、人与事物将会怎样显露出它们的“最后一手”?
|
| 關於作者: |
|
周理农,1963年出生于南京,现仍居此地。目前为自由撰稿人、社会理论工作者和诗歌批评实践者。著有《被诅咒的诗人》。
|
| 目錄:
|
第一部
保罗·策兰:“黑太阳”、灰烬句法或一种死亡写作001
上篇
一词性地质学的时代003
二隔着“话语之栅”004
三“暴动的忧伤”006
四一只轮辐攀向发生地的黑色田野008
五《山中会话》010
六诗人的立场就是世界的膝盖014
七词与物015
八诗人的生存作为世界的凶兆017
九“我与你”019
十出自一个动作的认识的发生021
十一作为艺术构件的自然023
十二在梦幻的沙盘上024
十三“签名”026
十四解构“绝技”029
十五诗歌主权的声音:节奏031
十六诱使真实出场的条件:意象033
十七障碍即是道路:晦涩034
十八他者性的深渊:碎片037
十九记忆、幽灵、踪迹040
二十纠缠042
下篇
二十一《子午圈》045
二十二语言的现场047
二十三“我没想到死亡毁了这么多的词”050
二十四当“看”变成一种假设053
二十五“荒原”中的材料:作为一种对实在的根本体验055
二十六朝着主体被拒绝的方向……057
二十七“我对记忆的热爱超过一切”060
二十八疯癫:与世界的恶意进行决绝之地062
二十九词语的灰065
三十“向死而在”068
三十一抒情就是作证072
三十二在不再谈论光明和黑暗之后077
三十三事物的悲剧状态080
三十四在一块差异之地上082
三十五当“语言自己在说话”时,这里有着一个不能识透的事物086
三十六在语言中的幸存088
三十七“不要放弃你的欲望!”091
三十八一个舍弃了自己内心的身体093
三十九“终结主体”与人们言论中的空白097
四十“夜越深,客人越美丽”101
第二部
勒内·夏尔:大地、辩证法与生者的知识105
上篇
一两个诗人107
二对拒绝本身的拒绝,对反叛本身的反叛108
三“用另一种方式起身的能力”111
四大地之上,世界到来114
五居住在自己回答中的诗人116
六人是存在最狂热的器官119
七“愤怒和神秘”121
八重说兰波126
九辩证法:一种在动物的盲魂里永远感到紧张的语言129
十在梦幻中,我们达到叙述的顶点133
十一潜意识导论137
十二再论潜意识140
十三荒诞:作为人的一种非庇护状态142
十四对“说”的体验145
十五格言与格言诗148
十六为什么要写诗?150
下篇
十七非理性:那一场大火,使我们的绝望感到了狼狈154
十八使一切东西贬值,这就是人类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157
十九诗歌:从缺乏造成的伤口中流溢出来的过剩161
二十在写作中,“我的劳动力在流亡”164
二十一一粒种子在田地里变得“无参照”了167
二十二这不是疑惑,而是苦闷169
二十三“老婆,你为什么脸色煞白?今晚有客人吗?”171
二十四人类孤独的另一种定义175
二十五为了不让相爱的人们扫兴,请历史走开178
二十六“躺着的岔路,忧郁之完美”181
二十七不可能性原则或“主体性的黄昏”185
二十八在大地上,“同一个东西的永恒回归”188
二十九引用即是相遇,相遇即是作品191
三十片断:“景观”,一个失去了大地性的大地195
三十一“当代”:一个表现为“当下之脱节”的东西200
三十二结论:这个世界到底能从诗人那里得到什么?204
后记:在一个言说的“黑太阳”下208
|
| 內容試閱:
|
一 词性地质学的时代
保罗·策兰是一个死亡诗人。他的诗作为锤子碎裂、客体号啕的死亡指证之地,这里也是对词性进行拷问的一片狼藉的现场。
在文明的裂口上,摸索着词义的缝合处,诗最终是燃成了灰烬的手指的残骸。
在策兰的诗中,死亡比什么都自信,但疼痛更纯粹,它一如石头,属于这个没有仁慈的世界的盲目的收获;在他的诗中,石头比什么都多,而需要被石头保护的东西,一如夜之惊悸中的盲魂,它断定自己的命运只是有欠于一次毁灭。
诗歌似乎就是这个世界的仁慈,它把一种不可剥夺的怜悯转变成了词性地质学时代里的某种生硬的谣曲,这就是现代诗歌的抽象抒情方式,在这里,语言直接作为本质的显现被拿出来晾晒,最后它的干燥和枯涩的风格,就像沙与沙的聚集,已经成为思的一种当代条件。
也许,并没有这样一个词性地质学的时代,对保罗·策兰来说,他只是按照诗歌本身的尺度,把石头变成了更加敏感的人性材料。一如在艺术中,材料作为对实在的根本体验,带来了一种强制性的思辨,那里有着一个难以识破的存在的敌意的幅度:“一个世界/疼痛的收获。”(《苍白声部》,孟明译)
在一个语言的损失需要沉默来补偿,从而使人类的理解力仍然显得完整的时代,这个文明留给诗人的余地,不是诗人被迫屈从着的沉默,而是他在自己手头的工作中感到了对人的无限怜悯,因而也就有了保罗·策兰所说的诗人不能去与黑暗会合的“光明之迫”。
在这种“光明之迫”中,当诗人“不能黑着脸走向你”,那么他就只能“黑着脸退回天堂”。
这就是说,由于遭到来自光明本身的压制,人们把任何一种斗争方式都看做是被黑暗侵染过的,因此人们采取行动的能力受到了削弱,而诗歌也就不可避免地变得萎缩了。
二 隔着“话语之栅”
现实与诗歌之间的对角线构成了压制住诗人的荒芜风景的二次音,正是在这里,策兰的诗一一检验了他和他的时代所共同经历的东西,不过这也仅仅是为了保持属于诗歌自身的话语,使诗歌能够挺立住,就像信仰在今天所能做的一样。
在通向语言真实的道路上,人们最终会遭遇到诗歌本身:一种有关这个时代生存的,既是本真的,又是终结性的话语触及,在这里,人们太阳穴相撞的斗争已经模式化,世界抛锚了,深渊缝在人的声音上,开端被一只甲虫认出,但仍然还有一个尚未受到世界邀请的希望,它向着世界,重新“抛出拖缆”。
诗歌早已存在于某一个位置上了,只是还有待于“从它先前的非存在状态传递出来”(引自《保罗·策兰传》,费尔斯坦纳著,李尼译),这是属于语言自身的一个命运,就像诗人感觉到他的诗在等待着他,因而他不能放弃写作一样。语言通过诗人个人的声音找到了属于诗歌自己的话语形式。
诗人的生存似乎是为了使语言本身得到自由,但是隔着“话语之栅”,更自由的诗喂养着被禁锢的诗人,并伺机把他埋葬。
诗比诗人更自由,这就是诗的言说得以产生的唯一原因。
据说自由来自于上帝最初为人设定的一个深渊,而诗歌正是挺立在那里,“高处/旋风/骤起,比你们/更猛烈”(《谁站在你这边》,孟明译)。
保罗·策兰遭遇到了他自己的诗。他的诗见证了他,同时又毁灭了他,因为他在诗里把原初事件造成的伤口当做说话的嘴,迟来的嘴,结巴的嘴,也就是说,他展示了伤口,而不是缝合了伤口,因此他也是属于在奥斯维辛之后,终于没有挺过来的人之一。
策兰保留了疼痛,而疼痛既无话语,又无物,仅仅显示了一个受难的身体。一个劫后余生者的身体不可能像耶稣那样,用他在十字架上的伤口来赢得世界,但策兰的确围绕着他的疼痛,集中了一种对伤口隐喻的现代解读。灾难,身体,他者,语言的多样性、歧义和碎片……在这里,诗歌的晦涩,承担起了世界的阴惨之名。
一个伤口,也就是“推断性起源的中断”,没有身份的可怕的自由,唯一的声音,死亡提前的发生,本雅明称之为文学作品中的“讽喻”,德里达称之为“专用名词”的隐喻。
一颗迫切需要被挽救的人头无法对人们说出太早的话,他只能把记忆当做迟来的嘴,去说太晚的话,他在诗歌中说啊、说,他也向着空中去说,他觉得空中有一种东西在倾听,他自己也在听,然后做出申辩,一再地申辩,重复地申辩,然而问题在于,他听到了什么?他到底听到了什么?不知道,我们只是从策兰那里听到了一个受伤的言说本身。
在这里,就像卡夫卡所说的,世界拿走人们的希望,却给了他们一个确凿无疑的命运,正是由于这种分裂,个人在历史中变得特殊了,然后这种特殊变成了一种病理学,而病理学是人类一首未完成的歌,因为在这里产生任何回应都是不可能的。围绕着伤口,一切联系都是苍白无力的,这难道不是语言的命运?当灾难再也不能把人们集中在一起的时候,人们也就走到了世界边缘的尽头。一个仅仅发生在语言中的、从远处对人做着独自拯救的东西并不存在,它只是必将到来,而这就是诗歌,是吧?
保罗·策兰的诗是人类言说中的一道黑色的凝血,和星辰一起涌现在他的祖先——人类亚当的神圣的肋边。
后记:在一个言说的“黑太阳”下
如果在翻译作品中,我们的汉语就像太阳一样,在照耀着“别人的花园”,那么我们有时也误以为保罗·策兰的诗是用流放在德语里的汉语写成的,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是用流放在俄语里的汉语写成的,而翻译他们的诗,就是在一个共同言说的“黑太阳”下,说出我们与汉语在一起所经历的那种流亡。但是,由于诗歌只是出现在语言的一个救赎点上的,而翻译把这样一个救赎点带进了汉语内部,把它变成汉语自己在一个当下言说中的最终需求,因此,对于这个本来永远也不会发生在汉语中的事件,如果翻译诗歌就是用差异重写一次诗歌,那么每一次重写都是为了让滞留在外、流浪在外的汉语“到家”。
一部好的翻译作品只是作为一种汉语风格而存在的,否则你又能把这个已经不属于外语的语言放在何处呢?同样,一首翻译糟糕的诗,就像一个与翻译者相适宜的女子,对于他们命中注定的婚配,我们无话可说。所有的翻译作品都处在汉语内部的“他者”位置上,就像女人作为人类内部的“他者”,把男人的欲望拿到外面来实现为世界那样,诗歌翻译尤其反映了汉语自身的纯粹的欲望:通过对异域、异在和异思的渴求,使汉语本身得到自由。在汉语的这种“好客性”中,我们与自己母语的关系是纯粹官能症式的:在外来语言愈是能发生作用的地方,我们的汉语就愈纯洁,而汉语愈纯洁,对绝对不同于它的差异化语言的运用就愈到位。真正说来,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如果我们在自己母语内也是一个他者,那么对于我们与自己母语之间的官能症,这就像普鲁斯特所说的,“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于外语的语言写成的”(《驳圣伯夫》)。
因此,对我们来说,一切翻译作品都是通过使汉语预先自由,来让我们追随这种自由,而伟大的汉语的自由,不过就是人类话语活动本身的自由。在今天,人类话语活动构成了一个叫做“云语言”的东西,当然,这也就是人类唯一的“大语言”了:德国人把他们看到的这个“大语言”称作“德语”,法国人把他们看到这个“大语言”称作“法语”,中国人把他们看到的这个“大语言”称作“汉语”……也就是在这个作为人类“共生物生命”的语言范围内,翻译一方面在做着平等的和活性的语言交换,另一方面,人们又陷入到“翻译的丑闻”中永远也无法自拔,而诗歌的不可翻译性也就在于它有着一种抵制语言差异流失的止血功能。实际上,在一群互为他者或异乡人的言述中,真正打动我们的,是一种我们从未拥有过的生活,那里有着一个我们还没有思量过的世界;同样,一个说着汉语的人,无论他在巴黎、伦敦,还是莫斯科,他的不安在于他知道自己不属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也不属于他,但又是哪一种共同的命运把他带到人类的无数个地点?
也许正是出于人类这个唯一的“大语言”的缘故,人们终于把汉语弄得像是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种翻译风格:存在的语言作为汉语“原体”的泄露和发散,变成了汉语的“原思”……当然,汉语的“原体”和“原思”不过来自于汉语主体的纯粹虚构,但它们也是作为一个真正被隔绝了的东方(与海德格尔的希腊一样),在这里,我们失去的是一种作为自然的强力意志的混沌风格,而在此之后,我们就进入到各种方法论的争执,以及作为方法论之终结的后现代主义之中。在这里,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实际上是通过重建混沌来恢复一种适合于存在居住的语言风格,而对我们来说,这就像在古汉语诗歌阅读中所产生的无法解释的快感,在今天实则作为一种音乐的调性,一旦缺乏这种调性,汉语就会像“存在”一样,立即变成有待于重新被奠基的东西,因此,在这里,不可避免的,一些早已被荒废了的人只能把汉语当做沙子的语言,灌进自己的喉管,而海德格尔所说的“一个民族的天命”,在汉语里还始终没有被说出来……
在今天,我们的“天命”不过就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着的一场普遍的精神分裂:当愚蠢的、没有期限的封建制度与一个作为无限作弊系统的资本主义相遇时,这使我们每一个晚上都兴奋得难以入眠。这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送给我们的礼物了,我们像接受没有上帝的事实一样接受了这个礼物,不过剥开这个礼物的所有包装之后,我们发现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作品,这就是这个时代最终的内在之核。当然,这个事实与其他任何罪恶相比,并不更残酷,它只是让获得最高文学奖赏的人每一个晚上都为自己选择了写作而感到后悔不迭。
在这个时代里写作,总免不了面对一些最糟糕的人说话,最终是他们塑造了作品,这使写作者变得气急败坏,善意尽失,这就是在作品的内部,写作所遭遇到的命运了。现在,人们已经放下思想武器,直接开始肉搏了,从而使人类智慧有了一次彻底休息的机会;也许只有在目前得到休息的思想才能为人类下一场更加绝对的狂热做好准备,是吧?
再也没有一种能够带动整个世界来叙述,并用无从引领的引领方式来对我们说话的诗歌言论了,因为诗人已经无限地撤退到自己内心里去了,也许现实中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正是被他们储藏在自己的内心里,最后变成一头野兽,把他们可怜的个性撕得粉碎;也就是在这里,诗人发现世界唯一还在垂顾他们的东西,大概就是语言了,尽管他们的语言对世界的事物是束手无策的,但他们对语言的爱并不因此而减少。
在今天,简单地说,诗歌是让人失望的:它不占有术语,不占有观念,不占有机构,不占有任何一种使作品随之出现的思想的肇始和开端,也就是说,诗歌既没有从作品内部交流的历史中引出作品的源头(就像德里达所说的“画框”那样),也没有在世界的前沿,占据一个观察的位置,从而让自己参入到一种“进步的方法论”或方法论的终结中去,而诗歌本来可以在语言中置放这样一个观察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通过观察自身的观察行为,使一种观察关系变得可见,而这就是一个当代意义上的“作品”,是吧?在今天,诗歌似乎只是占有一个“哀悼”的位置了,而对于它的众所周知的损失,只有哲学和艺术所谈论的“终结”问题还在充当着“报丧者”的角色。
如果艺术是通过发明不同形式的外界指涉,以避免死于自我指涉之中,那么诗歌却往往把自身限定为一个仅仅发生在语言中的事件,并通过陶醉于语言自我指涉的感知力,从而避开了一种激进的批评姿态,这正如阿多诺所说的:“任何陶醉最终都是喜欢放弃的道路,而不是在自我实现中以原罪来对抗自己的概念。”这难道是说,一如通过十字架的透视来实现大地上的一种“罪与意义的统一”,诗歌也不被允许做着任何一种无限的自我放松的活动了?而实际上,诗歌早已在现实机制的酷刑下解体了,并明显带着败落下来的沮丧的特征,目前还在竭力把自己的招供伪装成似乎在与世界各说各的话。
在今天,当真理变得无路可走时,这并没有在人们中间引起一种千方百计地去思考的勇气,相反,在放弃建构立场的地方,人们又重新把一切交付给了混沌,而混沌作为不可观察的那一派悄然滑入的意象,就像大地上的“永恒回归”一样,一切发生在这里的“思想事件”,也都在这里被外在地销蚀着,直到重新变成“深藏不露”的东西:在这里,人们必须要把一个根本的东西的产生,当做最终还是无法解释的事件,从而制造了一个断裂,也就是为思想保留一个可操作的命名空间,这就是今天人们认识行为的最主要模式了。因此,真正说来,人们需要混沌的,是在其中可以永久隐匿一个故意不说出来的东西,这样才能产生可供思想叙述的无限丰富的“剩余”或“残余”,否则知识分子又能做什么?而当那个故意不说出来的东西终于变成一个公然的笑料时,人们又不免要问:“知识分子到哪里去了?”最终说来,人们通过混沌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永远是一种作为镜像的对等的缺席:现实在掩盖着“没有现实”的事实、事件在掩盖着“没有事件”的事实、观念在掩盖着“没有观念”的事实,这难道不是说,人们今天在艺术中发明出各种观念,也只是为了让自己“没有观念地活着”?实际上,所有这些遮蔽作为权力在知识中的运作,它们只能被处于社会边缘人物的大胆言论所突破,一如尼采那样,他们都属于“在那些独一无二的瞬间敢于与存在的独一无二性相对峙的人”,也就是在这里,诗歌作为一种世界基本张力的构成性要素,难道它不应该把自身重新定义成人类言说中的一个“例外状态”或一个“特例”?
诗歌终究是在一种非存在状态中自己让自己出现的语言,它总在说着不可能被说尽的话,这就是诗的风险:只有那个还没有被真正地说出来、还没有被唯一地表达出来的东西才能够侵犯和威胁诗歌,除此之外,需要被保卫的诗歌的确是不存在的,相反,诗人倒是需要一份职业或养老保险来保卫他自身。当然,反抗也并不能造就诗歌,它只是在说明一个与诗歌主权有关的状态:由于不想看到主体的卑微,反抗宁肯去质疑“机构”,而不是主体自身。在今天,一个承认自己不再有任何反抗权利的诗人,他最乐意做的事情莫过于为诗歌辩护,因为只有在这种辩护中,他才可以去剥夺别人的反抗权利,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逆转自己受辱的处境了,是吧?但在这里,由于所有人都处于无权的状态而使诗歌变得纯粹了吗?没有,相反,诗歌在今天终于变成一个在酷刑下招供的场所了,就像现实本身在想方设法地造成主体的卑微,而不是在人们中间激发出一种千方百计地去思考的勇气那样,至少诗歌再也无法继续过着它自己的尊严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是存在于人们对过去诗歌的一段记忆之中了。因此,真正说来,诗人已经精神分裂了,诗歌只是被他们用来改变自己在这个腐败现实中的必有的谵妄,正是在这里,一如在酷刑下,诗歌变成了人类言说中一个“黑太阳”,而在它的腐烂的光线下,只有一个处于过度虚构或神秘谵妄的世界——这个世界最骇人的真理,无疑属于一个从腐朽机构内部的“老败类”那里不小心吐露出来的话语的类型:到了某个时候,“他相信自己有本事坐在全世界的上面拉屎”(引自《历史和心理分析》,德·塞托著)。
在一个“主体性的黄昏”中,只有艺术品在闪耀:那一个个躲在物的表现背后的盲魂,最后都被折叠进大地自身的那一重混沌之中,而那一混沌“任悬于广袤之上露出神的俄尔浦斯空灵的鬼蜮伎俩”(勒内·夏尔语),这就像是回到艺术上的一个前原罪时代,只是这一次由于人们不知自己将身落何处,而这就是诗歌在今天的可言说之处了,是吧?
在一个“黑太阳”下,一如在极地的夜里,在成片的、泛着金属光泽的屋顶下,人们因为这样一个无所不在的内部的沉重性而昏昏欲睡了;在这时,只有写作的刑具还在吱吱作响地燃烧着言语:这一点点灵知之光把整个宇宙的黑暗都当做自己正在承受的酷刑了。
写于2014年3月 南京
|
|